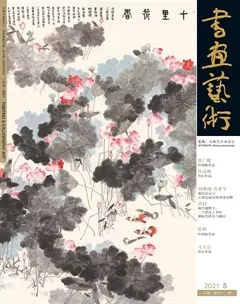觀的啟示與古典繪畫(huà)空間本體詮釋
劉繼潮 黃更生
劉繼潮 1944年生,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中國(guó)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安徽省美術(shù)理論研究會(huì)會(huì)長(zhǎng)。曾任安徽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院長(zhǎng),安徽省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安徽省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
黃更生 安徽舒城人。2005年畢業(yè)于四川美術(shù)學(xué)院,獲碩士學(xué)位,同年任教于安徽大學(xué),安徽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
一、空間研究的遭遇及背景
明代以前的中國(guó)繪畫(huà),一直生存在自足、自為、封閉的文化環(huán)境中。自明代始,隨著西方傳教士的來(lái)華,西洋繪畫(huà)傳入中國(guó),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的理論思潮也隨之而來(lái)。1729年《視學(xué)》出版,作者年希堯,生年不詳,卒于乾隆三年(1738年)。《視學(xué)》是國(guó)人最早研究介紹西方繪畫(huà)透視理論的一本書(shū),作者是能夠“認(rèn)真地評(píng)論了中國(guó)畫(huà)法的長(zhǎng)處和缺點(diǎn)”的人[1]。有了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的對(duì)比與參照,中國(guó)畫(huà)家的平靜生活不復(fù)存在;有了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理論的介紹與影響,中國(guó)古典寫(xiě)意繪畫(huà)再也無(wú)法純粹化。《視學(xué)》的出版具有編年史的意義,標(biāo)志古典中國(guó)畫(huà)自足、自為、封閉的生存環(huán)境從此被打破。讓年氏沒(méi)有料到的是,《視學(xué)》介紹的西方科學(xué)透視理論,竟成為古典中國(guó)畫(huà)空間研究揮之不去的陰影。
20世紀(jì)初,陳獨(dú)秀提出“因?yàn)橐牧贾袊?guó)畫(huà),斷不能不采用洋畫(huà)的寫(xiě)實(shí)精神”。當(dāng)時(shí),蔡元培、徐悲鴻、林風(fēng)眠、早期的劉海粟等都有類(lèi)似看法。連高揚(yáng)傳統(tǒng)文人寫(xiě)意精神的陳師曾,在《文人畫(huà)的價(jià)值》一文發(fā)表的兩年前,即1919年時(shí)也說(shuō):“我國(guó)山水畫(huà),光線遠(yuǎn)近,多不若西人之講求,此處宜采西法以補(bǔ)救之。”(1)當(dāng)年中國(guó)畫(huà)壇,圍繞“新”與“舊”的爭(zhēng)論而陷入混亂與恐慌。
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的中國(guó)畫(huà)大討論,是在科學(xué)至上的語(yǔ)境中展開(kāi)的,在中西繪畫(huà)比較研究中,一般多將注意力投在筆墨和造型兩個(gè)熱點(diǎn)上。唯有宗白華另辟蹊徑,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中國(guó)畫(huà)的獨(dú)特空間問(wèn)題。宗白華首先發(fā)掘出沈括“以大觀小”的獨(dú)特價(jià)值,并由此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表現(xiàn)的獨(dú)特性,回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畫(huà)壇對(duì)中國(guó)畫(huà)的種種懷疑和非難。宗白華開(kāi)創(chuàng)了中西繪畫(huà)空間比較研究之先河[2]4。
現(xiàn)當(dāng)代關(guān)于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理論的研究,基本上以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的透視原理,來(lái)套說(shuō)、扭曲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獨(dú)特的空間理論。時(shí)至今日,關(guān)于中國(guó)畫(huà)的空間問(wèn)題和“以大觀小”的理論研究,仍深陷在盲區(qū)之中。所謂的“中國(guó)畫(huà)透視理論”,即“散點(diǎn)透視”“動(dòng)點(diǎn)透視”的理論,充斥于各種各類(lèi)的美術(shù)教材之中,充斥于關(guān)于中國(guó)畫(huà)的“研究”“概論”“欣賞”等讀物中。當(dāng)下,依然以散點(diǎn)透視、焦點(diǎn)透視的概念強(qiáng)加于古人,依然用散點(diǎn)透視的理論誤導(dǎo)著今人。
二、觀的啟示
20世紀(jì)90年代,我們因嘗試山水創(chuàng)作,而開(kāi)始關(guān)注中國(guó)古典山水畫(huà)神秘的空間問(wèn)題。與此同時(shí),沈括的“以大觀小”理論亦隨之進(jìn)入我的興趣中心。過(guò)去,有學(xué)者把沈括的“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 解釋為:把山水大物當(dāng)小物“看”,如人“看”假山。在這里,沈括文本里的“觀”字被置換為“看”字,這一簡(jiǎn)單而輕松的置換,為“以大觀小”之“觀”,找到了明確的“看”的對(duì)應(yīng)語(yǔ)詞的解釋。但,面對(duì) “觀”與“看”的互相置換,筆者敏感到,雖一字之差,其中的問(wèn)題暗藏某些玄機(jī)。“觀”與“看”,遂成為我們一再琢磨、推敲,深度反思古典繪畫(huà)空間問(wèn)題的兩個(gè)關(guān)鍵詞。
對(duì)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問(wèn)題,特別是對(duì)“以大觀小”奧理的研究,現(xiàn)成可供借鑒的理論與資料十分缺乏。近現(xiàn)代,以散點(diǎn)透視解說(shuō)古典繪畫(huà)空間已普及為常識(shí)。在散點(diǎn)透視的干擾與遮蔽下,古典繪畫(huà)空間研究想要有所突破、有所發(fā)明,實(shí)非易事。現(xiàn)有辭書(shū)及資料中有關(guān)“觀”與“看”的詞條,沒(méi)有能提供我所需要的具有啟發(fā)性的解釋。當(dāng)時(shí),苦于對(duì)“觀”字內(nèi)涵了解的貧弱,更苦于雖感覺(jué)到問(wèn)題而找不到破解方法的困窘。
在十分無(wú)助、無(wú)奈的心境下。筆者漫無(wú)目標(biāo)地在圖書(shū)城哲學(xué)類(lèi)書(shū)架上搜尋,一本暖灰色書(shū)脊的書(shū)《易學(xué)本體論》,非常偶然地進(jìn)入我們的視線。封面簡(jiǎn)潔大方,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翻看目錄,其中一條標(biāo)題:“論‘觀的哲學(xué)意義與易的本體詮釋”,眼前一亮,立即買(mǎi)下這本書(shū),迫不及待地趕回家翻到77頁(yè)。
作者說(shuō):“‘觀是一個(gè)無(wú)窮豐富的概念,不能把它等同于任何單一的觀察活動(dòng)……”又說(shuō):“‘觀是一種普遍的、沉思的、創(chuàng)造性的觀察。”[3]81讀到有關(guān)“觀”的這些從未有人論說(shuō)過(guò)的內(nèi)容,我異常振奮。作者關(guān)于“觀”的哲學(xué)內(nèi)涵的論述,明確、精辟、深刻,完全契合我內(nèi)心對(duì)“觀”的某種學(xué)術(shù)期許。這時(shí),才注意到作者是成中英先生,美籍華裔哲學(xué)家。他的話像一泓清泉,使我空間研究的初苗轉(zhuǎn)現(xiàn)生機(jī)。自己一下走出了空間研究的死胡同,視界豁然開(kāi)朗。成氏所說(shuō)的不能把“觀”等同于“任何單一的觀察活動(dòng)”,其所未明言之點(diǎn),就是我所理解的:不能把“觀”等同于單一視覺(jué)的“看”。
對(duì)“觀”與“看”生發(fā)的中西古典繪畫(huà)文化分野的特殊屬性,過(guò)去無(wú)人注意,更無(wú)人研究[4]67。近現(xiàn)代反而硬性套用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的一套理論,衍生出所謂“中國(guó)畫(huà)寫(xiě)實(shí)”“中國(guó)畫(huà)透視”“散點(diǎn)透視”等流行說(shuō)法,客觀上遮蔽扭曲了傳統(tǒng)繪畫(huà)的本來(lái)面目,肢解了傳統(tǒng)繪畫(huà)的話語(yǔ)體系,模糊了中、西古典繪畫(huà)空間的根本性差異,以至陷入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的話語(yǔ)強(qiáng)勢(shì)之中,而失去發(fā)展民族文化的根本自信。
是成中英先生第一個(gè)從哲學(xué)高度,對(duì)《易經(jīng)》“觀”的特征作了精辟的概括和深刻的詮釋。《易經(jīng)》之“觀”,是成中英先生《易學(xué)本體論》首次發(fā)現(xiàn)、發(fā)明的理論重點(diǎn)和亮點(diǎn)之一。
成中英先生認(rèn)為:八卦來(lái)自圣人“觀”的活動(dòng),一旦圣人設(shè)計(jì)了八卦,就能夠更多地觀察事物及其活動(dòng)。“觀”的過(guò)程總是一個(gè)開(kāi)放的過(guò)程:從事物的實(shí)際活動(dòng)中識(shí)別出形式,把形式應(yīng)用于事物以更好地理解事物[3]79。《易經(jīng)》中的“觀”描述和界定了觀察、認(rèn)知、理解世界萬(wàn)物和萬(wàn)物世界的一種方法論(從理性意識(shí)的觀點(diǎn)出發(fā))和過(guò)程。成中英先生認(rèn)為,作為“象”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的“觀”,是所有重要文化活動(dòng)和文明活動(dòng)的意義、靈感、動(dòng)機(jī)的無(wú)窮源泉。《周易》哲學(xué)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可以說(shuō)非常的源遠(yuǎn)流長(zhǎng)。中國(guó)文化故可稱(chēng)為“易的文化”,中國(guó)哲學(xué)故可稱(chēng)為“易的哲學(xué)”,而中國(guó)人的思維方式亦可稱(chēng)為“易的思維方式”。“易道也就成為中國(guó)哲學(xué)思想的原點(diǎn)和源頭活水了”。[3]46成氏對(duì)“觀”的極具開(kāi)拓性和原創(chuàng)性的探究與詮釋?zhuān)瑤椭P者認(rèn)清了“觀”在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歷史演進(jìn)中,所應(yīng)有的深遠(yuǎn)而深刻的文化意義,堅(jiān)定了我直覺(jué)把握到“觀”的問(wèn)題的自信,提升了我對(duì)“觀”豐富內(nèi)涵的視界。
受成中英先生學(xué)術(shù)成果的啟發(fā),筆者追溯到“以大觀小”之“觀”的傳統(tǒng)文化之根。“以大觀小”文本,是傳統(tǒng)文化孕育、積淀的結(jié)果。也就是說(shuō),中華文化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悠久傳統(tǒng)是沈括文本生成的土壤。回歸、重建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以“觀”為統(tǒng)挈的理論體系,具有深刻的當(dāng)代意義和實(shí)踐價(jià)值。從傳統(tǒng)文化原點(diǎn)——“觀”起步,可以詮釋民族古典繪畫(huà)本體的獨(dú)特性和世界性,歷史地描述中國(guó)繪畫(huà)自為的發(fā)展軌跡,清醒地認(rèn)識(shí)民族繪畫(huà)自在的本來(lái)面目。
筆者認(rèn)為,《易經(jīng)》對(duì)中國(guó)古典文化、中國(guó)美學(xué)及藝術(shù)的影響,最深刻、最根本的一點(diǎn),就是“觀”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因此,對(duì)“觀”的哲學(xué)內(nèi)涵的深入挖掘與深刻理解,將是解讀“以大觀小”、古典畫(huà)論,以及古典文論與古典美論等的最重要的知識(shí)準(zhǔn)備與路向。“觀”,是把握、闡釋“以大觀小”真義的最初路徑。
過(guò)去,對(duì)“以大觀小”研究,以“看”置換“觀”,是科學(xué)主義、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理論對(duì)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寫(xiě)意傳統(tǒng)的拒斥。正是諸如此類(lèi)不經(jīng)意的、簡(jiǎn)單化的學(xué)術(shù)疏漏,模糊了中西繪畫(huà)在本體和方法上的文化差異,從而造成現(xiàn)當(dāng)代對(duì)古典繪畫(huà)長(zhǎng)達(dá)一個(gè)多世紀(jì)的誤讀,隨之而來(lái)的是扯不清的學(xué)術(shù)糾纏和歷史的沉重。
西方繪畫(huà),注重視覺(jué)的“看”,注重對(duì)視網(wǎng)膜成像的科學(xué)原理的研究,以科學(xué)透視學(xué)、色彩學(xué)、解剖學(xué)為依據(jù),精確再現(xiàn)視覺(jué)的近大遠(yuǎn)小、環(huán)境色、光影體積等,在二維平面上,制造虛幻的三維空間。西方古典繪畫(huà)之“看”,是對(duì)視網(wǎng)膜映象的機(jī)械復(fù)制與再現(xiàn)。嚴(yán)格地說(shuō),西方文藝復(fù)興至19世紀(jì)前的古典繪畫(huà),選擇了視覺(jué)反映論的路徑。反映論再現(xiàn)的是視覺(jué)真實(shí),偏向于外在世界對(duì)象性思維。西方畫(huà)家依賴于“看”的視覺(jué)反映的方法,強(qiáng)調(diào)在場(chǎng)性,多畫(huà)視覺(jué)直接所見(jiàn),追求忠實(shí)地模擬客體真實(shí)。因此,“看”遂成為西方古典繪畫(huà)的本體和方法,成為西方古典繪畫(huà)寫(xiě)實(shí)性的本源[2]56。
由于“觀”的規(guī)定,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的形神發(fā)展軌跡,完全不同于西方古典繪畫(huà)的寫(xiě)實(shí)再現(xiàn)。自顧愷之提出“以形寫(xiě)神”之后,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由寫(xiě)“神”而寫(xiě)“意”、寫(xiě)“真”、寫(xiě)“趣”、寫(xiě)“心”等,文人畫(huà)追求“逸筆草草,不求形似”“遺形取神”“得意忘形”。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本體之觀,回避科學(xué)原理,重視人文情懷,不依賴科學(xué)的精確與準(zhǔn)確的再現(xiàn),而畫(huà)貯存的意象和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古代畫(huà)家之“觀”選擇本體宇宙論的路徑。本體論偏向于內(nèi)在世界本體性思維,是表現(xiàn)原生態(tài)的自然真實(shí),重原比例、原結(jié)構(gòu),重常形常象,重層次空間等,因此,“觀”成為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的本體和方法,成為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寫(xiě)意性的本源[2]86。盡管如此,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受《易經(jīng)》“中正以觀天下”思維的影響,始終沒(méi)有摒棄具象,而流轉(zhuǎn)于“似與不似之間”。
把“觀”與“看”置于中西繪畫(huà)比較的視野中研究,“觀”和“看”已經(jīng)從漢語(yǔ)一般字詞的概念,轉(zhuǎn)化提升為具有中西古典繪畫(huà)不同方法論和本體論意義的文化概念和符號(hào)[4]67。
從沈括發(fā)明的“山水之法”與“真山之法” 清晰界定與區(qū)別起[2]62,進(jìn)而探究“觀”與“看”的文化分野,厘清與重建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的真正傳統(tǒng),在當(dāng)下具有十分緊迫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和當(dāng)代意義。從深層觀之,方法之辨乃是本體內(nèi)在意志選擇進(jìn)向之辨。恰中了成中英先生本體詮釋學(xué)的理路,即本體乃是方法之本體,方法乃是本體之方法。由于本體之“觀”和主體之“看”不同的內(nèi)在規(guī)約,而生“山水之法”與“真山之法”的不同路徑。筆者認(rèn)為,沈括“以大觀小”的理論洞見(jiàn),是《易經(jīng)》類(lèi)比思維智慧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將“以大觀小”之“觀”與《易經(jīng)》之“觀”相勾連,接續(xù)且融通古老文化傳統(tǒng)悠遠(yuǎn)的歷史淵源,是自然的合理的邏輯推導(dǎo),完全沒(méi)有學(xué)理上的牽強(qiáng)。“以大觀小”蘊(yùn)含并擁有來(lái)自中國(guó)哲學(xué)源頭活水的內(nèi)在根據(jù),更加突顯古典繪畫(huà)之“觀”內(nèi)涵的深刻、厚重與獨(dú)特。
三、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本體詮釋
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本體詮釋?zhuān)庠诨厮荨⒔咏袊?guó)古典繪畫(huà)創(chuàng)作內(nèi)在機(jī)理與歷史真實(shí),意在彰明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的獨(dú)特路向與體系,意在厘清中、西古典繪畫(huà)本體與方法的根本差異。同時(shí),彰顯中華視覺(jué)文化的獨(dú)特價(jià)值與當(dāng)代意義。易之道彰明本體宇宙為太虛絪缊之氣和合渾成。“一陰一陽(yáng)謂之道”,陰陽(yáng)之氣含分化變動(dòng)之機(jī),是宇宙本體生生不息運(yùn)化生成的根據(jù)和原動(dòng)力。成中英先生認(rèn)為,《周易》哲學(xué)的“太極”和“道”作為原始的本體詮釋學(xué),其“觀”的方法,發(fā)展為一個(gè)理論或“宇宙觀”。“觀”的理論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條件、途徑和方法[3]82。
成中英先生認(rèn)為:“觀”是一種事物自然存在呈現(xiàn)的境界,是主體與客體綜合為一的直覺(jué)方法,可名之為“觀的觀點(diǎn)”。而“觀點(diǎn)”是一種突出的預(yù)設(shè)前提并具有理性目標(biāo)的認(rèn)知與評(píng)價(jià),可名之為“觀點(diǎn)的觀”。中國(guó)哲學(xué)盡多“觀”照,西方哲學(xué)則盡多“觀點(diǎn)”[5]。成中英先生的研究成果幫助我們從哲學(xué)的高度,理解中西古典繪畫(huà)的本體差異。西方古典繪畫(huà)以焦點(diǎn)透視為預(yù)設(shè)前提,以視網(wǎng)膜成像之“看”為根基,其“觀點(diǎn)的觀”是“片面的靜止固定的結(jié)構(gòu)”。西方古典繪畫(huà)“觀點(diǎn)的觀”有時(shí)而窮,主體受視域、視距、空間位置等諸多因素限制,無(wú)法進(jìn)入純粹自由的創(chuàng)造境界。
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之“觀”是事物自然存有、呈現(xiàn)的境界,沒(méi)有預(yù)設(shè)前提,是“觀的觀點(diǎn)”。“觀”是綜合經(jīng)驗(yàn)的直覺(jué)體驗(yàn),是記憶、想象的創(chuàng)造,而不選擇單一再現(xiàn)視網(wǎng)膜成像的路徑。“觀”的世界,是詩(shī)化的世界,是審美的世界,是超越有限而生成無(wú)限精神自由的世界,故而能展現(xiàn)一個(gè)包含一切的整體的動(dòng)態(tài)的純粹自由的創(chuàng)造過(guò)程。成中英先生肯定筆者的理解與運(yùn)用,寫(xiě)道:“為了說(shuō)明這一‘觀的無(wú)觀點(diǎn)或‘觀的超融觀點(diǎn),劉教授用了‘游觀一詞,我覺(jué)得是非常適當(dāng)而生動(dòng)的。此一觀念可說(shuō)結(jié)合了莊子的‘逍遙游的觀念與我的‘觀的概念,是有創(chuàng)意的,也是有實(shí)踐的內(nèi)涵。”[2]3
在相對(duì)封閉的文化地理環(huán)境中,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自發(fā)且自覺(jué)地生成“本體之觀”的獨(dú)特創(chuàng)作理路[2]71, 實(shí)踐并創(chuàng)造出獨(dú)特的空間表現(xiàn)和筆墨語(yǔ)言形式。筆者堅(jiān)定地認(rèn)為:在西方古典繪畫(huà)寫(xiě)生路徑之外客觀地歷史地存有的另一條畫(huà)學(xué)路徑——即悠久的、明晰的自在自為自成體系的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的獨(dú)特寫(xiě)意路徑(2)。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寫(xiě)意表現(xiàn)的獨(dú)特體系,為世界藝術(shù)版圖中繪畫(huà)風(fēng)格多元化與多樣化的文化生態(tài)構(gòu)建,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xiàn)。(參見(jiàn)所附示意表)
易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莊子曰:“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荀子曰:“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tīng)恳玻h(yuǎn)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zhǎng)也。”(3)宗炳曰:“澄懷觀道。”王微曰:“目有所極,故所見(jiàn)不周。”張璪曰:“物在靈府,不在耳目。”邵雍更明確地說(shuō):“觀物者非以目觀之,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6]沈括曰:“大都山水之法,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可以看出,中國(guó)古代先賢反復(fù)地質(zhì)疑以單一視覺(jué)反映而定物的路徑。
智慧的古代畫(huà)家們,在對(duì)《易》的意象性融通內(nèi)化的歷史過(guò)程中,創(chuàng)發(fā)了古典繪畫(huà)之“觀”——獨(dú)特的本體經(jīng)驗(yàn)的綜合直覺(jué)。在心理的層面,古典繪畫(huà)“本體之觀”與“心源”一體而相通。
古代文人畫(huà)家人生經(jīng)歷與人格修煉的綜合素養(yǎng),含蘊(yùn)有儒、道、釋的智慧和詩(shī)、書(shū)、畫(huà)、印的綜合趣味。“觀”超越單一的視覺(jué),是“心源”與五官感覺(jué)相互引發(fā)、溝通、交融,是“耳目?jī)?nèi)通”“六根互用”“無(wú)目而見(jiàn)”的境界,是靈心妙悟、感而遂通的頓悟與開(kāi)顯[7]。生命的本體之觀以內(nèi)在心性,感造化自然之性靈,得心源情感之熔鑄,以生成意象世界。造化自然在沒(méi)有進(jìn)入人的本體之觀之前,與人本體之心“同歸于寂”。當(dāng)人的本體之觀與造化自然相遇,相摩而相蕩,觀其所感、感其所觀、觀其會(huì)通時(shí),造化自然便會(huì)“一時(shí)明白起來(lái)”,此即“心源”之有得也。“造化”是從藝術(shù)家“心源”中流出來(lái)的意象創(chuàng)造,是“心與道合”達(dá)至的最高境界。故而,余英時(shí)斷言:“中國(guó)藝術(shù)與現(xiàn)代一度流行的反映論絕不相容,如果僅‘師造化而不‘得心源,藝術(shù)作品中所顯現(xiàn)出來(lái)的事物即使與‘造化中的原型惟妙惟肖,在中國(guó)藝術(shù)家眼中也無(wú)多價(jià)值可言。”[8]
本體詮釋學(xué)即是方法論與本體論的融合,用方法來(lái)批評(píng)本體,同時(shí)也用本體來(lái)批評(píng)方法;在方法與本體的相互批評(píng)中,創(chuàng)造與綜合而融為一體,廓清意義以接近真實(shí)。以“觀”為本體的天人合一的路向,不同于那種認(rèn)識(shí)與分析、主觀單向反映的模式,而是主體之心與客體之天地相摩相蕩、互滲互動(dòng)與融合和諧。本體之情感滲入物象之原,物象之原的神韻又滲入“觀”之本體,山水意象緣此而創(chuàng)生。
筆者以沈括發(fā)明的“山水之法”為切入點(diǎn),向上追溯,從古畫(huà)論文本和畫(huà)跡遺存中探究古典繪畫(huà)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理?yè)?jù)。荊浩之前,已有“丈山尺樹(shù),寸馬分人”的記述。荊浩在《筆法記》中,從對(duì)山水畫(huà)“似”與“真”的辨析,從對(duì)“二病”的批評(píng)否定中,最終導(dǎo)出關(guān)乎山水畫(huà)生成根基的獨(dú)特發(fā)現(xiàn):即“須明物象之原”的重要理論[9]。荊浩的洞見(jiàn),也是對(duì)魏晉山水畫(huà)“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10]107的單一視覺(jué)階段的批判。“物象之原”是荊浩對(duì)“丈山尺樹(shù),寸馬分人”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理論化提升;是荊浩自覺(jué)地對(duì)本體宇宙——“物象之原”的發(fā)明與彰顯。在荊浩的認(rèn)知中,山水畫(huà)創(chuàng)作以“物象之原”為體,以“丈山尺樹(shù),寸馬分人”為用。至此,古典山水畫(huà)本體與方法即宇宙本體論的路向基本建立,體與用趨于明晰而完整,山水畫(huà)理論體系的建構(gòu)也就順理成章。
荊浩的“物象之原”既是一個(gè)富有思辨性哲學(xué)意味的概念,又是一個(gè)“其理幽奧”[11]實(shí)踐性很強(qiáng)的畫(huà)學(xué)概念。“物象之原”,當(dāng)指物象原始的、恒常的、天然的原生狀態(tài),亦指物象之本原、本根,即世界萬(wàn)物自己如此、自己原來(lái)的狀態(tài)。“物象之原”既含有作為物質(zhì)世界的本然之義,也含有自然而然即天然之義。可以認(rèn)為荊浩的“物象之原”就是道家的所謂“自然”。中國(guó)古典山水畫(huà)創(chuàng)作不選擇再現(xiàn)視網(wǎng)膜變象的路徑,不刻意節(jié)選孤立靜止的視域所見(jiàn),而追求物象自己本來(lái)如此、自自然然之本體自然的真實(shí)。
中國(guó)山水畫(huà)最早的遺存相傳為隋展子虔的《游春圖》卷。《游春圖》卷已徹底擺脫魏晉山水畫(huà)“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10]107的單一視覺(jué)階段。《游春圖》卷描繪的遠(yuǎn)山高聳,層疊蜿蜒以及山高于樹(shù),樹(shù)高于人,已暗含唐人發(fā)明的“丈山尺樹(shù),寸馬分人”的原比例智慧。
荊浩的《匡廬圖》軸峰巒層疊,深遠(yuǎn)縹緲,氣勢(shì)雄偉。在繪畫(huà)史上承前繼后,成為宋代山水畫(huà)表現(xiàn)“大山大水”的先導(dǎo)。筆者認(rèn)為,荊浩山水畫(huà)理論建設(shè)的重大貢獻(xiàn)是:在王維提出“丈山尺樹(shù),寸馬分人”之后,及時(shí)地準(zhǔn)確地發(fā)現(xiàn)了“物象之原”,批評(píng)了“二病”貴似失真的路徑,反思了“物象之原”對(duì)繪畫(huà)空間創(chuàng)造的內(nèi)在根源性、基礎(chǔ)性與決定性,使個(gè)體經(jīng)驗(yàn)升華為具有哲學(xué)普遍意味的理論[2]90。“物象之原”和“丈山尺樹(shù),寸馬分人”既是古典山水畫(huà)的本體和方法,又是達(dá)到“圖真”至高境界的內(nèi)在根基。宗白華80年前對(duì)中國(guó)畫(huà)空間表現(xiàn)的超前判斷是:“中國(guó)畫(huà)家并不是不曉得透視的看法,而是他的藝術(shù)意志不愿在畫(huà)面上表現(xiàn)透視看法。”而筆者的思考與詮釋?zhuān)瑸樽诎兹A的判斷找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內(nèi)在理?yè)?jù)。
自唐至明清,中國(guó)古代畫(huà)人圍繞“丈尺分寸”所做的持續(xù)的反復(fù)的記述與思考,表明中國(guó)古代畫(huà)人對(duì)物象之原和原比例的一貫重視與堅(jiān)守,其深層表現(xiàn)為中國(guó)古典寫(xiě)意繪畫(huà)空間理論強(qiáng)盛的生命力。從展子虔的《游春圖》卷,到荊浩的《匡廬圖》軸獨(dú)特空間圖式;從“丈山尺樹(shù),寸馬分人”經(jīng)驗(yàn),到“物象之原”的理論發(fā)明,據(jù)此可以看出:物象之原和原比例理論,既是對(duì)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遺存的理論綜合與概括,也得到古典繪畫(huà)遺存圖式的一致性支持。古代畫(huà)跡圖像與畫(huà)學(xué)理論相為表里、相互驗(yàn)證的軌跡清晰而明確[2]95。
古代畫(huà)家“游觀”[2]102,多取驢、舟或步行,速度緩慢而時(shí)間充裕,零距離、全覆蓋動(dòng)態(tài)而連續(xù)地觸摸真山水,以達(dá)“遍歷廣觀”“盡得其態(tài)”。古代畫(huà)家在真山水中“游”,是融化儒家“游于藝”和莊子逍遙游意趣的獨(dú)具中國(guó)特色的美學(xué)范疇。“獨(dú)與天地精神往來(lái)”,在自然山水中神游,畫(huà)家敞開(kāi)本體之“觀”,動(dòng)態(tài)而連續(xù)地觸摸真山水,享受著精神的清淡與愉悅,沉浸于人生的虛靜與自由。在觀、游、悟、品中體驗(yàn)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自然境界。“本體之觀”統(tǒng)攝之下的“目識(shí)心記”,是古代畫(huà)家在真山水中把握物象的獨(dú)特工夫。“游觀”和“目識(shí)心記”[2]154的工夫,從本體和方法上規(guī)定了古典山水畫(huà)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機(jī)制,即不選擇再現(xiàn)視網(wǎng)膜成像的現(xiàn)場(chǎng)記錄的理路。正是“游觀”,即本體的視覺(jué)常態(tài)與山體共高低所生經(jīng)驗(yàn)的記憶與綜合,創(chuàng)生了經(jīng)典的山水畫(huà)空間獨(dú)特圖式。需要指出:“游觀”與散點(diǎn)透視、動(dòng)點(diǎn)透視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2]118。
西方古典繪畫(huà)之“看”的路徑是:人“看過(guò)去”記錄視覺(jué)反映視域節(jié)選的靜態(tài)空間[12]。畫(huà)家依賴于模擬視覺(jué)的映象,局限于再現(xiàn)視網(wǎng)膜映象的視域節(jié)選,是塑造視覺(jué)映象的真實(shí),是模擬視覺(jué)映象近大遠(yuǎn)小的透視比例。遠(yuǎn)與近,在視覺(jué)反映論的空間中,呈現(xiàn)為靜態(tài)的絕對(duì)性。現(xiàn)場(chǎng)記錄視覺(jué)反映視域節(jié)選再現(xiàn)的風(fēng)景畫(huà),其畫(huà)面空間遠(yuǎn)與近的性質(zhì),表現(xiàn)為共時(shí)性的、絕對(duì)性的特點(diǎn)。而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之“觀”的路徑是:人“走過(guò)去”體驗(yàn)時(shí)間綿延中動(dòng)態(tài)的宇宙自然本體空間。“游觀”創(chuàng)生的山水畫(huà),呈現(xiàn)的是物象的本體存有之自然真實(shí),是時(shí)間綿延中物象“折高折遠(yuǎn)”妙理的變通,是本體有機(jī)整合后創(chuàng)生的意象比例。遠(yuǎn)與近,在宇宙本體論的綜合經(jīng)驗(yàn)空間中,呈現(xiàn)為動(dòng)態(tài)的相對(duì)性。“游觀”創(chuàng)生的山水畫(huà),畫(huà)面空間的遠(yuǎn)與近的性質(zhì),表現(xiàn)為歷時(shí)性的、相對(duì)性的特點(diǎn)。空間的生成是有機(jī)動(dòng)態(tài)的循環(huán)往復(fù),是有生命、有氣韻、有精神的自由的意象空間。意象空間蘊(yùn)含著有限對(duì)無(wú)限的向往,剎那對(duì)永恒的表現(xiàn)。
拈出“本體之觀”“物象之原”等畫(huà)學(xué)概念,意在揭示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寫(xiě)意體系的內(nèi)在理?yè)?jù)。“本體之觀”與“物象之原”互摩互滲,引申出古典繪畫(huà)寫(xiě)意體系的實(shí)踐智慧——“游觀”和“目識(shí)心記”。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獨(dú)特的寫(xiě)意觀、造型觀與筆墨觀等,進(jìn)而,由此生成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的價(jià)值追求——意象的自由精神。(參見(jiàn)所附示意表)筆者認(rèn)為,是空間和筆墨的對(duì)偶概念,共同構(gòu)成民族傳統(tǒng)繪畫(huà)的兩大獨(dú)特性[2]263;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的理論體系自有永恒的理想境界和獨(dú)特的價(jià)值系統(tǒng)。
四、對(duì)“觀”的哲學(xué)的未來(lái)展望
本文描述了受成中英先生創(chuàng)造性發(fā)明的《周易》“觀”的哲學(xué)的啟發(fā),筆者學(xué)習(xí)、運(yùn)用本體詮釋的理路,對(duì)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問(wèn)題進(jìn)行研究、探索與詮釋的真實(shí)過(guò)程。可以說(shuō),沒(méi)有對(duì)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原點(diǎn)——“觀”的理論認(rèn)同、吸納和運(yùn)用,就沒(méi)有本人專(zhuān)著《游觀: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本體詮釋》一書(shū)的出版(4)。成中英先生很看重筆者的研究成果,百忙中為拙著作序以示鼓勵(lì)。
依筆者之見(jiàn),成中英先生發(fā)明的《周易》“觀”的哲學(xué)和本體詮釋學(xué),是哲學(xué)史上的里程碑。隨著成中英先生哲學(xué)思想的傳播與擴(kuò)散,隨著“觀”的哲學(xué)和本體詮釋學(xué)為人們所接受與了解,必將對(duì)中國(guó)文化研究、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產(chǎn)生深刻且深遠(yuǎn)的影響,必將進(jìn)一步開(kāi)發(fā)中國(guó)美學(xué)、詩(shī)學(xué)、畫(huà)學(xué)、書(shū)學(xué)、戲曲學(xué)等的獨(dú)特價(jià)值和新的研究路徑,必將為中、西文化藝術(shù)比較研究,提供廣闊的背景和深度的空間。
注釋?zhuān)?/h3>
[1]劉汝醴.視學(xué)——中國(guó)最早的透視學(xué)著作[J].美術(shù)家(香港),1979(9):43.
[2]劉繼潮.游觀: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本體詮釋[M].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11.
[3]成中英.易學(xué)本體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
[4]劉繼潮.“觀”和“看”的文化分野對(duì)中西繪畫(huà)史的意義[J].美術(shù)研究,2008(4).
[5]李翔海,鄧克武.成中英文集四卷:本體詮釋學(xué)[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09.
[6]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美學(xué)教研室.中國(guó)美學(xué)史資料選編:下冊(cè)[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1:17.
[7]陳育德.靈心妙悟——藝術(shù)通感論[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4-7.
[8]余英時(shí).“游于藝”與“心與道合”[J].讀書(shū),2010(3):40.
[9]劉繼潮.荊浩“物象之原”的發(fā)現(xiàn)與理論重建[C]//張曉凌.荊浩國(guó)際學(xué)術(shù)論壇文獻(xiàn)集·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3:95.
[10]王伯敏.畫(huà)學(xué)集成:上[M].石家莊: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2002.
[11]沈子丞.歷代論畫(huà)名著匯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3.
[12]劉繼潮.高居翰的困惑[J].美術(shù)研究,2008(4):45.
參考文獻(xiàn):
(1)轉(zhuǎn)引自林木.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畫(huà)研究[M].南寧: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00:9.
(2)關(guān)于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理論體系的歷史存有,當(dāng)下國(guó)內(nèi)研究者對(duì)此仍有懷疑。早在20世紀(jì)30年代,俞劍華說(shuō):“地?zé)o論中西,時(shí)無(wú)論古今,繪畫(huà)之方法僅有一種。一種何?即寫(xiě)生是也。寫(xiě)生者畫(huà)之始,亦畫(huà)之終也。”在俞劍華的認(rèn)識(shí)中,西方寫(xiě)實(shí)繪畫(huà)的寫(xiě)生路徑與體系是唯一擁有科學(xué)理論的繪畫(huà)。
(3)《荀子》350頁(yè),中華書(shū)局2012年3次印刷。中華書(shū)局出版的《中國(guó)美學(xué)史資料選編》收有荀子關(guān)于美學(xué)問(wèn)題14則(見(jiàn)該書(shū)48頁(yè))。但沒(méi)有收入《解蔽》篇的“遠(yuǎn)蔽其大”“高蔽其長(zhǎng)”有關(guān)視覺(jué)變相的內(nèi)容。限于筆者所見(jiàn),在其他的美論、畫(huà)論資料中,亦未見(jiàn)相關(guān)內(nèi)容。發(fā)掘出荀子的論述:“從山上望牛者若羊”“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證明宗白華的判斷是一種洞見(jiàn):“中國(guó)畫(huà)家并不是不曉得透視的看法,而是他的‘藝術(shù)意志不愿在畫(huà)面上表現(xiàn)透視看法”,“中國(guó)山水畫(huà)卻始終沒(méi)有實(shí)行運(yùn)用這種透視法,并且始終躲避它、取消它、反對(duì)它。如沈括評(píng)斥李成仰畫(huà)飛檐,而主張以大觀小。”宗白華.美學(xué)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20.
(4)劉繼潮著《游觀: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本體詮釋》,三聯(lián)書(shū)店,2011年1月北京1版。2011年1月,成中英先生發(fā)郵件鼓勵(lì):“任何理論或發(fā)現(xiàn)的影響都不是一兩天的。必須不斷耕耘方發(fā)揮作用,一旦傳出影響就加快了。”2013年12月30日,“游觀智慧——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理論與實(shí)踐學(xué)術(shù)專(zhuān)題展暨研討會(huì)”在安徽合肥亞明藝術(shù)館舉行,參見(jiàn)《中國(guó)文化報(bào)》2014年3月9日8版,《美術(shù)》2014年5期的相關(guān)綜述。
注: 1.示意圖將“觀”與“看”,作為中、西繪畫(huà)的原點(diǎn)與起點(diǎn),以本體詮釋而層層推演。 2. 示意圖表欄內(nèi)打“√”部分,為過(guò)去學(xué)者中、西繪畫(huà)比較曾涉及的層面,僅限于局部比較。3. 中、西繪畫(huà)比較于材料層面,過(guò)去已有表述,本表不再納入。4. 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論界沒(méi)有搞清楚傳統(tǒng)寫(xiě)意繪畫(huà)體系的內(nèi)在機(jī)理,故而中、西古典繪畫(huà)比較難以清晰進(jìn)行。5. 中、西繪畫(huà)比較研究,必須預(yù)設(shè)特定的時(shí)、空范疇。這里特指中西古典繪畫(huà),即中國(guó)隋唐至清代的寫(xiě)意繪畫(huà),西方文藝復(fù)興至19世紀(jì)前的寫(xiě)實(shí)繪畫(huà)。6.請(qǐng)參見(jiàn)拙著《游觀:中國(guó)古典繪畫(huà)空間本體詮釋》 、拙文《再讀荊浩》。
本文責(zé)任編輯: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