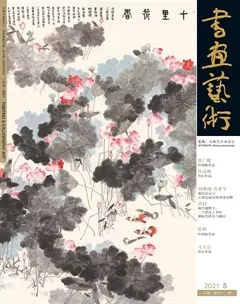碑學視野下:二十世紀上半葉碑帖的消長與融合
洪權 1979年生于揭陽,字知久,號鴻廬,齋號雪泥軒。藝術學博士。現任教于廣州美術學院,講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書法評論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廣東省青年書法家協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小欖印社理事、嶺南印社理事兼書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廣州市青年書法家協會主席團成員、易大廠與嶺南印學研究中心主任。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50余萬字。出版專著有《廣東歷代書家研究叢書·易孺》《豇豆紅館:易大廠詩詞書畫印圖攷》《當代嶺南中青年書法家作品選系列叢書·洪權卷》等。
摘 要:碑學觀念自明末清初以來不斷被強化并逐漸地成為書壇主流觀念,至晚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將此觀念與時代書風呈現推向高潮。此過程中,書壇中帖學一枝獨秀的局面被打破,書法的取法資源更是由此得到極大的拓展,書法的發展穿梭于碑帖語境的消長之中。20世紀書法的發展是在碑學由極盛甚至偏激不斷回歸理性的道路上穿梭前行。通過梳理20世紀上半葉碑帖語境下書法發展歷程的復雜狀態,考察20世紀上半葉碑學觀念之嬗變,并分析此觀念下書風所呈現之面貌的特征與得失,從而更為清晰地認識到近現代書法發展的走向,對未來書法發展也不無裨益。
關鍵詞:碑學;帖學;碑帖融合;碑體行草書
牟言
雖然“碑學”概念最早由康有為(1858年―1927年)于《廣藝舟雙楫》中提出,但是,碑學的發展可以追溯至晚明,晚明諸家表現式的書風已經和傳統文人帖學書風有很大的差異(1),雖然沒有明確的實據可確認他們對于碑的臨習、取法,但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書風已然是傳統帖學書風所難以涵蓋和闡釋的,而這種書風又恰恰暗合了碑學興盛之后的書風審美取向。張瑞圖行草書大量引入方折特征已經偏離了帖學行草書中的使轉核心筆法,倪元璐的厚重起筆和線條中間運筆過程的凝重提按動作已經不同于帖學行草書的率意、干凈、流暢特征,黃道周的奇崛雄肆、右上橫向取勢書風已經游離了帖學溫文爾雅的審美取向……傅山“四寧四勿”觀念的提出,旗幟性地表明碑學的濫觴,誠然,或許傅山并沒有明確的提倡碑學意識,然而這個觀念的內涵卻基本上表現出碑帖之間的審美差異性,以及吻合了碑學的審美趣味。晚明這種不同于帖學的書風并沒有因為清初“康董、乾趙”的主流審美導向而消沒,清初鄭簠取法漢碑的隸書借古開新引領一批追隨者,金農、鄭板橋等揚州八怪從不同的角度在帖學的基礎上結合碑學技法和理念創作出別開新面的書法風格。金農獨創的漆書線條中間部分的厚拙,以及其中的提按筆法、造型體貌明顯是對碑版大量攝取的結果,鄭板橋公開表明將隸書筆法揉入其亦楷亦行的獨特風格之中——“六分半書”……鄧石如在篆隸楷等碑派書體實踐上的巨大成功,為碑學地位的確立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石,預示著碑學興盛的到來,而阮元和包世臣從碑學理論宏觀(碑學、帖學來源與地位)與微觀(碑學技法)上提供了邏輯嚴密的理論支撐,碑學由此確立并獲得與帖學對等的身份。晚清趙之謙、何紹基、康有為等人在碑派書法實踐上的巨大影響和引領,以及康有為等人在碑學理論上進一步將碑學地位推向極致,由此,碑派書風走向高潮甚至打破了與帖學對等的地位而走在書壇的主流取向上。
一
清末民初時期,整個書壇處于碑學書法的熱潮之中。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總結式地將碑學推向頂峰,所謂“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1]1313在此之前,阮元尊碑理論的破冰而出,必然遭到千年帖學傳統派的抨擊,盡管“阮元從史學范疇建立起宏觀的碑學理論框架,但他也沒有深入到北碑內部的技法范疇。”[2]168所以從微觀上構建碑學可以與帖學抗衡的并能行之有效的技法范疇的任務就落到包世臣的身上,而包世臣構建的“萬毫齊力”“五指齊力”“中截與中實”“大小兩九宮之法”“筆毫平鋪”“卷毫右行”“提鋒暗轉”等碑學技法都指向帖學。阮元在提出尊碑的過程中并沒有對帖學進行壓抑,可以說是碑帖并舉,但是包世臣則明顯地將尊碑建立在卑帖的基礎之上,當然,包世臣的卑帖主要是卑唐,再由此而輻射到其他朝代,為碑學最終瓦解并取代帖學奠定了基礎,然而他所構建的“北碑”概念還是沒有溢出阮元的規定。康有為雖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帶有很強政治傾向的《廣藝舟雙楫》,但他卻成為碑學理論的集大成,因為阮元和包世臣碑學理論“除了其思想淵源還規定在啟蒙思想范圍之內外,他們的碑學理論本身已很少表現出啟蒙思想的痕跡”[2]172,而有別于此,康有為是在書法本體論、認識論層面全面深刻地批評帖學而實現碑學的近代轉換,具有近代藝術精神特征。然而,即使康有為的“碑學”范疇已經延伸到漢碑甚至金文領域[3]779,784,但他在繼阮元、包世臣之后進一步將“碑學”范疇限制在北魏(數量多)和部分南碑(數量少)之中,碑學到了康有為這里,其范疇被進一步的狹窄化,走向極端,康有為指出“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可宗”[3]826,從《碑品第十七》和《十六宗第十六》[3]826,830兩節即能窺知這一點。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稱“張孝廉裕釗……真能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尤為集大成也”[1]1384-1385也就不足為怪了。觀張裕釗(1823年―1894年)魏碑楷書,雖然其打破了唐以來帖學一路的楷書范式,在魏碑語境中創作出一種屬于自己的藝術風格,但是,他的魏碑楷書顯然是在極力追求“碑味”而失之自然,強調魏碑中刀切感的轉折、鉤等筆畫而又失去了毛筆書寫的自然性,強調魏碑線條的硬朗而又失去了內在質感的豐富性,徒有魏碑框架卻離魏碑實質亦遠。從學術邏輯演繹考察此現象,或許并非康有為眼光的局限性所致,而是康有為帶有強烈偏激色彩的理論所致,張裕釗只是作為支撐康有為碑學理論的一個例子。無怪乎康有為責趙之謙學北碑而“有罪”[1]1385,顯然,趙之謙北碑楷書的格調、技法內涵遠勝于張裕釗。康有為的這種批判觀念是在碑學極盛時期的一個縮影,由于對碑學價值的無限放大和付諸實踐的極力推行,必然會從矯枉過正的道路上走向另一個胡同。
無獨有偶,晚清書法紅極一時的陶濬宣(1849年―1915年),其魏碑楷書極力地模仿魏碑、墓志等碑版進行創作,其書作不僅得到帝師翁同龢的垂青,而且梁啟超也極力推崇。陶濬宣的魏碑楷書不僅在書友之間享有名氣,而且也代表著官方的審美情趣,清代“光緒通寶”銀元、角子、銅元的模字皆為其手筆。陶濬宣魏碑楷書之所以得到如此的推崇,是碑學書法鼎盛時期走向極端氛圍下的產物,與此同時,其書作被官方所推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他也就必將走到刻板、“印刷體”的道路上,因為官方的追求更傾向于實用性和大眾性,由此,藝術性也被削弱。對于藝術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結局。單純從技法的角度來考察陶濬宣的魏碑楷書,很難找到其缺陷,各個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到位,然而,其中卻很明顯能感覺到一種不自然的工藝感和描畫感,并極力夸張碑的方筆,四平八穩、了無生氣。民國中后期,馬宗霍已經看出其不足之處,其在《霋岳樓筆談》中稱:“心云寫北魏,亦有時名,然法《鄭文公碑》與《龍門造像》未能得筆,徒具匡廓,刻板凝重,絕無意致,宜蒙匠手之俏。”[4]李瑞清(1867年―1920年)、曾熙(1861年―1930年)在此時也享有盛名并推崇陶濬宣北魏楷書,他們二人并稱為“南曾北李”,其書風在書壇引起比較大的影響,并收了眾多弟子。1915年,上海題襟館書畫會成立時,吳昌碩任名譽會長,其二人與王一亭、吳待秋、馮超然等人任名譽副會長。當時上海書畫名人薈萃,而李瑞清和曾熙卻能居此高位,可以看出書壇對他們書作的推崇。李瑞清和曾熙私交甚密并皆以碑派書體名世,書風相近。他們都極力地探索怎樣用柔軟的毛筆表現碑體的金石味,為了達到這個效果,他們大量的運用“顫筆”追求碑體法書中間線條的厚度和碑味,在他們的篆、隸、楷中皆表現得非常明顯,行草書(或說碑體行草書)則轉折僵硬而失去了行草書使轉的流暢。李瑞清和曾熙的探索在一定歷史局限性的語境中也取得了初創者的意義,然而,由于過分地追求金石味以致有造作之嫌,或者言之,他們的書作只是碑學極盛時期的一種極端表現和去帖學柔弱的矯枉過正。
雖說在這個時期,碑體書法基本上都難于脫離碑學觀念極盛的語境,但也有少數的書家能走在時代的前面并獲得歷史的認可。何紹基(1799年―1873年)隸書取法漢碑并取得較大成功,筆力雄渾,如屈鐵枯藤,然而,其中的用筆也時常體現出類似于后來李瑞清、曾熙等人的“顫筆”,當然,其隸書書寫性遠勝于李、曾二人,這也為他以碑入行草書做好了鋪墊。何紹基盡量將自己的碑派凝重沉著的用筆融入行草書之中,這也是碑學確立至此表現得最為成功的范例,為后代碑體行草書的探索提供了方法性的啟示,然而其中也還透露出不自然的一面,而且,何紹基基本上以行書為主,其還很難自如地將碑派用筆揉入草書之中。何紹基的篆書表現能力和水準則與其隸書、行草書相差甚遠。被康有為認為是學碑“有罪”的趙之謙(1829年―1884年)其實卻在這個碑學熱潮中保持著一份清醒,他的魏碑楷書、行書線條皆在運用碑的體勢、筆法的同時沒有丟棄帖學的自然書寫,行筆流暢而不乏碑體的厚重,雖然有些后人認為趙之謙的碑體書法顯得“柔弱”(2),然而,筆者認為這種“柔弱”正是其學習碑體書法的敏銳性和前瞻性。在當時眾人幾乎皆在帖學低迷而碑學大放光彩的時代背景下惟妙惟肖地臨習碑版,重碑版之凝重、犄角欹側、外露的張力等,帖學的優點已被這種語境遮蔽,天資聰穎的趙之謙以輕松的筆調將碑的厚重化于隱性,不管是他的魏碑楷書,還是篆書、行草書皆如此,以致在他這個時代,我們很驚訝他對碑版書法的高超解讀。當然,由于“巧”的審美主導其總體藝術精神和行筆過快以致筆墨“留”的意味過少,他的書作顯得“氣體靡弱”也就不難理解了,而其行草書在橫向取勢的魏碑楷書框架之下上下字的引帶顯得過于牽強。
在清季民初時期,整個書壇幾乎籠罩在碑學的熱潮之中,書家對碑派書法取法進行大量的探索,由于處于尊卑抑帖的語境之中,他們對碑體的探索更多傾向于碑中求碑,一味追求碑的雄強恣肆和形體上的張揚,以致將書法又推向帖學的另外一個反面。可幸的是,有些藝術視角敏銳的書家已經開始對發展一千多年的帖學傳統重新審視并提取其中有效成分以“柔化”碑學被過分解讀的不足。
二
民國中期,在經歷了此前碑學幾達狂熱的風潮之后,具有敏銳藝術視角的書法家開始反思前代或者自己之前的觀念和書風呈現樣式。康有為晚年對自己年盛時期的碑學觀念有所改變,他也開始意識到此前自己觀念的偏激,其晚年寫的“天青竹石侍峭茜,室白魚鳥從相羊”聯句(此聯現藏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見香港《書譜》第76期),在款中寫道:“自宋后千年皆帖學,至近百年始講北碑,然張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鄧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帖,包慎伯全南帖而無碑。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3)由此可以看出,康有為畢竟是一大家,他能在自己帶有政治偏激意味的《廣藝舟雙楫》抑帖觀念中慢慢地意識到帖學的優點并進行反思,從其晚年較為成功的作品中那份重視書寫性流暢性的表達里可窺見端倪。很多時人費解李瑞清晚年鐘情于法帖,而他自己卻非常清楚其所實踐的價值,“李瑞清不恤花費大量的時間研究帖學,也給我們有這樣的啟示:在書法環境(照相術對印刷術的影響等)和碑學自身發展局限性等等因素的促使下,最終書法將走向碑帖融合之路。故統觀民國時期的書法大家,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他們的書法創作都不期而然地走在同一路上——將碑、帖與今、章、狂草等等各種資源熔為一爐而從中醞釀新的創作‘基因”[5]。由此,李瑞清的書學觀念吻合了書法發展的邏輯,并在其碑帖融合的實踐中得到一定成效,其較為成功的是對大篆的解讀和嘗試碑體行草書創作,雖然其中的啟示意義大于實踐意義,但是,這種價值往往在特定時期顯得更為可貴。此時期出現了一批把握時代脈搏的藝術家,他們雖然已經意識到前期碑學發展的不足并嘗試進行解決,而他們的落腳點還是在碑學上,也就是他們以審美傾向壯美的碑為中心,從書法發展邏輯中演繹調整之前偏激的碑學理念和實踐行之有效的方法。換言之,他們是站在碑學的立場上調節碑帖之間的矛盾并探索相互融合的渠道。正是這種不無偏袒的立場使得他們的書法實踐帶有難以舍去的僵硬,這或許也是書法發展必然經歷的階段。
自鄧石如成功激活了小篆的魅力以來,隨著訪碑的不斷深入、金石學研究的興盛和對青銅器等大篆字體的深入研究,以及晚清照相術在印刷業中的運用,大篆也逐漸進入書法家的視野,書法家們對其開啟了實踐性的探索。經過朱為弼、楊沂孫、吳大澂、俞樾等人在文字學上的梳理并基本上總結出大篆的書寫原則(指向可讀性的字體),更為可貴的是,吳大澂對大篆研究的貢獻不僅僅在于文字學上,他對大篆實踐性的探索使得大篆向書法藝術邁進一步。“如果說金文的正確書寫方式是任何一個書寫者都必須遵守的‘規則,那么,對金文的字形結構和章法的‘改動‘扭曲甚至‘變形,則體現了書寫者對如何才能富有‘美感地以金文進行書法創作的理解。在用大篆書寫的信件里,吳大澂提供了一個如何在恰當的金文字形范圍內進行富有獨創性地突破的范本,或者說,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金文書法與其他已被書法史接受的書體一樣,并不是只能對銅器銘文的字形結構進行亦步亦趨地描形,而是完全也可以融入書寫者的獨特個性的”[6]。吳大澂用小篆的筆法來解讀大篆,以致他的大篆書法線條顯得“單薄”而缺乏金石味,也即吳大澂在筆法上并沒有突破和解決大篆的核心問題。此后,李瑞清、曾熙等人為了解決大篆的金石味問題,他們注重澀行和線條中間部分的筆墨張力,然而,由于在行筆過程中過分地提按甚至顫筆以致失去了書寫的自然性。李瑞清等人對大篆的貢獻在于他們意識到大篆金石味的線質核心問題并進行大膽的嘗試,雖然其中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這種探索啟示了下一代書家對大篆的創作 方向。吳昌碩(1844年―1927年)一生以《石鼓文》為創作的主要取法資源,他以《石鼓文》為中心訓練自己的書法線條,其早、中、晚年各個時期臨習作品面貌各不相同,從早年對《石鼓文》體貌的亦步亦趨實臨到中晚年特別是“六十變法”之后,他的大篆書法面貌基本形成,七八十歲則更是恣肆爛漫。吳昌碩篆書能取得這樣的成就與其藝術觀念和對書法線條的敏銳把握有關。首先,吳昌碩早年臨習顏魯公書,且其一生對顏真卿的書法和人格都很敬佩,顏真卿書法乃是繼二王之后開創了與二王清勁、遒逸不同的具有篆籀氣、毛澀感、古拙的風格,這種書風必然會顯得更為張揚、大氣、不拘小節。吳昌碩欽佩顏魯公首先是在自身書法風格審美情趣上有了自己的定位。其次,吳昌碩將《石鼓文》的結體有意地調整為左低右高,而且這個幅度特別明顯,有些結構繁復的字被安排得“節節升”,有一種昂首挺胸的感覺,這個調子或許也暗合、支撐了他崇尚“壯美”的書風和對金石書法重構性的成功解讀。再次,吳昌碩大篆書法中最為后人推崇和崇敬的乃是線條。吳昌碩60歲以后臨習的《石鼓文》已經拋開了《石鼓文》之“形”,而是在體會、臨習大量金文之后直追《石鼓文》之“神”,他是用一種體悟來臨習《石鼓文》。后來有人詬病其臨習得不像,其實這是對書法學習階段性不同的理解不深入所致。吳昌碩60歲以后的臨習已經是進入了第三個階段的“見山是山”,吳昌碩解讀大篆的書法線條已經不再是吳大澂那種光潔、平鋪的小篆筆法了,他注重裹鋒、行筆過程的松動提按、逆行產生的毛澀筆觸而又將這些筆法揉入書寫的自然性之中,所以,他的書法線條既顯得厚重古拙、金石味十足而又書寫性很強,這是大篆書法線條質感第一次被如此完美地被解讀。從這個角度來說,吳昌碩大篆書法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其所開創的風格,而更重要的在于其解決了自朱為弼、莫友芝、吳大澂、趙之謙、何紹基等等書家以來對大篆筆法探索的總結性解讀和“完美性”表現。
三
碑體書法中不包括行草書書體,行草書乃是帖學的主要表現載體,若能將碑體書法與行草書進行有效糅合,那將是更為深層次的具有突破性的議題。趙之謙、何紹基已經對此進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趙之謙習北碑取橫勢,其碑體行草書的連綿筆畫與行草縱向取勢不無矛盾之處,很多地方顯得牽強。何紹基以凝重為主要基調,其碑體行草書持重而難行,行筆還多留有不自然的提按動作。當然,趙之謙和何紹基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已經不易,其實他們的實踐已經是走在歷史前面并且預示著碑體行草書創作的可能性,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擺脫時代語境,他們的行草書還是處于初級的碑體與帖學行草書結合階段,還存在很多的相悖之處。靜態的碑體欲與動態的行草融合需要長時間的探索才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故,碑學興起以來行草書的發展顯得稀少,怪不得楊守敬說:“國朝行草不及明代。”[7]
《流沙墜簡》、漢晉簡牘、敦煌寫經等大量帶有草書意味的早期草書墨跡的出土、出版,對晚清民國書界產生很大的影響。這些墨跡不再是那些被奉為經典的法帖所能包含,似乎這些民間性的帶有強烈時間距離的陌生趣味墨跡與碑刻有天然的親近因緣,以致,這些墨跡的出土和出版很快就被藝術視角敏銳的書法家重視并嘗試進行臨摹、創作。這些包含大量行草書意味的墨跡更多展現的是章草體(有些學人認為帶有波磔的才是章草,其實這是誤解,章草主要是字字獨立的草書,橫向取勢,有些帶波磔,有些沒有波磔,皆可歸類為章草)。章草以單字成形為主,極少多字連綿而下,即使有連綿部分也是以筆勢貫之而已,所以,此書體與碑體書法的單字經營較為接近。與連綿的行草書相比較,章草更容易在碑帖融合之中找到突破口,由此,在這個碑帖消長時期,章草較快地受到進行碑帖融合書家的關注和探索。并且,隨著這些章草墨跡的出土,章草研究也被重視起來,沈曾植、王世鏜、卓定謀、劉延濤等人對章草進行較為深入地研究并為碑體章草創作提供了理論基礎。如“沈曾植在章草研究的成就在于成功的融章草筆意于行草書中,形成了行草書新的審美內涵;王世鏜的章草研究側重于對章草的規范與法度的研究,提倡用篆隸筆法寫章草,并融合章今,最終成為一代大家;卓定謀以學者的身份研究章草,所著《章草考》收集的章草歷代著述最為詳備,成為研究章草最重要的資料;劉延濤的《章草考》是嚴謹的章草研究論文,該文充分地利用了新出土的簡牘資料,對章草的源流問題有很多新的觀點,劉延濤的章草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8]以致,民國時期有一批書家進行章草創作并以此名世,例如沈曾植、于右任、馬一浮、羅停最、章炳麟、羅復堪、王世鏜、王蘧常、卓定謀、余紹宋、林志鈞、劉延濤等等諸家。沈曾植(1850年―1922年)早年為應對科考曾經打下了堅實的帖學基礎,中年后對北碑、造像等大量地臨習,晚年逐漸探索碑帖融合的可行性,并主要在碑體用筆與章草的相結合上做了大量的探索。特別是對《流沙墜簡》著力甚多,其弟子王蘧常也曾言:“先生于唐人寫經、流沙墜簡亦極用力,晚年變法或亦得力于此。”[9]當時,《流沙墜簡》對書界的影響頗大,鄭孝胥曾云:“自《流沙墜簡》出,書法之秘盡泄,使有人發明標舉……則書學之復古,可操券而待也。”[10]沈曾植對《流沙墜簡》的推崇可考,他在題跋王珣《伯遠帖》中說:“內府收王珣《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11]324沈曾植將《流沙墜簡》與《伯遠帖》相比對,可以看出他對《流沙墜簡》的重視。不僅僅他自己對《流沙墜簡》等章草重視并進行臨習,而且還勸自己的學生也關注之,其弟子王遽常曾說:“四公教以讀書分類札紀之法,又曰:‘凡治學,勿走常蹊,必須覓前人優絕之境而攀登之,如書法學行草,已為人摹爛,即學二王,亦鮮新意。不如學二王之所出——章草,自明宋、祝以后,已成絕響,汝能興滅繼絕乎?”[12]沈曾植對章草的研究很多,皆散見于他的著作之中,他并不是淺嘗而止,他對書法史的發展進行宏觀上的梳理并對章草發展的淵源流變進行探究,最終提出創作章草的意義。沈曾植考察《急就章》寫道:“《急就章》自松江本外,世間遂無第二刻本。松江石在,而拓本亦至艱得。余求之有年,僅得江寧陳氏獨抱廬重刻書冊本耳。集帖自《玉煙》外,亦無摹《急就》者。思元、明書家,盛習章草,所資以為模范者,未必別無傳刻也。況《玉煙》搜羅舊刻以成,固明見香光敘文中,無庸疑也。”[11]57當然,若只是單純地進行章草創作,沈曾植的碑體草書并不能取得如此的成就,關鍵是,他將凝重、古拙的北碑用筆揉入章草之中。其用筆樸拙生辣,線條雄渾酣暢,章法縱橫捭闔,呈現出一種充滿磅礴大氣的有別于歷史上其他書家的行草書風格。當然,由于沈曾植是以碑學的立場來解讀章草,他不管是在行書還是草書中都顯得碑的味道表現過重,以致,他的線條凝重有余而流暢不足,行草書的使轉更多被替換為斬釘截鐵的方折,結構在追求生拙奇肆中顯得怪異。
四
民國晚期,隨著碑學的發展,學人慢慢地意識到前階段對碑版的過度推崇和解讀,雖然有矯正帖學痿弱不振的價值,但是,這種“過度”也使書法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一棍子打倒整個帖學又帶來了新的問題。“書壇對碑學的把握不斷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在追求金石氣勢的過程中丟失了細部的考究而顯得粗糙,與此同時,帖學的韻味和技法受到極大地削弱,書法更多的只剩下外殼的張揚、粗獷霸悍和雄奇角出,而缺乏書法傳統的審美內涵。”[13]這個時期的書法家已經意識到作為與帖學對等地位的碑學存在的合理性,也是有價值的,但是,帖學不能因此而受到打壓,應該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對待碑帖之間的優缺點的互補,不應該把文化救國之心理簡單地移植到書法藝術上來。碑帖只是書法取法資源的對象,它們本身并沒有優劣高低之分。沈尹默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基本上臨習碑版,其大概48歲之后開始轉習法帖、行草書等[14]。沈尹默自己也說:“一直寫北朝碑,到了1930年,才覺腕下有力。于是再開始寫行草。”[15]奇怪的是,與沈尹默齊名的“南沈北于”的于右任(1879年―1964年)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轉換自己的學書方向,于右任說:“余中年學草,每日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16]從此推知,于右任開始臨習帖學、草書的時間大概在1927年至1930年之間。深究兩位大師不約而同地學書轉變,他們以敏銳的藝術嗅覺發現了碑學的發展需要有帖學的滋養,才不至于使碑學走向粗野的一面,或者說碑學需要帖學的熏陶來完成其“雅化”的轉換。當然,照相術、印刷術的快速發展,以前只有王公貴族才能一睹其真顏的珍貴法帖開始逐漸地走入尋常百姓家,學人眼前展現了琳瑯滿目的各類碑帖學習資料,他們的視野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寬廣,他們可以更為全面、直觀地審視書法的發展脈絡和深究其中的內理,甚至嗅出書法未來有價值的走向,而前期書家在碑學立場上進行碑帖融合嘗試的優缺點成為他們的出發點。更為可貴的是,以沈尹默、于右任為代表的這個時期的書家,已經拋開了碑帖之間的桎梏,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思考和實踐碑帖之間的價值并將之進行有效糅合,不管是碑分量多還是帖分量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合理地重構碑帖資源以形成有價值的體勢。
此時期,沈尹默的帖學觀念和實踐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帖學為中心的藝術圈,例如喬大壯、汪東、章士釗、馬公愚、潘伯鷹、鄧散木、白蕉等人與帖學大家,然而,從歷史影響力來說,此時期以沈尹默為領袖的帖學派還不具備與以于右任為中心的碑帖融合書派進行抗衡的群體力量,沈尹默的影響力在建國之后才慢慢地彰顯出來。于右任幼年以趙體為基礎,并在學習王羲之行草書中打下基礎,旋即進行大量的版本臨習并達到瘋狂的程度。經過20多年搜尋大量碑版并進行研究和臨習,于右任對碑學書法的研究不可謂不深。鐘明善說:“以篆、隸、草書筆法入楷在北魏碑志、六朝寫經中時或見之,然而以魏楷結字為基礎,有意識地將篆隸筆法乃至行草筆勢用于楷書、行書,且糅合得如此和諧自然,則近世書家中當首推于右任先生。”[17]于右任對碑體書法的研究已經跳出了立場的偏頗問題,那些刀刻、風化嚴重的碑版書法在他的毛筆下一一得到“復活”,既有碑的雄強厚重也不失毛筆的自然書寫性,所以說,于右任對碑版的臨習與創作是成功的。他在學習碑體書法的過程中共收集到480余塊碑版并最后捐贈給西安碑林,為中國書法藝術留下了珍貴的資料。上面已經提到,于右任中年時期轉向臨習帖學類的行草書,特別是對草書的關注,并于1932年在上海創立標準草書社,邀同好者,共同研究。于右任萌想從實用的角度編寫一本《標準草書》,首先選擇章草作為“母本”,后因“字字獨立”“一字萬同”并與當時草書書寫習慣不符合而否定。再選“二王”法帖中的草書為底本,固然“二王”草書為書法藝術之正宗,然而由于其又過于藝術化,與其“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標準有違駁之處,由此,他最后以這四標準碑為準繩,遍尋歷代法書,歷經數年而成《標準草書范本千字文》。于右任正是基于清以來中國行草書被書界“遺忘”,甚至“國朝行草不及明代”的狀況,從行草書復興是歷史需要的角度來恢復行草書的價值。另外,從于右任選擇“母本”書法的角度來看,他并沒有偏重于哪碑哪帖,而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選擇,這個態度的轉變看來平常無極,然而,其中卻透露出他對歷代法帖的客觀關照,這是碑學以來一個立場上的轉變,他已不再像沈曾植那樣站在碑學的立場上來取法資源,而是將碑帖二者皆視為平等,合者而取不合者則棄之(4)。有些學人批評于右任的“標準草書”過于實用性,從而削弱了草書藝術性的一面。其實不然,于右任創編“標準草書”是因其官本身份對大眾文化普及的需要而必須站在實用的立場上為之,而其自身的行草書創作則是站在藝術的立場上生發的,他說:“字無論其為章為今為狂,人無論其為隱為顯,物無論其為紙帛為磚石為竹木簡。”[18]似乎世間萬物皆為其用之,這是一個高視野的關照。觀于右任中年習行草書以后的作品,瀟灑自如、氣勢磅礴、古今盡收筆底,他將碑體書法的厚重、古樸、雄強化無形于行草書之中,是碑學興起以來,第一個將碑帖糅合得如此恰如其分的人。王澄在《一代書家于右任》一文中說:“真正意義上的草書融入碑意,獨于右任一家,它產生于歷經了碑學振興后的特定時期,同歷代草書有著質的不同。因此,筆者為其提出一個新名稱,曰‘碑體草書。”這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創造,這種被稱為“于體”的“碑體草書”其價值已經溢出了書體本身,它的出現將為后代書家的創作提供一種新的方法啟示。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于右任結識了一位當時不出名的書家王世鏜(1868年―1933年),并被他的碑體章草藝術水平所驚訝,稱之:“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并。”王世鏜早期遍習碑版書法,而后與沈曾植類似被新出土的《流沙墜簡》、漢晉簡牘、敦煌寫經等草書打動并進行研習,其所創造的碑體章草就碑帖融合的角度來說要比沈曾植略勝一籌。于右任是有眼光的,他接王世鏜來上海一同研習“標準草書”,并資助其出版《重訂章草草訣歌》,由此王世鏜的書名大顯并被歷史留住,他的出現還促成了近現代章草熱進一步的升溫。在沈曾植的碑體章草書的啟發之下,后來出現的王世鏜、鄭誦先、高二適、王蘧常等一批章草大家,他們考訂章草、探索碑體書法與章草融合的可能性,在章草領域開創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為后代留下了可供參考的成功范例。
在此時期,吳昌碩傳下的弟子基本上沒有走出其范式,只是在老師的陰影下搖擺,其中潘天壽、沙孟海能擺脫老師的藩籬并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面貌且取得不俗的成績,此二人的書法價值主要體現在建國之后,將另文再論。
結語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碑派書法觀念從鼎盛時期的唯碑是尊、抑帖、詬病唐碑開始,書作注重金石味、粗獷甚至走向粗野,偏離了書法的自然書寫性和內涵韻致,這一點李瑞清、康有為晚年皆有所察覺,只是缺乏實踐的時間來完成思想之理路。民國中期,部分藝術視角敏銳的書家意識到前期的不足并開始關注帖學,從帖學中吸取養分來滋潤碑學的張揚,吳昌碩雄強大氣的大篆回應了這種碑學理念,他將鄧石如以來書家在小篆書寫性的成功上與金文的裹鋒、絞轉、中實等金石味筆法進行有效的結合,創造出傲視古今的大篆作品范例;而沈曾植將新出土的章草墨跡糅入北碑筆調之中,這是繼趙之謙、何紹基之后進一步深入的探索碑體與行草書的融合,然而,此時期的書家還是站在碑學的立場上來捏取帖學有效元素。民國后期,藝術家開始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調節碑帖之間的桎梏,將碑帖皆視為書法臨習創作的取法資源,于右任為最具代表者,他的行草書一派自由瀟灑而不再是一味外露式的粗獷,而碑體的厚實、古拙、雄強的質感又在其線條之中處處可見,創造出一種帖面碑質的成功的碑體行草書,這是曠古未見之樣式,對后代書法的發展具有指明性的啟示意義。20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皆處于極大動蕩時期,書法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概外,經歷了一個激蕩的時代,碑帖之間的消長,限于篇幅只能對書法本體之外的文化因素另文再述。
〔廣州美術學院科研項目(19XSC15)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康有為.廣藝舟雙楫[M]//崔爾平.明清書論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2]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M].河南: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3]康有為.廣藝舟雙楫[M]//黃簡.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4]馬宗霍.書林藻鑒[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44.
[5]洪權.論胡小石碑體行草書及其對當下書法創作的啟示[J].書畫藝術,2009(4):66-73.
[6]洪權.在走向金文書法的途中——一種對吳大澂創始中的金文書法創作的檢討[N].書法導報,2007-12-12(7).
[7]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714.
[8]吉德昌.民國時期章草理論之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1:Ⅰ.
[9]王蘧常.憶沈寐叟師[J].書法,1985(4).
[10]崔爾平.明清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944.
[11]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外一種)[M].上海:上海古籍版社,2009.
[12]王運天.二十世紀書法經典·王蘧常卷[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130.
[13]洪權.1949-1979:中國書法繁榮前的準備[J].書法賞評,2010(1):28-35.
[14]費在山.沈尹默先生學書年表[J].文教資料,2011(4):14.
[15]馬國權編,沈尹默著.論書叢稿[M].臺北:華正書局,1989:148.
[16]于右任.標準草書(第十次本)[Z].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
[17]鐘明善.于右任書法藝術管窺[J].書法,2010(6):75.
[18]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自序[J].中國書法,1998(6):2.
參考文獻:
(1)白林坡.明末清初關中“前碑學”研究(上)[J].榮寶齋,2009(6):62-71.文中以關中為基點對“前碑學”的存在進行考證,并得出明末清初書家對碑學書法資源的大量涉略。
(2)對于“柔弱”問題,劉恒有自己的看法“由于趙之謙在用筆上深信包世臣‘萬毫齊力的主張,務以鋪毫疾行為目標,再加上字形的欹斜低昂和行筆過熟過快,因此看上去偏鋒扁筆較多,俏媚而不古樸。”見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216.其實在此還有一個原因,現所見的趙之謙楷書基本上皆是40歲之前的作品,此后,他的作品比較少見,主要是他認為為官取功名比藝術更重要。
(3)在康有為晚年手卷題跋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千年來無人能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篆隸鐘鼎哉!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漢隸、陶鐘鼎!合一爐而冶之,苦無暇,未之逮也。”
(4)徐暢,王東明.于右任的書法藝術觀[ J ] .書法之友,1995(4):15.于右任僅歷代碑刻拓本和墨跡本《千字文》就搜集到了一百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