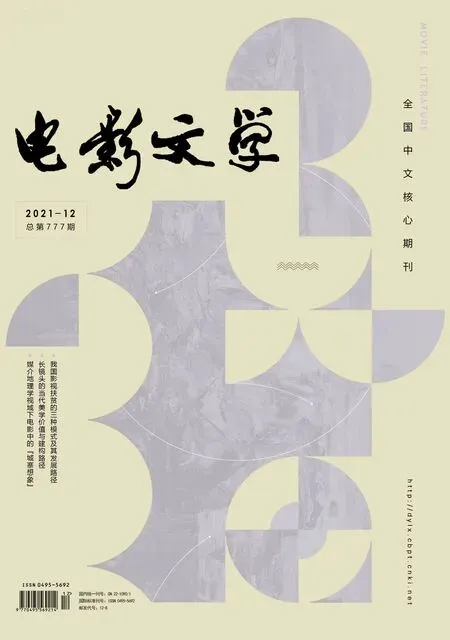價值消解:《你好,李煥英》的劇作征候與喜劇審美研究
李軼天(重慶移通學院藝術傳媒學院,重慶 401520)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辛丑年伊始,選擇大年初一上映的電影共七部,其類型涉及喜劇、動作、奇幻、動畫等,亦不乏諸多實力派演員,而由賈玲執導的電影處女作《你好,李煥英》大獲好評,以黑馬之勢領跑春節檔。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5月7日,該片上映85天,票房54.12億,賈玲憑借此片成為全球單片票房最高的女導演。中紀委更是評論該片:“李煥英”是現實中無數母親的縮影。
電影《你好,李煥英》改編自2016年賈玲的同名小品,以賈玲親身經歷為為創作背景,講述了賈曉玲在母親遭遇車禍后穿越時空,重返母親年輕時代,以圓夢為意與母親再次相遇的故事。該片打破了傳統喜劇模式,采取笑中有淚的悲喜劇模式,看似簡單的故事情節讓人有所笑、有所泣、有所思。
一、喜中蘊悲,潛藏深思
(一)“歡樂言辭”暗揭“曲終人散”
著名喜劇表演藝術家陳佩斯提出“悲劇內核”時曾指出:“一切喜劇都有一個悲情內核。笑是果,悲是因。”電影《你好,李煥英》恰如其分地體現了這一點,悲劇意識作為喜劇效果的一種建構手段越發明顯地展現在觀眾視野當中。該片開篇以幽默的旁白簡短地介紹了賈曉玲的成長歷程:出生九斤八兩,學會的第一句話是“再來一碗”,幼兒園拉褲子是常事,上學后經常被叫家長。以至于母親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你能不能給我長長臉?”高考結束后,賈曉玲為了給母親長臉,做假證將成人教育錄取通知書換成了首都戲劇學院錄取通知書。在慶功宴上被揭穿后,母親李煥英推著自行車與賈曉玲喪氣離場。賈曉玲對母親說:“我將來一定有出息!”母親扭頭說:“那肯定的。”來自李煥英的定格鏡頭讓這一切變得更為堅定,母女兩人騎自行車并有所憧憬的情景滿是溫存。然而短暫溫存之后迎來的卻是一場意外的車禍,轉場醫院,由喜入悲。
在醫院里,一場穿越讓賈曉玲來到1981年與李煥英相遇,此時的李煥英是勝利化工廠的一名女工,年輕的她一改賈曉玲對母親“從我有記憶起,媽媽就是個中年婦女的模樣”的傳統記憶。驚訝之余,賈曉玲的目的是讓母親李煥英更快樂,幫她買到了全廠第一臺電視機,鼓勵她參加排球比賽,安排相親,她曾構想,若自己不是李煥英的孩子,母親應該過得比現在好。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故事充滿喜劇元素,臺詞作為表象呈現,實現了“話語建構—信息傳遞—意義理解—效果生成”的循環過程。作為喜劇電影情節的構建者,臺詞加強電影喜劇性、增強敘事性,與此同時其寓意具備“隱蔽性”,需要受眾結合自身審美感受電影文化內涵。
劇情發生轉折在賈曉玲與冷特的對話里,賈曉玲提及自己總是把褲子摔破,漸漸地母親便學會給破舊的褲子縫上可愛的圖案。一句“可是我媽現在還不會縫啊”讓知道真相的賈曉玲崩潰而泣,揭示了李煥英與賈曉玲同時穿越至此,賈曉玲為了讓母親更開心,李煥英則在迎合之中想讓女兒釋懷。用喜劇劇情展現悲情內核,印刻電影主題蘊意。
(二)“笑順父母”引發“及時行孝”
提及“孝道”可追溯至春秋時期,《左傳》釋義盡心奉養、尊敬父母。觀古詩以明志,唐代孟郊之詩《游子吟》更是提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電影《你好,李煥英》在宣傳時打出“‘笑順’父母”的口號,采取一語雙關,既強調了電影的喜劇性,又凸顯了電影主題“孝順父母”,亦可帶動兩代乃是三代人的觀影沖動。
所謂電影內涵主導解碼,是受眾群體針對電影創作者所編訂符碼的解讀,結合電影敘事及人物形象塑造所傳遞的文化意象的認知及理解。在此過程中,若電影創作者占主導地位,則可引導受眾群體感知電影符碼,傳遞內涵思想。在電影《你好,李煥英》的結尾處,賈曉玲開著敞篷車,想象著母親穿著綠色皮衣坐在自己身旁,母女二人有說有笑。幻想如同流星,一閃而過,定睛望去,副駕駛的座位空空如也,賈曉玲失落的表情恰如其分地展現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傷楚。就受眾心理學而言,創作心理與接受心理高度融合,電影文化意象被受眾群體盡數認同,形成傳播雙向互動,引領傳統文化,涵養百姓情懷。
二、空間交疊,構建形象
(一)穿越時空,多維呈現
電影《你好,李煥英》打破固有敘事時空,采取時空重構并進行敘事,以穿越時空的方式展現了少女時代的李煥英,時空定格為1981年,以醫院的電視機為轉場,黑白、彩色交疊,實現時空轉換。受眾跟隨其后,時代感加強,以賈曉玲的視角看年輕時代的李煥英并展開故事。伴隨著劇情的推進,受眾逐步發現電影的敘事線還有李煥英的視角,從她穿越到勝利化工廠時,看到騰空而落的賈曉玲,一邊沖過去一邊喊“我寶”,暗示受眾她其實早就知道真相。當母女二人相遇時,李煥英給賈曉玲的身份是省城二姑家表妹李樂瑩,作為母親的李煥英一路配合女兒,以至于連銀幕前的受眾一起蒙蔽。
《電影藝術詞典》如此形容電影:“電影,通常被認為是時間和空間的藝術,電影時間是由放映時間、敘述時間和心理時間構成的。”電影敘事所涉及的時空關系并非現實世界的時空延續,而是電影美學的一種連貫性表達。本片在敘事方面采取了時間重構與空間重構,在時間重構方面將現在與1981年相連,1981年的場景是情感追憶與重新抉擇,這包括對母親青春的追憶,在成為母親之前的李煥英也是一個敢愛敢恨、努力拼搏、愛笑的少女;包括賈曉玲一心撮合沈光林與李煥英,只為改寫母親的生活軌跡。而關于現在的時間里,電影留下的篇幅似乎有所縮減,究其原因是逃避現實的心理狀態,作為賈曉玲的視角,她不愿意在真實時間里感受母親離去的痛楚,從而選擇逃避。在空間重構方面,物理空間的重疊與交融讓劇情更具吸引力,給予受眾群體感同身受的現場感;意識空間的交叉帶領賈曉玲、李煥英重返夢境,在這場夢里,她們帶著各自的秘密努力讓對方開心;意象化的多時空重塑,讓電影的感情線更具感染力。
(二)形象多元,真摯母愛
該片所講述的故事與其說是關于母親的故事,不如說是關于母愛,乃至親情更為貼切。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電影中的母親形象被消解其外形美,以善良、奉獻、無私等美德為主的內在美呈現為主,這就是該片中賈曉玲的印象中母親始終是一位中年婦女的形象的原因。這貼合傳統認知范疇,而該片正是本著對此模式的消解,呈現李煥英的少女形象,在成為母親之前,她首先是她自己,一個活潑陽光的女孩形象。
文化融合與女性視角引發母親形象的多元化,而李煥英的傳統女性形象仍然存在著,是對女兒毫無保留的愛。關于這一點,在電影中有諸多細節均可表現。如賈曉玲在幼兒園拉了褲子哭著回家,李煥英一邊給她洗一邊笑著安慰說:“我們比別的同學年紀小才會這樣,說明曉玲很聰明。”來自母親的安撫,讓兩個人都笑逐顏開。賈曉玲考上了省藝校,母親送她上了長途車,退掉了原本的車票,在漫雪飛舞的冬天獨自走路回家。母女兩人醉酒后,李煥英用瘦弱的身軀艱難地扛著賈曉玲回家。
令人驚喜的是,李煥英的人物形象并非止步于傳統女性形象,作為母親,其身上有更為光鮮的開放式教育理念。賈曉玲在樓下仰著頭大喊:“李煥英!”迎來的回復是:“喊什么呢,小王八蛋!”母女對話可見二者保持平等地位,母親對女兒充滿包容度和同理心。
三、嚴肅沖突締造喜劇力量
(一)假定情境的戲劇性
“假定性”一詞最早源于戲劇理論,是藝術家根據認識原則與審美原則對生活的自然形態所做的程度不同的變形和改造。“情境”則是戲劇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戲劇理論家D.狄德羅在提倡嚴肅劇(即正劇)時指出,如果說性格是過去喜劇中的主要表達對象,那么在嚴肅劇中,情境則是主要對象。而黑格爾把“情境”提升為各種藝術共同的對象,他在討論戲劇特性時,把情境、沖突動作聯系起來,構成完整的內容體系。電影作為受戲劇影響頗深的藝術門類,在劇作創作方面亦有假定性的審美特性,情境更是組成敘事的主要部分。
《你好,李煥英》的劇情是在假定情境中展開的,穿越至1981年是時間上的假定性,勝利化工廠則是環境的假定性。在這種假定情境中,賈曉玲與李煥英的公眾關系為表姐妹,賈曉玲清晰地觸碰到了李煥英的青春年代,為了配合彼此,她們更像是演員在規定情境中的角色扮演,對所扮演的人物進行體驗與表現,從而達到了在規定情境中熱情的真實和情感的逼真。這種主觀意識上的帶入性表演,給劇中人物設身處地的體驗感,通過行為呈現和動作體系凸顯假定情境中人物的性格特點。假定性情境可以增加電影本身的活力與張力,真實的表現母女二人的精神世界;從受眾角度而言,一改被動接受,用想象去補充和豐富電影本身未曾表達的內容,讓故事更為豐盈。假定情境增加了電影本身的戲劇性,跌宕起伏的故事設置、人物關系、喜劇性構建該片的外在戲劇性;而細膩的人物內容活動及情感流露則組成了電影的內在戲劇性。內外交融之中,演員與受眾群體形成良性互動,演員通過表演傳遞電影主題,受眾加之自我解讀使其得以升華。
(二)人物戲劇沖突
作為電影的主觀表現者,人物設置及人物沖突尤為重要,人物之間的矛盾、對立將推進劇情的開展,在人物沖突的發展過程中激發機制設計成為影片的轉折點。激發機制引發人物戲劇沖突,如羅伯特·麥基所言:“激勵事件偶爾需要由兩個事件構成:一個伏筆,一個分曉。”
《你好,李煥英》主要的人物沖突為賈曉玲與李煥英這對母女,賈曉玲想改寫母親的生活,當她得知母親與父親結婚時執意拆婚,甚至勸李煥英去離婚。在賈曉玲看來,李煥英這是走回了老路;可李煥英的一句“實這輩子我過得挺幸福的,你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讓賈曉玲陷入了沉思,因為在她看來李煥英的一生并不快樂,而此處在人物戲劇沖突上解讀了母親的感知。在該片中,母女的沖突占主要地位,除去主角之外的配角依然精彩,如冷特這個人物的設置。冷特是游離于劇情之外的一個邊緣人物,以至于受眾會覺得可有可無,其實則不然。冷特是一個游手好閑的小混混形象,在劇中最大的人物沖突在于醫院那場戲,母親患病入院,父親對他大發雷霆,稱其從沒有讓媽媽省心過。傷心之余的冷特對賈曉玲闡述,如果我媽媽生的不是我,應該比現在幸福得多。可以說,“冷特”這個人物設置是賈曉玲自我意識中的一個縮影,這段劇情也激發了賈曉玲撮合李煥英與沈光林的決心。
人物戲劇沖突讓情節推進與細節展現更為直觀,配合演員表演的個性化、臺詞的性格化、多線敘事與色彩交織,套以喜劇外衣,讓整部電影戲劇沖突點增多,可觀性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