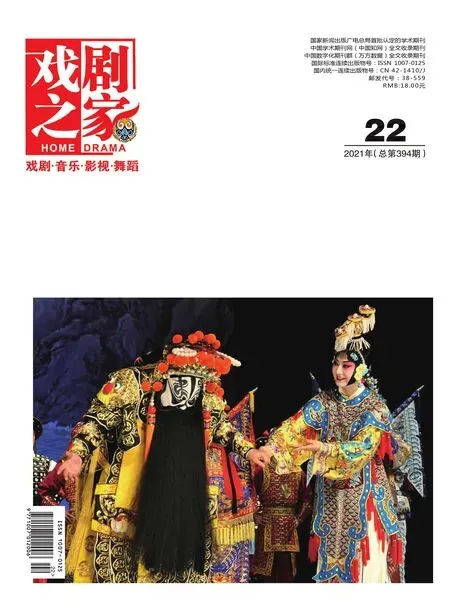浮世悲歡:桑弧都市三部曲中的中年群像
梁夢葦
(武漢大學 藝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放眼當下中國影視市場,“中年”話題逐漸成為創作者們的涉獵傾向,“中年”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在影視創作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萬箭穿心》中的中年武漢女人李寶莉對苦難生活的支撐,還是《夏洛特煩惱》中的中年無業男人夏洛對美好過往的幻想,亦或是《我不是藥神》中的中年離異男人程勇對人生價值的抉擇,無一不在構建著當下社會的中年群像。
回顧中國影史,也有不少作品對“中年”這一話題展開過敘述和探討,但真正以中年形象為主角,深入人物內心,通過個人的心理狀況和生活境遇去反映中年群體對自我歸屬與自我認同的追尋的作品還在少數,而桑弧導演在1947-1949 年期間創作的三部電影正是為數不多的聚焦于中產階級中年群體的作品。《不了情》中中年企業家夏宗豫和家庭女教師虞家茵的愛與克制,《太太萬歲》中中年主婦陳思珍在家庭關系里的處事之道,《哀樂中年》中中年校長陳紹常對往后余生可能性的執著追求,都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即使拿到21 世紀的當下,仍然能與觀眾產生相應的共情色彩。
在20 世紀40 年代,革命戰爭題材一直穩居影視創作話題的前列,尤其是上海這一形勢紛繁復雜的大都市之中,而桑弧導演沒有選擇重點表現在革命浪潮中奮勇向前的年輕人,也沒有選擇重點描繪動蕩不安中底層人民的苦難經歷,他只是抓住了大都市中那一縷煙火氣,跳脫出大的政治格局,回到人本身,回到社會大背景之下中年人必經的困頓,用其作品的另一幕后人物張愛玲女士的話來說,便是:浮世的悲歡。
一、中年哀樂:喜劇表達的諷刺性
桑弧導演是一位擅長喜劇表達的導演,但他的“喜”往往不滿足于停留在觀眾所獲取的愉悅感上,更多的是要通過這種喜劇化的語言表達去揭示上海中產階級市民生活的“哀樂”,在歡樂中夾雜著辛酸,在熱鬧的場面中營造出世俗悲歡,這是桑弧導演獨有的作者風格,也為戰后都市喜劇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方向。在此之前,喜劇場面的營造大多趨向于夸張的動作、快速的語言交替以及緊張奇特的環境背景,但在桑弧的影片中,喜劇表達更凸顯了一種隱喻性和諷刺性,在美國“神經喜劇”的基礎之上又融入了上海自身的地方特性,以及上海本地中年階層的真實困境,在層層遞進的喜劇語言之中暗藏著“悲苦”的本質。
在桑弧都市三部曲中,《太太萬歲》的喜劇氛圍最為濃厚,影片一開始就以“打碎杯子”、“飛機和輪船”以及“菠蘿蜜”等幾個誤會接替呈現來烘托整體的喜劇風格,情節推進緊湊,關鍵信息內部聯系明晰,引導著觀眾進入一個頗具趣味性的生活情境。而《太太萬歲》的結尾更是展現了桑弧喜劇風格中“以喜襯悲”的諷刺意味,影片以陳思珍原諒丈夫,二人重修舊好的“大團圓”方式結尾,符合喜劇電影的敘事邏輯,但這樣“破鏡重圓、破涕為笑”的結局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觀眾們的探討,因為其對“快樂”的解釋其實并不快樂。在上海這樣一座被現代生活方式以及現代思想沖擊過的大都市,陳思珍本身擁有著獨立生活的智慧和對抗壓迫的力量,但她仍然選擇妥協和屈服,因為完整的家庭和和諧的夫妻關系是她前半生所追尋的信念,也是她眼前不忍舍棄的“生存依賴”。因此在影片中,都市的現代化進程仍然沒有辦法動搖父權壓迫和男性話語權的根莖,雖然是喜劇的設定,但隱藏的卻是都市中年女性對人生道路的一種選擇,諷刺的卻是現代與傳統的矛盾碰撞之下產生的“悲壯”效果。同時,影片中的另一位女性角色一如既往地在“香山咖啡館”重復著那句“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告訴過第二個人”,再次提升諷刺感,又不知下一位將要經歷與陳思珍同樣的境遇的中年女性身在何處,又將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不了情》和《哀樂中年》雖沒有《太太萬歲》這么鮮明的喜劇指向,更偏向于“正劇”,但桑弧導演仍在其中運用了自己較為熟悉的喜劇筆觸來調和影片節奏和整體風格。《不了情》中虞家茵的父親作為一個“反面人物”每次出場都帶有一定的喜劇效果,一邊吹著“以前家里有很多傭人”的牛,一邊找女兒要著“洗澡”的零錢,甚至不顧道德約束極力撮合女兒和有著家室的夏先生,令人哭笑不得。父親這個喜劇人物雖不是主角,卻對主角的情感選擇產生了重要作用,他是虞家茵無法擺脫的原生陰影,是一個只為了利益而談感情的中年男人,使得虞家茵更加無法正視自己與中年企業家夏宗豫的情感,只得無奈選擇放棄。《哀樂中年》的諷刺性則是一種更直接的、外在的、喜聞樂見的態度,在人物對話中提出了“中國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卻沒有中年”以及“中國人太看重死,卻不考慮怎么活”的現代思想。最后主角陳紹常干脆在自己的“墓地”上蓋起了學校,開始了“新的生命”,此時的觀眾除了為這種人生態度而欣喜雀躍之外,大概也在這種喜悅的氣氛中思考著自己的生命價值,這是中年人陳紹常的突破,也是桑弧導演想要通過積極陽光的基調為觀眾傳遞的一種不同于往常的力量。
正如桑弧導演自己在采訪中說的:“我覺得在‘笑’中間還應該有一些苦澀的味道,這樣的喜劇才是比較好的喜劇”,他把中產階級中年群體的茫然無措用幾分戲謔的方式隱藏在嬉笑怒罵之中,反而是對真實生活的一種尊重。“中年”是人生中最漫長最復雜最悲喜交加的一段時光,桑弧導演沒有用中國電影一貫的“苦戲”手法去描繪,沒有將自己鏡頭下的人物拖入直觀悲慘的境地,因為現實生活中的多數時候大抵如此,不溫不火地行進著,像一杯慢慢冷卻的白開水。桑弧導演的喜劇像是往這杯水里加了一包彩色的粉末,看似奇幻動人,而它的本質,仍舊是一杯白開水罷了。
二、中年隱喻:人物刻畫的現實性
在傳統的“影戲觀”當中,通常“將二元對立、善惡分明的人物服務于情節敘事的需要”,而桑弧導演影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逐漸突破了影戲電影“二元對立人物美學原則”的成規,擺脫了傳統“影戲”當中人物臉譜化的特點和教化性的功能,還原了真實生活當中人物的多面性,使得人物形象更具現實性和說服力。在都市三部曲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盡量保持了其獨特的個性,但又拓展了其社會共性,在共性與個性、內在與外在的共同加持下,做到了沒有完全的“好人”,也沒有完全的“壞人”。
桑弧導演對《哀樂中年》中的角色們都沒有給予明確的價值判斷,人物的選擇和做法都是基于所處時代的生存價值觀和自身成長的思想構成,對于冷漠的世情,作者沒有批判,只是以冷靜客觀的視角去展現,反而道出了最為真實的中年況味。男主人公陳紹常的人物刻畫,先從其境遇開始,大兒子陳建中事業有成,礙于身份地位和世人眼光,陳紹常需要“被退休”來配合兒子的階層要求。而這種住在洋房里“養尊處優”的日子其實并不好過,兒女有了各自的生活重心所以疏于對他的照顧和陪伴,他只能靠種花養魚來填補生活的空缺,這仿佛是這座大都市對于中產“老年人”的共同規則,是“享樂主義”價值觀對個體的馴化方式。這部作品的人物刻畫不僅僅折射出了那個時代的價值選擇,更是超越了時代,將觸角伸向了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里常常被忽視的中年群體。在當下社會,每個中年人也都面臨著自己的人生選擇,屈服于社會規則還是繼續追尋夢想,到達一定階段后是安于天命還是破圈前行,這種自我審視在《哀樂中年》中早已揭示,但中年群體的“浮世悲歡”又遠不止于此。《不了情》中,虞家茵的內心矛盾也有著強烈的揭示性和現實性,雖然她最終選擇舍棄了感情,展現了人物的道德操守和人性的“善”,但在她抉擇的過程當中,仍然體現了人性中的那一分“惡”。她一邊制止著自己介入他人的家庭,一邊又期盼著夏宗豫的妻子“病死”,這種“天使”與“惡魔”的混戰在每個人的人生抉擇當中都曾出現過。人性本身就是復雜多樣的,生活中絕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亦如此,在至善和至惡中常常會有一個中間的“灰色地帶”,這是虞家茵的內心,也是人性的現實。
同樣,《太太萬歲》當中的陳思珍也是一個有著豐富層次的角色。張愛玲對這個角色的文字表述是“粉白脂紅地笑著,替丈夫吹噓,替娘家撐場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蓋”,短短幾句倒和古文學中王熙鳳出場時的“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有幾分神似。在影片當中,陳思珍是一個八面玲瓏的扯謊“慣犯”,但這一個接一個的謊言又不得不被稱為“善意的謊言”,因為這是一個顧全大局的好妻子、好兒媳、好當家的煞費苦心,她的目的總是好的。她的行事作風極具領導力,是家里的“頂梁柱”,但她卻無法代表女性力量的崛起,因為她始終受困于“夫權”、“父權”之中。雖然陳思珍主動提出離婚時的一番話——“到了今天,我實在太疲倦了,從此以后,我也不說謊了,從此以后,我也不做你的太太了”,可以從中看到這個中年主婦的女性意識覺醒,但很快,陳思珍式的“娜拉出走”宣告失敗,丈夫還借此調侃了她一番,“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咱別到律師這兒來鬧笑話好吧”。因此,我們無法斷定陳思珍的做法是對還是錯,也許往后的日子,她又要重復著自己“善意的謊言”,又要日復一日地和生活周旋,但社會上千千萬萬個“陳思珍”仍然存在,她們相夫教子,“其樂融融”。
桑弧導演都市三部曲中的人物皆無強烈的善惡判斷,他只是一層一層地揭開生活的真相,將“現實性”融入角色的詮釋之中。在動蕩無常的繁華都市,我們仍然無法忽視現實生活當中的“煙火氣”,在歷史大潮的變革時期,我們也仍然需要去關注獨立的生命個體。雖說藥廠老板、全職太太和小學校長這樣的階層在大都市中都擁有著一定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但他們都來到了人生的中年階段,和所有中年群體一樣都面臨著情感、家庭以及人生的各種問題,他們在各自的精神世界中掙扎,希望尋求對于自我方向的肯定。當時剛剛年過三十的桑弧導演懷著一顆共情的悲憫之心將這類人群的真實境遇挖掘出來,這不僅僅是當時中年人的生活常態,其實也是未來時空中一代又一代中年群體的現實隱喻。
三、中年話題:市民文化的創新性
從抗戰勝利到新中國成立期間,中國電影從戰爭的艱苦環境中逐漸復蘇,涌現了一批優秀作品,例如《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等,它們真實地展現了戰時人民所遭受過的苦難,以及戰后底層人民支撐生活的不易,將歷史的洪流和革命的浪潮作為影片的主要背景,將人民的抗爭精神和不屈的品格作為影片所要傳達的主要內核。不可否認的是,這類題材銘記了歷史,也對底層市民文化投以了深切的關懷,但對于20 世紀40 年代來說,有一類人群也在市民群體中混沌不安地掙扎著。這類人群沒有沖在抗戰第一線,也沒有被沉重復雜的社會壓得喘不過氣,他們“隨波逐流”,在新的生活方式中尋找著自己的歸屬。他們是小有成就的中產階級里的中年群體,他們無法賭上自己前半生的積累一心投入革命,也無法在紙醉金迷驕奢淫逸的世界里獨善其身,他們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跟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他們只是想著怎樣“生活”。
桑弧導演突破了戰后中國電影的主導方向,選擇了自己最為熟悉,也是在都市空間里無法被忽略的市民群體,開始了主流方向之外的探索。桑弧都市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和家庭構成皆來自于上海的中產階級,他們是企業家是商人是銀行家,他們出入在繁華的商埠和高級的娛樂休閑場所,他們用現代化的方式生活著,勾勒出了當時作為“遠東第一金融中心”的上海的原貌,這與桑弧導演自身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桑弧導演從小生長在上海,他與上海共同成長,上海的時代動蕩和歷史更迭都是他的人生底色,因此上海的市民文化自然而然地也成為了桑弧都市影像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甚至《哀樂中年》中長子建中的身份與形象也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和他周遭的經歷。因此,桑弧的都市三部曲將視角對準上海的市民生活,在描繪中年群體的內心糾葛的同時,也點明了特殊時代背景下每個人做出的自我選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在那個傳統與現代思想激烈碰撞的時代,桑弧導演的這三部作品都提出了中年人的情感選擇問題。《不了情》中的藥廠經理夏宗豫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發妻沒有情感基礎導致精神出軌,而妻子為了保全家庭和虛榮苦苦哀求,情感皆走向悲劇。夏宗豫在物質資料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仍然空虛,追尋著缺席的“妻子”角色,這是中產階級中年市民在物欲橫流的社會,在快速發展的大都市中的一份缺憾。《太太萬歲》中的“太太”陳思珍在各類家庭關系當中盡心調節,希望做一個完美的家庭主婦,最后卻落得難堪,四處不討好。“太太”表面上八面玲瓏活得通透,是新興社會生活當中的“能手”,實際上仍然免不了為了維系家庭而做出自我犧牲,在都市化的進程中販賣“謊言”,從而迷失本真。《哀樂中年》中的陳紹常住在洋房別墅里享受著“晚年”生活的“天倫之樂”,當著讓旁人都羨慕不已的“老太爺”,但他仿佛已經看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最終做出破除傳統束縛,和朋友的女兒敏華結婚并重返校園的決定。這個決定實際上代表著個體意識和現代意識的覺醒,是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市民文化中現代意識的集中體現。
除卻情感選擇,“消費”與“娛樂”這兩大外在因素同樣也是導演包裝角色的一種手段,亦是當時上海市民空虛心靈之外的華麗軀殼。“照相機”、“電影院”、“咖啡館”、“胸針”、“西裝”、“洋娃娃”這些西方元素充斥在市民生活當中,為塑造中產階級中年群像奠定了基調,也展現了消費文化對市民身份的重新界定的重要性。這些角色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奮力追趕,漸漸忘卻和丟失了自身內心的平靜,在“四十不惑”的年齡左右反而更為迷惑,“我是誰?我想要什么?我的未來應該如何度過?”成了這些中年群體需要思考的問題。中年話題也許在那個時代并非社會的主流問題,但在社會變革的現代化進程中,總歸有那么一群人,活到中年卻面臨著自我價值的評判和自我認同的躊躇,導演桑弧發現了,編劇張愛玲發現了,所以對這個群體投出了濃烈的人文關懷,并嘗試著將他們以影像的形式留在早期上海市民文化的這一頁。
四、結語
在當下的社會語境和文化語境之中來看,桑弧導演在文華公司期間攝制的“都市三部曲”——《不了情》《太太萬歲》《哀樂中年》可以說是極具現代意識和研究價值的藝術精品,提升了20 世紀40 年代中國電影的人文內涵。但在其“出生”的時代,這些影片其實并沒有得到文化界的認可。左翼影評家們甚至指出了《太太萬歲》的三大“罪狀”:桑弧導演的文化境界不成熟,沒有和下層工農走到一起;張愛玲的文字和作品是嗎啡餅干;石揮的表演下流。在以“教化”為主要目的的影視創作背景下,桑弧對物欲社會的描寫、對“享樂主義”的渲染確實沒有直接“教育民眾,啟迪民智”,因此遭到了文化評論界的抨擊。但隨著文化語境的變遷,桑弧導演作品的前瞻性逐步顯現,張愛玲的文字對人文關懷的細膩程度得到認可,“話劇皇帝”石揮通過“體驗派”方式詮釋的各個角色作為范例供表演專業的學生學習,“老夫少妻”、“婚外戀”、“中年危機”這些話題也作為新一輪的熱點侵占影視市場,我們才真正理解了文華公司對于自身藝術作品品質與內涵的執著追求。
實際上,桑弧導演的都市三部曲所講述的故事都是極平常的故事,家長里短,細枝末節;其關注的人物也是極易被忽略的人群,中產階級,中年人生。但正是這些平常的故事和普通的人物促成了更加完整的社會構成,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這些極少被提及的每一個中年人生活中的“哀樂”,也是社會變革浪潮下的一朵朵“浪花”。
電影首先是“藝術作品”,而后是“商業產品”,除卻推動市場之外,電影人也在堅持一種“初心”,回顧中國電影發展史,經典作品之所以被稱之為經典,就是因為有無數電影人把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融入了自己的“初心”。在桑弧導演的作品當中,作者與觀眾互為依托,影視創作者在電影中投以關懷精神,觀眾在電影中獲得內心慰藉,這是探索“人”本身的價值,也是電影作品細水長流潤物無聲的基礎。回歸當下影視市場,我們在關注“互聯網”關注“大數據”,考慮流量考慮市場的同時,是否也可以將鏡頭從大時代發展拉回到大時代下的“人”本身呢?“浮世”從未消逝,每一個人的人生長河中都有各自的“悲歡”,影像語言能做的便是投射出最平常最真實卻又最細微的那一面,跳脫出一貫的浮躁與喧嘩,或許每一個時代都是“最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