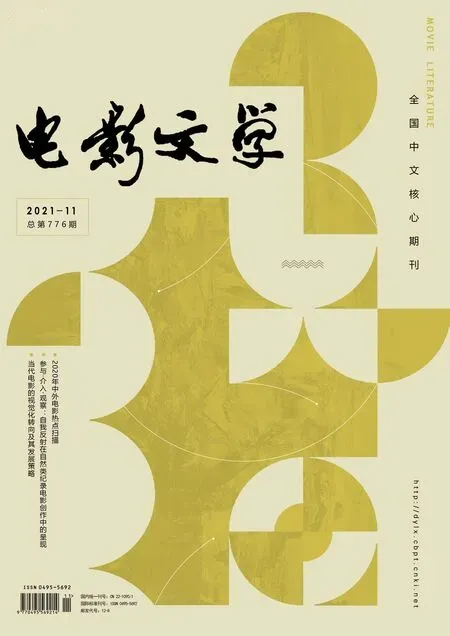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女人的哭泣”:劉冰鑒電影的性別隱喻和文化反思
朱柏成
(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7)
目前在中國知網、維普網、萬方網等國內大型文獻服務平臺搜索關鍵詞“《哭泣的女人》”“《男男女女》”“《硯床》”“劉冰鑒”,發現當下的學者多把關注目光聚焦在其中的單一文本讀解上,缺少深入的關聯對比研究。此外,針對第六代導演劉冰鑒的研究也尚在少數,且主要集中在訪談錄和創作風格兩方面。
故本文力圖深度解讀劉冰鑒執導的《哭泣的女人》《硯床》《男男女女》中蘊含時代記憶的空間建構與性別隱喻,并以《找到你》《親愛的》《七月與安生》《少年的你》《嘉年華》《狗十三》等近些年來女性題材電影為觀察視點,回望劉冰鑒導演所塑造的女性角色,窺視電影銀幕中的現代中國女性思想與處境的變遷圖史。
一、底層場域:集體記憶的真實美學
《哭泣的女人》在美學層面上,延續了作者之前在《硯床》《男男女女》作品中所貫徹的紀實風格,正如導演自己所言:“我幾乎是和我當下的所見所感來同步做我的電影。”劉冰鑒攫取自己的人生經歷、時代記憶與人生感悟,描繪出彼時女人悲慘境遇的真實圖景,其影像中的長鏡頭、大景別以及手持鏡頭所具有的紀實美學風格更來自導演對世界的觀念轉化成視覺表達的偉大嘗試。
(一)長鏡頭:“釘在墻上的蒼蠅”
正如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對長鏡頭的肯定:“長鏡頭的呈現能使觀眾保持在一個客觀的地位,去觀察持續性的空間原貌,以最接近現實世界的角度觀察他們眼前的影像。”在《哭泣的女人》中,導演尊重時空的連貫性,多次采用了長達30秒以上的長鏡頭,來減少攝影機和創作者對事件的干預,營造了一種非強制性、開放型的完整式觀影模式。如影片開頭的第一幕畫面就長達45秒:王桂香于清晨起床,準備出門賣碟賺錢,而同在枕邊的丈夫不僅抱怨輸了錢,而且仍昏睡在床上;王桂香和男友李友敏第一次去他人家中哭喪的片段,更是以一個長達兩分鐘的全景鏡頭予以呈現。這里的攝影機更像“釘在墻上的蒼蠅”,冷靜且極為客觀地展現了一種底層群體的生活圖景,給予受眾充分思考的余地。
不僅是《哭泣的女人》,《硯床》《男男女女》中也出現了大量的長鏡頭,如《硯床》中吳家少奶奶和阿根道別的場景,《男男女女》中青姐和阿夢同居的片段。這些長鏡頭的呈現符合攝影機復制生活真實的照相本性,再現導演記憶中女性的生活環境和角色特征,并展現被攝對象行動的全過程,給予觀眾一種正在處于某個特定環境中的真實質感。
(二)大景別:幕外空間的思考
景別作為完成電影、電視畫面空間塑造的重要形式,也是導演美學風格建構的重要元素之一。劉冰鑒在其創作生涯中始終堅持著現實主義的攝影風格,《哭泣的女人》也不例外。該片中充斥著大量的遠景和全景鏡頭,如王桂香為他人哭喪、王桂香嗓子難受臥床休息等等片段。
這些大景別表現開闊的空間格局和場景設計,配合長鏡頭,使觀眾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對畫面的豐富信息做出反應,繼而從畫面中獲得現象學派胡塞爾所稱之的“心象”,即一種重現的記憶活動。相比于快節奏的特寫和近景鏡頭,大景別的“心象”能夠讓受眾從長時間且信息豐富的畫面中聯想到與自身經歷相關的人生記憶,進而生成嶄新的意念化產物。比如,有曾經參加過喪禮的觀眾,長時間地凝視王桂香為他人哭喪的場景時,可能會陷入曾經參加過喪禮的回憶之中,繼而會結合影像情境,生成關于“死亡”“生存”等意象的新認知。
再者,大景別能夠給予演員塑造角色的更多權力,交代豐富的環境信息,建構其空間關系以及影像美學的總體基調。在《哭泣的女人》中,王桂香的生活環境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原先王桂香和丈夫陳庚生活在繁華的北京都市中,但自身衣著以及居住環境的雜亂與都市景觀格格不入,并不斷受到城市人的“阻擊”。然而,王桂香回歸到農村后,衣著打扮仍受著老鄉們的譏笑,所謂的“根”也不再包容和無私,而是裹挾了“羨慕”“計較”“鄙夷”等種種狹隘的思緒。劉冰鑒借助大景別,從多重角度交代人物關系和影像信息,建構出一種城鄉對立的文化場域。
(三)手持鏡頭:浸入式的情感體驗
論對手持攝影的偏愛,不得不提到第六代導演的婁燁,在他的《春風沉醉的夜晚》《浮城謎事》《推拿》《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等作品中,無不都采用了“解放的攝影機”。在這種鏡頭運動中,畫面內部元素具有不可預料的特征,晃動的畫面充滿著呼吸感,觀眾仿佛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介入劇情敘述情境之中。
同為第六代導演的劉冰鑒,在《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中也采用了不穩定的手持鏡頭來強化故事的紀實質感和情感張力。《男男女女》中,小博被迫離開青姐家,到沖沖家暫住,此時畫面便是由手持鏡頭捕捉了小博的背影,表現出一種不甘又無奈的情緒;《哭泣的女人》之中,王桂香和李友敏在網吧門前爭吵時,導演同樣利用手持攝影機的長鏡頭毫無保留地展現出兩人復雜的心境:一面是李友敏想勸阻王桂香放棄解救陳庚的私欲,一面是王桂香想堅守“婦道”的執念,由此受眾能夠清晰地感受兩個人物的情緒碰撞以及內心掙扎。
劉冰鑒影像作品中所采用的晃動鏡頭雖然會使得畫面失去了一定的信息完整性,但它帶來的情感張力卻是其他鏡頭所不具備的。尤其是,當受眾在觀看手持鏡頭捕捉的女性形象時,搖晃不定的畫面和真實質感的聲音同時占據觀眾的視聽感覺器官,兩者共同作用,受眾在心理上能夠更快地接受鏡頭所提供的信息,也更容易被女性人物流露的細膩心情與復雜思緒所滲透。
二、物語隱喻:彼時女性的悲慘圖景
處于 20 世紀末期和 21 世紀初期的中國女性遠沒有西方女性那樣幸運,受到思想解放浪潮的洗禮,彼時的她們仍深受著中國封建性別文化的影響,背負著難以想象的心理壓力和物質負擔。劉冰鑒尤為關注彼時底層女性的現實遭際,在《硯床》《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這“三部曲”中,通過書寫多重殘酷物語展現她們的生存邏輯、精神世界、感情生活以及生命體驗。
(一)性欲錯亂:以“身”衛“綱”
性欲是人與生俱來的本性,但中國的性動機受限于傳統倫理文化的束縛,長期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尤其是女性的性欲行為。然而,在劉冰鑒的作品中,女性的性欲行為表現得極為混亂,但究其本質仍是為了守護封建文化的“夫為妻綱”。《硯床》中的少奶奶和少爺在多次“房事”后無果,在父母的“生子接代”傳統觀念施壓之下,少爺竟勸妻子出賣身體與仆人結合,來獲得“種子”;《男男女女》里的青姐發覺自己喜歡上了小博后,迫于丈夫的存在不得不打消追求真愛的想法;《哭泣的女人》中的王桂香在丈夫被送進牢中后,竟愿與監獄長肉欲結合來尋求拯救丈夫的機會。從這些女性肉體或精神的出走意義而言,“婦女只有按照宗法制度和世俗男性所期待的樣式塑造自己,才能適應社會和家庭的規范”,男性對于物欲、情欲、思欲的渴望程度,往往會導致女性產生錯誤的性欲觀念或行為。
如同朱迪斯·巴特勒所持有的觀點:性別,“它具有意圖同時也是操演性質的,而操演意味著戲劇化地因應歷史情境的改變所做的意義建構”。在劉冰鑒的電影作品中,女性性欲的背后往往有著男性身影,他們的背叛、救贖以及欲求改變著女人們的未來行為與內在信念,也正是導演對于兩性肉體的銘刻考量了彼時男性權力的歷史意義和社會地位,借以引發大眾對傳統性別文化的沉思。
(二)人格面具:空洞的情感容器
劉冰鑒影片中所塑造的女性人物深受家庭道德、社會輿論、文化思想等多種文化觀念的壓迫,她們被迫戴上“人格面具”,“用來平衡無意識領域的欲望與外界現實之間的關系”。《硯床》中的吳家少奶奶與男仆人交合后,對他產生了莫名的情愫,然后礙于丈夫的存在,不得不隱藏潛在的想法;《男男女女》里的青姐和丈夫本沒有了感情,但由于法律上的夫妻關系,仍在一起居住;《哭泣的女人》中的王桂香丈夫入獄后,使她顛沛流離,又對情人產生依賴,但出于婚姻的責任,不得不通過哭喪掙錢來保釋丈夫。可以發現,這些人物的遭際都展現出彼時女性受到傳統封建思想的桎梏,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抉擇、觀念以及心緒都受男性的牽制,時刻偽裝自己的情感流露、人生追求以及多重欲望,自身仿佛一具空殼的皮囊。
《哭泣的女人》中提及的哭喪文化,是中國落后地區長久延存的一種地域風俗,本質是一種后輩追悼先輩的儀式,借以表達對逝者的內心不舍和崇高敬意。而在該片中,這種數千年沿襲的傳統卻成為一種另類的表演和生意,血脈之間真情蕩然無存。王桂香作為哭喪人,在不同人的喪禮上用戲曲式的舞蹈表演來替他人祭奠前人,且從未哭泣,而小女孩津津一直都在哭泣。恰恰她跟丈夫、跟情人的關系完全崩潰,對生活的追求陷入絕望時,卻流下了眼淚。可見,她之前哭喪時所戴的“人格面具”是受他人所迫,雖然具有現實的外在表征,但內在情感卻是空洞的。當“虛偽的面具”被現實因素所碾碎時,掛著眼淚的臉龐完整且真實地暴露無遺。另外,極具思辨性的地方是,影片中逝世的人都是男人,唯獨一位年邁的女性,其三個兒子在生前格外不孝順,死后還道貌岸然地宣稱“要給母親辦全城最風光的葬禮”,彼時男性面具之下的“丑陋人格”被導演揭露了出來。
(三)多重規訓:男權社會的“失語者”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女性理應遵守婦道,在家服侍男性,照顧孩子和父母,沒有權力去尋求和男性一樣平等的地位。這一思想是在數千年的男性話語權力的多重規訓下所生成的,其手段及過程在劉冰鑒的電影中也被多次描寫。
劉冰鑒的電影作品之中,男性的話語權的獲得及闡釋主要是通過兩種手段:言說與暴力。在《哭泣的女人》里,男性角色多是公職機關人員,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和維權者,而作為底層女性的王桂香多次受到“規矩”的懲罰。比如,沒收了王桂香碟片的男城管,沒有主動充公,而是欣喜地準備“分贓”;王桂香試圖把丈夫贖出去,監獄長先是暗示五千塊錢不夠,后又與王桂香行了“茍且之事”;在丈夫陳庚被擊斃后,男警員面無表情地握著王桂香的手脅迫她按手印,不給她任何說話的余地。再者,影片中王桂香在情感生活中深受男性言語的欺騙和壓榨,他們極其無能和懦弱:陳庚無能還好賭,軟弱沒主見,進了監獄后還對前來探監的王桂香哭訴監獄生活的難熬,求她早點把自己贖出去;李友敏享受著王桂香的肉體帶來的樂趣,但當妻子與她爭吵時,卻像孩子一樣不敢吱聲,不愿意對其負責。與之相反,劉冰鑒片中女性往往是社會的底層群體,與生俱來就遭受著被社會嫌棄的悲慘命運。比如,《哭泣的女人》中三歲的津津因是女孩被父母拋棄,由王桂香收養,而王桂香也沒有任何親戚,始終是孤身一人;《硯床》中少奶奶在年輕時,自身的情感需求無人重視,只是被當成一個“生育機器”,年老時,又因身體不佳,被家人與外人所嫌棄。
劉冰鑒通過描繪男性在身體、言語以及思想上對女性的“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以及它們在該權力的程序——檢查——中的組合”,把“丑陋的男性”塑造成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監督者、維護者和裁決者,展現出彼時女性在社會環境、家庭生活、精神世界的無奈與凄慘。
三、借鑒與思考:反觀近年來女性題材電影的成長之路
縱觀劉冰鑒影像作品中吳家少奶奶、王桂香、青姐等女性形象的遭際,不難發現她們的意志、思想以及行為多是由男性所決定,這也反映出處在20世紀末期和21世紀初期時中國女性的弱勢地位。但伴隨中國的經濟、教育、法律和文化快速發展,原先封建的性別思想禁錮也日漸式微。據2019年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的報告顯示:相比于2005年,歷屆女性人大代表的數量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女性用于家務勞動的時間明顯減少,女性是家庭戶口中戶主身份的比重也得到提高。此種女性賦權的現實境況在當下的電影銀幕中,逐漸呈現出一種別致的景觀。
近年來,《找到你》《親愛的》《七月與安生》《少年的你》《嘉年華》等國產女性題材電影不僅沿襲了劉冰鑒犀利的現實主義寫實風格,更是利用劇情結構、人物設置、視聽語言等多重手段來諷刺和抨擊封建的性別文化,揮舞起男女平權的思想旗幟。這些影片中女性不只限于鄉村村姑、家庭主婦、務工婦女等底層群體,也涵蓋現代都市生活中律師、白領、學生等高中階層群體,她們所面臨的境遇已與《紅高粱》《菊豆》《哭泣的女人》等第五代、第六代導演作品中所描繪的女性命運大不相同,展現了當下不同群體女性的生命遭遇、情感生活以及思想作風。比如,《找到你》中律師李捷的離婚原因不是家庭暴力、性欲不滿、移情別戀等傳統女性容易面臨的問題,而是沒有共同語言;《七月與安生》中的李安生不再是受父權隨意宰制的少女,她放浪不羈愛自由,打破傳統倫理的束縛,和多個男人發生性關系;《少年的你》中的魏萊雖然是女性,但憑借出身卓越以及跋扈性格,成為學校的“校霸”,肆意欺凌他人。
可見,當下國產女性題材電影凸顯出中國女性在政治權力、社會地位、思想風氣等多方面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但她們擁有的一切與男性所享受的多種“特權”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依然會受到男性的欺壓而質疑作為“女性”的身份價值。《找到你》中的保姆孫芳飽受丈夫施加的家暴,迫于殘酷的窘迫境遇,她偷走了雇主家李捷的孩子;《親愛的》里的李紅琴是一位不能生育的農村婦女,錯信丈夫的話,認為孩子是在深圳撿來的,為此與田文軍、魯曉娟兩人爭奪兒子;《少年的你》中陳念和董小蝶長期受到校霸們欺凌,前者誤殺了魏萊,后者則自閉到跳樓自殺;《嘉年華》中的小文被男官員玷污后,不僅無人幫助她,而且社會和家庭又變相來對她施暴。這些女性的凄慘遭際無疑揭露出當下社會中的一種殘酷現實境況:“社會留給女性的選擇,還是相對少”,“對女性的要求,還是相對多”,“中國女性生活幸福度很低”。
綜上所述,相比于劉冰鑒作品中的女性命運,近年來的女性題材的電影仍裹挾著明確的性別立場,呈現了當下社會幽暗角落中女性的悲慘窘狀。值得指出的是,這類影片具有強烈的現實訴求,凸顯出現代女性的開放思想和主權愿望——尋找在兩性對話中的平等地位。但縱觀近年來的中國電影市場可以發現,堅持現實主義陣地的女性電影在數量上還是寥若晨星,規模及投入仍無法與懸疑片、喜劇片、動作片等泛娛樂化的類型電影相當。
結 語
劉冰鑒導演用紀實質感的鏡頭語言傾訴出帶有時代記憶和家鄉意蘊的女性故事,把底層女人的“哭泣”譜寫成一種諷刺男權的“寓言故事”,隱喻著女性精神家園的頹廢與凋零,以及女人對男性特權的憧憬。從歷史縱向的維度,審視當下的女性題材電影中的個體命運,不難發現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鏡頭下女性形象已悄然位移,現代女性對物質生活、情感品質以及人生理想等多方面需求已經透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但在社會權力、財富收益、家庭地位、心理狀態等多方面,女性仍與男性有著不小的差距,這也意味著謀求性別平權的“吶喊聲”正亟待借助更多具有現實批判性的女性題材電影之力來予以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