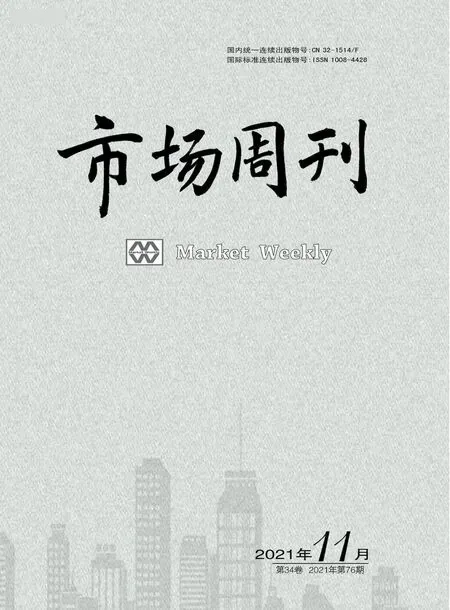論電商平臺的差異化定價行為
于 洋
(天津大學,天津 300072)
2018年,“大數據殺熟”這一概念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并入選“2018年度十大新詞語”。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各種手機軟件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給人們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侵害人們合法權益的行為。根據媒體的報道,滴滴、美團、淘寶、京東等平臺都出現過“殺熟”現象,涉及衣、食、住、行等領域,對消費者權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一、電商平臺差異化定價行為的經濟學角度分析
電商平臺的差異化定價行為就是指當前在電子商務領域存在的“大數據殺熟”行為,具體來說就是指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時候,電商平臺的經營者會對不同的消費者制定不同的價格和價格策略,這種差異化的定價行為所實施的標準是不同消費者的購物習慣、歷史消費記錄或者經濟水平等。
在經濟學中,這種行為被稱為價格歧視,電商平臺將自己獲得的顧客信息用在自己的價格策略中,不僅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經營成本,而且能夠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所以這種行為在經濟學上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二、電商平臺差異化定價行為的違法性
從法律角度來講,表現形式為“大數據殺熟”的這種差異化定價行為實際上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有一定的損害。
(一)侵犯了網絡消費者的知情權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電商平臺對于自己銷售的商品和提供服務的價格以及與其他消費者進行交易時制定的價格雖然并不需要對消費者進行告知,但是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情況理應包括經營者是否實施了差異化定價行為以及進行差異化定價行為所依據的標準和考慮的因素等,這些都會影響到消費者是否進行交易以及如何進行交易。而電商平臺故意隱瞞差異化定價的行為很明顯已經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
(二)侵害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平等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公平交易權就是民法平等原則在具體法律中的體現,平等原則允許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差別,但是為了確保公平,合理差別需要比例原則對其加以限制,在進行差別對待時,需要符合目的正當性、程度最小以及適當原則的規定。從現有的“大數據殺熟”案例來看,電商平臺采取的差異化定價行為是沒有正當理由的,電商平臺僅僅是因為部分消費者對價格不敏感或者對該平臺的忠誠度較高就采用更高的價格,而且消費者沒有任何渠道知道也沒有辦法拒絕電商平臺的這種“殺熟”行為,這顯然是一種不合理不公平的交易條件。
(三)威脅用戶個人數據安全
電商平臺利用互聯網這一工具,把消費者在瀏覽網頁或者進行線上購物時留在網絡中的個人數據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收集與分析并挖掘更多的信息,對用戶進行“畫像”,從而實現精準營銷。電商平臺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獲取到消費者的隱私數據,這成為個人數據遭受到威脅的主要原因。在通常情況下,由于消費者的個人數據在后續的使用過程中擁有巨大的潛在價值,所以電商平臺獲得這些個人數據之后不會主動地刪除或者銷毀,為了從中挖掘更多的信息使自己獲得更大的利益,電商平臺往往會對這些數據進行二次或者多次利用。在線上交易中,平臺往往會采用一些消費者無法拒絕的方式侵害消費者的個人數據權,比如沒有經過消費者同意就進行個性化的推送,在用戶瀏覽網頁時默認勾選了同意獲取地理位置或者通訊錄的選項等,諸多現象都反映出個人數據在被過度獲取與濫用。
三、差異化定價行為的定性
在被“殺熟”之后,很少有人能夠采用法律的方式來維權并獲得救濟,一方面是因為維權的成本相較于損失來講更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目前法律上對電商平臺的“大數據殺熟”行為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性。
(一)價格歧視
在經濟學領域,價格歧視有三種類型:一級價格歧視是指經營者所制定的價格正好處在消費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臨界點,比如拍賣模式。二級價格歧視是指經營者對消費者實行區別定價,定價的標準主要是消費者的購買數量,比如“第二杯半價”的活動。三級價格歧視是經營者根據不同消費者的消費情況或者不同的消費群體制定不同的價格,如學生半價活動。
電商平臺收集消費者的個人數據并分析其喜好與消費習慣,從而預測消費者愿意為某件商品或者服務支付的最高價格,按照這種意愿在消費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臨界點進行區別定價,這已經構成了經濟學領域的價格歧視。但是“大數據殺熟”很顯然并不為大家所接受,在法律層面應該得到負面評價,僅僅用價格歧視并沒有完全表達出“大數據殺熟”的法律性質。
(二)價格欺詐
電商平臺主觀上有欺騙消費者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隱瞞真相、區別定價的欺詐行為,使消費者遭受到一定的損失且損失與欺詐行為具有因果關系,所以這在法律上,完全符合欺詐的構成要件,屬于價格欺詐。價格欺詐的學理基礎是民法中的欺詐,所以也應當遵循民法中關于欺詐的規定。
《禁止價格欺詐行為的規定》中規定了價格欺詐的含義。價格欺詐的核心要素就是經營者只將虛假的信息告訴了消費者,而對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情況進行隱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的消費者知情權的范圍沒有包括經營者與其他消費者之間的交易價格等信息,但是需要考慮到網絡購物與傳統消費方式的不同,消費者在與電商平臺進行交易時,只能看到屏幕上呈現的平臺為自己這個賬號發送的專門價格,而很難獲取到其他人的價格信息,這些信息會對消費者是否購買該商品或者服務造成影響。可以認為消費者有權了解一切可能影響自己是否會選擇以及如何選擇該商品或者服務的信息,電商平臺應該盡到對這些信息進行合理披露的義務。“大數據殺熟”很明顯對消費者隱瞞了真實的信息,告知其虛假情況使消費者做出選擇,已經符合價格欺詐的構成要件。
(三)算法權利與數據的濫用
技術是中立的,電商平臺既可以使用算法技術來提供更好的服務,同樣也會在利益的驅使下侵害消費者的權利。“大數據殺熟”就是電商平臺為了挖掘個人數據的價值,濫用算法權利并侵害消費者數據的表現。在實際的網絡交易過程中,電商平臺通常會利用技術手段獲取一些非必要的信息,比如年齡、性別、通訊錄、設備信息等,從表面看,電商平臺在收集這些信息的時候都詢問了消費者同意與否,但事實上很多時候消費者只有同意經營者收集這些信息之后才能繼續進行交易。
個性化算法推薦直接將消費者與經營者連接起來,從而影響購買與銷售。同樣的商品或者服務本應該制訂相同的價格,但是掌握了個人數據的電商平臺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對消費者“畫像”之后再定價,用更低的價格吸引更多的新客戶,對老客戶進行價格收割,這種追逐利潤的銷售策略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根據成本定價的規則,消費者在此過程中被客體化,成為被掠奪的對象。所以說,消費者權利遭受到侵害是“大數據殺熟”的表面現象,算法權利與數據的濫用才是這種行為的根本原因與實質。
四、差異化定價行為的保護路徑
(一)價格歧視角度
《價格法》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經營者不能有“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務,對具有同等交易條件的其他經營者實行價格歧視”的行為。但是這一條明確規定只有其他經營者才是價值歧視行為的行為對象,消費者并不屬于侵害對象的范圍。
《反壟斷法》中價格歧視的主體是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并且需要這種歧視行為的程度已經損害到市場競爭秩序。在實踐當中,把電商平臺認定為《反壟斷法》中的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是非常困難的,然而一些電商平臺雖然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卻能利用自身的資源或者技術手段將其他的平臺擠出市場。而另外一些大型的電商平臺雖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平臺本身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是需要進行更詳細的認定的。
(二)價格欺詐角度
消費者購買商品或者服務實質上是與經營者訂立了一個買賣合同,經營者在訂立合同的過程中隱瞞了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情況讓消費者在受欺詐的情況下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并訂立合同,是一種欺詐行為。消費者若在受欺詐的情況下實施了民事法律行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合同。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該制度的構成要件包括:經營者客觀上有欺詐的行為,消費者遭受了實際的損失,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價格欺詐與消費欺詐在構成要件上是一致的,電商平臺的區別定價行為構成了消費欺詐,消費者有權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主張懲罰性賠償。
(三)算法權利與數據濫用角度
并非“大數據殺熟”過程中收集的所有數據都直接與消費者的人格權有關,電商平臺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和挖掘是為了獲得更有價值的消費者個人信息。是消費者的整體數據被運用于“大數據殺熟”過程中,而不僅僅是敏感的個人信息。具有使用價值的個人信息才在我國法律所保護的信息范圍之內,主要是與公民隱私有關的部分,并不是全部的信息。在“大數據殺熟”過程中,平臺旨在了解消費者和整個市場的情況,所以獲取收集的數據并不僅僅限于一些與身份屬性相關的信息。電商平臺之所以敢利用算法權利進行“大數據殺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國個人數據方面立法的缺失。法不禁止即自由,在市場經濟與獲得的實際利益的驅動下,平臺只會變本加厲,獲取更多的消費者剩余,所以完善個人數據的立法,對這種不正當的行為進行規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