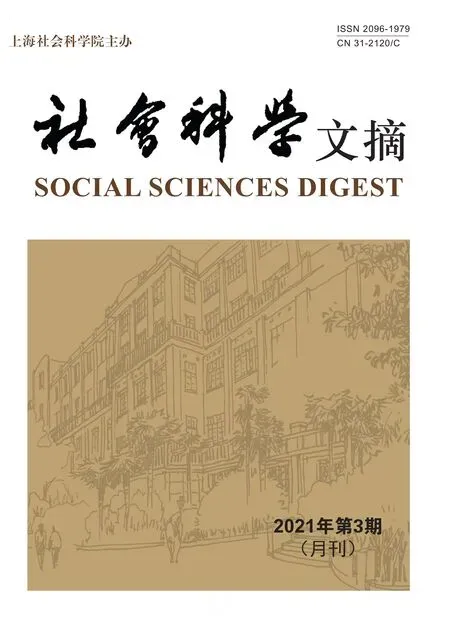人工智能技術對戰爭形態的影響及其戰略意義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計算機系統等人造物表現出來的像人類一樣思考和行動的智能,是研究基礎理論并開發相關應用系統的科學。在信息科學中,可將其定義為從環境中感知信息并執行行動的自主行為體的研究。每個自主行為體實現一個把感知序列映射到行動的函數。當前,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成為對人類社會起關鍵作用的顛覆性技術,其應用必然將影響戰爭形態和大國戰略平衡,從而影響國際安全。
研究現狀與科學技術事實
戰爭形態的內在本質是戰斗力生成模式,是指人、武器和編制體制等基本要素的性質及其相互關系,獲取和發揮軍隊作戰能力的標準樣式、運行機制和一般方式。以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為基礎,一般將戰爭形態劃分為冷兵器戰爭、熱兵器戰爭、機械化戰爭和信息化戰爭四種。既有研究認為,人工智能技術將對戰爭形態產生顯著影響。這主要指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信息化時代中戰爭形態向無人化、自主化、智能化的方向演進。然而,既有研究的不足在于:對人工智能技術本身掌握尚不夠準確,對技術及其進步造成影響的定性研究中,研究方法尚不夠完善。這會導致高估人工智能系統的能力,得出超出現實的結論。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本質依然是數據處理,其應用系統擅長處理邊界明確、規則清晰、價值易于量化的任務。在掌握科學事實的基礎上,可以采用小樣本定性研究方法,在實際過程和場景中重構技術因素的影響,分析人工智能技術對戰爭形態的影響。
人工智能通過締造效能更高的作戰體系改變戰爭形態
信息化作戰體系由互動的單元和結構構成。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增強現有作戰單元或參與創造新的作戰單元,改變單元在信息化環境下的作戰能力和作戰成本。以單元為基礎,作戰體系的結構特征也逐漸演變。在單元和結構賦予的能力基礎上,信息化作戰體系的實際作戰過程亦發生演變。戰爭形態因而改變。
(一)人工智能對作戰單元的影響
作戰單元是作戰體系中的基礎子系統,是直接擔負作戰任務的個體,在不同時代的作戰體系中,士兵及其操縱的裝備是最基本的作戰單元。人工智能締造更高效的信息化作戰體系,作戰單元是基礎。人工智能技術將增強現有作戰單元能力并推動新的作戰單元出現,促進作戰單元效能提升。
一方面,無論對于既有的有人或無人作戰單元,還是正在研發的無人作戰單元,當前水平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可以顯著增強其在信息化環境下的作戰能力,增強對戰場態勢的感知能力和信息處理的能力。在信息化時代中,戰場態勢主要包括圖像、音頻、電磁信號等,隨著信息化作戰對抗能力的提升,作戰環境日趨復雜,對于攜帶傳統傳感器的作戰單元而言,獲取并處理這些信號成為難題。而人工智能系統可以通過戰斗、演習、日常任務和模擬過程中得到的數據,在有監督或無監督條件下自主學習,從而實現對復雜和高不確定性的戰場態勢的快速識別與處理。在此基礎上,可以借助經由日常訓練得到的人工智能系統進行下一步的作戰行動。總之,在作戰單元層面,現有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顯著增強不同單元的作戰能力。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了無人作戰單元的應用,從而大幅降低了先進的信息化作戰單元的成本。當前主要的無人作戰單元包括無人機、無人潛航器和各類機器人。傳統的無人作戰單元,由操作員遠程操縱,不能自主作戰,且任務相對單一。而新的無人作戰系統將在不同作戰空間中執行傳統作戰任務,例如,利用無人機空戰,奪取制空權。在人工智能技術進步的前提下,無人系統理論上可以不斷自我訓練,實現演化,最終形成更加完善的作戰能力,在自主作戰中發揮大于等于傳統有人平臺的作戰效能。在作戰效能大體相同或更高的情況下,無人作戰單元的優勢在于更低的成本,主要是從制造、訓練到形成戰斗力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更低。總之,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明顯降低了信息化作戰體系中作戰單元的成本。
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促使信息化作戰體系之中作戰單元效能提升,同時成本下降。只有在此前提下,信息化作戰體系的結構演進才成為可能。而只有隨著體系結構演進而形成更加先進的網狀結構的情況下,整個作戰體系的效能方能明顯提升。
(二)人工智能對作戰體系結構的影響
信息化作戰體系的結構是指單元排列的方式,表現為空間拓撲關系。人工智能技術和其他先進技術共同作用,提升作戰單元的作戰效能并降低其成本,從而使單元構成的信息化作戰體系結構進一步向去中心化的動態網絡發展演進,這不僅可以增強系統的態勢感知、信息處理及火力打擊能力,而且可以增強系統的任務靈活性和戰場生存能力。
在冷兵器時代和機械化時代中,作戰體系圍繞指揮中心逐層構建,形成樹狀結構。而在信息時代中,通信技術、自動控制技術和裝備制造的總體進步使作戰體系演化為網絡狀結構,其不足在于,體系中的每個節點并不是等價的,在戰略、戰役和戰術層面都存在所謂的關鍵節點,其主要分為三類:關鍵的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與偵察(C4ISR)設備、指揮控制中心和火力平臺。而當關鍵節點減少到一定程度,就無法組成網絡狀的信息化作戰體系,作戰體系將失去作戰能力。因此,在信息化時代的體系對抗之中,首要作戰目標是摧毀對方體系的關鍵節點。當前,至少在西太平洋地區軍事沖突的假想場景中,中美都具備了在信息化作戰體系整體支持下利用先進的技術裝備,精確打擊并摧毀對方關鍵節點的能力。
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理論上可以改變信息化作戰體系的網絡結構,減弱作戰體系依賴關鍵節點的脆弱性。先進無人單元作為高效能、低成本的作戰單元,逐步改變信息化作戰體系網絡結構的性質,可以構建去中心化的作戰網絡,作戰效能更高,而且任務靈活性和生存能力提升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傳統網絡結構的脆弱性。
首先,更高的作戰效能體現在兩個方面:自主處理更加復雜的戰場態勢,并利用數量優勢達成更好的打擊效果。技術的發展使戰場中出現“信息超載”,經過訓練的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增加傳感器數量,組成傳感器網絡,用“云服務器”重構戰場態勢,構成具有去中心化網絡結構的信息化作戰體系,提升復雜環境下作戰效能。無人作戰單元形成的“作戰云”還提供更強的火力打擊能力。效能高、成本低的自主協同無人集群可以突破傳統的數量限制,并利用數量優勢提升打擊能力,實現低成本的飽和攻擊。
其次,去中心化的動態網絡結構使得信息化作戰體系的任務靈活性和生存能力顯著提升。任務靈活性指以先進無人單元為主構成的作戰網絡借助模塊化設計、模塊化生產的先進任務模塊可以更好地執行不同任務。去中心化的動態網絡結構帶來的生存能力則在戰役和戰術層面具有重要意義:其一,對于智能無人集群,現有的防御體系并沒有成本足夠低的解決方案;其二,先進無人單元組成去中心化的網絡,其具備自組織的性質,當集群的部分單元被防御系統摧毀時,具有相同或者相似功能的多個單元仍然可以組成完整的作戰體系,作戰效能沒有根本性削弱。
總之,結構由單元組成,人工智能技術促使先進智能單元產生,從而構建了更加高效、健壯的去中心化動態網絡結構,增強信息化作戰體系的效能。其中靜態能力是改變戰爭形態的基礎,進一步分析評估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還應將其放在動態的戰爭過程之中。
(三)人工智能對作戰過程的影響
動態的過程分析或評估,是指不僅分析技術因素帶來的靜態能力變化及影響,而且基于軍事科學的一般知識,利用公開信息,將確定的能力放在戰役和戰斗的假想場景下分析評估。總體而言,當前水平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顯著增強作戰體系及其單元在博伊德循環(OODA Loop)中的行動速度和質量,從而在分秒必爭的信息化戰場對抗中提升作戰體系的優勢。
博伊德循環,是指作戰過程中觀察、調整、決策和行動的循環往復的過程。觀察是指人員和傳感器獲取戰場信息;調整則是利用信息修正舊的戰場態勢,形成新的戰場態勢;決策是指根據戰場態勢選擇行動路線;行動則是最終執行決策,并評估和檢驗上一循環的效果。在戰爭中,無論戰略、戰役還是戰術層面,作戰雙方的博伊德循環在對抗過程中相互影響。信息化對抗中,能夠更快完成一個博伊德循環的一方,能夠獲取明顯的戰場優勢。
人工智能技術則可以加速博伊德循環,同時提升博伊德循環中部分環節的質量。在觀察環節,人工智能技術將明顯提升獲取信息的速度和質量。在調整階段,人工智能技術有助于更加高效地重構更高質量的戰場態勢。決策環節中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在短時間內參與甚至主導決策,并直接接入行動環節。最后,在行動環節上,以前三個環節的優勢為基礎,無人系統、有人系統和有人/無人系統有機融合的系統能夠使行動環節效能更高。
總之,人工智能系統可以明顯提升博伊德循環過程的速度和質量,而在實際對抗中,一旦一方博伊德循環的速度大大快于對手,就會使對方無法跟上戰爭節奏,從而導致系統性崩潰。因此,人工智能技術能顯著增強既有信息化作戰體系和未來先進無人系統的實際作戰效能。
(四)人工智能技術如何改變戰爭形態
現有水平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提升信息化作戰體系中作戰單元的效能,幫助構建更高效更先進的網絡結構,在作戰過程中提升博伊德循環的速度。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現有水平的人工智能技術是信息化作戰體系的“賦能器”(Enabler),其可以顯著改善和提升現有作戰系統的生存能力、信息處理能力和打擊能力,提升信息化作戰系統的效能,從而推動戰爭形態向基于智能單元的信息化戰爭轉變。然而人工智能作為“賦能器”的界限在于,人工智能技術推進戰爭形態的演化進程,而沒有推動戰爭形態的代際變革,并且這類顛覆性技術不直接作用于戰略層面。在以上結論和相關科學事實的基礎上,可破除對于人工智能和智能戰爭的迷思,進一步分析該技術的戰略意義。
人工智能技術的戰略意義
(一)人工智能技術有利于維持常規領域脆弱的戰略平衡
中美之間的相互常規威懾,其原理在于:雙方的信息化作戰體系,都具備超越地理空間限制,在不同作戰維度打擊敵方作戰體系關鍵節點的優勢打擊能力。從技術角度而言,對作戰體系關鍵節點的打擊難于防御。在信息化常規局部戰爭的場景中,雙方相互摧毀作戰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將使雙方作戰體系失去作戰效能。體系失能這一兩敗俱傷的必然結局將迅速顯現并導致巨大的成本損失和戰略后果,造成當前條件下不可承受的損失。因此,雙方具備了充分威懾能力,即實現相互常規威懾的必要條件。以威懾能力為基礎,雙方都展示出使用這種能力的決心,并通過有效的信息傳遞證明威懾可信性,威懾成功具備了必備要素。盡管這種相互威懾穩定程度低于20世紀60年代之后基于相互確保摧毀(MAD)的相互核威懾,但和相互確保摧毀成為被廣泛接受的概念之前的核威懾一樣,能夠維持大國間和平。
人工智能技術進一步提升雙方作戰體系效能,推動戰爭形態向基于智能單元的信息化戰爭演進,大國的常規威懾能力進一步增強。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和其他先進技術在這一時期不可能將大國整個信息化作戰體系整體改變為去中心化的網絡結構,整個作戰體系依然依賴指揮中心、軍事基地、機場、雷達站等關鍵節點,這些節點的生存力和脆弱性沒有根本性改善。而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研發的先進智能化作戰單元及其構成的子系統,可以發揮自身更好的生存力和打擊能力來打擊關鍵節點。在基于智能單元的信息化戰爭中,對抗雙方實際上具備了新的、效能更高的非對稱打擊手段,可以更加高效地摧毀對方的關鍵節點,國家的常規威懾能力增強。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智能無人集群在可預見的未來還無法取代傳統關鍵節點。這同樣意味著智能無人集群增強了戰役和戰術層面的打擊效能,但無法根本降低大國的信息化作戰體系在戰略層面上的脆弱性,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在新的打擊能力面前更加脆弱,即作戰體系摧毀對方體系關鍵節點能力增強,國家的常規威懾能力增強。
進一步而言,從長期看來,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智能無人集群理論上有可能在常規威懾框架內提供有限的二次打擊能力。此外,在智能無人集群大規模投入實戰之前,人工智能技術同樣可以基于已有的裝備,提升當前信息化作戰體系的效能。
總之,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增強大國的常規威懾能力。大國的常規威懾能力還將隨著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及其與其他領域的先進技術的深度融合持續增強。在進一步確保信息傳遞的可靠性,并制定符合威懾能力的威懾戰略的情況下,相互常規威懾實際上更趨于穩定。
(二)作為信息化作戰體系的賦能器,人工智能技術對核領域影響很小
首先,理論上人工智能技術當然可以提升大國針對其他大國核武器的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但在現實中依然面臨數據限制和刻意的欺騙等難題,以及不可超越的物理限制。其次,大國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不會因情報、監視、偵察能力的提升產生顯著變化。再次,人工智能技術對核武器的突防能力影響很小。人工智能技術無法對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造成關鍵影響,大國間戰略穩定性沒有本質變化。并不能因為人工智能技術改變戰爭形態和增強常規威懾能力的前景,就認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將對核領域造成相似的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對大國間相互核威懾和戰略穩定性的影響很小。
(三)人工智能技術的戰略意義
人工智能技術改變戰爭形態,從而增強和平的預期,降低大國間戰爭的可能性,這正是此項顛覆性技術的戰略意義。在常規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增強大國信息化作戰體系的作戰效能,實質是增強了大國的常規威懾能力,假以時日,人工智能技術和其他顛覆性技術共同作用,理論上可能促進常規領域中特定的二次打擊能力出現。在信息時代,大國間相互常規威懾因而更趨于穩定。
結語
人工智能對戰爭形態的影響是國際安全與戰略領域的一項基礎研究。在科學事實和合理理論推導基礎上分析人工智能如何改變信息化作戰體系的作戰單元、體系結構和作戰過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人工智能技術及其進步推動信息化戰爭向基于智能單元的信息化戰爭演變。在此基礎上,當戰爭形態的逐漸演進和軍事力量作戰效能不斷進步,國家的常規威懾能力提升,更利于相互常規威懾的有效和穩定。同時,大國間核威懾和戰略穩定性并未受到人工智能技術的顯著影響。因而可以確定,人工智能技術及其進步的戰略意義在于,其改變國家的特定能力,進一步降低大國間戰爭與沖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