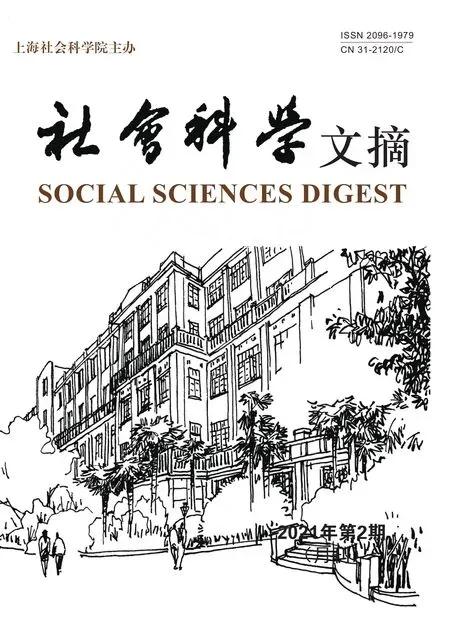時間維度與戰略目標
文/徐進
時間是戰略規劃的內在要素。然而在現有的戰略研究中,時間被忽視了,研究者們并未意識到時間維度對于制定和認識戰略的重要性。本文將主要探討時間與戰略目標之間的耦合,即為什么時間維度對戰略目標的設定至關重要。具體而言,本文擬研究三方面問題:時間為什么必須與戰略目標相耦合?時間如何與戰略目標相耦合?扭曲時間維度的因素及后果是什么?
時間與目標的耦合
在戰略規劃和執行過程中,戰略目標的設定與調整至關重要,它是戰略的龍頭,并影響到戰略步驟、戰略操作和戰略評估等一系列后續操作問題。一個戰略目標的合理性涉及戰略行為主體的利益、資源、能力、壓力和時間等多個要素,其中利益、資源和能力是行為主體能夠較好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的“知己”;壓力(或者叫干擾因素)是行為主體無法徹底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的“知彼”;時間是指戰略目標在多長時間里達成或維持,它是“知己”與“知彼”之間的一個橋梁,使兩者能夠有效溝通,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目標。因此,目標與時間的耦合非常重要,目標應當是有時間限制的目標,沒有時間限制的目標將導致執行者難以操作。比如,在作戰指揮中,上級給下級下達命令時通常有時間限制,即命令你部何時抵達何地,或命令你部何時達成何種戰斗目標。如果沒有時間限制,下級將不知如何執行或者將貽誤戰機。在軍事指揮以外的領域,帶有時間限制的各類戰略目標廣泛存在,比如中國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五年計劃等。
(一)時間為何必須與戰略目標耦合
時間維度對于戰略目標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幫助決策者確定合理的戰略節奏和制定相應的戰略步驟。既定的戰略節奏和戰略步驟又將影響行為主體動員資源的力度,以及影響外在壓力的程度。以黨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戰略和黨的十五大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例,這兩個戰略合起來規劃了中國從1980年到2049年的國家發展戰略,堪稱中國的大戰略。這個大戰略的終極目標是中國要在2049年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這樣長的時間段里,中國政府把這一大戰略目標又切分成若干階段性目標,包括解決溫飽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對于每一個階段性目標,中國政府都明確了時間限制,比如黨的十三大報告要求中國在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2000年建成小康社會,2049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基本實現現代化;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中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49年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增加了一個階段性目標,即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可以看出,上述每一個階段的時間跨度都在十年以上,從目前執行的情況來看,戰略階段的劃分和階段性戰略目標的設定都比較合理,因此戰略節奏是比較得當的,既不顯得十分緊迫,也不顯得時間過于松馳。合理的戰略節奏使得中國政府在制定和執行具體的政策時既不至于過度動員和運用國家資源,使國家經濟和社會進入一種“亢奮”狀態;也不至于動員乏力,使國家經濟和社會進入一種“惰性”狀態。另外,合理的戰略節奏也使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不至于上升得過快,沒有使有關國家因中國的崛起而過早地形成對華敵意或制衡性同盟。
反之,如果一個戰略目標的時間限定過緊,則會出現一系列后續問題,包括戰略步驟過密、戰略節奏過快。過快的節奏要求行為主體加大加速資源動員力度,從而造成資源的過度消耗,引起人力物力的緊張,最終欲速而不達。
在這方面,中國也是有沉痛教訓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在十五年內趕上美國(所謂的“超英趕美”)。根據這一目標,會上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任務和指標。會后,全國各條戰線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大躍進”的結果當然可知。仔細分析起來,志在“超英趕美”本身并無錯誤,錯誤的是時間設定,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可能在十年和十五年這兩個時間段內實現“超英趕美”的戰略目標。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由于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認識不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加之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之后,沒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就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分析這段話可以得知,黨在反思“大躍進”失誤時是有幾個遞進的層次的。首先,黨認為當時設定的在十五年內“超英趕美”這一目標過高;其次,過高的目標帶來過急的操作步驟,即所謂“急于求成”;再次,為了“急于求成”,就只好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最后,在夸大主觀因素的趨動下,不切實際地動員資源,結果造成嚴重后果。
(二)時間如何與戰略目標耦合
戰略目標有剛性目標和彈性目標之分。剛性目標就是到時候必須實現的目標,因此這類目標比較易于衡量,特別是易于定量衡量。彈性目標雖然也有時間限制,但這類目標有一定的模糊性,不易于定量衡量。因此,彈性目標的表述比較原則和模糊,給決策者留有一定的余地。還有一種可能性是,決策者不能確定在執行期內所受內外因素的制約情況如何,所以給自己留下一定的操作余地。
如果我們把時間維度分為有時間限制和無時間限制,把目標分為剛性目標和彈性目標,則可得到四種類型的戰略目標。第一種是有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這類戰略目標的特點是易于衡量,很多能夠轉化為具體的衡量指標,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強,內外因素較易于控制。中國的五年計劃、“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都屬于這類目標。
第二種是無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這類目標具體又可細分為兩個亞型。一是長期性目標。長期性目標是指需要長期維持、沒有時間限制的目標,這類目標的衡量有模糊性,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強,內外部因素復雜但可以控制。美國維持世界霸權和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戰略目標就屬于這類目標。二是無法確定時間限制的目標。這類目標易于衡量,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較強,但因內外部因素復雜且難以有效控制而無法確定達成目標的具體時間。比如,中國兩岸統一就屬于這類目標。
第三種是有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這類目標的衡量有一定的模糊性,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較強,但內外因素復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和美海軍2035年遠景規劃中提出的規劃目標就屬于這類目標。
第四種是無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這類目標的衡量有一定的模糊性,行為體戰略執行能力較低或者內外環境復雜且難以有效控制。比如,日本早在19世紀80年代左右就逐步形成了要稱霸東亞的戰略目標(日本稱之為“大陸政策”),但對于何時能夠達到這一目標沒有任何表述。這主要是因為日本當時國力不強,戰略執行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還面臨西方列強(特別是沙俄)和中國的阻礙,它能否以及何時能夠擊敗中國和沙俄,存在太大的不確定性。
扭曲時間維度的因素及后果
影響時間維度的因素比較多,包括但不限于大戰略目標、歷史因素、國內因素、國際因素、個人因素。如果一項戰略是國家大戰略的組成部分或是其階段性戰略,則其戰略目標的時間限定就受到國家大戰略的制約。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對時間維度都會產生影響,但相比而言,國內因素的可控性遠遠高于國際因素。個人因素在時間維度問題上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視,領導人個人的意愿與風格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時間維度。
上述因素都有可能扭曲時間維度,從而造成戰略目標偏移的后果。在理論上,扭曲時間維度有兩種情況,一是拉長時間進度,二是縮短時間進度。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通常是被動選擇,即因種種因素的限制不得已而為之,旨在避損,而后者是主動選擇,即因種種因素而蓄意為之,旨在獲益或爭先,并且前者對大戰略的危害遠小于后者。拉長時間進度可能會對達成大戰略目標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很難有決定性影響。比如,實現大陸與臺灣的統一是中國的大戰略目標之一。朝鮮戰爭爆發后,美海軍第六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隨后美蔣結成軍事同盟。考慮到中美在海軍實力方面的巨大差異,中國不得不將兩岸統一的策略由“武力統一”改為“和平統一”,并承諾給予臺灣當局相當優惠的統一條件。貫徹“和平統一”方針肯定拉長了祖國實現統一的時間,但很難說對實現統一的目標造成嚴重傷害。
本文將側重于研究縮短時間進度的情況。縮短時間進度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目標不變,但壓縮時間進度,擬提前達成目標;二是時間進度不變,但提高目標水平,以期達成更高的目標。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可能有三種:夸大外部威脅、機會窗口、突發事件。任何單一或幾種因素的組合都有可能導致目標偏移現象的出現。
第一,夸大外部威脅。本文討論的威脅指的是一種威脅認知或者感知,即基于對對手能力和意圖的認知而產生的對方在未來可能對自身利益造成損害的預料。在國際關系中,權力結構本身通常是良性的,但是被決策者所認知的權力結構往往是惡性的,決策者會傾向于過度認知體系內存在的威脅,夸大對手行動的威脅性,從而制定出過高的目標。
國家決策者對于對手威脅的過度認知受到國際結構因素的影響,包括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和安全困境。正是因為國家生存在一個無政府的、自助的國際體系內,再加上國家意圖和國際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出于自身安全考慮,國家常常將其他國家的軍事力量視為一種敵對的、進攻性的威脅。于是,夸大外部威脅是國際社會經常發生之事,因為對對手實力和行為的任何無視和輕視態度都可能是對自身安全的不負責任,當兩個國家都秉持這種威脅認知時,一種被杰維斯稱為螺旋模式(spiral model)的沖突模型便會產生。
從國家內部來看,統治集團也存在夸大外部威脅的傾向。哪怕對手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有限意圖,統治集團也有可能夸大對手威脅,以滿足自身特定利益需求。特定利益集團可以通過游說等方式成功挾持國家政策,而前者可以從對外擴張本身中獲益。但更多的情況是,統治精英并不必然從對外擴張本身中獲益,而是從與之相伴而生的民族主義、社會團結和社會動員中獲益。通過夸大外部威脅,統治階級就可以為自己的統治和社會資源的獲取提供一個合法的正當理由,甚至可以借此轉移國內矛盾,平息國內存在的對其統治的各種挑戰。隨著時間的發展,因為后坐力效應和自我實現等心理因素,不單單是特定的宣傳對象,最后整個社會乃至統治精英自己也逐步相信夸大后的威脅論調,這種論調形成的自我和社會壓力還可能進一步推動統治階級擴大原定的戰略目標。
第二,抓住機會窗口。窗口指的是一個國家相對實力即將衰弱或是正在衰弱的一個時期,可從三個層面進行識別,分別是機會窗口(一種正在減弱的進攻性機會)和脆弱性窗口(一種正在成長的防御性弱點),長期窗口(產生于均勢過程中的緩慢趨勢)和短期窗口(產生于能迅速改變均勢的軍事行動),內部(軍事和經濟)窗口和外部(外交)窗口。因此,本國和他國絕對實力的變化都可能打開特定的窗口期,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窗口,都會引起“現在比以后更好”的判斷。這就會促使國家從謹慎變得好斗,易于采取過度的擴張性政策,提前行動,追求過高的超前目標和權力。因為決策者認為,若是現在不這么做的話,將永遠失去這個有利的機會。此外,決策者通常認為窗口期存續時間短暫,稍縱即逝,因此,需要在窗口關閉之前趕緊抓住所謂的良機。而這會導致戰略前期準備倉促進行或被簡化,戰略決策缺乏足夠的基本判斷信息,進一步加劇上述情況。
另外,針對實施階段的目標偏移情況來說,抓住自身機會窗口期的決策心理同樣具有解釋力,但是這里的機會窗口通常指的是特定戰略行動開辟的暫時性的戰略優勢。短暫的戰略優勢通常會鼓動決策者追求戰略目標的進一步升級,一方面是因為決策者通常具有“乘勝追擊”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為戰略資源已然投入,決策者很難在輕易取勝后便及時收回資源。例如朝鮮戰爭時期,美軍會采取越過“三八線”的戰略升級行動就與其在仁川登陸后打開的軍事優勢窗口有一定關系。
第三,突發事件帶來的情勢轉變。回顧國際關系史,一些突發事件的確會對一國的戰略目標產生直接影響。從短期來看,突發情況可能直接導致戰場局勢的變化,例如十月革命的勝利直接導致俄國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戰場形勢。從長期來看,突發事件會對一國的戰略目標造成無法預見的持久影響。例如美國在經歷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兩場消耗性戰爭后基本確立了戰略克制的方針,基本不再深度卷入海外軍事沖突,但是“9·11”事件的爆發直接導致美國決心在全球打擊恐怖主義勢力,從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造成了巨大的戰略損耗。
思考與結論
時間維度與戰略目標的耦合問題可以出現在任何國家的戰略規劃和執行當中。如果大國出現這一問題,其后果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會更大。在大國當中,崛起國與守成國應當更加注意這一問題,因為它們對國際關系的發展可能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探討戰略目標的時間維度問題對我們研究當前大國戰略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大國要有戰略定力。從中長期來看,大國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順境和逆境。順境時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困難,逆境時則容易急躁冒進。蘇聯入侵阿富汗是典型的在順境時高估自己、低估困難的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是典型的急躁冒進的案例。因此,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崛起國都要保持戰略耐心,不輕易改變時間或調整目標。
其次,要給戰略目標設定合理的時間限制。要么在既定的時間段里設定合理的目標,要么為目標的達成設定合理的時間限制。戰略目標與時間維度的合理結合取決于多種主客觀因素和內外因素,但是要特別注意控制個人或小團體因素的影響。不管是個人還是小團體,都容易壓制反對聲音的出現,犯“一言堂”的錯誤。
最后,大國要能及時回調止損。一旦出現戰略目標偏移現象,大國要能及時發現,及時回調,及時止損。對于大國來說,及時回調止損的困難在于前期的沉沒成本比較高,導致船大難調頭。這方面的負面案例很多,比如美國結束越南戰爭、美國結束反恐戰爭、蘇聯結束阿富汗戰爭,等等,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