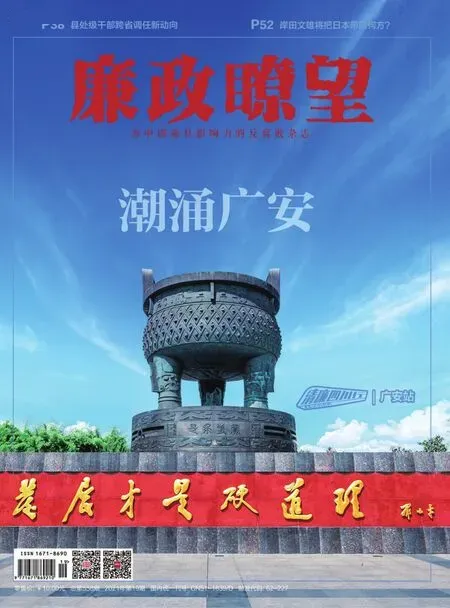主動吸毒的人怎有臉自稱“受害者”?
│文 本刊全媒體見習記者 肖鑫睿
10月11日,已經淡出公眾視野多年的宋東野突然發布長文為自己叫屈,起因是他的線下演唱會因他人“惡意舉報”被取消,他覺得自己3年禁演期已經過去了,可是還是有人不肯原諒他。在文中,宋東野稱自己是毒品的“受害者”,并稱“殺人的一直都是販毒者,不是我”。文章發出后不久,宋冬野微博被禁言。
許多網友對宋冬野的這番叫屈并不買賬。5年前,宋冬野因吸食大麻被拘留,在一檔法制節目中,他承認自己已經吸毒兩年,原因是“可以激發創作靈感”。如今,他的理由變成了藝人行業是“抑郁癥和精神疾病的重災區”,自己是因為外界的壓力才吸毒。
他夸張地描述了自己當藝人承受的壓力,“幾乎準備好要毀滅自己”,把吸毒描述成唯一的出路,認為沒有誰能“扛得住這個被偽裝成糖的毒藥”,始終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找借口。此外,他還用“工作人員、樂隊成員的辛勤努力”“幾千名觀眾的期待”等說辭對大眾進行道德綁架,企圖把自己包裝成“敢于為藝術獻身”的犧牲者。殊不知,千千萬萬投身演藝事業的人,誰又是必須靠吸毒維持這份熱愛的呢?
又是擺出“文藝圈缺我不可”的態度,又是打著“只想靠音樂這點手藝養家糊口”的同情牌,宋冬野的說辭招致許多人反感,有句評論一語中的:“那你干嘛非要當藝人呢,工廠還缺擰螺絲的呢,不還是圖這行賺錢快嗎?”
在我國,吸毒并不入罪,販毒才算犯罪。但是,吸毒不算犯罪更多是因為考慮到有人會落入圈套,在不自覺中接觸到毒品。而宋冬野自己也說“毒品是個深淵”,卻仍然一頭扎進去,明明是自己害了自己,還大言不慚,說是販毒者的“供”一直在單方面創造著“需”。可是,毒品的供需關系從來不是單方面的。
吸毒者不能單純地稱自己為“受害者”,是因為不能只看到吸毒對身體造成的損害,其社會危害性也是不容小覷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說,人吸毒以后往往會出現精神上的障礙,對社會造成威脅,另外為了滿足毒資的需要,吸毒者可能會實施盜竊、搶劫等侵犯財產的犯罪。
更不要忘了,還有許多緝毒警察用生命堅守在禁毒一線。云南警察張從順在抓捕毒販時被手榴彈炸死,其子張子權繼承父親遺志成為緝毒警察,在辦案途中又因過勞犧牲;李敬忠在抓捕毒販時身中兩槍壯烈犧牲。公安部曾發文痛批吸毒明星復出:“在這條罪惡的利益鏈上,吸毒者也是一環”,“那些為吸毒而花出去的錢都變成了毒資買了子彈,打在了緝毒警的身上!”
因此,吸毒者必須為自己的放縱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可能是身陷囹圄,也可能是家破人亡。同樣是自食惡果的人,公眾人物怎就有臉自稱“受害者”?更何況,他們的日常行為和價值觀更加容易暴露在公眾視野中,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使其失去公眾關注自然是合情合理。在涉毒藝人中,諸如李代沫、陳羽凡等絕大多數都銷聲匿跡。
今年9月,中宣部印發《關于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確加大對違法失德藝人的懲處,禁止劣跡藝人轉移陣地復出。這不僅體現了對文娛領域從業人員的底線要求,也響應了公眾對凈化文娛環境的期待。
此前,說唱歌手PGone的一首歌曲因包含教唆青少年吸毒和侮辱婦女的歌詞被下架,其本人也因為諸多劣跡問題而遭到封殺,今年試圖通過發布兩首新歌復出,但歌曲上架平臺后不久就被下架,連賬號也被注銷,宣告其復出計劃失敗。
就像有評論說到,很多時候不是一句“只聽歌不看人”就能解決問題的,錯誤已然鑄成,不要再拿所謂的“音樂夢”來粉飾劣跡,這種推卸責任的言行只會顯得自己更加幼稚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