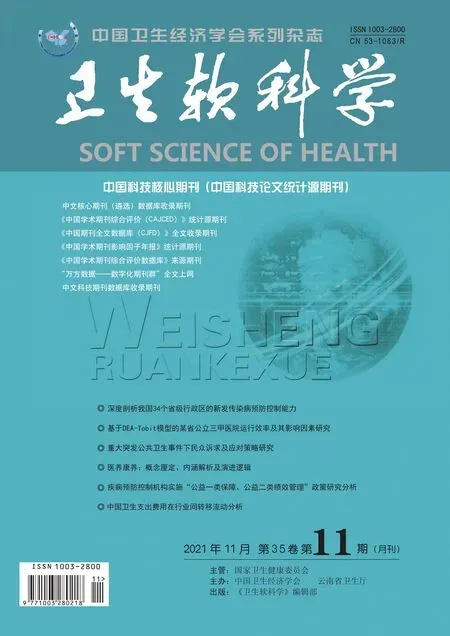結構變動視角下新醫改十年湖南省衛生總費用籌資及流向變化分析
王靖宇,張加奇,周良榮,王 瑩,李 玲
(湖南中醫藥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8)
衛生總費用(Total Health Expenditure,THE)是以貨幣形式作為綜合計量手段,全面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間內(通常指1年)全社會用于醫療衛生服務所消耗的資金總額[1]。來源法和機構法為當前兩種主流核算衛生總費用的方法。200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為衛生總費用籌資及流向的良好發展指明了方向。本研究從結構變動的視角,對新醫改10年來湖南省衛生總費用進行分析,找出其變化特點、宏觀規律,為政府制定目標、做出關于衛生總費用發展的決策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衛生總費用來源法與機構法核算數據來自歷年《湖南省衛生統計年鑒》《衛生健康財務年報》《社會保險基金決算》等,個別數據根據現有數據及相關參數進行估算或來自典型調查。
1.2 方法
結構變動度分析法是一種動態數據處理方法,它能有效地反映數據的總體特征及其變化趨勢[2]。本研究采用此方法分析新醫改10年來湖南省衛生總費用籌資及流向變化情況,設立結構變動值(VSV=Xi1-Xi0)、結構變動度(DSV=∑|Xi1-Xi0|)以及結構變動貢獻率(結構變動貢獻率=|Xi1-Xi0|/ ∑|Xi1-Xi0|,i=1,2,3……)3個指標。
2 結果
2.1 新醫改10年湖南省衛生總費用情況
從近10年來源法與機構法核算結果來看,湖南省2010-2019年衛生總費用籌資規模不斷擴大,占GDP比重呈上升趨勢。來源法衛生總費用由2010年的739.78億元上漲到2019年的2771.68億元,年均增長率為30.32%。機構法衛生總費用由2010年754.41億元上漲到2019年的2621.07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7.49%。見表1。

表1 2010-2019年湖南省衛生總費用情況
2.2 新醫改10年湖南省衛生總費用籌資結構及變化
近10年來,政府衛生支出和社會衛生支出逐年增長,分別從2010年的213.19億元和203.05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709.78億元和1184.36億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5.88%和53.70%。從費用來源所占比重整體趨勢來看,政府衛生支出和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占比呈下降趨勢,而社會衛生支出占比呈上漲趨勢,由2010年的27.45%上漲到2019年的42.73%,見圖1。

圖1 2010-2019年湖南省衛生總費籌資結構變化情況
從結構變動值來看,政府衛生支出和個人現金衛生支出都為負數,呈負向運動,其占比在降低;社會衛生支出除2017-2018年為負數,其余年份均為正數,其占比一直在增長,呈正向運動。從結構變動度來看,2010-2019年湖南省衛生籌資的總體結構變動度為30.57,其中最大的為2014-2015年,變動程度為8.62,2011-2012年變動程度最小。從結構變動貢獻率來看,2010-2019年社會衛生支出衛生費用籌資結構貢獻度最大,達50%,其次是個人現金衛生支出,政府衛生支出的貢獻率最小,見表2。

表2 2010-2019年湖南省衛生籌資的VSV、DSV及結構變動貢獻率
2.3 新醫改前后湖南省衛生總費用機構流向及結構變化
從衛生總費用機構法流向來看,流向公共衛生機構費用占比整體呈下行趨勢,從2010年占比10.60%降到2019年的7.28%。門診機構費用占比先升后降,整體從6.43%降到5.11%;流向藥品零售機構費用的占比在2013年后呈現下行趨勢,到2018年、2019年僅占11.93%、8.62%。流向醫院機構費用占比在2010年較2009年下降將近2個百分點,到2017年基本穩定在55%左右;2018和2019年流向醫院費用占比又超過了60%。見圖2。

圖2 2010-2019年湖南省衛生總費用機構流向
2010-2019年,除其他以外,醫院與衛生行政和醫療保險機構結構變動值為正數,藥品零售機構結構變動度最大,醫院次之,分別為17.69和13.87,同時,這兩種機構對湖南省衛生總費用結構變動貢獻率排前兩位,見表3。

表3 2010-2019年湖南省衛生總費用機構流向的結構變動值、結構變動度及結構變動貢獻率
單從醫院費用機構流向來看,新醫改10年來,縣醫院與社區服務中心的結構變動值為正數,呈正向運動。縣醫院的機構變動最大,數值為9.60;城市醫院排第二,數值為7.16。縣醫院對衛生總費用結構變動貢獻率最大,除其他外,社區服務中心貢獻率最小。見表4、圖3。

圖3 2010-2019年湖南省不同醫院費用比重變化趨勢

表4 2010-2019年湖南省醫院費用機構流向的結構變動值、結構變動度及結構變動貢獻
3 討論與建議
3.1 湖南省衛生總費用籌資及流向規模均呈增長趨勢
新醫改10年,來源法及機構法核算結果均表明湖南省衛生事業投入穩步增長,這為湖南省衛生事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代表了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對衛生事業以及居民健康的重視程度,湖南省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逐漸增加,且從2013年來源法和機構法均超過5%的基本要求,2019年分別達到6.82%和6.74%,反映了湖南省居民對衛生健康服務的需求日益加大。
3.2 政府衛生投入不足,衛生籌資結構仍需不斷優化
優化衛生籌資結構才能進一步緩解居民個人醫療負擔,使居民都能享受到公平可及的醫療服務。10年來,湖南省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占比持續下降,2019年占比31.66%,平均降速3.42%,按此推算,2020年占比約為30.58%,高于國務院頒布的《“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中要求的2020年底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28%左右。與此同時,湖南省衛生籌資規模不斷擴大,但政府支出比重下降,未實現2009年新醫改提出的“逐步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比重”的要求,且與美國(2013年政府衛生支出占比43.2%)等發達國家差距巨大。社會衛生支出結構變動值為15.28,呈正向運動,結構變動貢獻率高達50%。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財政壓力增大,僅僅依靠政府加大對衛生事業的投入來改善衛生籌資結構不符合現實,因此進一步完善社會醫療保險(不含政府補助)制度,鼓勵社會資本辦醫以及對社會衛生固定資產的投入,規范商業保險市場,出臺相關的捐贈援助政策,如免稅等[3],成為進一步減輕居民醫療負擔,降低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占比的有效途徑。建立“政府投入為主,社會籌資為輔,個人承擔些許責任”的具有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衛生費用籌資機制至關重要。
3.3 衛生費用流向不合理,存在衛生配置效率低下風險
3.3.1 費用主要流向醫院的趨勢沒有改變
10年來,湖南省衛生費用超過50%仍流向醫院,且醫院結構變動值為正數,說明占比有所增加。在流向醫院的費用里,又主要集中在城市醫院與縣醫院。這說明分級診療制度在控制衛生費用流向尚沒有起到明顯效果。流向醫院費用占比過高成為湖南省居民醫療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推動公立醫院改革,深入實施公立醫院績效考核,貫徹各級醫院功能定位,使其多承擔急診與各種疑難雜癥住院服務,將常見病多發病、康復治療等服務下放到基層醫療機構[4]。建立完善的基于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分級診療體系,引導患者流向,重構就醫結構。這些措施都有助于改變費用流向。
3.3.2 基層醫療機構資源配置不合理
湖南省僅有14%~18%的衛生費用流向基層衛生機構(社區服務中心和衛生院)。社區服務中心的結構變動值為正數,僅為0.59,衛生院則為-3.90,整體流入基層衛生機構的費用降低。一則說明基層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并沒有提升,醫療收入來源不足。二則流入基層醫療機構資源較少,不同服務層級衛生機構之間衛生費用配置不合理,出現“重城市,輕農村,輕基層”的醫療資源倒置現象[5]。WHO關于衛生籌資戰略的中期評估報告指出,基層可以解決大約70%的衛生干預措施和80%的基本衛生服務[6]。財政上加大對基層衛生機構的投入,引導并推動優質的“硬件”和“軟件”資源下沉,提升其服務能力。擴大基藥目錄以滿足常見病、慢性病的用藥,使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就能滿足老百姓日常用藥需求。推動采用靈活的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周期。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與分級診療、首診在基層等制度并行,引導患者到基層就醫,形成合理的就醫秩序、費用流向,緩解湖南省居民就醫負擔。
3.3.3 對公共衛生機構所起的作用認識不足
10年來,湖南省公共衛生機構結構變動值為-3.32,這說明公共衛生機構投入不足且占比下降,湖南省衛生投入存在“重治療,輕預防”的問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預防所產生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尚未被意識到,普遍對公共衛生服務工作不重視。公共衛生機構提供的服務,如健康體檢、疾病防控、婦幼保健等,都具有“成本低,效益好”的特點。將預防服務納入醫保報銷范圍,進一步完善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制度,發揮其戰略性作用,引導居民從傳統的“重治療”向“重預防”轉變。建立穩定的公共衛生事業投入機制,創新科研和社會化服務機制。健全公共衛生醫師制度[7]。從而降低居民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占比,減輕居民就醫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