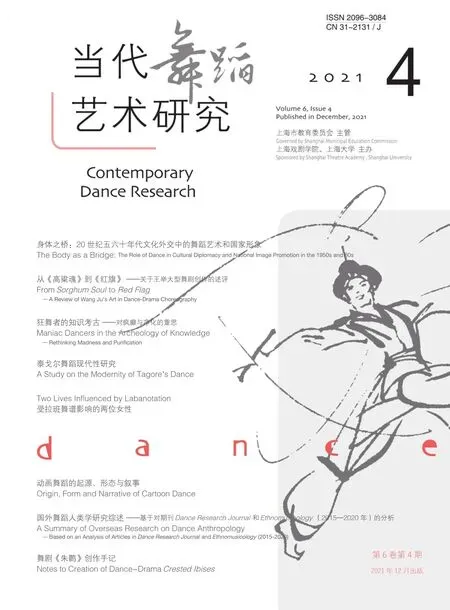時代·語言·審美
——當代中國“新古典舞”創作分析
陳 苗
本文對中國“新古典舞”概念的界定與分析,是基于學界長期以來對“古典舞”的討論而展開的。自20世紀40年代舞蹈人對“中國古典舞”的探索開始,到20世紀70年代末北京舞蹈學院為籌建本科教育系中國古典舞專業進行的“36次會議”,再到以北京舞蹈學院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創建與發展,“中國古典舞”的學科建設在百家爭鳴中形成了“身韻古典舞學派”“敦煌古典舞學派”“漢唐古典舞學派”,學界圍繞“中國古典舞”的討論和實踐至今仍未停止。吳曉邦認為中國古典舞建設的核心在于“古典精神”:“中國古典舞的概念應與中國古代作家與民共憂患的精神內涵一致,因此要從舞蹈的內容出發,它首先著眼于古代社會人民大眾在苦難生活中真情實感的流露。”①于平整合了吳曉邦先生“從舞蹈內容出發”“與民共憂患”“古典精神”等觀點后進一步分析:“中國古典舞‘是從舞蹈內容出發的’(不能糾纏某種歷史形態),而這種‘舞蹈內容’又應該以‘中國古代作家與民共憂患的精神’為根據”;[1]116“‘古典’絕不僅僅是個時間或者時代的范疇,‘古典精神’也絕不僅僅是指某個特定時代里特有的東西,現代生活中也有‘古典精神’”[1]116。孫穎在《四論中國古典舞——關于古典精神》中談道:“中國古典精神說到底,就是從物質和精神文明這兩個方面所體現的民族智慧、民族個性、民族的道德風尚和民族文化的品位。”[2]66劉青弋也曾指出:“中國古典舞的學科建設不僅僅是技術、動作、風格以及運動的方法問題,還有在其中顯現的文化問題。”[3]我們必須“注重區分古典舞及其相關的文化建設的不同層次、不同方向和不同任務:本體形態——稱謂‘古典舞’(其任務是將活態傳統進行歷史博物館式的保存、展示,讓后世將其作為有啟發意義的歷史進行不斷的回顧)。而其發揚形態——稱謂‘新古典舞’(其任務是對傳統以繼承為主的發揚,通過實現傳統文化推陳出新,使得傳統文化得以發揚光大)。”[4]
這些討論讓筆者以審慎的態度思考那些被冠以“古典”之名的舞蹈創作。基于以上討論,本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以古代舞蹈語言形態表現“古典精神”的劇目統稱為“新古典舞”。“新古典舞”不受時間的限制,但因時代差異,劇目的身體語言及審美風格呈現出不同的狀態,民族精神一直是其建構與發展的核心追求。故而本文進一步將1949—2021年國內有關“新古典舞”的創作劃分為四個時期。四個時期分別呈現出不同的精神風貌:一是1949—1966年,語言形式探索與民族精神初建時期;二是1976—1989年,多維視角審視與民族精神塑造時期;三是1990—2012年,個體生命張揚與民族精神深化時期;四是2013—2021年,“一體多元”呈現與民族精神升華時期。本文將依托“新古典舞”劇目,分析不同時期“新古典舞”創作的意識、形式與語言,并提煉其所蘊含的“古典精神”。
一、“新古典舞”的歷史分期與精神風貌
社會轉型與政治制度變革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政治制度變革必然影響人類的社會活動,影響文化的變化、發展,“社會轉型是推動社會文化形態轉型的動力,分別體現在觀念層面、制度層面和物質層面”[5]176。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文藝則是時代的號角。“一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與時代同步伐,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6]中國的“新古典舞”在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四個時期的劇目所體現的“古典精神”始終契合時代風貌與群眾心理,亦可由此清晰尋覓到國家意識對“新古典舞”文藝創作的影響。
(一)1949—1966年:語言形式探索與民族精神初建時期
20世紀上半葉,中國舞蹈的狀況是:“舞蹈同時并存著三種政治文化核心意識:‘人的意識’‘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7]在此文化氛圍影響下,這一時期,以《飛天》《寶蓮燈》《荷花舞》《春江花月夜》《長綢舞》《小刀會》等為代表的“新古典舞”劇目,在救亡圖存的回溯中,重塑民族精神,創作的重點突出表現為中華民族不畏強權、砥礪前行,重拾民族自信,恢復生產生活,積極建設新中國的主題。另外,以“新古典舞”名義存在的“紅色舞蹈”也體現著古典精神和古典品格。“在中國,‘紅色舞蹈’是中國舞蹈創作的主流。‘紅色舞蹈’的創作既是舞蹈家的個人意志的體現,也是全社會基于同一文化心理的精神所需,這一文化心理的精神需求和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密不可分。”[8]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新古典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反帝反封建的主題,歌頌民族堅貞不屈的意志和精神,如民族舞劇《小刀會》對帝國主義的反抗;《寧死不屈》中男女主角對惡勢力的反抗;《寶蓮燈》中三圣母、劉彥昌、沉香與宗法維護者二郎神、哮天犬及巨龍的搏斗,表達了正義的力量。這些劇目中男女主角對于正義的堅持,面對惡勢力時大義凜然的氣勢,面對困難時百折不撓的堅持,表現了人民大眾反封建、求解放的斗爭精神。二是歌頌社會主義祖國與美好生活,如《荷花舞》和《春江花月夜》等。《荷花舞》中,戴愛蓮先生一方面借鑒民間舞蹈的形態,另一方面模擬荷花在自然環境下的生長狀態。舞蹈中的手臂動作、步法、隊形和服飾,營造出朵朵蓮花水上漂的意境,更表現出新中國如荷花般生長的蓬勃氣象。三是塑造新社會、新人形象,尤其是工農兵和英雄的形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勞動人民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農兵群體“翻身當家做主人”的豪邁表現在“新古典舞”中就是對工農兵形象的歌頌,也映射出人們對英雄氣概和英雄精神的崇尚。盡管上述三個方面的主題表現各有側重,但都有共同的特點——人民群眾成為主角和頌揚對象。這樣的主題轉變,使得舞蹈脫離“女樂”的歷史認知,在“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大語境與時代的推動下創新舞蹈的表現形式,這類劇目的題材和內容不乏“紅色舞蹈”。有學者認為這類作品不符合古典舞對“古典人物”的要求,但是從舞蹈語言上分析,這些作品大多采用傳統京昆戲曲動作。筆者認為,這些劇目符合前文所定義的以“古代舞蹈語言形態表現‘古典精神’的劇目”,應屬于“新古典舞”。“對于‘紅色舞蹈’而言,舞蹈是載體,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思想和信念是靈魂。它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傳達的是價值觀念”[9]。這種意識在中國“新古典舞”劇目中表現為對英雄人物的塑造,不論是民族舞劇《小刀會》中周秀英、劉麗川、潘啟祥這樣的英雄,還是《炸碉堡》《黃繼光》中的軍人楷模,或是《風暴》《劉胡蘭》中的人民群眾,都在借塑造“舍小我,成全大我”的民族精神,展現對英雄的歌頌,以及人民當家做主的昂揚風貌。
(二)1976—1989年:多維視角審視與民族精神塑造時期
經歷了文化創傷的中華民族,迫切需要重拾文化傳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外開放”等文化和政策導向,也為文藝創作注入了新鮮血液。這一時期,文化領域面臨著究竟是回歸傳統還是全盤西化的激辯以及“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討論,“新古典舞”的編導們逐漸在迷惘中找到平衡,更注重立足本土、回歸傳統,也在中西文化碰撞、古今文化交匯中迎接新的機遇與挑戰。
首先,“新古典舞”在延續與拓展中強化“民族”概念的認知。這一時期“新古典舞”劇目的精神內涵,延續“十七年”時期自強不息、無畏犧牲的精神,通過塑造典型人物來突出典型形象。代表作品有《金山戰鼓》《木蘭歸》等。在《金山戰鼓》中,梁紅玉的勇敢退敵化為清晰的三段體式結構。作品借用京劇中的武旦技巧,巧用道具,通過“大五花擊鼓”“大甩腰擊鼓”等擊鼓方式突出身段上的閃轉騰挪;節奏上強調輕重、剛柔、強弱的對比;情緒上圍繞著“抗敵人、保家園”的情懷,在動靜之間展現梁紅玉御侮折沖、大義凜然的氣節。“新古典舞”編導還進行了新的探索,從古今文化交匯中挖掘傳統的精髓,以今人視角進行藝術創作。如舞劇《文成公主》,將唐代仕女圖中的人物形態融入古典舞身體語言,創造性地結合了藏族舞蹈,成功地塑造出文成公主的形象,并刻畫出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伉儷情深的感人故事,以此追溯中原與邊疆地區的歷史淵源與血脈交融。此類劇目的典型代表還有《醉劍》《盛京建鼓》《長城》《昭君出塞》等。
其次,“新古典舞”還在尋根中轉變創作題材選擇方向,表現內容更加豐富。“許多編導開始注意從民族文化最深層的底蘊中尋找最富于舞蹈精神的東西。”[10]92以《絲路花雨》為首,編導深入研究了敦煌壁畫中的舞蹈形象,并將其中獨具特色的“S”形體態及具有代表性的“反彈琵琶”舞姿進行提煉,將其與古典舞語匯融合,開創了后來被稱作“敦煌古典舞學派”的先河。由此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仿古舞蹈之風,被稱為“中國古代樂舞復興”[10]86。以歷史學和圖像學的視角審視“新古典舞”,編導們通過深入研究文獻、文物壁畫等史料,提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舞蹈姿態進行藝術再創造。“仿古樂舞”再現了我國古代樂舞藝術之風采。應該說,“仿古樂舞”的出現,亦是對傳統“雅樂”的再認識,如《仿唐樂舞》中有《觀鳥撲蟬》《白纻舞》《面具金剛力士》等舞段,分別體現出輕盈飄逸之“文”韻與雄健古樸之“武”風,展現出唐代舞蹈的多元與繁榮。除“仿古樂舞”,“新古典舞”編導們還將視角聚焦在花鳥魚蟲類自然景觀,選取與時代風格和個人意志相契合的事物,借鑒傳統語匯對舞蹈本體進行研究。如《小溪·江河·大海》中借助古典舞“圓場步”的“形”,精心設計的隊形調度流轉蜿蜒,塑造出小溪、河流、大海的形象,由此實現“新古典舞”身體語言的“意象化”創造。
再次,“新古典舞”在中西對話中推動創作思維革新,表現手法更為豐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大量西方思潮涌入中國。“新古典舞”編導的觀念受人文主義和現代主義等思潮的影響,打破了常用的傳統敘事手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交響編舞法的運用,編導在保持舞蹈藝術“獨立自主權”的同時,從音樂形象出發完成意象化的舞蹈創作,群舞《黃河》是“新古典舞”編導們運用這一創作手法的成功果實。這部作品以古典舞身體語匯為基礎,根據“黃河”意象塑造所需,編導在作品中弱化了古典舞動作中源于傳統戲曲動作的固有審美及藝術表達,結合音樂的交響化手法為動作賦予了新的內涵。動作的起伏、強弱和音樂的起伏、力度一同營造了不息的河水、澎湃的波濤和奮勇抗爭的身軀;調度的分合和音樂的結構暗中呼應,表現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的團結之力。作品“避開了用動作交代外在故事情節,也避開了對于抗日戰爭的各種事件的表面描繪,而是把黃河所代表的精神做了大大的抽象化處理”[10]105,這是中西編創思維融合對傳統舞蹈元素的解構與重構,把“新古典舞”創作推向了更高的階段。
(三)1990—2012年:個體生命張揚與民族精神深化時期
這一時期,伴隨著民主進程的推進,文藝創作呈現多元態勢,“強調對個人自由價值的追求和保障”[5]158。中國“新古典舞”創作沿著上一時期的方向走上更加寬廣的道路。
這一時期,“新古典舞”創作中重視對個體生命境遇的表達,突出對人的信念、欲望、精神狀態的表現。如孫穎先生的“漢唐”系列,還有《秋海棠》《竇娥》《旦角》等作品,均將人文關懷聚焦到個體生命之上。《秋海棠》與《旦角》以三段式結構展現戲曲藝人的生命歷程與境遇,出袖、收袖、抖袖、揚袖,起落間飽含著藝人對舞臺的熱愛;身體的舒展與佝僂,雙足的收攏與躍起展現主人公命運的高潮與低谷。如此以情感人、關懷個體生命境遇的“新古典舞”劇目還有《九歌·山鬼》《萋萋長亭》《竇娥》《孔乙己》等。《九歌·山鬼》通過祭祀山鬼的舞動,隱喻今人內心的躁動與渴望。舞蹈突破傳統劇目中女性單純、善良、堅韌、賢惠、無欲等刻板形象,通過古代楚地巫舞的想象,創造性地展現女性應有的欲望與情思,山鬼的迷狂在肢體夸張的造型與扭動中展現。這是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對人性的重新認識與發現,是人道主義關懷帶來的對人正常欲望的尊重、理解與釋放。《踏歌》《綠帶當風》《麗人行》《春閨夢》等莫不如此。
這類富有人文關懷的作品以及其所體現的個體生命抒發的轉變是值得注意的,這種變化不僅是社會開放程度提高后對個體生命境遇的觀照,亦是“民族精神”的立體挖掘。此類劇目數量漸增,創作向度跨越古今。如男子獨舞《風吟》便是在自由的創作氛圍中,編導向內尋求個體生命感悟的佳作。《風吟》的創作動機源于編導張云峰兒時在高高的草垛上體會風兒拂過面頰,揚起衣襟,隨風飛翔的記憶。這化為“新古典舞”對傳統美學“無垠、自由”的身體折射。《風吟》沒有使用傳統敘事方式造境的做法,轉而嘗試以抽象的動作展現傳統文化意蘊,正是當代人對“遠思長想、舒意自廣”的哲思延續。此類劇目還有《輕·青》《碧雨幽蘭》等,這些劇目無疑是“新古典舞”編導們汲取傳統文化精神的自由言說。
除了個性的抒發和張揚,這一時期“新古典舞”對民族精神的探索不斷豐富和深化。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學熱、“唐裝漢服”熱、歷史題材電視劇的高收視率等文化風尚,都是民族精神的新表達。“新古典舞”對民族文化精神建構的重視,正是這一時期民族精神建構內涵的豐富、民族情感整體共鳴豐厚的結果。如《秦俑魂》等作品的出現,無疑是“新古典舞”建設初期“斗爭”“解放”的深化。孫穎先生的《謝公屐》等“漢唐”系列作品,展現中國文人的通透、質樸的情懷,劇目貌似瀟灑的“游山玩水”,其實心中依然系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與操守。孫穎先生借“新古典舞”劇目重現文人風骨,是對古代文人精神風貌的尊敬與推崇,亦是其在挖掘民族智慧、民族個性、民族道德和民族文化品格過程中的有力印證,是從古至今中國文人的家國意識與自我身份認同。進入21世紀,政策和文化導向的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強調“文化自信”,使中國以大國姿態走向復興。“新古典舞”的創作也表現出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與探尋,題材選擇與民族精神塑造方面,既關注個體生命,也表現出對于傳統文化傳承的深入探索與大膽構思,體現出中國文化傳承的自信與擔當。從《秋海棠》到《愛蓮說》《屈原·天問》,從《謝公屐》《風吟》到《扇舞丹青》《書韻》《我欲乘風歸去》,均可看出這一時期藝術家們在個體生命張揚與民族精神建構方面的探索、繼承與深化。
(四)2013—2021年:“一體多元”呈現與民族精神升華時期
借鑒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北京舞蹈學院古典舞主任王偉教授提出了古典舞發展的“一體多元”概念。她認為,中國歷史傳統舞蹈文化長河中,“新古典舞”的定義與發展依靠一家之言難以盡述,“身韻古典舞”“漢唐古典舞”與“敦煌古典舞”共同構成了“新古典舞”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批“新古典舞”中彰顯著民族精神。近年來,國家一級編導馬家欽的“昆舞”探索,劉青弋教授的“雅樂回家”“追問古典:中國古典舞‘名’‘實’之辨”系列,劉建教授的漢代壁畫身體實踐工作坊和田湉副教授的“俑”系列演出,表現出對“新古典舞”獨特的歷史的闡釋與解讀。
在漢唐“新古典舞”方面,孫穎先生開拓的多元路徑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此時期的《心存漢闕》、舞劇《李白》中的《踏歌》、舞劇《孔子》中的《采薇》、北京舞蹈學院中國古典舞2015級漢唐“子衿班”的《響屐舞》等,再探新韻。在敦煌“新古典舞”方面,《大夢敦煌》《并蒂蓮》《迦陵頻伽》以及史敏的敦煌教材和劇目系列,均為立足藝術、文化、民族精神的綜合探索。在“古舞新風”方面,《唐宮夜宴》《唐印》等作品在不同的向度中呈現藝術家們對“新古典舞”中的“古代題材”的情有獨鐘,隨著網絡平臺的興起,一些作品掀起民族文化的新熱潮。如舞劇《杜甫》中的群舞片段《麗人行》。在舞的揮灑中展現出女性的力量,在忽而連貫、忽而頓挫的動作中體現女性的掌控力,在身體重心的小范圍快速調度中描繪出唐朝宮娥青春健美的游春圖。
這也是民族情感的整體共鳴。這一時期,中國新古典舞創作體系中歌頌民族精神的內容表現在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入傳承與自信展現上。身體語言的選擇上,“新古典舞”在“古典”的限定之下,在解放與限制的矛盾中尋找出更為“自由”的身體舞動:一方面不再拘泥于前兩個時期探索的,或已經形成的新的程式性身體語言,選擇更加開放自由;另一方面在舞蹈身體語言表達上追求準確中的豐富和多元,體現出中國文化傳承的自信與擔當。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新古典舞”創作,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框架下的民族精神升華,是在民族自信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契合中言說中國表述。
從以上分期可以看出,中國“新古典舞”始終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探索作為內在追求,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下將形式、語言和民族精神同個人“言語”相結合,傳達出展現時代風貌的“新古典精神”。從1949—1966年,舞蹈語言的形式探索與民族精神的初建,1976—1989年,多維視角審視與民族精神塑造,到20世紀90年代對個體生命的尊重與關注,再到近10年間在“文化自信、民族復興”意識下對傳統文化的賡續與發展。1949年至今的探索,“新古典舞”從傳統文化中不斷挖掘,投射到“新古典舞”劇目中,呈現出一種隨時間延續內涵逐漸擴大的趨勢。
二、“新古典舞”舞蹈語言與審美風格的演變
從舞蹈語言體系建構和審美風格的變化來梳理“新古典舞”,實際是回到開篇提及的學界關于“古典”兩字之爭下形成的不同古典舞學派。“它們集聚起來的歷史碎片形成的訓練體系,建立的屬于語言體系中的語素和語匯部分,而非語言體系的整體,而在其中他們一些想象的、創新的、吸收的外來文化的成分則不屬于古典舞之列。”[11]本文認為“身韻古典舞學派”“敦煌古典舞學派”“漢唐古典舞學派”三大學派雖然“語源”不同,但三種古典舞蹈語言形態的建構與發展都體現“守正創新,篤行致遠”的“古典精神”。下文將基于“新古典舞”劇目的歷史分期,闡釋“新古典舞”語言的當代表達與審美風格演變。
(一)“新古典舞”舞蹈語言的繼承與當代表達
20世紀50年代,脫胎于戲曲的“身韻古典舞學派”作為最早的語言形態探索,拉開了“新古典舞”“言語”構建表達的大幕。1957年,北京舞蹈學校古典舞教研組的教員們在“京、舞、體”三種語言的作用下,借鑒芭蕾經驗,做出了諸多嘗試。“一、有選擇地把戲曲訓練的基本功、身段和毯子功合并為一門課。……二、身段教材,從不同‘行當’,表現不同感情的千變萬化的手的動作和姿勢中,提煉了常用的‘手的八個基本位置’……‘腳的基本位置’……。統一了動作的規格和要求,把原來的戲曲動作給予了新的規范。三、初步借鑒芭蕾教材的結構方法,從繁雜的戲曲技巧動作中,尋找共同的基本能力……。四、采用音樂進行練習:從最簡單的單一動作開始,直至組合練習,均配上音樂伴奏。”[12]教員們也創造了“穿掌蹦子”“倒踢紫金冠”等富含民族審美意味的技巧。《牧笛》《春江花月夜》《東郭先生》《風暴》《白毛女》《劉胡蘭》《為了祖國》《張羽煮海》《寶蓮燈》等小品和大型舞劇也在這一時期孕育而生。“對于中國古典舞的認知來說,能從‘戲曲舞中的舞蹈動作’擴大到‘戲曲舞蹈’、擴大到‘戲曲舞蹈’之外的‘古典舞蹈’,超出了‘李正一時代’封閉狀態的‘科學訓練’的有限理論,因為屬于美學和藝術范疇的古典舞主要是一種人文學科的身體認識。”[13]614毫無疑問,建立在傳統文化和“古典精神”同當代發展相結合基礎上的“古典舞身韻”系統,經過近12年的實踐,取得了可喜成績。
1979年,大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以佛教藝術——敦煌莫高窟的歷史遺存為藍本,選取、提煉敦煌舞特有的“S”形曲線運動規律和反彈琵琶伎樂天的舞姿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孫穎等編導們嘗試將靜態歷史資料變成動態形象的做法,給“新古典舞”注入一針強心劑。通過挖掘漢代畫像、畫磚、敦煌壁畫等圖像資料研究語言本體形態,并嘗試將其重置于歷史語境中,給“新古典舞”進一步傳承傳統文化打開了新思路。“漢唐古典舞學派”重在“立”,“塑形、重心、平衡、速度力量,跳、轉、翻,向在流動中訓練重心平衡,訓練速度,訓練氣息,側重肩胸,側重腰臀。再將課堂結構調整為上肢、下肢、氣韻、心態,而后再轉向意境化、情調化、個性化以表演為主的終結階段”[2]135。敦煌舞的語匯體系“在手姿、手臂、脖頸、身腰、跨步、腿腳的形態上,形成的彎弧、高度傾斜、擰曲動作及連接組合,以及貫通身心的‘S’形內在韻律曲線,構成敦煌舞表演體系與戲曲舞蹈身韻學派的中國古典舞體系的基本分野,同時構成敦煌舞獨特的美學價值與藝術風格”[14]。通過分析不同古典舞學派的語言及形態,不難發現,不論何種形式都無法避免需要思考和研究“古”與“今”的關系,究竟是“作古”還是“訴今”,或許“新古典舞”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尋覓語義構建當代人心中的‘古典’”,即要解決核心“語義”的問題。“當中國古典舞以異質化的芭蕾基訓元素、體操訓練元素(本質上同樣是異質的西方體育文化)、戲曲元素與武術元素充當自己的科學訓練保護傘時,其身體文化和身體美學便被依次同質化,形成共時狀態的雜糅,而不是細化自身的‘動作體系’。”[13]616從20世紀80年代舞劇《銅雀伎》以及“尋根述祖譜華風”等二十多個劇目的創作實踐,內含了“新古典舞”創建者對古代舞蹈的創造與挖掘,“強調民族化,強調對歷史傳統的接續,強調我自成章,強調文化特色”[2]135。同時也展現了這一時期“新古典舞”建設者們對傳統文化的執著探索。“新古典舞”創作應當正視古今之文化審美差異,認識到“舞蹈的歷史是舞蹈不可割裂的精神流變史,歷史的舞蹈在當代還值得被重新提起的理由,其實是當代舞者精神的無所歸依或靈魂的出竅走火”[1]176。不論是戚夫人的“翹袖折腰”、楊貴妃的“霓裳羽衣”,還是曹子建的“凌波微步”、李白的“歌月舞影”,對于當代人而言,真正的意義或許在于通過不同的舞蹈形態體悟歷史文化、反觀當下的精神文化。傳統與現代新的矛盾是現代化運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沖突,“適應現代世界發展趨勢而不斷革新,是現代化的本質,但成功的現代化運動不但在善于克服傳統因素對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傳統因素作為革新的助力。”[15]
“新古典舞”語言融入現代文化因素正是先行者深入傳統文化、深入現代文化,對兩者進行語言分析、取舍后,按照現代民族審美的要求成功融入現代文化因素所致。2000年以后中國“新古典舞”的語言選擇呈現現代審美影響下的多元化態勢,如《扇舞丹青》《碧雨幽蘭》《孔乙己》《我欲乘風歸去》《愛蓮說》《且看行云》《月滿春江》《濟公》《點絳唇》《麗人行》《滿江紅》《墨舞流白》《故國》《大河三彩》《西施別越》等。這些劇目題材多樣,但語言上卻不約而同地根據主題、人物形象、舞段結構所需,采取為我所用的表達方式,是“新古典舞”創作者們有意識地將“古典精神”置于當代文化語境中,闡釋民族傳統當代身體語言建構的有益實踐。
《碧雨幽蘭》《愛蓮說》《麗人行》等作品是“新古典舞”舞蹈語言的當代表達。這些作品的舞蹈語言看似自由、隨意,并不刻意追求傳統舞蹈之形,但在舞蹈中卻刻意保留并強調“圓”“流”的舒展線條,將舞蹈的身體語言和獨具匠心的服飾、道具與音樂設計合為一體,呈現至關重要的古典女性身體語言。這些“新古典舞”的身體不僅塑造了“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出淤泥而不染”的古代麗人,更舞動出現代的佳人和清新可人的女子形象。舞蹈語言再現“撐著一把油紙傘”的丁香姑娘的漫步,又或是借唐代麗人的端莊舞姿與荷塘蓮花的造型,在熟悉的動作程式中輕盈的躍起與落下,在油傘的開合中,在麗人的擰身回首與蓮女的身姿柔韌盤旋中,仿佛讓我們看到歷史畫像和文獻中“裊娜腰肢溫更柔”的倩麗與蓮步輕移的風流。這些身體語言也展現了當代女性中靈動與熱情的時尚身姿,仿佛是21世紀初升的太陽,少了一份惆悵與彷徨,多了一份現代人的自信與歡躍,更一改學界對中國“古典舞”“怨婦”似的抱胸縮肩、自怨自艾的批判。而《孔乙己》《濟公》等劇目在動作語言創造上另辟蹊徑,以幽默、輕快的動作主體,輔以生活化動作和情景性動作的“鼠竄”“醉酒”等,表現人物的生活日常與命運,動作語言的整體格調讓人耳目一新,中國傳統文化的幽默感在“新古典舞”劇目中得以展現。除此之外,“新古典舞”的現代探索一方面繼續在本體上開掘,如“昆舞”“雅樂回家”“漢代壁畫身體實踐工作坊”“俑”系列等實踐從不同側面對“新古典舞”語言進行探索和充實,呈現出舞人的自覺和反思精神;另一方面,借鑒融合武術、書法、傳統儀式等的身體語言實踐也在不斷拓展和深化中。
中國“新古典舞”的創作一方面是為了表達,另一方面是為了尋找并建構中國的舞蹈身體語言體系。因此,無論是選材、立意、結構,一切創作環節和技法都是應圍繞“新古典舞”這一核心關鍵詞展開。只有把握住這個關鍵,方能將經過選擇的、適合中國“新古典舞”發展的文化因素融入創作。在借鑒現代觀念和語言的過程中,中國“新古典舞”創作中現代因素的融入應更好地利用現代理念、創新手段與方法來傳承傳統文化。《扇舞丹青》便是成功的范例,作品中的身體語言借鑒了現代觀念的“解構與重構”以及空間的大開大合,但身體語言行云流水,氣韻綿綿不斷,充分展現了中國人從古至今對“和”的追求——小中見大、以簡勝繁、均齊和諧、對稱平衡、陰陽相合、主從有序、對比反襯,相得益彰,在動態的調節中,身體的各部分重心牽制,以保持平衡穩定,體現出“和諧”的意味。其身體語言充分表達了中國古代辯證法的辯證關系:矛盾對立之中的滲透與互補。此類優秀劇目如《書韻》《醒獅》《龍兒》等的大量產生,一方面與“李唐身韻體系”的挖掘與推廣有直接關系,表現了創作者們在動作語言體系與審美風格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再反思與再闡釋,表現“新古典舞”創作者們對民族精神的尊重、繼承與深思;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創作者們對現代元素和現代觀念“為我所用”的創造性借鑒與發展。
(二)審美風格的單一與多元
“風格是藝術的精魂和個性體現,舞蹈的風格又蘊含在語言體系、語言形態、語言的文化屬性之中,構成藝術形式。”[2]126藝術家由于所處的時代不同,藝術作品亦必然帶著時代的風尚。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人的審美意趣也在不斷轉變,中國“新古典舞”的審美由探索時期的單一嘗試,逐漸隨時代而變,在繼承中不斷突破審美局限,賦予“古典精神”現代審美意味,尤其是在大量以女性為主要表達對象的“新古典舞”劇目中,不同時期女性審美的變化或可以鏡鑒“新古典舞”審美風格的單一與多元。
“在中國古典舞創建之時,我們的目標是要‘創建現實主義的舞劇藝術’,因而在路徑選擇上必然‘關注中國舞蹈現實主義的傳統’。”[1]4“新古典舞”創作和審美也秉承這一原則,尤其是在第一個歷史分期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男女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不愛紅裝愛武裝”,幾乎所有女性都迷戀綠軍裝、藍工裝。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人和“建設者”,人們對女性的審美趨于中性。20世紀50年代的“新古典舞”中,被廣為認同的女性審美是《小刀會》中英勇無畏、熱情高漲鬧革命的周秀英;60年代是《紅色娘子軍》中的共產主義戰士吳清華。即使在1976—1989年“多維視角審視與民族精神塑造”這一分期的早期“新古典舞”劇目中,愛情題材的表達仍較為隱晦,甚至被忽略,愛情和憂思讓位于宏大敘事和民族精神的追求。如《新婚別》中,編導用翻身、急速旋轉、跳躍、連續的跪步行走揭示女主人公內心的痛苦和擔憂;用跪、拜來表現男主人公內心的掙扎。男女主人公之間的不舍與依戀還被“物化”在服飾和道具運用上:一方面新婚夫妻分離的痛苦在舞袖與舞劍中綿延;另一方面用舞袖與舞劍斬斷兒女情長。女性的舞蹈語言同這一時期的民族精神建構和英雄崇拜呼應,是中性的,是陽剛、堅毅的,是帶著革命力量型的審美形象,對于“封、資、修”的批判使女性溫柔、嬌媚與陰柔的特質被富有革命氣息的鏗鏘有力的審美取代。
然而,特殊的歷史時期總是短暫的,特殊時期的女性美學追求也將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回歸到女性與生俱來的美學形態之上。20世紀80年代之后,女性的溫婉之美、陰柔之美和女兒之態在大量“新古典”劇目中得以展現。這也表現在對“女樂”審美的辯證認識上。作為中國古代舞蹈史上的一脈傳統,“女樂”是一道文化風景,也暗隱諸多滄桑,棄其“女樂誤國”的奢靡,取其陰柔、嬌媚、靈動俏麗以及玉帽錦衣的瀟灑爽利,女性美的彰顯為“新古典舞”賦予無限風情、無限意味。
古代舞蹈的資源被重視、被挖掘,繼而以多元審美被表現。無論是基于“身韻”建立的“圓流周轉”的身體美學,還是由泱泱漢風中取形而來的“厚重質樸”,抑或從敦煌壁畫中挖掘的帶有異域和宗教特質的美學,都使“新古典舞”的審美由單一走向多元。這也有賴于創作者對傳統文化的動態分析,跨時代的文化“要去并行研究當代文化及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16]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舞臺上,“新古典舞”劇目中佳人翩舞其間,美姿、美意、美德并現,女子群舞《踏歌》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孫穎先生將自己50年的心血傾注其中,從動作到服裝、從音樂詞曲到舞美燈光無不自己設計。其作品既有女性的婉轉柔媚之美,舞者雙肩內斂,下頜側含的體態是二八年華的古代少女遇見心上人時的不安與羞澀,訴說著對心上人浪漫而執著的愛情期待;又有漢代的厚重質樸之美,側傾的頭、回旋的軀體、松弛自得的踏步讓人流連忘返,觀之沉醉。搭在肩頭半遮面的纖手、擺動的身體中一次次回眸的嬌羞,都訴說著“但愿與君長相守,莫作曇花一現”的柔媚。這典型的東方女性審美和表情達意是柔和、曲回,讓人迷醉、不可抗拒,全舞在令人心曠神怡的流動轉踏中使無數中外觀眾為之傾倒。審美的多元體現作品還有《相和歌》《俏花旦》《麗人行》《綠帶當風》《舞綢伎樂》《楚腰》《桃夭》等。這些“新古典舞”作品不僅展示了成熟女性的端莊柔美,還有少女的活潑天真,更有巫女的迷狂與豪放,表達了現代社會對于女性審美的多元向往。
“新古典舞”中女性審美形態的變遷折射出編導們對中國審美精神的思索和藝術轉化,“中國文化的重建的問題事實上可以歸結為中國傳統的基本價值與中心觀念在現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調整與轉化的問題。”[17]中國“新古典舞”為何在20世紀的中國重建,并且得到專業舞者的關注與大眾的歡迎,除政治因素之外,正是因為“新古典舞”建設與發展契合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需要,更進一步說,是契合了當代中國社會大眾的審美心理需求。
因此,作為中國“新古典舞”的舞蹈編導,要想在作品的審美形態上進行創新,編出既有“古”韻,又符合當代的審美需求、廣受觀眾歡迎的作品,要立足創作本體、舞蹈本體,樹立“本體意識”。一方面,需要堅守古典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土壤;另一方面,要以藝術家的智慧超前一步,將古今結合的藝術思索轉化成藝術形象。當然,對“新古典舞”從創立至今的各類身體語言的掌握更是審美把握的根本前提。
結 語
綜上所述,“新古典舞”在當代的發展中,“民族精神”“古典意蘊”“語言形式”“當代構建”“文化認同”等話題依然是永恒的熱點。“新古典舞”的創作和發展并非靜止的概念,而是在變化中將“名”與“實”的矛盾與融合統一在“新古典舞”身體語言的繼承與創造上,從自由與限制中開拓出一條古今結合之路,在藝術表達與文化自信的塑造中尋找最佳路徑,傳承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
中國“新古典舞”的創作活動同新中國一起成長,歐陽予倩、吳曉邦、戴愛蓮、唐滿城、李正一、孫穎等先輩們篳路藍縷,艱難探索“新古典舞”語言的同時,也進行著民族精神的重塑;陳維亞、張羽軍等創作者們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積極汲取傳統文化養分,回應社會現實問題。如今“新古典舞”的編導們對個體生命情感的訴求和多元文化審美的追求,使他們回歸“新古典舞”語言之源,既要海納百川,又要守正創新,尋找符合古代舞蹈語言形態的身體語言,挖掘“新古典精神”。70余年“新古典舞”的創作實踐說明:中國“新古典舞”的當代建構不是一般時間意義上的“當代”,而是背靠傳統、對應當下的“當代”。中國“新古典舞”的當代建構,不應受“古”字的限制,不是異域語言的移植與拼貼,更不是從傳統到現代的簡單遷移,而是追尋“古典精神”價值之源。這也就要求“新古典舞”創作時注意當代語境,借“古”之形,完成“借古喻今”的文化輸出,使“古典精神”深入人心。唯此,才算完成“新古典舞”的使命。
【注釋】
① “中國古典舞”和“古典精神”之關系的辯證思考,需要從人民立場和社會環境的角度認識。吳曉邦進一步論述道:“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杰出文人如屈原、司馬遷和杜甫等,都具有憂國憂民的博大胸懷,與黑暗現實拼死抗爭的偉大情操,因此,他們能夠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不惜忍受巨大的痛苦,歷盡艱辛,創造出了不朽的作品。這就是他們的古典精神。”參見:吳曉邦舞蹈文集編委會.吳曉邦舞蹈文集:第3卷[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15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