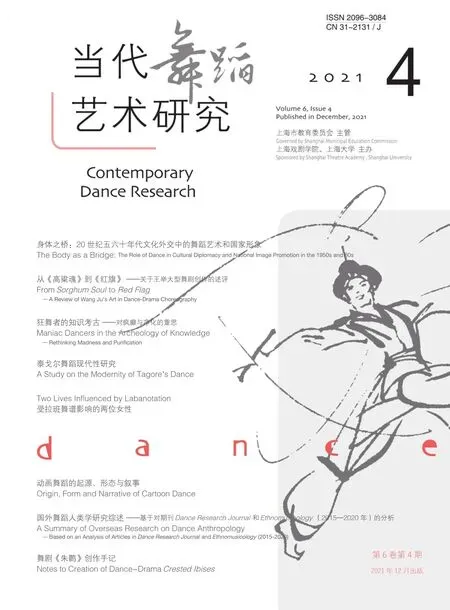舞劇《朱鹮》創作手記
佟睿睿
舞劇《朱鹮》的編創靈感,來自2010年上海世博會日本館的“心之和·技之和”主題中拯救朱鹮的故事。上海歌舞團團長陳飛華觀看后深受感染,決定將這一度瀕臨消失的美好生靈以舞劇的形式表現,于是數次帶領團隊赴陜西洋縣和日本佐渡朱鹮自然保護區采風,訪談朱鹮保護專家,收集影音資料。作為編導,我始終認為必須對創作主體有深刻的認識。為此,我深入了解朱鹮的生活環境、習性特征以及相關文化背景,不斷豐富創作積淀,以支撐長達4年的編創和排練之路。
朱鹮是世界珍稀鳥類,是吉祥和幸福的象征。從久遠的農耕時代開始,朱鹮就與人類和諧共處。步入近代,人類快速奔向現代化生活,令自然不堪重負,破壞了朱鹮繁衍所必需的藍天碧水,致使朱鹮種群在19世紀70年代瀕臨絕跡。直到1981年5月,中國科學家在陜西洋縣發現僅存的7只野生朱鹮,一度被宣告滅絕的“吉祥之鳥”才重新飛進人類視線。在人們的悉心呵護下,朱鹮種群不斷繁衍,目前全球已經超過5 000只。舞劇《朱鹮》由此觸發,通過講述跨越千年的人與朱鹮的情緣,以朱鹮的生命哀歌作為“曾經的失去”,來呼喚“永久的珍惜”,以舞蹈的身體和藝術的方式引發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關注和思考,用朱鹮舞動的羽翼呼吁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
一、角色形象:仙凡之間
(一)朱鹮/鹮仙
我認為《朱鹮》應該呈現大跨度的時間線,從農耕時代到近現代。要實現這種穿越的結構設計,朱鹮就不能只是普通的鳥類,而是要賦予其一定的神性,這樣它才能夠在不同的時空中流轉,從古代到近代,再到現代,經歷“三生三世”。因此,我將朱鹮的形象設定為具有神性的“鹮仙”,暗合中國神話傳說中的“七仙女”,也契合被發現的7只野生朱鹮。我相信當7只野生朱鹮重新出現在人們——特別是那些跋涉苦尋的愛鹮人的視野中時,其驚喜不啻看到七仙女下凡,這構成了舞劇形象設計的重要動機。朱鹮安靜內斂、敏感脆弱,給人以神秘感,還被奉為“圣鳥”“神鳥”。從美麗卻瀕臨滅絕的鳥,到中國傳統神話的“仙”,再到具有穿越性的“神”,朱鹮的形象就有了多重性格。
(二)樵夫/愛鹮人
如果說朱鹮是通過“鹮”和“仙”的形象設計來使其滿足時間大跨度的需要,那么,我們應該設計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才能使其與“鹮仙”對應呢?找來找去,最后找到最符合“農耕時代”的人物——“樵夫”。
樵夫的“普通”與鹮仙的“神性”構成差異性,樵夫的身份特質又能夠使其更自然地與鹮仙一起實現穿越,成為“愛鹮人”。為了實現從“鹮的世界”到“鹮的毀滅”的強烈對比,我們也考慮過其他人物角色,比如僧侶等,但發現這些角色局限性較大,同鹮仙的故事發展有一定的割裂。鹮仙和樵夫沒有處理成男女相愛的關系。農耕時代,樵夫是很平凡的角色,本身就有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他進山砍柴,與正在水邊嬉戲的鹮仙們相遇,人與鹮仙相偎相依的動情“雙人舞”主要是展示人與自然的和諧之景,在舞蹈設計上則盡量避免令觀眾將其理解為樵夫與鹮仙相互傾訴彼此愛意的“男女之戀”。這種相互依偎的情感更應是人類對朱鹮、對自然、對世界的愛和敬畏,是超越物種的愛,是和諧共處的愛,是“天地大美”的意象化的表達。農耕時代人類還能夠將自己放置在與其他物種平等的位置上去看待和理解這些生靈,還沒有變得像現在這樣高傲自滿。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所有欣賞朱鹮、愛著朱鹮、保護朱鹮的人都是古代“樵夫”,他們自然地成為當代愛鹮人——“記者”和“老者”,或是今天其他身份的普通人。正因為具備這種身份轉換的可能,舞劇接下來發生的情景才具有合理性,角色的設計也更富有深意和層次感,“當代記者”用鏡頭記錄被惡劣生態環境吞噬的朱鹮,以及鹮仙生命的凋零,而“老者”也同朱鹮在博物館中完成最后的相見。舞劇《朱鹮》在表演時,“樵夫”“當代記者”“老者”都由同一位男演員扮演,從“樵夫”到“愛鹮人”的過渡,這種人物的設置不僅彌合了舞劇從遠古到當代時間跨越,也有人類與自然、與萬物之間亙古不變的生命聯結的意味。
二、舞劇結構:時間穿越
我之前創作的舞劇大多有強烈的情節沖突和起承轉合的敘事結構,但舞劇《朱鹮》完全不同,它分成上下兩個篇章,如果加上尾聲,也可以說分為三個篇章。《朱鹮》的時間線非常清晰,即“農耕時代”和“當代社會”,舞臺場景也在詩性的田園美景和現代惡劣的環境之間轉換,這種對比貫穿舞劇的創作主題。
“用生命的透鏡來看藝術”是我編創時對自己的要求。《朱鹮》的結構也基于一種對生命的觀照。生活在農耕時代的人們與自然、山水之間有著天然的親近,這些遠古印記自帶著“生命律動”,作為編導,我要做的是通過肢體的“韻律感”將這份生命的律動表達出來。因此,在第一幕農耕時代中,我通過“踏春行”“人鹮戀”“鹮的世界”三個重要舞段,著意展現出農耕時代人類與萬物和諧相處,悠然自得的家園景象,也將鹮仙的美、主要情節和人物關系在這一幕中呈現。
第二幕現代社會則風格突變。這種轉折是我做本劇的編導思維——以對照的方式來結構作品。舞劇中間的結構一般是圍繞著起承轉合之“轉”進行的,《朱鹮》的“轉”通過審美和風格意義上的“轉”來實現,而不是戲劇沖突。當然,這種“轉”不能脫離一定的語境。因此,正如大家看到的,第一幕青山綠水的田園景象消失后,緊接著時空轉換進入現代,舞臺的燈光和場景也隨即以灰暗的色調來暗示環境的惡化。除舞臺場景變化之外,更深層和細膩的“逆轉”發生在鹮仙和群鹮的身體形態方面,她們的動作由展翅飛舞的直立輕盈轉為脆弱無助的弓背跌倒,不同形式的奔跑以及“錯亂”的舞臺調度綜合起來,進一步表達出生態污染對朱鹮生存環境的危害。如果說舞劇的第二幕中,“朱鹮的無助”和“朱鹮之殤”讓舞臺蔓延無盡的悲涼,為喚起觀眾對朱鹮命運的反思進行了情緒鋪墊,那么,一切的情感以及人鹮“和諧之美”的撕裂最終在“朱鹮之死”中達到高潮(或反高潮)。也正是循著“對照式結構”更深入地推進,才設計出“朱鹮之死”的舞段。
我特別希望觀眾能將“朱鹮之死”與第一幕的舞蹈以“比照”的方式進行觀看,體會舞劇的大結構。當最后一只朱鹮在憂傷的大提琴伴奏中以“花幫步”出場,這只瀕死的“鹮仙”如泣如訴的獨舞便是朱鹮生命凋零前的最終表達,它的死亡及其代表的物種瀕危與第一幕在湖畔展臂拂波、極具生命活力的“群鹮之舞”構成強烈的反差,我相信觀眾應該能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舞者身體呈現出的極致的美好和極致的悲傷。當鹮仙奄奄一息倒地、俯身垂首,用盡最后的力氣抖動它的羽翼時,已不再需要編導去做過多的陳述和修飾,讓這種“毀滅式”的唯美動態結束舞段,讓悲痛的哀鳴回蕩在天地之間吧。我想,這一舞段與《天鵝之死》具有同等的藝術感召力,也只有當觀眾看到了“朱鹮之死”的舞段時,舞劇《朱鹮》才是完整的。
舞劇最后的篇章發生在“博物館”中,這一場景是我在最初考慮結構時就已經確定下來的。人類不乏死的歷史,一部分存在于博物館中,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我時常思考,我們的許多“文化遺產”,是否最后也只能在博物館中才能尋找到它們曾經存在的證明?如果不受保護,朱鹮可能會是這種命運。正是這些思考,讓“博物館”篇章在創作過程中自然地流淌了出來。在舞美方面,起初創作團隊設計了一個寫實的博物館場景,但我認為舞劇中的“博物館”并不需要寫實,也不需要復雜的舞臺裝置和布景,它應該呈現出一種意境。舞劇創作本來就要以舞寫意。所以,“博物館”篇章最后呈現出一種具有意象性和哲思性的符號——舞臺上空緩緩降下一個玻璃罩,將朱潔凈扮演的鹮仙罩進去,朱鹮成為承載生命記憶的“標本”。
“博物館”篇章,“朱鹮的展覽”舞段我曾嘗試過三種版本,版本之一是教師帶著學生來博物館參觀,在展柜前看到了朱鹮的標本。但最終我還是推翻了這一構想,因為“感化”遠比“教化”更能沁入人心。所以,“朱鹮的展覽”只有學生出場,他們和白發蒼蒼的老者/“愛鹮人”在同一空間相遇,朱鹮美的印記留在老者“環臂羽冠”的舞蹈化講述中,其中一位女學生在離開時擺出同“鹮仙”一樣的“環臂羽冠”造型,記憶的傳承和對生命的期盼在這一刻十分動人心弦。當所有人離去,白發蒼蒼的“愛鹮人”凝視著玻璃罩中靜止的鹮仙,將那枚象征生命之美的“鹮羽”——貫穿于兩幕中的信物歸還于鹮仙,將人鹮的情緣再續。因此,舞劇的結尾,我們才能夠重新回到伊甸園般的場景,24只朱鹮再次閑庭信步,款款而來,重新鼓起雙翼,迎來了本屬于朱鹮的天空和世界。
舞劇《朱鹮》正是得益于穿越和對照的結構,才在“古代、近代、現代”的時間維度中自然地承載了“美的和諧、美的毀滅、美的再生”。它無須講述具體復雜的故事,也不必寄身于情節沖突,它以舞蹈化、心理化的敘述方式,通過舞蹈的身體和東方意蘊引發深刻的反思,喚起觀眾的情感,從而認真思考人與自然、人與其他物種之間休戚與共的關系。
三、舞蹈語言:回歸本質
《朱鹮》是我在舞劇《南京1937》《水月洛神》創作之后向藝術本質和舞蹈本質的一次回歸。舞蹈的本質是編舞,身體是舞蹈唯一的媒介,因而在創作中最強調的就是藝術形象的塑造,它要求編導回到身體本身,而非過度考慮敘事和人物關系。《朱鹮》的一切表演都建立在對朱鹮藝術形象的認知上。因此,必須要凝練出屬于朱鹮的典型化和理想化的舞蹈語言,通過肢體將朱鹮的優雅、高貴,東方的矜持、含蓄,以及朱鹮的命運融入主題動作中。
以鳥類形態作為舞蹈的表現對象在舞蹈作品中并不鮮見。《天鵝湖》和《天鵝之死》在成為西方芭蕾史上永恒經典的同時,也創作出了“天鵝”的形象和動作語言符號,楊麗萍的《雀之靈》更是塑造出了家喻戶曉的藝術形象,在這些經典劇目的基礎上,再創作出能夠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和嶄新獨特的舞蹈語言其實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而且大眾對朱鹮太陌生了,它不像天鵝或孔雀那樣為人熟知,這些細節都給當初的編舞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但三赴日本巡演80場并受邀赴美國演出后,西方媒體紛紛稱贊《朱鹮》是“東方《天鵝湖》”,一定程度上說明朱鹮的舞蹈語言是成功的。
舞劇需要高度凝練出一個極致的藝術形象,使觀眾觀看時能接受角色的動作語言及其烘托的意境,并在其后還能回想起這一藝術形象,念念不忘。我創作中邁出的最為核心且首要的一步,是通過靜態的、具有“雕塑感”的身體造型確立“朱鹮”的身份。中國郵政在20世紀80年代發行的一套三枚的“朱鹮”主題郵票激發了我的靈感,在此基礎上,我提煉了“棲”“涉”“翔”等動作元素,最后凝練出了朱鹮這一“東方之鳥”最具代表性的造型——“環臂羽冠”,這也成為“雕塑感”和靜態造型的重要符號。然后我們集中精力糅合朱鹮的特性,根據它的動作特點,捕捉其腿部動作和脖頸形態。朱鹮的形象塑造和舞蹈語言的凝練是不斷重復的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我始終堅持的一點,就是不被任何一種風格或者表演模式框定。
“環臂羽冠”是舞劇《朱鹮》最重要的主題造型,它需要舞蹈演員充分地打開胸腰和肩胛,左手向后環頭遮額,右手下垂輕點于腰間,微微抬起下頜,全身的力量都匯集于雙臂折翅時肘間的內夾,然后再向上拎起,通過“背肩”強調側面造型的立體感與朱鹮的靈動,體現出朱鹮高貴、典雅、內斂的氣質。“環臂羽冠”不斷出現在舞劇中,開篇和結尾處24只朱鹮就以這一雕塑般的姿態排成一列,沿著底幕款款走來,展開“鹮的世界”的同時,從“人”幻化為“鹮”,又從“鹮”幻化為“仙”,這是舞劇中非常重要的畫面。應2021年央視春晚的邀請,舞蹈《朱鹮》同億萬觀眾見面,就選擇了這一畫面,群鹮精致細膩、矜持柔婉的造型及舞步將朱鹮的美呈現到極致,通過寧靜和諧的“一字線”調度向觀眾傳遞“鹮的世界”。玻璃罩中成為“標本”的朱鹮也以“環臂羽冠”造型來匯聚視覺焦點。
“靈動感”是塑造朱鹮獨特身體語言的另一特點,以手臂閃爍般輕顫、演員指尖與頭部不經意抖動以及手臂瞬間的肌肉聯動“傳遞”來表現,小而脆的發力急切又短促。觀眾在這種身體語言中感受到朱鹮的警覺和脆弱,這些動作細節其實也是對朱鹮內在特性的一種外化。朱鹮生性敏感,我們去日本佐渡采風時,見到稻田中的野生朱鹮,即便離得很遠,也要小心翼翼,生怕驚擾到它。聽解說員說,曾經有一只朱鹮因為游客說話的聲音太大,竟一頭撞向玻璃墻以死抗議。朱鹮對生存環境要求的苛刻,對周圍環境的極度敏感反倒為我們提供了創作靈感。所以,在群鹮“水邊嬉戲”的場景中,其中一組動作設計的是群鹮雙手交叉于胸前表現自我呵護,指尖持續地閃爍微顫配合頭部短促的運動變化之后瞬間靜止,表現其敏感的性格特質。這些細微的身體動作同樣是情感的延續,讓觀眾感受到“粉紅色精靈”的敏感、靈動與夢幻。
群鹮舞蹈語言的內在動律中還有“傾斜感”,即身體向前而并非直立的狀態,氣息的流動帶領身體的延展和舞姿的連接,由隱而顯。與此同時,我還將“傾斜感”與大量豐富的舞臺調度來展示“飛翔”,構建“人鹮和諧”的意境。舞劇第一幕為群鹮設計了持續不斷的大幅度的調度推動情感結構的發展,長達13分鐘,不斷激發觀眾的視覺。上半場的結尾處,還有9對鹮與人的“雙人舞”依次流動穿插,表現農耕時期人們與各自的鹮仙共舞。“傾斜感”形成的調度使觀眾感受到虛實相生、延綿不斷的舞臺空間,朱鹮美好靈動的生命特質在舞臺上飛翔涌動、傾瀉而出。
四、審美追求:東方意蘊
中國本土藝術需要古典美學的藝術意象,中國舞劇同樣要捕捉這種東方美感和中國氣質,無論是情境的營造還是東方身體美學的表達,落實到舞臺表現上就在于“曲線”的深意,以及“非重心”的身體前傾形成的弧線,從而共同營造圓美流轉的“象外之象”。舞者上身雖保持直立,在行走和奔跑時交替踮立腳尖,呈現朱鹮修長的體態,但不同于芭蕾審美規范下的“開、繃、直、立”,它的身體意象及審美應是東方意蘊的表達。為了能讓觀眾感受朱鹮形象的東方美,在抓住朱鹮典型動作形態的基礎上,通過屈肘、夾背等動作元素強化舞者的身體曲線;調度上使用了大量弧線而非類似芭蕾中對稱的直線,強化圓融之美和流動之美。朱鹮角色形態的具象轉化為抽象的藝術語言,延展出了氣韻綿延的動態舞臺空間,營造了富有深意的意境空間,使觀者仿佛置身于群鹮環繞的仙境之中。
我經常同舒巧老師討論,舞劇編創中非常重要的是舞蹈的“多義性”和“延展性”,它體現在作品的藝術意味和氛圍中,這其實是中國美學對中國舞劇創作的一個追問,而這恰恰是作為編創者需要提供給觀眾的。通過對舞臺表演意境的創設,觸發觀者的移情和想象,使觀者被激發出的審美意象主動地填補留白空間。虛實相生,無畫處皆妙境,舞臺上留白空間的審美表達就是為了喚起觀眾的情感體驗。朱鹮的舞蹈語言一定是有著寫實性的、是形似的,但同時更是寫意的,是神與意的外化。所謂的“意”,就是弦外之音,是可以被深挖的情感,它需要深長的感興意味。如此,才能使觀眾在簡單的舞劇情節之外體會到情感的復雜性和不平凡的身體,以及人們對生命的思考。
舞劇《朱鹮》的東方審美意蘊還體現在音樂、服裝設計和舞臺布景上。首先,整部舞劇的音樂不僅包含中國民族音樂的風格,還伴有管弦樂的配器,其中上半場琵琶和簫演奏的主題,其音色使舞劇在意蘊的表達上更具東方悠遠委婉的特質,下半場的大提琴與管弦樂的交響,使舞劇的表達更具有時間和空間感。其次,在服裝上也能看出我們的巧思。反復推翻設計后,舞劇創作團隊尋找到了一種特殊的顏色,我們將這種抒情、唯美而傷感的顏色稱為“朱鹮粉”,并將它滲透暈染在演員們的白紗拖尾短裙上,就是這一點“朱鹮粉”的鮮麗使世間所有生靈的生命變得鮮活。每位舞蹈演員的服裝也都獨立制作,甚至每一條舞裙的長短和結構都是不同的,因為每一只朱鹮的生命都是唯一的。西方舞蹈評論家對《朱鹮》的服裝設計給予了高度的贊揚,他們稱這是“會飛翔的布料”。再次,舞臺布景和燈光設計也使舞劇整體營造出猶如中國山水畫和花鳥畫般的意境美,大部分舞段還刻意采用了較為單一的色調,為舞臺呈現出充分的留白空間。整體以東方美學的意境和中國傳統審美基調講述著關于生命、回憶和朱鹮命運的故事。
我始終認為,編導在處理題材時一定要站在文化的角度考慮,無論是舞劇《朱鹮》還是其他作品,都要折射出清晰的屬于人類的共同話題,那就是去追求一種生命原初本性中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和最高境界。只有不斷沿著對這一主題的深入思辨,才能將中國舞劇創作推向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文化平臺。《朱鹮》就是這樣一部作品。舞劇的最后一幕,當玻璃罩緩緩降落,舞臺亮起,鹮仙成了一個真正的“標本”。我希望觀眾能透過這一畫面,看到并非僅有這一種物種消亡,還有很多物種的生命都曾因為人類的忽視而逝去,舞蹈創作也需要通過觀者的審美想象引申出更深刻的意涵。《朱鹮》達到了這樣的效果。
上海歌舞團有一群非常出色的演員,在排練和演出中極為投入,尤其是主演朱潔靜和王佳俊帶來了幾近世界級的表演。演員們不僅出色地完成了角色塑造,更讓肢體觸碰到了朱鹮的靈魂。我被他們的表演深深感動。最令人欣慰的是,許多觀眾一如八年前的我,因舞劇而結識朱鹮,愛上朱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