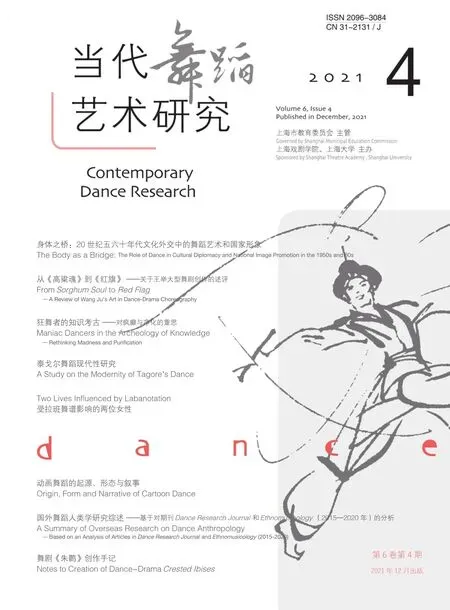中國民族民間舞創作的當代話語表達
——第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評獎述評
毛雅琛
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濟南市人民政府、中國舞蹈家協會、山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中共濟南市委宣傳部、中國文聯舞蹈藝術中心、山東省舞蹈家協會承辦,濟南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濟南市舞蹈家協會協辦的第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評獎的終評環節,于2021年10月25—27日在山東濟南隆重舉行。
自2021年5月中國舞蹈家協會發布《第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評獎通知》后,共有來自全國3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國舞協團體會員單位和5個中直院團以及10個新文藝群體、個人共328個作品報名參評。經過嚴格的初評、復評環節,共有43個作品脫穎而出,入圍終評,最終《陽光下的麥蓋提》《姥姥的田》《浪漫草原》《柔情似水》《瑤山夜語》《移山》6部作品獲得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獎。
從此次評獎的終評作品分析來看,在作品涉及的民族屬性層面,共有漢族、藏族、蒙古族、朝鮮族、黎族、苗族、哈尼族、壯族、傈僳族、羌族、拉祜族等17個不同民族的舞蹈作品,反映出我國民族舞蹈文化的多樣性,以及當下民族民間舞創作對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深度關注與表達,其中漢族、藏族、蒙古族的舞蹈作品集中,達到了半數以上。在演出單位層面,由各院校選送或聯合選送的作品達28個,可見院校已經成為民族民間舞蹈創演的主要陣地。在舞蹈形式層面,群舞作品共有35個之多,且6個獲獎作品皆為群舞,占據著絕對優勢。在題材與內容的選擇上,既有展現新時代農、牧民現實生活的《陽光下的麥蓋提》《浪漫草原》《姥姥的田》《山歌》,也有注重審美意象傳達的《柔情似水》《雨形》,更有對民族文化、民俗風情的挖掘與描摹,例如展現土瑤風俗的《瑤山夜語》、再現神話傳說的《移山》,以及以“粵繡”文化為依托的《粵繡悅美》和“羌繡”文化為依托的《云上》。
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當下,“荷花獎”作為業內唯一具有權威性和導向性,標志著中國專業舞蹈藝術最高成就的專家獎,從其發布的評獎通知不僅可看出對民族民間舞創作的導向,在不足百字的作品要求中,“創新性”出現了兩次,也足以說明組委會對于“創新”的重視和強調。在三場精彩紛呈的終評演出中,也的確顯現出民族民間舞創作在題材、主題、內容、形式等各個層面的創新。10月27日第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蹈發展研討會“‘互聯網+’下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及傳承策略”如期舉辦,數十位業內專家針對議題結合評獎中的參賽劇目進行了深入探討。
在評獎演出及研討會的背后,還關涉著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多個向度的現狀與問題。例如:民族民間舞的創新性發展、融媒體時代下民族民間舞的創作與傳承,以及民族民間舞創作對傳統素材的挖掘、對當代生活的表達、對傳統與當代的把握、對民族民間舞教學的反饋、對民族民間舞學科建構的遠期影響,等等。在傳承中創新、打造當代經典,一直是民族民間舞創作的追求,但是傳承與創新、傳統與當代的取舍與平衡并非單一維度的問題,還涉及作品內涵與外延的方方面面。透過此次“荷花獎”的參賽作品,可以看到民族民間舞創作在不同維度上的當代話語表達。
一、民間文化的“深扎”
談到此屆“荷花獎”民族民間舞創作的源起,就不得不提中國舞協主辦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簡稱“深扎”)的創作采風活動,感動編導的常常是那個地域的人們所獨有的生命狀態以及對于生活的獨特感悟,用舞蹈家協會主席馮雙白先生的話來說,“好作品需要的是人文的眼睛和心靈的感應”。《陽光下的麥蓋提》《年輪》等作品皆是“深扎”后的創作產物。令全場沸騰的《陽光下的麥蓋提》幾乎是毫無懸念地獲得了此次評獎的最高分。這部由新疆藝術學院舞蹈學院選送的作品,是編導在2021年3月跟隨中國舞蹈家協會、新疆舞蹈家協會赴南疆參加“深扎”采風創作活動時獲得的靈感。在刀郎之鄉麥蓋提縣,編導被一群席地而坐的老人深深吸引,在熱烈的舞者旁,老人們打著手鼓、唱著歌沉醉在歌舞的世界里忘乎所以,強烈的陽光灑向老人,照在他們仰起的臉上,還有瞇起的眼睛和白色的胡須上……靈魂與陽光相通的老人感動了編導,編導又通過作品把感動傳遞給了每一位觀者。在這段時長7分30秒的男子群舞中,既有完整的結構、清晰的層次,又有明確的時空關系和宏大的時代主題。當領舞者伸開雙臂沐浴著燦爛的陽光緩緩起舞時,當21位帥氣的維吾爾族小伙子伴著高亢的歌聲盡情舞蹈時,當山東鼓子秧歌的元素幾乎天衣無縫地嵌合進維吾爾族的舞蹈語言中時,刀郎舞獨特的身體韻律加之舞者由心而發的濃烈情感,在那一刻傾瀉而出,瞬間席卷了整個劇場。領舞者仿佛就是那位唱到忘情的老者,背景音樂就是他的歌聲,他時而深情地凝望舞群,時而融入舞群不分彼此,群舞部分時而像發生在老者眼前的生動畫面,時而又像是老人波瀾起伏的內心獨白。雖然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作品演出的第三場評獎并沒有現場觀眾,但依然讓在場的眾多評委和工作人員被感動得落淚,并打出了98.50分的全場最高分,兩位點評嘉賓甚至用了13分鐘的時間單獨點評這部由心而發、向心而行的舞蹈佳作。
同樣源于“深扎”的作品還有四川音樂學院舞蹈學院的《年輪》,編導的創作靈感來自廣西壯族一個村落中大榕樹下的歌舞——2019年他參加中國舞協的“深扎”時,跟隨著老藝人走了很久的山路,來到一片開闊的場地,但令他意外的是藝人們并未選擇在開闊的場子起舞,而是來到一棵巨大的榕樹下,在樹蔭里唱起了古老的歌謠,平日里,村民們也會來到大樹下祈福……所有參加采風的人聚集在太陽暴曬的場子看著藝人們在樹下的歌舞。這一畫面和這個民族對于樹的眷戀與深情就在那一刻打動了編導,村民們在大樹下的生命狀態映射著他們所有的情懷。那棵帶給創作者無限靈感的榕樹最終幻化成高懸于舞臺正中、枝繁葉茂的巨大樹冠,燈光從樹冠上投射下的斑駁光影,為作品營造出了獨特的空間關系和環境場域。環繞在樹下的群舞,始終以地面空間的壯族舞蹈語言來呈現,雖有向上生長的動勢卻鮮少出現直立的動態,兩位領舞者則一直維持著環形的調度,時而奔跑、時而安靜,極具隱喻性的動作語言似乎象征著時間、陰陽、日月、天地、圖騰……始終圍繞著大樹和樹下的人們,見證著整個民族的繁衍生息。承載著生命的大樹是向上生長的,人們在樹下的日子是向下扎根的,樹下的人們既像樹根又像土壤,滋養著大樹,大樹則回饋給人們以清涼和庇佑,落葉歸根終又化為土壤,在生命的輪回中生生不息。
對于民族民間舞的創作而言,想要保持風格的純正,就要不斷地返回民間。在《年輪》的編導楊暢看來,雖然15天的“深扎”時間無法深刻地了解一個民族,更多的是個人對這個地域或文化的理解和感受,但這個感受卻非常重要,可能正是源自這個民族細微而幽深的動人之處,也正是這些感受提供給編導以創作方向。一如上述兩個來自“深扎”的作品,源于民間、扎根人民,以人民的身份起舞,舞的是人民的心聲,被人民感動,又反過來感動人民。
二、民間審美的意象創新
民族民間舞創作的創新性發展既包含內涵層面的創新又包含形式層面的創新,在此次“荷花獎”的評獎活動中,有些作品雖然是傳統的題材、傳統的動作語言和傳統的舞臺調度,但在審美意象的層面卻給觀者帶來全新的體驗,既有《花語》中的人生如花之境,又有《雨形》中的上善若水之境……作為中國傳統美學的核心概念,所謂“意象”亦是情景交融,正如朱光潛先生在《論美》一書中的開場白:“美感的世界純粹是意象的世界,超乎利害關系的世界”[1]。
在此次評獎中,最具美感的作品可能就是《柔情似水》了。這部由四川藝術職業學院選送的女子群舞正如它的名字,在視覺與聽覺的雙重維度呈現出柔情似水的整體質感。作品以瀘沽湖邊摩梭人的“甲搓舞”為動作元素,以當地民謠“夜歌”為音樂元素,在甲搓舞的傳統調度上延展、流動,沒有具體的人物和情節,甚至沒有強烈的情感起伏,始終如水般溫潤柔軟,卻給人以強烈的美的感受。那么,這種“美”從何而來?用黑格爾的話說,“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2]。在休謨看來,美“只存在于觀賞者的心里,每一個人心見出一種不同的美”[3]。而《柔情似水》的美更接近于中國傳統美學的回答——“美”在意象。冰藍的色調、空靈的音樂、精致而又講究的動作編織,共同傳遞出了作品不同層次的美:水的澄澈之美,女性的溫柔之美,還有內心的豐盈、祥和之美。在極簡的形式和動律中暗藏著編導深厚的創作功力,在不動聲色間便讓所有的意象如水般靜靜流淌,圣潔、高貴,沁人心脾。
而另一部讓人回味無窮的作品當屬北京舞蹈學院選送的《雨形》,作品從醞釀、排練到最終呈現,足足用了兩年的時間。因為長鼓的聲音在傳統意象中代表著雨的聲音,所以作品名為《雨形》,加上象征雷聲的小鑼、象征風聲的大鑼和形似云的圓鼓,共同構成了自然中雨、雷、風、云的意象。編導池咚咚在韓國留學時看到的導師表演時的照片是他創作的最初靈感,也構成了作品的基礎形態:右手鼓槌向上、左手鼓槌向下,分別代表著陰與陽,以溝通天地。而在動態層面,編導選取了甲骨文的“雨”字作為舞者的身體形態,加之朝鮮族舞蹈本身的呼吸動律,形成了作品的基本動律,雨的不同形態與聲響以及編導心中的雨,最終幻化出了舞臺上的《雨形》。舞蹈的動態,長短的構成,服裝的選擇,都極其用心,編導個人對傳統文化的解讀也最終成就了《雨形》難以言說的高級質感。無論是形態、動作,還是色調、意境……都流露出中國傳統美學的獨特意味,仿佛與天地勾連,與自然互通。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間審美的意象創新中,道具常常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民族民間舞的創作而言,道具多為樂器、用具、裝飾或象征之用,例如《果沃情》中的琴,《歡騰的高原》中的熱巴鼓,《雨形》中的朝鮮鼓,《生生回響》中的碗、筷、青苗,以及《花語》《鷴》中不同質感的扇等道具,都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為作品的整體表達增色不少。而此次評獎中還有一些作品的道具使用并未局限于此,例如《瑤山夜語》《姥姥的田》《秋熟》《一條大河》等,其道具直接參與舞蹈的本體表達并被編導賦予了多重的表意功能,道具與舞蹈動作相得益彰的配合,使民族民間舞小作品的意象營造能力進一步強化和延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瑤山夜語》,這部由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平桂區文化廣電和旅游局、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群眾藝術館選送的作品有著鮮明的地域屬性,編導以瑤族中人口最少、僅廣西賀州才有的一個支系——土瑤古老而獨特的婚戀習俗為創作依據,以“情人房”為作品展開的核心線索,無論是動作設計、結構層次還是道具使用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土瑤少女情竇初開之時,父母會在家旁搭建小木屋,并在這里開啟一生中最為甜蜜的愛情世界,所以小木屋又被稱為“情人房”。作品以少女從群舞組成的情人房中醒來為切入點,道具竹竿所傳達的不同意象貫穿作品始終,時而是登高的梯子,時而是表達愛意的傳聲筒,時而又成為戀人相會的獨木橋……巨大的竹竿在群舞演員的手中翻轉、搖擺,不僅營造出作品的不同時空,更成為舞蹈本體表達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延展了舞臺的立體空間,甚至產生了“高空威亞”的視覺效果。而竹竿的助力也使雙人舞的動作編排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男主角手撐竹竿用雙腳掛著女主角在空中搖擺的瞬間,讓人耳目一新、過目難忘。作品首尾呼應,以戀人相聚于情人房中結尾。道具與瑤族舞蹈語言的巧妙融合,展現了賀州土瑤古樸神秘的民俗風情和土瑤青年純粹而真摯的動人情感。
以道具使用而令觀者記憶猶新的還有來自南京藝術學院舞蹈學院的《秋熟》。編導關健的創作靈感來自吳曉邦先生的同名畫作,以江蘇的民間舞蹈“蓮湘”為主要素材,并對“蓮湘”的傳統道具進行了全面改造,不僅有多種形態且代表著多重意象,實現了道具從線到面的延展與轉換。由“棍”形展開的金色扇面成為整部作品的點睛之筆,既升華了主題,更營造出了“秋熟”的核心意象,為觀者帶來了全新的視效呈現。同樣賦予傳統道具以新意的還有浙江音樂學院的《一條大河》,作品以安徽花鼓燈為基礎素材,通過群舞的身體動態、隊形調度,尤其是對傳統道具——扇子的創造性使用,營造出水的流動之感和大河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感。道具的多義使用在推動情節、表達情感、營造意境的同時參與舞蹈的本體表達,帶有鮮明的民族和文化屬性。
三、既有“文本”的創造性轉化
作為此屆“荷花獎”評獎的東道主,山東本地的民族民間舞創作備受矚目,其中既有與時俱進的《在你身邊》,又有原汁原味的《貨郎小小俊翠花》,特別是《濟南的冬天》《移山》《板兒一響當哩個當》等作品對既有“文本”如散文、神話傳說、油畫、山東快書等的創造性轉化,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山東藝術學院舞蹈學院選送的男子群舞《移山》,其創作靈感源自徐悲鴻的油畫作品《愚公移山》。作為《列子·湯問》中家喻戶曉的神話傳說,“愚公移山”的故事早已成為中國人固有的文化記憶與典型符號,而油畫作品所呈現出的視覺畫面也早已深入人心。對于民族民間舞的小作品而言,要進行怎樣的轉化與發展才能讓人耳目一新呢?編導并沒有復刻油畫的樣貌,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油畫的質感,并沒有講述愚公移山的故事,甚至沒有設置具體的人物,卻通過移山者的群像將持之以恒、移山不移志的精神內核表達得淋漓盡致。作品以山東鼓子秧歌為基礎元素,保留鼓子秧歌“穩、沉、抻、韌”的動律特征,結構的設置與主題動作的選擇簡約而考究,移山者仿佛從遠古走來,但他們堅韌的內心似乎能穿越時空與觀者相通,在不斷重復、加強的“揮鎬”動態中凸顯了“移山”的意義感和歷史的厚重感,更使作品充滿了雋永的藝術張力和“恒道”的哲學意味。
山東藝術學院的另一部作品《濟南的冬天》取材于老舍先生的同名散文,同時融入了編導對濟南冬天的獨特感受。如何用動態化的舞蹈語言表達“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之境是創作的難點,編導以海陽秧歌的動律為基礎,運用其中的“裹擰”展現人在寒冷時的身體動態和孩童的純真質樸,“小房子”的道具實現了舞臺時空及想象與現實的分割,并透過孩子的視角和雪中的嬉戲完成了對冬的描摹,冬天體感上的寒冷與老城濟南帶給人內心的溫暖形成鮮明對比,也由此完成了對濟南之冬由“溫晴”到“溫情”的意象營造。與其說這是舞蹈版的散文詩,不如說是編導與老舍先生在濟南冬天的一次美好邂逅。
而山東青年政治學院舞蹈學院、濟南市歌舞劇院的《板兒一響當哩個當》將看似毫不相關的山東快書與舞蹈巧妙相融,營造出山東快書舞動起來的樣子,說書人和快書中耳熟能詳的故事瞬間都鮮活起來了,且毫無違和感。對“文本”或“前文本”的創造性轉化,加之編導對文本的再闡釋,讓民族民間舞的創作既有濃郁的地域風情,又有匠心獨運的當代表達。
四、當下生活的多性化表達
相較于此前的“荷花獎”評獎,本次參評作品接近“非遺”樣貌的傳統創作大幅縮減,只有《歡騰的高原》《貨郎小小俊翠花》《果沃情》等;與此同時,對于現實生活的深切關注成為此次評獎的一個顯著特點,《浪漫草原》《三個老阿佳》《深山里的女高阿媽》《山歌》《姥姥的田》《再唱山歌》《尕娃踏浪歸》《在你身邊》《父親的馬絆》等作品皆是對當下生活的觀察、思考與展現。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當深山里的古老民族也開始民族服裝與運動鞋混搭、民族舞蹈與“抖音”舞蹈并存之時,民族民間舞蹈的創作也出現了顯見的變化。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地道的民族舞?又如何在不斷變化之中守護民族文化的精神與內核?這些是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重點與難點,編導們也在各自的思考中做著不同的探索與嘗試。
如果要在上述現實題材的舞蹈創作中選擇一個最為輕松、幽默的作品,一定非《浪漫草原》莫屬。這部由呼和浩特民族演藝集團、民族歌舞劇院有限公司選送的作品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不到7分鐘的時間里囊括了極其豐富的內容,仿佛一部微縮的小型舞劇,有人物、有細節、有布景、有愛情、有生活,還有完整的起承轉合。在民族民間舞的小作品創作中,編導并沒有止步于簡單的情節和情緒的展現,而是深度挖掘當代生活的點滴細節,在傳統的蒙古族舞蹈語言和音樂中融入現代元素,使其更加契合新時代牧民自然、本真的當下狀態,讓濃郁的生活氣息在舞臺上鋪陳、流轉,仿佛就是你我的日常。同時,作品也呈現出“90后”編導鮮明的創作路徑與風格,其中既包含著對經典劇目的致敬,也有對當下生活的關照,還有對蒙古族舞蹈傳統創作模式的顛覆。在詼諧中用心刻畫的是當代蒙古族青年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勤勞樂觀的生活現狀,以及未來可期的從容幸福。
同樣深度關照生活的作品還有長春人文學院選送的《姥姥的田》,雖然是傳統的農耕題材,且以吉林地區獨有的東北“袖頭秧歌”為動作素材,但在整體呈現上卻有著與傳統東北秧歌作品完全不同的質感,處處流露著編導對于生活的細膩感觸和對于生命的人文關懷。作品從暮年姥姥的背影切入,仿佛最后一次卻又像曾經的無數次那樣走向自己心愛的田,這就是她的天地與歸屬,在這里她似乎看到了那個豆蔻年華的自己,嬉戲、勞作、結婚、生子……編導通過倒敘、閃回等方式,通過道具草帽的一物多用,以第三方視角將姥姥平凡而又偉大的一生生動再現,擬人化的麥田就像姥姥的孩子一般,得到姥姥悉心的照料,與此同時也陪伴并見證著姥姥人生中的每一個重要的時刻,人與黑土地之間的那份“耕耘—養育—反哺”的深厚情感仿佛一幅色彩濃烈的油畫,隨著姥姥的一生徐徐展開。當姥姥的田變成火紅、金黃的豐收色彩,姥姥走向了生命的盡頭。最讓人動容的是,當姥姥離開后,后輩的年輕姑娘繼續幫姥姥照看她心愛的田,一如當年的姥姥,四季輪回,共生共舞。
上述兩個作品都是在新時代新農村建設背景下展開的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編導們以當代人的現實生活為核心表達對象,深度關照當下、挖掘素材,運用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的手法,透過平凡而又普通的小人物展現人文關懷的厚度與溫度。一段段舞蹈,一幅幅畫面,無一不是在表達創作者對這片土地、這個民族深深的熱愛與眷戀。
五、主題提煉的與時俱進
在傳承民族傳統的基礎上弘揚主旋律,進行題材的創新是此次評獎的另一個顯著特點。例如:新時代背景下以“脫貧攻堅”為核心主題的《清清甘泉水》《再唱山歌》《深山里的女高阿媽》《姥姥的田》《陽光下的麥蓋提》,以及環保主題的《牧人》,“建黨”主題的《山歌》,“抗疫”主題的《在你身邊》等,所表現的皆是當下的熱點。
其中,北京舞蹈學院的《山歌》,以濃郁、地道的藏族舞蹈語言和層層遞進的結構、調度,在舉手投足間將來自雪山之巔的藏家兒女對黨的深情款款道出。青海省演藝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清清甘泉水》作為“深扎”之后的現實題材舞蹈創作,再現“全國脫貧攻堅楷模”——青海省班彥村“易地扶貧搬遷”的事跡。云南藝術學院附屬藝術學校的《深山里的女高阿媽》以傈僳族的舞蹈語言和大量生活化的場景,生動再現了“時代楷模”“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感動中國2020年度人物”張桂梅兼具黨員、校長、教師、“媽媽”四重身份的感人事跡。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的《再唱山歌》則用藏族古老的語言和堅定的舞步,展現“扶貧致富”的宏大主題。而當《陽光下的麥蓋提》的編導看到援疆的駐村干部與當地人民相處融洽、水乳交融,且山東日照又恰巧對口支援麥蓋提時,便有了舞臺上刀郎舞與鼓子秧歌的對舞與相融。《在你身邊》則以山東鼓子秧歌和海陽秧歌為主要語言,在“抗疫”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在一線的兒子與在家中的母親兩個空間的共同呈現,展現了中華兒女共抗疫情的使命擔當和無私大愛。
當下的很多民族民間舞創作不再滿足于相對單一的情感抒發和民族風情的展示,而是緊跟當下的時代熱點與焦點。對于編導而言,想在短短幾分鐘的作品中展現濃郁的民族風情同時又包含相對完整的人物刻畫或情節線索,對于民族民間舞的小作品創作來說是不小的挑戰。雖然有些作品對于現實的挖掘還流于表面,并且民族民間舞素材與現實生活的結合也稍顯生硬與脫節,但是依然能清晰感受到作品期望以民族民間舞蹈的傳統語言觸碰、探討現實問題的訴求。
第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評獎代表著近兩年來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最高成就,同時也映射著當代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在不同層面的現狀與問題。
一是在創作素材的來源層面,不斷地返回原點,在“深扎”中深掘素材,創作出真實可感并與觀眾心意相通的民族民間舞作品,或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中長期浸潤、不斷累積,最終成就“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舞蹈佳作,都是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有益通途,但也依然存在對于民族素材走馬觀花的采風和浮光掠影的采擷等現象。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的前提首先是對傳統的深刻感知與尊重,否則很容易導致舞蹈語言屬性的混亂和對民族文化實質的偏離。
二是在當代生活的表達層面,從20世紀50年代的“深入生活”到當下的“深扎”采風,再到“現實題材”創作在數量上的大幅增加,便可清晰地看到民族民間舞蹈創作走向的變遷。變化是世界的本質,民族民間舞蹈在原生狀態下的發展、變化亦是無法規避的事實,而且對于當代生活的關注本就是當代創作的主要表達。在此次評獎中既有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的現實題材舞蹈創作,也有只停留在對于現實生活表層展現的應景之作,題材本身沒有好壞,重點在于如何應用舞蹈語言進行妥帖的當代話語表達。
三是對于傳承與創新的尺度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其中的平衡與取舍并非單一維度的簡單問題,在全球化高速發展、“國潮風”全面崛起的當下,如何與時代接軌又不失民族屬性,是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最大難點。在此次評獎中,不僅有對審美意象創新性發展、文本創造性轉化、舞蹈道具多義性使用的成功范例,也有一些作品的呈現并不盡如人意,如舞蹈語言風格和屬性的模糊,如果拋開服裝很難分清究竟是什么民族,究竟應該歸屬于什么舞種,發展與轉化的前提首先是對民族根性的堅守與傳承。需要考慮“度”的還有舞蹈中服、化、道及音樂、燈光的使用,好作品的每一處細節都應精雕細琢,彼此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然而很多時候,助力舞蹈的燈光、音樂反倒成為舞蹈表達的羈絆,要么過于隨意要么過度使用,正如評審專家在點評會上所指出的,過于濃烈的色彩、炫目的燈光及隨意拼接的音樂會帶來審美的混亂。
對于民族民間舞的創作而言,新而有度是追求更是挑戰,評獎的終極目的是促使民族民間舞蹈創作更好地發展。我們應在成就中不斷反思與前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進程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從心出發、為人民而舞,讓民族民間舞蹈成為承載中國文化的“新國潮”,用當代的民族舞蹈話語書寫中華民族的精神圖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