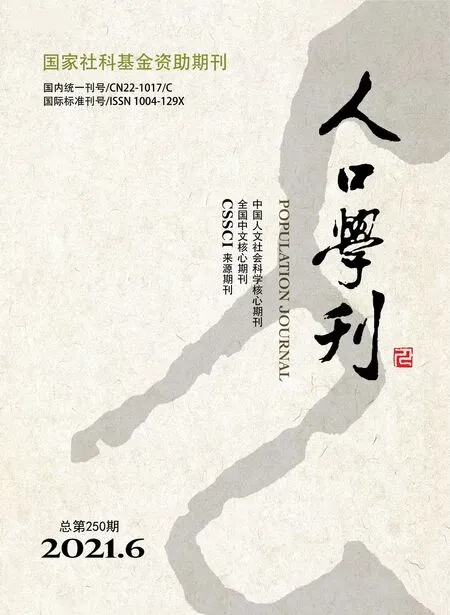教育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研究
李銘娜,回 瑩
(1.長春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2.廊坊師范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一、引言
教育是一種培養人的社會活動,任何個人的成長成才都離不開教育。無論個體的起點、基因、階層、地域的差異有多大,教育在對個體傳授知識、啟迪智慧的過程中是最為公平的一種方式。個體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積累的知識就越豐富,個體綜合能力的提升也越明顯,未來更好發展的基礎越穩固。所有個體素質和能力的提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社會效應,Heckman指出教育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1]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教育的積極作用,伴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力度也不斷加大。1993 年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的目標。與此同時,居民個人的教育觀念也在逐漸增強。根據2020年中國教育發展公告,2019年我國的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89.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51.6%。大量接受良好教育的個體顯著改善了我國勞動力供給的質量,有效滿足了經濟社會建設對各類人才的旺盛需求,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隨著個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個體的工資收入也顯著提高。教育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的方式影響勞動力的貨幣收入和物質收入。[2]岳昌君和劉士杰等學者研究發現教育能夠顯著影響勞動力的工資收入水平。[3-4]劉生龍等基于2007-2009年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分析義務教育法的實施對教育年限和教育回報率的影響,研究發現教育為中國城鎮居民帶來了約12.8%的工資回報。[5]然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個體往往具有更突出的個人能力,其高工資收入很可能是因其能力獲得的,并非完全是教育的結果①個人能力的形成與教育密切相關。但是,個體基因等先天異質性差異對個體能力存在著重要影響。教育作為個體能力培養的后天手段,對于能力的單獨作用機制和效果有待明確。。高估教育回報率很可能會夸大教育的作用,使得部分個體片面追求學歷教育,盲目推崇“學歷至上”的就業法則,形成高分低能、高學歷畢業生就業難、高學歷低工資等怪現象,進而推諉于教育質量,提出過度教育等偽命題。教育究竟能不能提高個體工資水平,是一個關系我國教育評價和個體選擇的重要命題,既需要深入的理論分析,更需要大量數據進行經驗研究。
因此,本文在教育影響個體工資收入的理論分析基礎上,利用2017 年中國流動人口調查數據,從流動人口的角度考察不同教育程度對工資收入的作用效果,以期為教育提高個體工資收入提供可靠的經驗證據。本文首先分析個體教育程度、就業類型和工資收入水平的關系,三者分別反映了教育層次結構、就業結構和工資結構。其次,基于全國流動人口調查的數據樣本分析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最后,分別研究教育對體力勞動者、混合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影響②混合勞動是指工作崗位需要相當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而非偏向于體力勞動或者腦力勞動的某一種。。研究發現教育對我國個體的工資收入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這對于肯定教育、鼓勵求學、加大教育投入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個體通過教育能較快完成自身基礎知識積累和能力的提高。而人力資本是決定個體工資收入的重要變量,因此,教育能夠對個體的工資收入產生顯著影響。人力資本是凝結在勞動力身上的具有累積性和遞增性的社會資本,[6]其主要包括體現為知識、技能等的智力要素和意志品德、能力、體力為主的非智力因素。人力資本具有知識效應、外部效應和溢出效應,能夠有效地促進勞動收入的增長和社會產出的增加。Schultz認為人力資本的知識效應是指接受過教育培訓的勞動力具有較強的經濟決策能力,在有效的資源配置中能抓住收益增加的機會,進而帶來勞動收入的增加。[6]Becker通過人力資本的成本收益函數來分析知識效應的均衡條件,其中,成本包括個體在人力資本形成過程的時間投入和產品投入兩種要素,收益主要為貨幣收入和效用收入,當邊際成本現值等于未來收益現值時,人力資本達到均衡值,個體實現人力資本收益的最大化。[7]Lucas 在《論經濟發展的機制》中闡述了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運行機理,人力資本的提高在促進產出增加的同時,也引起了社會平均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而社會平均人力資本決定了社會運作效率,企業和個人能夠從社會運作效率提升中獲取收益。[8]考慮人力資本的正外部性效應,個體不僅能夠通過教育提升自身人力資本獲益,還能夠通過社會整體人力資本提升而獲益。此外,除了正式教育外,Arrow提出“干中學”的人力資本形成觀點,強調實踐學習的重要性,并且“干中學”的知識擴散傳遞作用更加明顯,具有不同人力資本的個體間相互學習會產生更加顯著的正外部性效應,[9]進而促進勞動力生產率的提高和工資收入的增加。Romer將知識生產引入到生產函數中,指出人力資本是知識生產的重要變量,具有高水平人力資本的國家也具有高水平的知識產出,高水平的技術水平使得個體具有高水平的邊際產出和工資收入。[10]如果將教育、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工資收入視為一個符合經濟邏輯的因果鏈,那么教育就能夠顯著地提升個體的工資收入水平,這也是解釋發達國家(地區)比欠發達國家(地區)具有高水平個人收入的重要理由之一。
在連接人力資本與工資收入兩個變量時,就業類型是一個關鍵變量。毫無疑問,社會分工的存在使得不同的工作崗位需要不同人力資本水平的個體來匹配。一個個體的人力資本水平和特點基本決定了該個體的職業選擇。Lucas 將勞動力擁有的人力資本劃分為體力型人力資本、一般型人力資本和專業化人力資本,有且僅有專業化人力資本的勞動力才能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8]絕大多數成年健康個體均具有體力型人力資本,一般型人力資本需要個體接受完基礎教育,專業化人力資本則需要接受更長的專業化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使擁有專業化人力資本的個體具有加強的創新協作等能力。也就是說,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資本水平也就越高。對應于不同的人力資本類型,工作崗位可以相應地分為體力勞動、混合勞動、腦力勞動三種。其中,一般型人力資本和專業化人力資本因需要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其就業崗位以混合勞動和腦力勞動為主,體力型人力資本普遍從事的是同質性體力工作。不同類型的就業崗位對應的工資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異,普遍而言,腦力勞動的工資收入要高于混合勞動的工資收入,混合勞動的工資收入又要高于體力勞動的工資收入。這種人力資本與崗位匹配的現象在我國表現為不同的企業性質對個體就業選擇的影響,即國有企業和合資企業因工作機會稀少求職競爭激烈,有較高的人力資本門檻,普遍聘用有專業化人力資本的個體從事腦力相關工作,提供相對較高的工資收入水平;大量擁有一般型人力資本和體力型人力資本的個體則普遍在民營企業從事與體力勞動、混合勞動相關的工作。個體就業企業的性質成為識別個體人力資本水平、就業類型與工資收入水平的重要標志。方福前和武文琪指出腦力職業工作者相比非純腦力職業工作者具有明顯的工資收入優勢,其中人力資本差異是導致工資收入差異的最主要因素,能夠解釋腦力職業工作者優于非純腦力職業工作者工資收入的70%。[11]
除了理論分析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外,隨著我國在1994 年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和1995年《教育法》的頒布實施①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個體就業不再由教育部門和人事部門決定,而是可以根據自身需求自主選擇工作崗位。,國內學者對教育能夠提高個體工資收入這一命題進行了實證檢驗。賴德勝基于1995 年中國收入分配狀況調查數據分析教育對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1995 年勞動力的教育收益率為5.73%,[12]相比李實和李文彬使用相同數據、方法、指標回歸得到的1988 年的教育回報率3.8%,[13]賴德勝認為中國的體制改革促進了教育的配置能力和生產能力的改進。李春玲利用2001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使用明瑟工資方程分析教育程度對個體勞動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2001年中國的教育回報率為11.8%。李春玲指出市場經濟體制的收入分配機制基本消除了長期存在的“腦體倒掛”現象,教育收益率將不斷提高。[14]然而,姚先國和張海峰認為由于存在明顯的城市-農村二元經濟結構,中國的教育回報率可能會存在城鄉差異,他們基于2004年企業和農村勞動力流動調查數據估計的城鎮教育回報率為8%,而農村教育回報率僅為4%,城市的教育回報率明顯高于農村。[15]為了進一步研究教育回報率的城鄉差異,張車偉基于2004 年上海、浙江和福建三地的“家庭動態與財富代際流動”抽樣調查數據發現中國的教育回報率為4.34%,屬于中等教育回報率水平,但是教育回報率呈現隨收入差距擴大而變化的“馬太效應”。[16]王德文等利用2005年《中國城市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和2006 年、2007 年春季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問卷調查》,基于拓展的明瑟方程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個單位,個體工資收入增加約5.3%~6.8%,此外,個體就業類型也會影響教育回報率。[17]
考慮個體的就業類型是影響教育回報率的一個關鍵環節,將個體從事的職業引入實證方程中。姚亞文和趙衛亞基于2006 年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數據分析了教育程度、勞動力職業對工資收入的影響,使用Oaxaca 對工資分解發現勞動力從事的職業屬性能夠解釋66%的工資報酬差異。[18]謝桂華運用勞動力自我職業選擇和技能轉換教育理論分析比較了城鎮和農村流動人口的教育回報率,研究發現非農流動人口的教育回報率高于本地人口的教育回報率,而農村流動人口中的高技能勞動力在經過一定時間能與當地人口的收入持平。[19]李強研究發現教育和技能培訓等人力資本對女性人口的就業決策產生顯著影響,同時教育水平也為女性人口帶來了收入的增加。[20]葉光基于2012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現狀調查數據,研究認為忽略個體的就業選擇差異可能會導致教育回報率的估計偏誤,修正的教育回報率表明就業機會是影響個體工資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21]為探討教育和就業對收入的影響機理,全磊等利用2016年鄂粵兩省農民工家庭生計調查數據,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和非農就業對個體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22]
對上述既有文獻進行分析,發現教育對個體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上述研究多使用教育年限作為教育的單一指標,較少對個體的教育程度進行細分,尤其是沒有結合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加強對高學歷個體的工資收入進行分析。為此,我們將教育程度劃分為高中及以下學歷、大專大學學歷和研究生學歷三個層次,重點研究高等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此外,上述研究普遍忽視了就業類型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雖然全磊等從所有行業中選取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進行研究,但并沒有從人力資本類型與就業類型關聯的角度進行分析。因此,我們將不同的就業崗位劃分為體力勞動、混合勞動和腦力勞動三種,分別研究不同就業類型下的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實證過程中,考慮了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婚姻等個體因素的影響,同時將流動時長、企業性質等可能影響工資收入的因素納入模型中,盡可能減少遺漏變量導致的估計偏誤。
三、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是2017 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調查數據,該數據的調查范圍覆蓋我國31 個省、市、自治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問卷調查內容包括流動人口的個人、家庭、工作和流動等信息。文章選取16 至60 周歲具備勞動能力的流動人口作為研究對象,剔除自營經商、雇主身份、工資收入為非正值以及周工作時長不足5 小時的流動人口,以確保個體收入來源于工資收入而非其他經營所得。另外,我們還對勞動力的就業選擇進行篩選,剔除無固定職業和職業為不便分類的流動人口,最終獲得54 660個有效樣本個體。
2.模型設定
借鑒明瑟對勞動力工資收入決定方程的研究,[23]將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視為教育和多種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實證模型的表達式如下:

其中,lnw為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對數,edu為個體的受教育程度,根據高中及以下、大專大學、研究生定義設定為分類變量,X為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性別、民族等個人特征變量。β為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系數,γ為其他解釋變量的待估計系數,α為常數項,ε為隨機擾動項。
3.變量說明
對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1)。被解釋變量工資對數的均值為8.201,流動人口的平均收入為4 265.504 元①此處勞動力的平均收入為未取對數的工資均值,并非工資對數的均值8.201對應的數值。。核心解釋變量教育的均值為0.314②這里為了分析方便,暫時將高中及以下、大專大學、研究生分別取值為0、1、2,按有序分類變量處理。,說明樣本中處于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個體數量要明顯高于大專大學和研究生兩種學歷的個體數量。根據個體的就業類型,將職業劃分為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和混合勞動三類,定義為虛擬變量,具體劃分方法是將專業技術人員和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劃入腦力勞動者,將公務員、辦事人員和商販人員劃入混合勞動者,將保安人員、保潔人員、餐飲人員、家政人員、建筑人員、快遞人員、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其他商業、服務業人員、其他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生產人員、運輸人員、裝修人員劃分為體力勞動者。該變量的均值為0.327,表明樣本中從事體力工作的個體數量要大于從事腦力勞動和混合勞動的個體數量。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此外,工作經驗和流動時長為連續型變量,其中,流動人口的平均工作經驗為4.1年,平均流動時長為10年。流動人口的性別、民族、戶籍、黨員、婚姻、住房、居民醫保為二值分類變量③以上變量的界定如下,性別:女性=1,男性=0;民族:漢族=1,其他=0;戶籍:非農=1,農業=0;黨員:是=1,否=0;婚姻:結過婚=1,未婚=0;住房:自有=1,其他=0;居民醫保:辦理=1,未辦理=0。,其對應均值分別為0.452、0.926、0.199、0.067、0.738、0.26、0.595,表明樣本中男性流動人口數量高于女性流動人口、漢族流動人口數量高于非漢族流動人口數量、農業戶籍流動人口數量高于非農業流動人口數量、非黨員流動人口數量高于黨員流動人口數量、有過婚史的流動人口數量高于未婚流動人口數量、在流動城市無自有住房的流動人口數量高于擁有自有住房的流動人口數量、辦理醫保的流動人口數量高于未辦理醫保的流動人口數量。行業、公司所有制性質、流入地區為分類變量①行業分別為租賃和商務服務,采礦,電煤水熱生產供應,電器機械及制造,房地產,紡織服裝,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化學制品加工,計算機及通訊電子設備制造,建筑,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教育,金融,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科研和技術服務,木材家具,農林牧漁,批發零售,其他制造業,社會工作,食品加工,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衛生,文體和娛樂,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醫藥制造,儀器儀表制造,印刷文體辦公娛樂用品,住宿餐飲,專業設備制造等32個行業;所有制分別為外商獨資企業,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共7種所有制性質;東部地區指隸屬于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的城市,中部地區指隸屬于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城市,西部地區指隸屬于四川、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的城市。。
四、實證分析結果
1.教育程度、就業類型和工資收入的關系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應分析流動人口教育程度、就業類型和工資收入三者的關系。首先,分析教育程度、就業類型和工資收入的基本表現情況。根據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將樣本劃分為高中及以下、大專大學、研究生三個子樣本,其對應的流動人口分別為38 164、15 843 和653 人,在總樣本中占比為69.82%、28.98%和1.19%(見表2),表明我國大多數流動人口仍然不具有高等教育經歷。根據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將其劃分為低收入(2 000 元以下)、中低收入(2 000 至5 000 元)、中高收入(5 001 至10 000 元)和高收入(10 000 元以上)四個類別,對應的流動人口分別為4 115、34 817、13 079和2 649人,在總樣本中占比為7.53%、63.7%、23.93%和4.85%,表明我國六成以上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集中于中低收入水平,達到高收入水平的流動人口較少。根據就業類型,將樣本劃分為體力勞動、混合勞動、腦力勞動三個子樣本,對應的流動人口分別為44 464、7 659 和2 537 人,在總樣本中占比為81.35%、14.01%和4.64%,表明我國大多數流動人口從事體力勞動,這與我國制造業全球第一、生活服務業發達的現實相符合。

表2 不同教育程度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分布和就業類型分布
其次,分析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與工資收入水平的關系。研究發現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流動人口人數在低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中高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的比重分別為9.43%、69.02%、19.88%和1.67%;大專大學學歷的流動人口人數在四種工資收入水平上所占比重分別為3.21%、52.5%、33.16%和11.12%;研究生學歷流動人口人數在四種工資收入水平上所占比重分別為1.23%、24.2%、36.6%和37.98%。顯然,高中及以下學歷和大專大學學歷的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基本集中在中低收入水平上;研究生學歷的流動人口工資收入更多地集中在中高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上。這表明流動人口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從事高收入水平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即流動人口接受的教育程度與工資收入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
再次,分析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與就業類型的關系。發現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流動人口從事體力勞動、混合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比重分別為80.61%、14.48%、4.92%;大專大學學歷的流動人口從事該類工作的比重為83.24%、12.89%、3.87%;研究生學歷的流動人口選擇從事體力勞動、混合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比重分別為78.56%、14.09%、7.35%。無論高中及以下、大專大學還是研究生學歷的流動人口,其就業選擇都是以體力工作為主,這反映了我國對普通勞動力的巨大需求和腦力勞動崗位供給的不足。大專大學學歷的流動人口從事腦力相關工作的比重較低,在就業類型上并沒有優于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流動人口,可能的原因是只接受大專大學的高等教育并不能在就業市場中優勝于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流動人口,其知識儲備還不能完全勝任腦力勞動的要求。此外我們的研究對象并非是應屆畢業的大學生,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對于當下的就業類型具有重要影響,高中及以下學歷的流動人口擁有的3年以上工作經驗可能足以抵消大專大學教育的影響。同樣的,研究生學歷的流動人口從事腦力勞動、混合勞動的人數較多,占比約為21%,反映了研究生教育對于就業類型的積極重要作用。姚亞文和趙衛亞認為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顯著增大個體選擇高級技術工作者、單位負責人、行政人員等腦力相關工作的概率。[18]個體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積累的知識就會越豐富。而且要想在研究生考試中勝出,個體普遍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和自控能力,這些會有利于個體形成自信和能力的長期增長,從而影響個體的職業選擇和崗位升遷。
最后,分析流動人口的就業類型與工資收入的關系(見表3)。發現從事體力工作的流動人口人數在四種收入水平上的比重分別為8.37%、63.41%、23.01%和5.21%;混合勞動者在四種收入水平上的比例分別為4.33%、67.93%、25.19%和2.55%;腦力工作者在四種收入水平上所占比例為2.4%、56.01%、36.15%和5.44%。不論是體力勞動者、混合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其工資收入的分布均呈中間大兩頭小的“梭形”,即在中低收入水平的比重最高,在中高收入水平的比重次之,在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的比重較小。這表明三種就業類型并沒有明顯的高低貴賤之分,即沒有對應于顯著的收入差距。雖然工作性質因是否以體力還是腦力為主而不同,但具體的工作崗位和內容才是決定工資收入高低的關鍵,就業類型對工資收入差異不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此外,互聯網大潮下涌現出的大量快遞、網約車等新型工作崗位,多勞多得、月薪過萬在行業內成為常見現象。這些都使得就業類型與工資收入沒有那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但是,腦力工作者還是更加易于獲得較高的收入,其在中高收入水平及高收入水平所占比重合計為41.59%,遠大于其他群體。

表3 不同就業類型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分布
2.回歸分析
以流動人口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分別建立并估計4 個線性回歸模型(見表4)。其中,模型(1)的解釋變量只有教育一項,參數估計結果顯示與高中及以下流動人口相比,大專大學教育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程度為32.4%;研究生學歷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程度為83.2%。模型(2)引入就業類型作為控制變量,估計結果顯示教育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仍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就業類型對個體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影響,相比體力勞動,混合勞動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為6.1%,腦力勞動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程度為20.7%。模型(3)將個人特征變量引入模型,參數估計結果顯示大專大學學歷、研究生學歷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正向顯著影響有所下降,估計系數分別為0.227和0.635,相比模型(2)的參數估計結果下降幅度約為10%和19.2%。由于工資收入受地域城市物價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影響,可以分析教育對個體凈收入的影響①凈收入是用名義工資扣除勞動力生活成本的收入,其中,生活成本是由勞動力月生活總支出和家庭人數計算得到的。。模型(4)將凈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參數估計結果為0.185 和0.651,雖然略低于模型(3)的估計結果,但是仍然顯示教育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我們的結論比較穩健。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工資收入也越高,與大專大學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提高幅度更大。

表4 教育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的回歸結果
分析模型(3)中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發現流動人口的職業、工作經驗、性別、民族、婚姻等個人特征變量對個體工資收入產生顯著影響。其中,流動人口的漢族身份、非農業戶籍、黨員身份、在婚狀態、擁有醫保、擁有住房均對個體的工資收入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流動人口流入城市所屬區域來看,東部地區的工資收入顯著高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略高于西部地區,估計系數分別為0.237和0.021,這與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現實一致。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顯著低于男性流動人口,估計系數為-0.277,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男性流動人口的工作強度大且在體力型勞動中占據優勢;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女性流動人口在就業過程中遭遇了性別歧視。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對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倒U 形”影響,一次項和平方項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027和-0.001,這表明流動人口起初的工作經驗對工資收入具有促進作用,但是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個體的年齡不斷增大,大約在13年后,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對工資收入的影響將達到峰值,隨后不斷下降,大約在27 年后轉為負值。現實中個體年齡對于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作崗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個體的體力勞動能力會因身體耐勞度下降而下降,老齡勞動力在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其工資收入也會低于年輕勞動力。如果一個個體在22歲開始參加工作,那么在35 歲左右達到自己的最佳狀態,隨后體力、學習能力等各項人體機能開始下降,在50 歲左右可能面臨著被動失業的風險。
為了更全面地分析教育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對根據就業類型劃分的三個子樣本分別進行回歸(見表5)。其中,模型(5)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流動人口為樣本,參數回歸結果表明大專大學學歷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顯著高于高中及以下學歷,溢價程度為22.8%,研究生學歷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也顯著高于高中及以下學歷,溢價程度為66.4%。模型(6)是以混合勞動為主的流動人口為樣本,參數回歸結果表明大專大學學歷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顯著高于高中及以下學歷,溢價程度為18.4%,研究生學歷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也顯著高于高中及以下學歷,溢價程度為45.4%。模型(7)是以腦力勞動為主的流動人口為樣本,參數回歸結果表明大專大學學歷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顯著高于高中及以下學歷,溢價程度為19%,研究生學歷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也顯著高于高中及以下學歷,溢價程度為50.1%。由此可知,無論是體力勞動者、混合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教育對個體的工資收入影響均是正向顯著的,研究生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正向影響最大;與此同時,不同的就業類型會影響教育的回報率,其中體力勞動者的教育回報率最大,其次為腦力勞動者,最后是混合勞動者,這也突出了體力勞動者中教育的稀缺價值,加強教育投入有利于提高體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反駁了社會上流行的讀書無用、學歷不值錢等消極論調。

表5 教育對不同就業類型個體工資收入影響的回歸結果
對表5 中的控制變量估計結果進行分析,發現男性流動人口、非農業戶籍、黨員、在婚狀態仍然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相比非黨員,黨員對體力勞動者、混合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溢價分別為7%、4.4%和9.3%,黨員對腦力工作的影響最高,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國家機關、黨群組織對工作人員的身份要求較為嚴格,更傾向于具有共產黨身份的個體。民族除了對體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有影響外,對腦力勞動者和混合勞動者不再具有顯著影響,這反映了我國民族團結、融合和諧穩定的社會局面。自有住房只對體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影響,估計系數為0.025,但對于混合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影響不顯著。一般來說,流動人口在流入的城市擁有住房是很少見的,擁有住房反映了流動人口愿意在城市長期居留的意愿和較強的家庭經濟實力,并不具備影響個體工資收入的合理經濟解釋,因此,其不能影響流動人口的工作收入是正常的。對于體力勞動者來說,擁有自有住房顯示其在當地具有一定的社會關系網,有較強的社會資本從而更加容易獲得高工資收入水平的工作機會,且能夠滿足傾向尋找穩定就業勞動力的企業需求,從而獲得比其他體力勞動者更高的工資收入水平。是否有醫保對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沒有顯著影響,這很可能是因為腦力勞動者的工作都具有居民醫保。工作經驗對體力勞動者和混合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倒U”影響,但對于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估計系數為0.016,這意味著腦力勞動者會隨著工作經驗的增長而不斷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水平,不受身體機能條件的限制。那么個體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就能夠獲得更長的工作時間,從而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相比于中西部地區,流動人口在東部地區工作仍然具有更高的工資收入,體力勞動者、混合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溢價幅度分別為24.3%、18.6%和22.3%;但是相比西部地區,工作在中部地區的混合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已經不存在顯著溢價的情況。
五、結論
教育關系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事關國家興衰的最根本事業。同時,受教育也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接受良好的教育已經成為人們生存發展的第一需要和終身受益的財富。面對社會上的讀書無用和學歷不值錢等消極論調,本文深入研究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歸納出“教育-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工資收入”的因果關系鏈,并指出教育能夠影響個體的就業選擇和工資收入,進而利用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調查數據,實證研究教育對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通過上述研究,獲得如下主要結論:
第一,教育、就業類型和工資收入存在緊密的相關關系。按受教育程度分為高中及以下學歷、大專大學學歷和研究生學歷三個類別,按就業類型將工作分為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混合勞動者三個類別,按工資收入水平分為低收入(2 000元以下)、中低收入(2 000至5 000元)、中高收入(5 001至10 000 元)和高收入(10 000 元以上)四個類別,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六成以上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集中在中低收入水平上,個體的工資收入基本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梭形”分布,八成以上流動人口從事的是體力勞動,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與工資收入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
第二,教育能夠提升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以全體流動人口為樣本,控制個體特征等因素對工資收入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高等教育能夠顯著正向影響個體的工資收入水平,相對于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個體,接受大專大學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個體的工資收入溢價幅度達到22.7%和63.5%,研究生教育對工資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加明顯。分別以體力勞動者、混合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為樣本的研究顯示,教育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仍然是顯著為正的,不同的就業類型會影響教育的回報率,其中體力勞動者的教育回報率最大,其次為腦力勞動者,最后是混合勞動者。
第三,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工作經驗、城市位置等均對個體工資收入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顯著低于男性。工作經驗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倒U”影響,即隨著工作經驗的增加,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會逐步增加,到達某一時間后又會逐步下降。而對于從事腦力勞動的個體來說,工作經驗對工資收入的影響始終為正。流動人口工作的城市位置對于工資收入具有顯著影響,東部地區城市的工資收入大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城市的工資收入大于西部地區,而對于從事腦力勞動的個體來說,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工資收入沒有差異。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結合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現狀,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鼓勵個體追求卓越,形成專業型人力資本。創新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創新急需大量高素質專業型人才的供給,發揮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技術水平。面對國外在部分高精尖技術上的卡脖子行為,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在某些領域的科技水平上存在著短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專業型人才的匱乏。大國競爭的關鍵是科技的競爭,而決定科技競爭成敗的是人才的競爭。國內城市競爭和企業競爭同樣如此,國內各大城市、互聯網大廠、高科技公司不斷上演搶人大戰,唯才是舉。只要是高素質人才、稀缺性人才在我國就具有廣闊的才能施展空間,因此成才是每個個體的最優選擇,成為最高水平人才就能夠獲得最高水平的回報,在培養自己成才的道路上盡可能投入是最符合經濟理性的,其可能產出是難以想象的。并且個人人力資本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的向好發展。
二是擴大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投入力度。在我國基本普及高中教育的前提下,高等教育應該成為我國財政投入的重點方向。長期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因多種原因而落后于世界知名學府的發展,大量優秀學生留學國外,為國外科技創新做出了重要貢獻。提高國內高校的人才培養能力,提供充足的經費支持,尤其是對科研教師隊伍、博士研究生提供有力的經濟支持,是留住人才和高校持續發展的關鍵。面對南方經濟發達城市對創建高校和爭搶一流學科的不計成本的投入,東北等具有較好高等教育資源的經濟低迷地區更應該警醒,進一步加大對高校這一優質資產的扶持,培養更多高素質人才,進而促進地區經濟轉型和拉動地區經濟增長。
三是形成崇尚讀書、獎勵專研的社會氛圍。終身學習是現代社會對每個個體的基本要求,一個個體在進入社會之前保持的學習時間越長,其知識儲備和學習能力越強,其基本功也就越扎實,未來發展的潛力也越大。毫無疑問,能力比學歷重要,但是能力的形成離不開艱苦的學習奮斗過程,這往往就是在校學習的過程、攻讀高難度學位的過程。對于當下中國廣大中下階層來說,讀書求知仍然是改變命運的最優選擇。學歷是甄選個體能力最好的信號,打擊假學歷,淘汰不達標高校畢業生,寬進嚴出,讓學歷值錢是高等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公眾共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