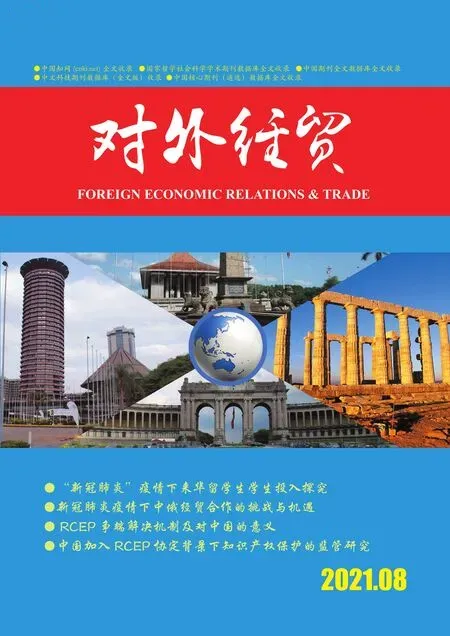“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涉外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zhí)行制度的思考
蔡懷君
(上海政法學院 國際法學院,上海 201701)
一、我國涉外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zhí)行的背景
“一帶一路”倡議覆蓋我國與眾多沿線海外國家政府、企業(yè)、公民等之間的貿(mào)易往來、投資并購等經(jīng)濟合作,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之間資本、人口、服務(wù)等跨國民商事關(guān)系的交往范圍進一步擴大,國家間交往得以不斷加深,直接或間接促使了我國涉外民商事案件承認與執(zhí)行的需求上升。截至2018年10 月,上海市五年審結(jié)涉“一帶一路”民商事案件2464 件,涉外文書在我國的承認與執(zhí)行需求顯著增長。根據(jù)追蹤統(tǒng)計,訴訟案件的文書結(jié)果并不代表著爭端的結(jié)束,涉外訴訟案件尤為如此。涉外判決如何在他國得到承認與執(zhí)行,已成為涉外案件訴爭能否得到妥善解決的關(guān)鍵要點。
出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現(xiàn)實考量,一直以來,我國與沿線國家之間都是在尊重沿線各國自愿的基礎(chǔ)上,鼓勵利用雙邊或者多邊投資協(xié)定、司法協(xié)助協(xié)議解決涉外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zhí)行問題。但我國與新加坡簽訂的雙邊協(xié)定沒有約定司法協(xié)助的內(nèi)容,與泰國簽訂的雙邊協(xié)定僅局限于送達文書和調(diào)查取證方面。因此,統(tǒng)一的、確定的涉外民商事文書承認與執(zhí)行協(xié)議制定與出臺對深化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具有重要意義。2019年7 月,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22 屆外交大會出臺了《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以下簡稱《公約》)[1],也影響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涉外司法協(xié)助體制,我國對該《公約》反映出的國際涉外司法協(xié)助規(guī)則發(fā)展趨勢進行解讀并作出回應(yīng),對于我國企業(yè)在海外進行投資、貿(mào)易等民商事活動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涉外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zhí)行情況
(一)互惠原則逐漸成為司法協(xié)助的重要依據(jù)
依據(jù)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guī)定和第二百八十條規(guī)定,就涉外生效判定、裁決,無論是我國法院申請外國法院承認與執(zhí)行,還是外國法院申請我國法院承認與執(zhí)行,都應(yīng)該依據(jù)我國締結(jié)的雙邊或多邊司法協(xié)助協(xié)議相關(guān)內(nèi)容,或者依據(jù)我國與該國之間的具體互惠關(guān)系進行審查。[2]其中,我國簽署的關(guān)于涉外司法協(xié)助內(nèi)容的雙邊協(xié)定和多邊協(xié)定仍十分有限,我國也尚未批準與司法協(xié)助相關(guān)的專門性公約,“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將對其依據(jù)提出需求。
我國在國際司法協(xié)助實踐中有將互惠原則作為依據(jù)之一的趨勢。在新加坡國內(nèi)法院對我國法院生效判決、裁定承認與執(zhí)行之后,我國法院便基于事實互惠原則,經(jīng)審核后對該國生效文書予以承認與執(zhí)行。但各國在互惠原則的國內(nèi)司法實踐不同,對于如何確定兩國之間是否存在“互惠關(guān)系”暫時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事實互惠與推定互惠原則在實踐中雖然已經(jīng)為我國與各國之間爭取較大空間與可能性,但各國對于互惠原則的有限適用并不能完全發(fā)揮其對司法協(xié)助的作用。
(二)涉外和解、調(diào)解協(xié)議承認與執(zhí)行不便
隨著國際貿(mào)易和國際投資的不斷深入,跨國民商事案件處置是國際法治的焦點之一。同時,國際民商事糾紛呈現(xiàn)出由于含有涉外因素這一特征,糾紛的解決方式與解決目的與國內(nèi)民商事爭議解決也有所不同。國際民商事往來中,當事雙方的合作關(guān)系維持有時比個案輸贏更重要。和解與調(diào)解由于其先天對合作關(guān)系的維持作用,作為法院外最常用的爭議解決方式恰恰對司法協(xié)助涵蓋的文書范圍提出了擴大要求。當爭議包含涉外因素,通過訴訟和解或司法確認程序達成司法和解協(xié)議后,依然不可避免要面對司法和解協(xié)議的域外承認與執(zhí)行問題。[3]
我國人民法院的生效調(diào)解書本身在國內(nèi)是可以作為強制執(zhí)行依據(jù)的。但由于調(diào)解書區(qū)別于法院判決、裁定,其并不能作為法院其他判決的基礎(chǔ)或者前提,不能完全保護當事人的程序權(quán)利[4],因此調(diào)解書一直沒有納入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的文書范圍。并且,由于各國對訴訟中及訴訟外達成的和解協(xié)議規(guī)制不同,該協(xié)議的性質(zhì)和效力認定在各國并不統(tǒng)一,這使得司法和解協(xié)議在域外承認與執(zhí)行難以落地。[3]
三、《公約》對我國涉外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zhí)行的影響
《公約》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全面面向國際民商事法律文書流通統(tǒng)一規(guī)則的國際性文書。2019年《公約》對其適用范圍、可以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的情形、申請執(zhí)行的文書要求等問題都作出最新規(guī)定,與以往國際承認與執(zhí)行跨國民商事裁判有較大變化。
(一)擴大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的締約國范圍
截至2021年,與我國訂立雙邊民商事司法協(xié)助條約的國家與地區(qū)在世界現(xiàn)存國家與地區(qū)中占比不足1/5,“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覆蓋率不足1/3,無法滿足我國對本國民商事裁判最大限度獲得國際承認及國民合法權(quán)益得到切實保障的現(xiàn)實需求。[5]在司法實踐中,事實互惠案例使得中國除了與少數(shù)幾個國家簽訂了承認和執(zhí)行判決的雙邊司法協(xié)助協(xié)議外,很少有基于具體互惠關(guān)系而主動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判決的情況。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現(xiàn)有成員國已達83 個,其范圍遠大于與我國簽訂了相關(guān)協(xié)議的國家。而且,韓國、美國、日本等與中國民商事來往密切的國家,一直只是依照事實互惠原則與我國進行司法協(xié)助,現(xiàn)《公約》的出臺彌補了中國與這些重要國際商民事貿(mào)易伙伴在司法協(xié)助領(lǐng)域的法律缺陷。未來,隨著各成員國的批準及非成員國的逐步加入,我國依據(jù)互相承認和執(zhí)行法院裁判條約的國家范圍也有望擴大。這將極有力地促進我國涉外民商事判決、裁定在外國的承認和執(zhí)行,促進我國商民事主體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提升我國在國際民商事貿(mào)易領(lǐng)域的形象與保護力度。
(二)拓展被締約國承認和執(zhí)行的法律文書種類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法院的司法文書的類型,僅限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已經(jīng)發(fā)生法律效力的判定、裁決。雖然另有司法解釋中涉及對外國法院作出的調(diào)解書,但也限于離婚調(diào)解,僅涉及民商事領(lǐng)域的極小部分。[6]《公約》第11 條,首次將司法和解協(xié)議列為可依據(jù)《公約》以判決相同方式被承認和執(zhí)行的外國法院司法文書類型。這為包括國際貿(mào)易、跨境投資在內(nèi)的國際民商事爭端多元解決機制提供了更優(yōu)的司法保障,也將有利于跨境交易的當事人選擇更多的方式以實現(xiàn)解決糾紛目的,對國際民商事領(lǐng)域司法合作影響深遠。
另外,根據(jù)《公約》第3 條中明確了“判決”的定義,只要法院是就實體問題作出的文書,不論稱謂與內(nèi)容如何,均可以依照《公約》得到承認與執(zhí)行。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可被承認和執(zhí)行的法律文書的范圍,解決了涉外民商事案件中訴訟費用、調(diào)查令等執(zhí)行問題,對于實務(wù)中國際民商事訴訟的許多細節(jié)問題進行了規(guī)范、完善。
(三)拓寬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互惠原則的適用類型
2016年,瑞士Kalmar Group AG 與江蘇紡織集團案①,系我國法院首次根據(jù)互惠原則承認執(zhí)行外國生效判決的案例。2020年,韓國彼克托美術(shù)式有限公司與上海創(chuàng)藝寶貝教育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案②,也延續(xù)了事實互惠原則,對該案予以承認與執(zhí)行。兩地法院根據(jù)中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guī)定,結(jié)合具體案件爭議,在查明外國法院對涉案爭議有管轄權(quán)并且對當事人進行了合法傳喚等事實后,確認外國的國內(nèi)法院曾對我國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予以承認和執(zhí)行之后,依據(jù)事實互惠的互惠原則作出同樣給予承認與執(zhí)行的裁定。[7]
《公約》的出臺,讓法律互惠作為互惠原則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shè)提供司法服務(wù)和保障的若干意見》第6 條中也明確,結(jié)合國際司法合作交流意向、對方國家承諾等情況,可以考慮由我國先行提供司法協(xié)助以積極促成互惠關(guān)系。[7]由此可見,雖然中國法院并沒有完全放棄事實互惠的實務(wù)做法,但《公約》拓寬了外國承認與執(zhí)行我國生效法律文書的法律依據(jù),迎合了“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現(xiàn)實需求與對外開放的國家戰(zhàn)略,或會成為未來中國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民商事判決的流行依據(jù)之一。
四、完善我國涉外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zhí)行的建議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涉外民商事往來日益增多、涉外民商事矛盾相應(yīng)增多的現(xiàn)實需求下,中國先后出臺了相關(guān)司法文件,意圖增進與各國的司法互信,積極推動在涉外司法協(xié)助領(lǐng)域建立互利關(guān)系。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民商事貿(mào)易發(fā)展趨勢對我國的互惠原則提出了寬松要求,我國勢必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法律互惠標準,就互惠關(guān)系的形式和方式提供更詳細、更寬松的法律依據(jù),對法律文書進行類別區(qū)分以適用有差別的、有針對性的互惠標準,明確互惠原則舉證責任的承擔與相應(yīng)法律效果等。
(一)制定推托承認與執(zhí)行的相應(yīng)規(guī)制措施
《公約》十三條第二款規(guī)定,締約國作為被請求國時,不能僅以該司法文書應(yīng)該在他國承認或執(zhí)行為理由,拒絕承認或執(zhí)行跨國司法文書。比如,被請求國不能僅以存在其他締約國符合《公約》第5 條之承認與執(zhí)行的基礎(chǔ)等條款為由,對他國司法協(xié)助請求進行逃避。該規(guī)定表明了《公約》對涉外司法文書的順利執(zhí)行予以法律保障的態(tài)度,并試圖以此提高跨國生效法律文書被予以承認與執(zhí)行的確定性。
雖然《公約》已經(jīng)在降低國際民商事爭端當事人解決糾紛的司法成本和司法保障上大有發(fā)展,但它并未對締約國作為被請求國時,逃避和推諉其他成員國跨國司法協(xié)助進行相應(yīng)的制裁規(guī)定。被請求國無理由逃避的,《公約》并沒有制定相應(yīng)規(guī)制,這意味著《公約》雖有反對推脫承認與執(zhí)行的態(tài)度,卻無法為此提供切實的司法保障。如此規(guī)定,僅依靠各締約國的誠信落實,無法將《公約》對涉外司法協(xié)助的規(guī)制意義與制度完善作用充分發(fā)揮,對《公約》的國際影響力與強制力、公信力有著一定打擊。我國在未來的雙邊協(xié)定、多邊協(xié)定或者國內(nèi)法律法規(guī)制定、修訂時,應(yīng)對被請求國推脫承認與執(zhí)行規(guī)定具體的、恰當?shù)膽土P性規(guī)制,如損害賠償。
(二)細化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互惠原則的參考標準
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法院生效法律文書是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處理跨境民商事糾紛時,有力、適當?shù)谋Wo中外當事人的利益就顯得尤為重要。2009年,海外集團與以色列籍公民Itshak Reitmann案③中,因為我國長期事實互惠的存在,對方在上訴過程中以我國未有承認與執(zhí)行以色列生效判決的先例為由,提出我國不具有承認與執(zhí)行以色列生效判決的潛在可能性。其提出的一系列案例證據(jù),比如英國、日本曾向中國提出承認與執(zhí)行請求,但因兩國之間沒有司法協(xié)助條約而被中國駁回等,這些理由無疑給案件造成了不小的阻礙。[8]
鑒于跨國司法協(xié)助在國際民商事貿(mào)易往來中的重要性,以及我國人民法院做出的法律文書在外國得到承認和執(zhí)行對保護在我國進行民商事活動的中外當事人的重要性,我國有必要對識別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民商事法律文書的承認和執(zhí)行制定具體的、客觀的、可執(zhí)行的標準,將互惠原則對司法協(xié)助的作用最大化。
(三)明確我國國內(nèi)對于涉外司法協(xié)助依據(jù)的優(yōu)先適用與時效問題
《公約》落地后,我國承認與執(zhí)行的依據(jù)將涵蓋互惠原則、雙邊司法協(xié)助協(xié)議和多邊司法協(xié)助協(xié)議等,具有多重法律規(guī)制,同一案件如何確定執(zhí)行與承認依據(jù)優(yōu)先適用的問題,國內(nèi)實踐案例還較為匱乏,國內(nèi)立法亦存在空白。程序正義才能保障實體正義,從國內(nèi)立法與司法層面對于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依據(jù)效力的優(yōu)先性作統(tǒng)一規(guī)定,有利于提高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的準確性與可預(yù)見性。
同時,目前我國簽訂的司法協(xié)助條約大部分都沒有涉及申請執(zhí)行的時效問題,僅涉及申請執(zhí)行程序適用被請求國的法律,時效問題屬于實體問題還是程序問題就成為了申請雙方較易產(chǎn)生分歧的重點問題。[9]《公約》第4 條第3 款依據(jù)原審國的可執(zhí)行性對時效問題進行了間接規(guī)定,由被請求國按照其本國法律規(guī)定來決定與申請執(zhí)行時效有關(guān)的爭議。參考此趨勢,我國國內(nèi)法律也可以通過在雙邊司法協(xié)助條約中對申請執(zhí)行時效的法律適用予以明確規(guī)定的方式及時改進我國關(guān)于申請執(zhí)行時效的法律規(guī)定。
五、結(jié)語
《公約》對司法合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司法建設(shè)、合作往來影響不一,將國際民商事糾紛的解決推進了一個新時代。《公約》的簽署已經(jīng)為我國涉外司法協(xié)助現(xiàn)在遇到的一些困境破解奠定了一定的基礎(chǔ),但建立完善的涉外司法協(xié)助制度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公約》也留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等待后續(xù)解釋及各國國內(nèi)立法實踐進行完善。應(yīng)該重新審視我國的涉外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zhí)行制度,完善我國現(xiàn)在涉外司法協(xié)助中的各項程序性規(guī)定,抓準《公約》趨勢推動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guān)司法解釋的完善,并依據(jù)《公約》在“一帶一路”建設(shè)中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司法合作。
注釋:
①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6)蘇01 協(xié)外認3 號。
②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9)滬01 協(xié)外認17 號。
③中國法院網(wǎng).以色列高等法院終審確認南通中院判決可在該國執(zhí)行系我國首例[EB/OL].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8/id/2960687.shtml.2017-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