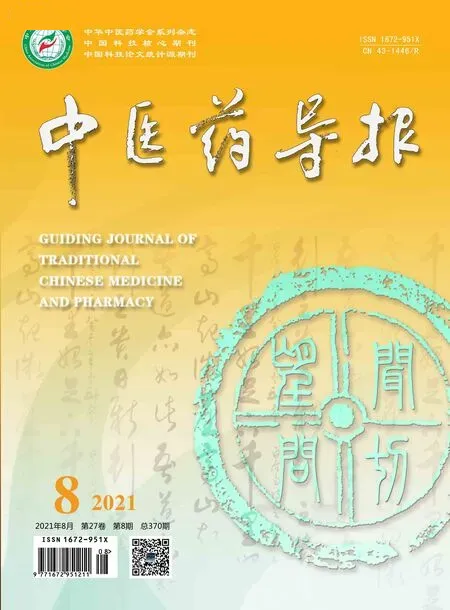漢黃芩素對膠原誘導性關節炎大鼠的治療作用及對NLRP3炎癥小體的影響
沈曉慶,王 晶,李婷君
(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遼寧 沈陽 110032)
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屬于一種以滑膜增生、炎癥細胞浸潤及關節病變破壞為主要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導致骨及軟骨的不可逆損傷,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活動及生活質量,給家人及社會造成了嚴重的負擔[1]。RA的發病機制復雜且尚未完全闡明,其過程是集機體固有免疫、適應性免疫及多種細胞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NLRP3炎癥小體是一種存在于細胞漿中的多蛋白復合物,由NLRP3、凋亡相關斑點樣蛋白(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spase recruitment domain,ASC)和半胱氨酸蛋白酶-1前體(cysteine aspartic acid specific protease-1precursor,pro-Caspase-1)組成,能調控促炎性細胞因子(包括IL-1β、TNF-α及IL-18等)的成熟,從而參與炎癥反應,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等密切相關[2-3]。有研究表明,RA模型中炎癥小體NLRP3、Caspase-1、IL-1β及IL-18水平明顯升高,與疾病的嚴重程度呈正比,且通過抑制NLRP3活性后,RA病理損傷明顯減輕,說明NLRP3可能為治療RA的有效靶點[4]。漢黃芩素為唇形科植物黃芩的主要藥理活性成分之一,屬于黃酮類化合物,具有抗炎、抗腫瘤等藥理作用[5]。最近研究發現,漢黃芩素對RA模型具有一定的治療作用。有研究表明,漢黃芩素可顯著抑制類風濕關節炎成纖維滑膜細胞增殖,誘導其凋亡,并可顯著下調炎癥因子IL-6水平[6]。但是對NLRP3的影響未見報道。因此,本研究通過建立膠原誘導的關節炎大鼠(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s,CIA)模型,探討漢黃芩素治療RA與NLRP3的關系,以期為明確漢黃芩素治療RA的作用機制提供一定的實驗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SPF級SD雄性大鼠48只,體質量200~220 g,由遼寧長生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許可證號:SCXK(遼)2018-0001。大鼠飼養于遼寧中醫藥大學實驗動物中心實驗室,室溫20~24℃,相對濕度40%~50%,自由飲食、飲水,光照和黑夜各12 h,適應性飼養1周后進行實驗。本研究中所有實驗方案均得到遼寧中醫藥大學實驗動物福利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批準號:IACUC2019005。
1.2 藥物與試劑 漢黃芩素(成都普菲德生物有限公司,批號:JOT-10317);弗氏完全佐劑(批號:SLBT1422)、弗氏不完全佐劑(批號:SLBT1714)、雞Ⅱ型膠原(批號:SLBV4134)(美國Sigma公司);地塞米松注射液(遼寧成大方圓藥房,批號:2006031);HE染色試劑盒(大連美侖生物有限公司,批號:MB9898-Nov-21D);IL-1β ELISA試劑盒(批號:20190520)、TNF-α ELISA試劑盒(批號:20190408)、IL-18 ELISA試劑盒(批號:20190621)(北京索萊寶生物有限公司);兔抗NRLP3一抗(批號:BA-3677-2)、兔抗pro-Caspase-1一抗(批號:BM-4291)、兔抗Caspase-1一抗(批號:BA-2220-1)、兔抗GAPDH一抗(批號:BA2913)、驢抗兔生物素(HRP)標記二抗(批號:BA-1062)(武漢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其余試劑均為國產分析純。
1.3 主要儀器Ti-S型熒光倒置顯微鏡(日本尼康公司);RM2016型石蠟切片機(德國萊卡公司);SpectraMax M5型酶標儀(美國Sigma公司);Western blotting電泳儀和轉膜儀(美國Bio-Rad公司)。
1.4 造模與分組48只大鼠中隨機選取8只作為空白組,剩余40只大鼠根據文獻報道的方法建立膠原誘導的關節炎大鼠模型[7-8]。將2 mg/mL雞Ⅱ型膠原醋酸溶液逐滴加入至等體積的弗氏完全佐劑中,邊滴加邊研磨,不斷研磨1 h。大鼠尾根部皮下散點注射上述弗氏完全佐劑200 μL。7 d后大鼠尾根部皮下散點注射含2 mg/mL雞Ⅱ型膠原的弗氏不完全佐劑200 μL。空白組大鼠于同時間點注射等體積生理鹽水。利用關節炎指數評分評價大鼠模型是否構建成功,評分標準如下,0分:關節無腫脹;1分:關節輕微腫脹;2分:關節中度腫脹;3分:關節嚴重腫脹;4分:關節嚴重腫脹并潰爛[8-9]。將4個關節的評分進行相加,累積評分≥4分表示CIA模型制備成功[10]。將造模成功的40只大鼠進一步隨機分為模型組、地塞米松組、漢黃芩素低劑量組、漢黃芩素中劑量組、漢黃芩素高劑量組,每組8只。
1.5 實驗給藥 漢黃芩素給藥劑量根據黃芩成人(5~10g/60 kg)臨床劑量與漢黃芩素在黃芩中的含量(25 mg/g),并按人與動物體質量系數換算得到;漢黃芩素低劑量為成人臨床劑量的2倍,中劑量為成人臨床劑量的4倍,高劑量為成人臨床劑量的8倍。地塞米松劑量根據體質量60 kg的成人的臨床劑量按人與動物體質量系數換算得到;即漢黃芩素低、中、高劑量組大鼠分別給予漢黃芩素灌胃,50、100、200 mg/kg;地塞米松組大鼠給予地塞米松灌胃,3 mg/kg;空白組和模型組大鼠灌胃給予等體積冷開水[11]。1次/d,連續28 d。
1.6 檢測指標
1.6.1 關節炎指數評分 分別于治療第0、7、14、21及28天對大鼠雙側后足關節進行關節炎指數評分。0分:關節無腫脹;1分:關節輕微腫脹;2分:關節中度腫脹;3分:關節嚴重腫脹;4分:關節嚴重腫脹并潰爛[8-9]。
1.6.2 炎癥因子水平 各組大鼠腹腔注射3.5%水合氯醛10 mL/kg進行麻醉,腹主動脈采血,3 000 r/min離心5 min,吸取上清,置于-20℃冰箱中保存,備用。利用ELISA試劑盒檢測各組大鼠血清中炎癥因子IL-1β、TNF-α及IL-18水平,步驟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
1.6.3 胸腺指數與脾指數 處死各組大鼠后,快速摘取完整的胸腺與脾臟,置于濾紙上吸干多余血跡,稱質量并記錄,根據如下公式計算胸腺指數與脾指數:胸腺(脾)指數=胸腺(脾)質量/大鼠體質量。
1.6.4 大鼠滑膜組織損傷病理觀察 剝離大鼠膝關節,置于4%多聚甲醛中固定,脫鈣液脫鈣4周后,制備石蠟切片。將切片置于70%、80%、90%及100%酒精溶液中水化,二甲苯透明2次,每次15 min,蘇木素染色液染色20 min,自來水沖洗;自來水浸泡20 min反藍,自來水沖洗;伊紅染色2 min,自來水沖洗;將切片置于70%、80%、90%及100%酒精溶液中脫水,二甲苯透明2次,每次5 min,晾干,中性樹膠封片。置于倒置顯微鏡下觀察各組大鼠滑膜組織病理變化。
1.6.5 NLRP3信號通路蛋白表達 將膝關節滑膜組織置于液氮中進行研磨,提取總蛋白,BCA蛋白檢測試劑盒檢測蛋白濃度,并調整蛋白濃度至一致,隨后進行蛋白變性,行SDS-PAGE電泳(電泳條件為100 V,電泳時間為90 min)、轉膜(轉膜條件為250 mA,轉膜時間為90 min)、封閉1 h,分別孵育NRLP3、pro-Caspase-1、Caspase-1或GAPDH一抗稀釋液(1∶1000),4℃孵育過夜;次日加入二抗稀釋液(1∶1 000)室溫振蕩孵育1 h。ECL化學發光,凝膠成像儀采集圖像光密度。Image J軟件進行分析,結果以NRLP3、pro-Caspase-1、Caspase-1蛋白與內參蛋白GAPDH的光密度比值表示。
1.7 統計學方法 利用SPSS 25.0軟件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關節炎指數評分數據比較利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其余各指標多組間比較利用單因素方差進行分析,兩組間比較利用LSD-t檢驗進行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各組大鼠關節炎指數評分比較 造模后,模型組,漢黃芩素低、中、高劑量組,地塞米松組大鼠關節炎指數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可用于后續研究。
組內比較:模型組大鼠于治療第7、14、21、28天后關節炎指數評分均明顯高于治療前(P<0.05),漢黃芩素低劑量組大鼠僅于治療第14、21天關節炎指數評分均明顯高于治療前(P<0.05);而漢黃芩素中、高劑量組大鼠于治療第7、14、21、28天后關節炎指數評分與治療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組間比較:治療第28天時,與模型組比較,漢黃芩素低劑量組大鼠關節炎指數評分明顯降低(P<0.05);治療第21、28天,與模型組比較,漢黃芩素中劑量組大鼠關節炎指數評分明顯降低(P<0.05);治療第14、21、28天,與模型組比較,漢黃芩素高劑量組與地塞米松組大鼠關節炎指數評分均明顯降低(P<0.05)。
分組因素與時間因素存在交互作用,變化趨勢相同,低、中、高劑量漢黃芩素治療后關節炎指數評分存在劑量依賴性。

圖1 交互效應輪廓圖
2.2 各組大鼠胸腺指數、脾指數比較 與空白組比較,模型組大鼠胸腺指數、脾指數均明顯升高(P<0.05);與模型組比較,漢黃芩素中、高劑量組及地塞米松組大鼠胸腺指數、脾指數均明顯降低(P<0.05),且漢黃芩素中、高劑量組之間存在一定的劑量依賴性。漢黃芩素低劑量組大鼠胸腺指數、脾指數與模型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漢黃芩素低劑量組大鼠胸腺指數高于漢黃芩素高劑量組及地塞米松組(P<0.05)。(見表2)
表2 各組大鼠胸腺指數與脾指數比較(±s)

表2 各組大鼠胸腺指數與脾指數比較(±s)
注:與空白組比較,aP<0.05;與模型組比較,bP<0.05;與地塞米松組比較,cP<0.05;與漢黃芩素低劑量組比較,dP<0.05
?
2.3 各組大鼠膝關節病理損傷情況 空白組大鼠膝關節組織結構正常,滑膜細胞增生、炎癥細胞浸潤、血管翳形成等病理改變不可見,關節軟骨表面光滑;而模型組大鼠膝關節組織細胞排列紊亂,滑膜細胞增生、炎癥細胞浸潤等病理損傷明顯,可見血管翳形成和大量變性壞死的軟骨細胞;漢黃芩素低劑量組大鼠膝關節組織細胞排列較紊亂,可見滑膜細胞增生、炎癥細胞浸潤等病理損傷,血管翳形成、變性壞死的軟骨細胞多見;漢黃芩素中、高劑量組及地塞米松組大鼠與模型組比較,膝關節組織細胞排列較為整齊,滑膜細胞增生、血管翳形成、炎癥細胞浸潤等病理損傷明顯減輕,變性壞死的軟骨細胞明顯減少,改善情況從強至弱依次為地塞米松組、漢黃芩素高劑量組、漢黃芩素中劑量組。(見圖2)
表1 各組大鼠關節炎指數評分比較(±s,分)

表1 各組大鼠關節炎指數評分比較(±s,分)
注:與治療前比較,aP<0.05;與模型組比較,bP<0.05;F時間主效應=10.912,P時間主效應=0.000;F分組主效應=182.258,P分組主效應=0.000;F交互效應=2.375,P交互效應=0.004
?

圖2 各組大鼠膝關節病理損傷情況比較(HE,×400)
2.4 各組大鼠炎癥因子表達比較 與空白組比較,模型組大鼠血清中IL-1β、TNF-α及IL-18表達水平明顯升高(P<0.05);與模型組比較,漢黃芩素中、高劑量組及地塞米松組大鼠血清中IL-1β、TNF-α及IL-18表達水平明顯降低(P<0.05),且漢黃芩素低、中、高劑量組及地塞米松組之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漢黃芩素低劑量組大鼠血清中IL-1β、TNF-α及IL-18表達水平與模型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各組大鼠炎癥因子表達比較(±s,pg/mL)

表3 各組大鼠炎癥因子表達比較(±s,pg/mL)
注:與空白組比較,aP<0.05;與模型組比較,bP<0.05
?
2.5 各組大鼠NLRP3信號通路相關蛋白比較 與空白組比較,模型組大鼠滑膜組織NRLP3、pro-Caspase-1及Caspase-1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升高(P<0.05);與模型組比較,漢黃芩素中、高劑量組及地塞米松組大鼠滑膜組織NRLP3、pro-Caspase-1及Caspase-1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降低(P<0.05),且漢黃芩素低、中、高劑量組及地塞米松組之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漢黃芩素低劑量組大鼠滑膜組織NRLP3、pro-Caspase-1及Caspase-1蛋白相對表達量與模型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3)

圖3 各組大鼠NLRP3信號通路相關蛋白比較(±s,n=8)
3 討 論
RA屬中醫學中“痹證”“歷節”“白虎病”等范疇。《黃帝內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所謂飲食居處,為其病本”,首次闡明了痹證的病因與外邪入侵人體有關。現代醫家認為RA病機為邪實正虛,虛實夾雜,且邪氣痹阻經脈為其根本病機,病變多累及筋骨、肌肉、關節甚至累及臟腑器官等[12]。黃芩為唇形科植物黃芩的干燥根,始載于《神農本草經》,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應用史。黃芩具有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止血安胎等功效,主治溫熱病、肺炎、痢疾、咳血、胎動不安、高血壓、癰腫癤瘡等[13]。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黃芩對大鼠類風濕關節炎具有一定的緩解作用,能夠抑制炎癥介質的釋放,從而緩解炎癥反應[14]。其主要藥理活性成分為黃酮類化合物,其中漢黃芩素屬于黃芩根特異性黃酮,具有較好的抗炎及抗腫瘤等藥理作用[15]。有研究表明,漢黃芩素能夠通過靶向NF-κB/MAPK信號通路改善CIA大鼠的RA樣病理損傷[11];漢黃芩素還可通過激活p38MAPK信號通路以誘導類風濕關節炎成纖維樣滑膜細胞凋亡,抑制其增殖,緩解RA[16]。本研究通過建立CIA大鼠模型評價漢黃芩素對其治療作用,結果表明中、高劑量的漢黃芩素可明顯降低CIA大鼠的關節炎指數評分,降低胸腺指數和脾指數,改善滑膜組織病理損傷,改善炎癥浸潤,對CIA大鼠具有一定的治療作用,與文獻報道一致[11];且漢黃芩素中、高劑量組與地塞米松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低劑量漢黃芩素對CIA大鼠的治療作用不明顯,說明其治療CIA存在劑量依賴性。
目前的研究認為,炎癥因子大量釋放與RA的發生與發展密切相關。炎癥細胞浸潤入滑膜組織內,可造成滑膜增生與基質破壞,從而加速RA的發展進程并加重其病理損傷,因此抑制炎癥因子產生與釋放是防治RA的重要環節[17-18]。IL-1β、TNF-α及IL-18是機體內重要的促炎性細胞因子,具有調節機體固有免疫與細胞免疫的作用,在RA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19]。IL-1β不僅能通過誘導內皮細胞表達黏附因子、基質細胞釋放趨化因子,還能夠誘導環氧酶2或者NO合成酶,從而加強機體炎癥反應[20]。IL-18能與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及成纖維樣滑膜細胞上的IL-18受體結合,發揮刺激作用[21]。本研究結果顯示,中、高劑量漢黃芩素可明顯抑制CIA大鼠血清中炎癥因子IL-1β、TNF-α及IL-18的水平,且與地塞米松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結果說明漢黃芩素可降低CIA大鼠的炎癥反應水平。此外,由于IL-1β與IL-18為NLRP3炎癥小體的下游效應分子,因此推測漢黃芩素抑制CIA大鼠炎癥反應與調控NLRP3炎癥小體有關。
NLRP3炎癥小體在RA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是機體固有免疫的重要組成部分,可通過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識別內源性或者外源性刺激因素,從而聚集Caspase-1并使其激活,并剪切IL-1β及IL-18的活性前體pro-IL-1β及pro-IL-18,促進其成熟,產生成熟的細胞因子并釋放,最終導致RA過程中的一系列炎癥反應[22-23]。為了驗證漢黃芩素抑制CIA大鼠炎癥反應是否與調控NLRP3炎癥小體有關,我們利用Western blotting檢測了NRLP3、pro-Caspase-1及Caspase-1蛋白表達。結果顯示中、高劑量的漢黃芩素能抑制CIA大鼠滑膜組織中NRLP3、pro-Caspase-1及Caspase-1蛋白表達,說明漢黃芩素減輕CIA大鼠炎癥反應可能與抑制NLRP3炎癥小體有關。
綜上所述,漢黃芩素能夠降低CIA大鼠的關節炎指數評分,降低胸腺指數和脾指數,改善滑膜組織RA樣病理損傷,并抑制NLRP3炎癥小體介導的炎癥反應來緩解RA的進展,為闡明漢黃芩素治療RA的作用機制提供了實驗依據,但是具體作用機制與作用靶點仍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