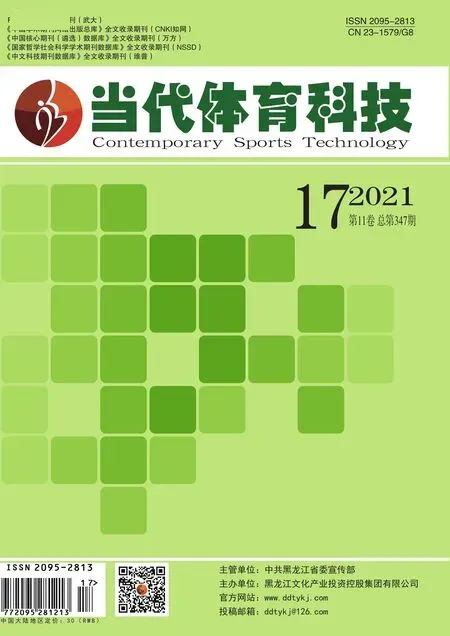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地域文化探微
陶坤
(懷化學院體育與健康學院 湖南懷化 418008)
“大湘西”是指地處湖南西部的廣闊區域,周邊與鄂渝黔桂四省交界,區域內分布著武陵山脈和雪峰山脈兩大山系,群峰環抱,山高水長,交通閉塞。區域內居住著土家族、苗族、侗族、瑤族和白族等40多個少數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等世居少數民族為主體,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經濟欠發達。但是大湘西各區域地緣關系密切,在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等方面都具有較強同一性的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地理單元。
所謂文化區就是指某種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種文化的人在空間上的分布[1]。而地域性文化是指,特定地域內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相互交融形成的極富特色的文化傳統[2]。“大湘西”民族傳統文化在地域性、民族性、歷史性和傳統性等方面有別于湖南省其它區域性的傳統文化,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大湘西“文化區”,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地域性文化”。大湘西的地域文化是指具有大湘西地理環境特征、人文環境特征的民族傳統文化,是在大湘西地域內經歷悠久的歷史形成的并被人們所感知和認同的各種文化現象集合。因此,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因素的雙重影響,造就了神秘而獨特的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地域文化現象,構成了完整的“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區”的結構和功能,該地域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歷史悠久、地域特征鮮明且民族文化獨特。大湘西具有豐富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從地域文化視域下解析該區域傳統體育文化的共性和區別,能夠更準確地把握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特征,促進該區域內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更好地發展。
1 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地域文化
“地域”是賦予其人文因素和歷史文化傳統的區域空間。作為地理空間概念,“地域”同“地區”“區域”有相同之處,但“地域”更多的是指一個歷史的和人們心理意識中所認同而約定俗成的空間區域。“地域文化”,實際就是從文化的角度區分地域,又從地域的角度分析文化[3]。把“大湘西”作為地域文化研究,它既是行政區域,也是文化區域。大湘西包括張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懷化市,以及邵陽市西部的隆回、洞口、綏寧、城步等縣,這些市(州)、縣地處湖南西部的廣闊區域,所以統稱為“大湘西”,并與湘南、湘中、湘北等湖南省的其它區域區別開來,在地域文化方面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文化傳統方面也形成了獨特的“大湘西地域文化”。
“大湘西”作為文化地理單元存在,是指該區域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傳統,該區域是江南丘陵向云貴高原山地的過渡地帶,區內山巒重疊,嶺谷交錯。雪峰山、武陵山群峰環抱,錯落有致,境內有沅水、酉水、辰水、武水、猛洞河等河流過境。區域內山高水長,地理環境惡劣,但與此同時卻生活著眾多的少數民族,并由此產生了許多文化特征相同或相似的、與該地域環境相一致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并發展成為大湘西地域文化標識。
由于地理環境的關系,湘西地區交通閉塞,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孤島,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侵蝕,保持著該區域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該區域廣泛盤踞著土家族、苗族、侗族、瑤族等世居少數民族,并以本民族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流傳于世,并充分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和從大區域外入侵的各種文化于一體,加上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造就了別具一格的民族文化資源。其中,各民族產生的諸多傳統體育文化資源,是生活在這片相對封閉區域內的各民族,為了適應險惡的地理環境和生存發展需要,共同產生的身體活動方式和健身手段,充分體現了大湘西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是各少數民族固有的傳統習俗、生計方式和精神信仰的重要載體。
2 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地域文化的多樣性
大湘西境域內居住著土家、苗、侗、瑤、白等40多個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以“小聚居、大雜居”的特點廣泛分布于大湘西全境,長期在大湘西相對固定的地區內繁衍生息,并與居住地的地理環境融合發展,在長期的生存發展中產生了體現大湘西不同地域文化特點的、反映各民族固有文化特征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正如斯圖爾德所說,地球上自然生境的多樣性,從本質上規約了住居在地球不同地方的人們的生計方式的多樣性。各民族文化在適應不同自然生境時所形成的特有生計方式,對于特定自然生境而言是極其有效的[4]。而生計方式的多樣性就會產生與地域環境相統一的文化,同時文化的多樣性也決定了生計方式的差異性[5]。
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作為大湘西最具代表性的少數民族,這3個民族長期生活在大湘西這塊廣闊的不同區域,相互交融、獨立發展,在長期的生存、繁衍和發展中產生了反映本民族特性的豐富的傳統體育文化,具有大湘西的地域文化特點,體現了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多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2.1 土家族的地域傳統體育文化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自治州的永順、龍山、保靖、古丈、鳳凰、吉首、瀘溪及張家界市的桑植、慈利等湘西北地區。土家族世代生活在崇山峻嶺、溝壑縱橫的武陵山區,其居住地環境優美,但地勢險惡,在生存發展中形成了彪悍淳樸的民族性格。土家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其民族意識、民族習俗及民族發展歷程主要依賴于各種傳統體育等文化形態來傳承和體現[6]。在生產、生活中形成了本民族獨特的宗教信仰和圖騰崇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土家族獨特的“擺手舞”“茅古斯舞”“儺舞”“土家族肉連響”等傳統體育運動形式。受土家族歷史傳統和文化特質的影響,這些獨特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深刻地反映出土家族的圖騰崇拜、喪葬習俗、巫儺祭儀和神話傳說及民族舞蹈等民俗文化事象、生計方式和精神信仰,體現出土家族的地域文化特征。
2.2 苗族的地域傳統體育文化
苗族主要分布和聚居在保靖、古丈、吉首、鳳凰、花垣、瀘溪、麻陽、靖州、城步、緩寧等廣泛的大湘西廣闊區域,這些地域地勢險惡、生存環境惡劣。而且苗族先民在歷史上屢受驅逐和歧視,為了躲避災難和戰爭,尋求穩定的生存環境,多次遷徙,不斷深入人跡罕至的大山腹地。因此,大湘西苗族多處于深山溝壑,人跡罕至的地方,過去苗人和外界很少接觸,與大自然和諧共存,依靠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本民族的頑強不屈延續著苗族發展,并創造了豐富和獨特的苗族傳統文化,因此他們更深刻地認識到自然的意義,這些內容深刻地體現在苗族的古歌及神話傳說中。大湘西苗族先民在惡劣的地域環境中,在與大湘西的山川、河流、密林的交融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為了生存發展需要的傳統體育運動形式和獨特的苗族體育文化,如百獅會、龍舟競賽等苗族傳統體育盛會,以及苗族弩射、苗拳、鼓舞等傳統體育項目,這些都源于苗族人民在山區地理環境中獲取生存資源的活動形式[7],體現出苗族的地域文化特征。
2.3 侗族的地域傳統體育文化
侗族主要分布于懷化市的新晃、芷江、通道、靖州、會同和邵陽市的緩寧等縣,位于湘西南溝壑縱橫的山地。侗族是一個山地民族,在崇山峻嶺、溪河密布的山區、半山區地帶,經過長期的探索和一輩又一輩先民的艱辛實踐,漸漸形成了有別于其他民族而又體現著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精神的傳統農耕生計方式[8]。山谷形成的峒是發展稻作農業的理想場所,使其稻作文化豐富多彩,產生了獨具一格的傳統文化藝術。其中“搶花炮”作為侗族地區流行最廣的傳統體育項目,是稻作文化在侗族地區民俗文化活動中的重要體現,充分表現了侗族的民間信仰、社會交往和鄉土文化功能,是與地域文化密切相關的侗族獨特的傳統體育文化形式。同時侗族也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民俗節日文化更是絢麗多姿,在這些節日中“多耶”、蘆笙踩堂、侗族斗牛、舞龍舞獅等傳統體育項目更是不能缺少,體現了農事習俗、祭祀習俗、生活習俗、社交習俗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侗族的地域文化特征。
3 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的地域文化特征
3.1 體現了大湘西各民族的悠久歷史
地域體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屬概念,是指一定地域范圍內人們以自然地理環境、風土民俗文化為背景所從事的與體育相關的身體活動的總稱[9]。由此,在不同的地域環境中會產生與之相統一的體育活動形式,正如“南人善泳、北人善騎”。地域體育文化是一種社會實踐,具有歷史和傳統性[10]。大湘西各少數民族先民自古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為了生存發展長期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斗爭、與外來的入侵抗爭,在與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沖突中實現交融發展,逐步形成了大湘西地區特有的傳統體育運動形式。
大湘西的土家族、苗族和侗族等少數民族都是歷史悠久的世居民族,長期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生息與共、不斷壯大,產生了絢麗多姿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民族體育文化。其中,土家族的“擺手舞”“茅古斯舞”,苗族的“鼓舞”“劃龍舟”,侗族的“搶花炮”“跳蘆笙”等傳統體育項目,是這些少數民族在本民族歷史發展長河中,適應地理環境和生存發展需要,與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信仰相統一,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身體活動形式,并完全融入到了這些民族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是群眾日常生活節律的體現,是日常的生產和生活勞動技能的展現,是本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教育手段和日常交往過程,體現了大湘西各民族的悠久歷史文化傳統。
3.2 呈現出大湘西地理環境的差異
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孕育而生,離開了地理環境這一基本的要素就無從談起這一文化及其特征[11]。大湘西地理環境的差異性,造就了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同樣具有大湘西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反映出大湘西不同區域生態環境所產生的地域文化,并與大湘西各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無論何地,文化的創造無疑是這一地域的居民在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發展生產過程中文明進化的必然產物。大湘西各民族所產生的傳統體育也脫離不了本區域的地理環境特點,是大湘西各族群眾在長期的社會生產實踐過程中,適應不同地理環境而逐步形成的身體活動方式,具有極強的地域性特點和地理環境的差異性。
在大湘西各區域生態環境中,武陵山巖溶山地生態區,屬湘西北地區,該區域山勢陡峭,峽谷幽深,人居生存環境險惡,生活在該區域的不同民族,為了適應生態環境,產生了鬼谷神功(一種傳統武術)、擺手舞、上刀梯、茅古斯、苗鼓舞等與該地理環境相適應的傳統體育項目;沅(陵)麻(陽)紅巖盆地生態區,處在湘西北、雪峰山中部和湘西南之間,該區域陵崗地面積大,山丘開發程度高,人居生存環境較險惡,生活在該區域的不同民族,為了適應生態環境,產生了劃龍舟、民俗舞龍舞獅、高腳馬、苗族武術、苗族斗牛等大量與該地理環境相適應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雪峰山中部山地生態區處在漣邵巖溶區、沅麻紅巖盆地區、雪峰山南部山區、新晃、通道中低山區之間,地貌以中山山地為主,次為丘陵崗地,該地域人居生態環境相對較好,生產力水平較高,生活在該區域的不同民族,為了適應生態環境,產生了如雪峰山民俗舞龍、沅水龍舟競渡等大量與該地理環境相適應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新(晃)通(道)中低山生態區包括新晃、會同、靖州、通道的全部,地勢南、北較高,中部略低,該地域植物生長繁茂,水稻種植為主,人居環境較優,生產力水平較高,生活在該區域的不同民族,為了適應生態環境,產生了侗族跳蘆笙舞、侗族斗牛、搶花炮、板鞋競速等大量與該地理環境相適應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大湘西不同地域,由于地理環境和地貌特征的差別,產生了不同的生態環境,形成了不同的生計方式,并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傳統體育文化,體現出大湘西地理環境的差異性。
3.3 展現了大湘西各民族的文化共性
大湘西地域文化區是以該地域獨特的地理環境為基礎的,長期生活在這塊神奇土地上的各民族群眾在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過程中產生的傳統文化,是該區域內與區域間多種文化沖突、融合的歷史發展過程形成的,并逐步形成了現在廣泛分布于大湘西各民族之間的傳統體育文化。
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體育的形式、結構和方法,尤其是在人類社會的初期,自然地理環境對體育的影響更直接[12]。大湘西多崇山峻嶺、溶洞暗河,生產力水平低下,各少數民族在這方以大山為主的土地上,在長期的生存斗爭和社會實踐中創造和形成了獨特的不同于其它區域和民族的山寨民族體育文化[13],與大湘西崇山峻嶺等環境相融合的山寨民族體育文化,體現了大湘西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共性。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豐富多彩,分布于大湘西不同地域和各少數民族之中,其中包括擺手舞、舞龍舞獅、武術、劃龍舟、斗牛、鼓舞、上刀梯、茅古斯舞、搶花炮、耍春牛和蘆笙踩堂等傳統體育運動項目,這些項目產生和形成于大湘西各民族的采集、耕種、漁獵、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等活動之中,受到大湘西獨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的深刻影響,體現了大湘西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俗文化意涵,具有大湘西各民族在生產、生活和信仰方面的文化共性,與大湘西獨特的地域文化相統一。
4 結語
大湘西境域內居住著土家、苗、侗、瑤、白等40多個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盤踞在地理環境險惡和地域特征差異明顯的大湘西不同區域,產生了與該地域生態環境和不同少數民族傳統生計方式相統一的地域傳統體育項目。這些傳統體育項目體現了大湘西各民族的悠久歷史、呈現出大湘西地理環境的差異性、展現了大湘西各民族的文化共性等地域文化特征。對大湘西各民族傳統體育地域文化進行研究,能夠更好地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發現大湘西地區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表現形式、文化內涵、價值功能等方面的異同,更好地把握大湘西不同民族的傳統體育文化特征,更精準地促進大湘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保護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