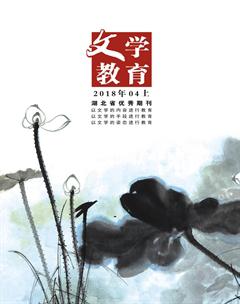評劉麗華的《載滿記憶的顏色》
劉麗華的創作,近兩年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從對哈爾濱老建筑寫作的開始,內傾的態度,凸現的越來越明顯,擺脫過去小抒情的寫作,進入歷史和文化記憶的思考。
劉麗華的散文新作《載滿記憶的顏色》,寫了少年時看過的綠皮火車,穿行在松林與小站間,它呼嘯而來,留在身后的是風聲和光線。挾著時間的風,沖開委積塵封的日子,她描述的綠皮火車,移覺各種感官,彼此挪移轉換,表示自己童年時的獨特感受。“我想象不出他們從哪里來,又去往哪里,他們終是要有個目的地的,正如他們曾經有過來處。一些東西在他們之間閃著光亮,那是陽光的回流效應,但這未能阻止車體內的躁動。當我的目光穿透空氣中的粒子,于某一處定格的時候,那些混亂的聲音依然以不同方式發出回響。”
她目睹一閃過去的綠皮火車,通過孩子的心中,發出對世界茫然的疑問。火車帶著風聲和煤煙味消失,兩根鋼軌泛著陽光,晃得眼睛有些疼痛。從這時開始,為什么?在遠方,猶如鋼軌一般,在心靈中向遠方延伸。瞬間的斷片,使孩子成長,這種痛苦影響一生。一個大的無法回答的問題,從視野中墜落,大地在喪失,讓孩子單純世界碎裂,有了漂泊的萌芽。
劉麗華無法忘掉少年的記憶,火車在旅途中留下的軌跡,依然清晰可辨,未隨著時間的黑暗模糊,甚至消失。當她對生命提出問題,在不斷地追問中,尋找生命的真諦。“綠皮火車在空曠的田野上飛馳,縱橫交錯的土地和林林總總的房屋被甩在身后。一縷煙霧尾隨車體彌漫出柴油的味道,擴散于空氣中。那些高低錯落、凸凹相間的山丘呈現出迷人的色彩,似水墨畫般駐入我們的視野中。一些旅客推開窗子,極力地呼吸,既享受泥土的馨香,又欣賞山野的神秘。”行走不是一般意義的旅途,從出發到目的,途中所經受的人與事,有色彩,有溫度,有獨特的感受。
一朵光焰燃燒,在身體里生長。這樣的感受,漫出的溫度帶著時間性,劉麗華對速度格外的敏感,每移動一步,時間就發生變化,留下的是記憶。奔跑的火車,非憑空虛構的產物,或用知識編織的想象,它是生命的舞臺。劉麗華有著自己獨立的感悟,綿密的筆致,呈現不同任何人的思想和情感。散文不要囿于字的表面,將文字變成散兵游勇,可以隨意的寫,牽強附會的拼湊。任何事物都有規律,好散文隱藏字句里,不是流于表層的浮淺,夸大其詞的自擂,大張旗鼓的花架子。
劉麗華的敘述,不是堆垛文字,淺白無味。時間是最好的證人,無需多余的話語吹捧,文字是生命的述說,對世界,對于人。文學不需要虛情假意,真情是文學的地基,如果缺少牢固的地基支撐,再高的樓也要塌落。散文必須有先鋒的思想切割生活,更多的關注人的生存狀況。
運輸工具的改進,使人類和世界發生巨大的變化,不可能事情變成為現實。大地突然間的收縮,使人們茫然的尋找答案。現代人生存的焦慮,如何為自己的定位和認同,擺在現實的面前。
故鄉依附在大地,那是血脈的源頭,它與漂泊者的牽掛,是保護心靈的地方。劉麗華所說“那聲音旋轉著,仿佛要擊毀車體的內臟才肯罷休。”強力的聲音形成一陣風暴,清除一切,摧毀一切。火車載著聲音的風暴,如今成為遙遠的故事。現在人是遠程相聚,屏幕上的影像記憶,感受不到生命的體溫,渴望地等待。
網絡的傳輸改變現實,坐在屏幕前,可以去世界任意的角落周游。聽各種鳥兒啼叫,看諸多的動物。這些聲音都是真空的,沒有旅途的軌跡,光標的閃動,使人的視覺匆忙地走過。不論去任何地方,都缺少陌生的新鮮感,還沒有到達之前,在網上搜索一下,電子風景、街道躍然而出,一目了然。人未離開原地,心已經漫游遠方。
作家不是收藏家,熱衷于對物品的搜集、儲存、分類與維護的癖好。回憶中修復時間的碎片,用情感的黏合劑,把它們重新粘貼在一起。循著紋絡察看每一處細節,挖掘歷史的真實。一座老站,在陽光下掙扎,鋪在大地上的陰影,瘋狂的吮吸光線,光明和陰暗糾纏著、晃動著。“由小站到老站,兩點一線的距離,我已往返多年。車廂里的故事在這密集與稀疏、真實與抽象的空間里依次上演。它折射的不僅僅是故事背后的生活,更是一段段鮮活的歷史。即便這抹墨綠已經退出人生舞臺,但它卻以精確的筆調,繼續將生活敘述下去。”劉麗華的少年記憶,在光線的強光下復活,回憶中獲得重生。文學不是復制生活,而是從生命中流淌出來的,能沖沒虛偽、浮躁。作家在剖析一段歷史,她作為年輕的女性,沒有陷于小情調的寫作中,那列綠皮火車從過去駛來,又向遠方奔去。車廂里的人與事留在時間中,劉麗華用文字描寫的這些事情,不會讓現實的法則毀壞掉,它是對語言的神性膜拜,和對時間的敬畏。
當綠皮火車掀掉蒙上的灰塵,跑進被技術切割碎裂的現實世界,它們相撞的時候,作家在修復真實的歷史,尋找心靈的返鄉之途。
寫作是生命的投入,用體溫暖熱文字,創作出來的作品不會浮躁。
高維生,著名散文家,出版散文集、詩集三十余種,主編“大散文”“獨立文叢”等書系,現居山東濱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