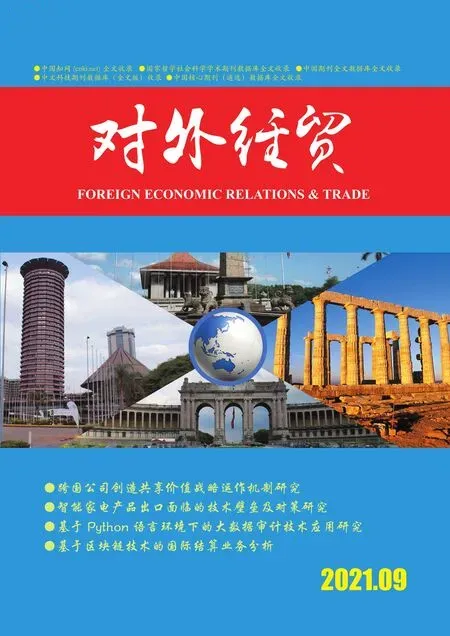公正世界信念研究綜述與展望
寧玉梅
(1.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2.玉林師范學院 商學院,廣西 玉林 537000)
一、公正世界信念理論的概述
(一)公正世界信念的概念
Lerner 在20 世紀60 年代最早提出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BJW)理論,并于80 年代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公正世界信念理論提出:人們相信其生活在一個得其所應得,所得即應得的世界。簡單地說,就是人們相信“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的信念。人們相信其生活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結果是可以預測的世界。這使得人們對世界有安全感和控制感。由于這種信念具有適應性功能,相反的證據具有高度的破壞性,因此人們有強烈的動機采取措施來確保他們的信念得到維持[1]。
(二)公正世界信念的維度
公正世界信念分為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和對他人的公正世界信念。即個體可以通過將自己的世界與受害者的世界分開來捍衛自己的公正世界信念,也就是說當個體觀察到一個無辜的人痛苦時,個體可以在心理上把他們放在一個單獨的世界里。有了這種合理化,觀察者們遠離了受害者,并保護了他們所居住的世界是公正的這一信念。
(三)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
當人們遇到如無辜者蒙難,好人遭厄運,與公正世界信念相違背的卻又普遍存在于現實生活的事件時,人們會有強烈的動機采取對受害者的幫助和補償(親社會)等的實際方式或對負面評價受害者的性格或品行,以消極的眼光看待受害者的命運,通過貶低、責備受害者等的心理方式來捍衛公正世界信念。
但是為什么人們需要相信一個公正的世界,并因此首先捍衛這個信仰呢?其原因是公正世界信念具有使個體能更好適應社會的功能。第一,更強的公正世界信念與更強的幸福感有關[2]。原因是公正世界信念在面對艱難環境時提供了一種對壓力的緩沖[3],與對他人和機構的信任有關[4]。第二,公正世界信念程度越高的人,越愿意抵制眼前的滿足,堅持追求更大、更長期的回報[5]。因為公正世界信念向人們保證,親社會行為是獲得長期回報的最有效方式:在一個公平的世界里,人們會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積極價值的貢獻(親社會行為)會導致長期的積極結果,而消極價值的行為會導致消極結果。第三,公正世界信念降低了人對死亡的恐懼[6]。因為如果讓人們面對死亡的現實而沒有任何心理防御,人們將會被恐懼所麻痹。而公正世界信念為個體應對這種沖突提供了緩沖。第四,公正世界信念為個體提供了生活的目的感,所以當個體的公正世界信念程度低時,其生活的目的感也低[7]。因為公正世界信念把這個世界描繪成一個個人可以獲得有價值的結果的世界,但只有當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時才可以獲得這些有價值的結果。
因此,公正世界信念具有正面和負面功能。公正世界信念具有使個體能更好適應社會的正面功能;而在對待遭受不公正事件的受害者上,則可能存在扭曲認知,冷漠和歧視受害者的負面功能。
二、公正世界信念理論的實證研究
對國內外核心期刊關于公正世界信念理論的文獻進行整理,總結出公正世界信念的前因變量、結果變量和公正世界信念作為中介變量、調節變量的實證研究。
(一)公正世界信念的前因變量的實證研究
Lerner 等(1976),Lerner(1977),Lerner和 Clayton(2011)提出,由于人類有發展內在方面(即從眼前的滿足轉向對長期目標的投資)的需要,因而大多數人在一個相對穩定環境的情況下會有形成對相信公正世界的需要。因此,公正世界信念的前因變量的研究表明,個體捍衛公正世界信念的動機主要是個體發展內在方面的需要。
(二)公正世界信念的結果變量的實證研究
Dalbert(1999),Sutton 等(2017)認為,具有較強的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而不是對他人的公正世界信念)的個體,其往往有更高的心理幸福感、積極情緒、感恩感、生活滿意度。此外,其感知到的學校壓力更低、有更積極的學校態度和更高的學術自尊和享受學校(Donat 等,2016)。Carfio 和 Nasser(2012) ,Nasser等(2011)發現,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與老年人整體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嚴重抑郁癥狀的減輕有關。它還與尋求報復、缺乏反思和沖動負相關(Strelan,2018)。
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在許多社會領域都與親社會結果相關。在組織中,具有較強的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的員工更有可能參與有利于組織的員工角色外的活動(Spence 等,2011)。具有較強的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志愿者其幫助他人的態度更積極(Correia,Salvado,& Alves,2017)。
因此,公正世界信念的結果變量的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給個體帶來的功能主要包括幸福感、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及公正世界信念給個體帶來的結果主要是親社會行為。
(三)公正世界信念作為中介變量的實證研究
國內學者陳亮等(2020)認為,公正世界信念是個體在兒童期遭受到心理虐待而使其在成熟期產生網絡欺凌行為的原因。劉廣增等(2020)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問題行為的中介因素。郭成等(2019)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是青少年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心理韌性的中介因素。田志鵬等(2017)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是兒童期虐待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中介因素。田媛等(2017)提出,網絡社會支持通過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影響中職生的生活滿意度。郭英等(2016)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是社會支持影響服刑人員的社會適應的中介因素。張莉等(2015)提出,父母支持和抑郁通過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影響生活滿意度。劉莉等(2015)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是社會支持影響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的中介因素。周春燕等(2013)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是家庭社會階層影響心理健康的中介因素。
國外學者Jian-Bin Li(2020)基于社會示威及新冠病毒爆發的情境研究,發現社會困境通過公正世界信念負向影響積極的未來目標。Xunlong Tian(2019)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既起到了大學生的負面生活事件與生活滿意度關系的中介作用,也起到了調節作用。
因此,公正世界信念作為中介效應的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如何以及為什么作為個人資源發揮作用的重要性。
(四)公正世界信念作為調節變量的實證研究
國內學者李志成等(2020)研究結果發現,公正世界信念不僅能調節職場不文明行為對旁觀者道義公平的作用,而且調節了道義公平在職場不文明行為與旁觀者工作有效性關系中的間接效應。侯玉波等(2019)發現,公正世界信念調節了網民的主觀階層認同與對網絡沖突事件的處理之間的關系。張陸等(2018)發現,公正世界信念調節了社交焦慮與手機成癮的關系。曹元坤等(2015)提出,公正世界信念在辱虐管理與敵對情緒之間起調節作用。
國外學者EC Hoolihan 等(2020)提出,公正世界信念調節了社會資本與心理健康的關系。Mingzhong Wang 等(2019)提出,公正世界信念調節了父母不偏袒行為與生活滿意度的關系。Jiang Ronghuan 等(2018)提出,公正世界信念和師生關系調節了青少年教師正義與學生班級認同之間的關系。Yubo Hou 等(2017)提出,公正世界信念調節了社會經濟地位和網上羞辱之間的關系。
因此,公正世界信念作為調節效應的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在因果關系中發揮調節作用的重要性。
三、公正世界信念理論的不足與研究展望
大量研究已經確定了公正世界信念與幸福感、積極的未來方向和實現人生目標及親社會行為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以及公正世界信念在面對無法解釋的災難、延長的負面生活事件、身體或精神疾病時的適應性應對。然而,公正世界信念如何以及為什么導致這些適應性的結果尚不清楚。因此,未來可以基于公正世界信念理論的基礎上延伸研究,以更深入了解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對于公正世界信念的水平測量,Dalbert(2001)利用截面數據發現,個體生命全程中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呈“U”型趨勢。未來應該采用追蹤研究更準確清晰地刻畫這一趨勢。且大多研究僅測量了個體在生命某一時點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其主要集中在12—21 歲的學生或大學生的測量,較少有研究針對幼童,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測量。由于不同群體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發展不同,未來研究應該對不同群體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進行測量,并充分考慮導致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存在顯著差異的影響因素。對于公正世界信念的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分析,大多學者主要利用截面數據及自我報告的調查問卷數據進行研究而導致不能準確檢驗公正世界信念與前因變量或結果變量的因果關系,未來應當采用追蹤研究以及嚴密的實驗設計方法,對公正世界信念的影響機制和結果變量進行探究。且在關于公正世界信念的前因變量的研究中對于個體為什么捍衛公正世界信念的機制解釋并不詳盡,未來可以在公正世界信念的前因變量研究的基礎上延伸,以便更清晰和更完整地理解個體捍衛公正世界信念的動機。對于公正世界信念作為中介作用或調節作用分析,未來應深入研究公正世界信念具體是通過哪個因素或哪些機制起到了中介或調節作用,以便進一步剖析公正世界信念作為中介作用或調節作用的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