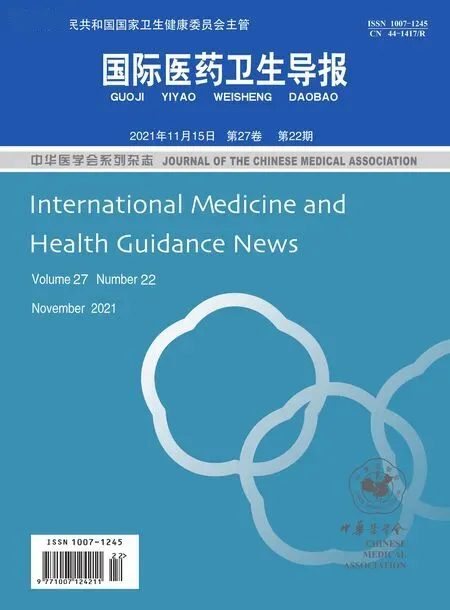血漿D-D和FDP的聯合檢測對髖關節置換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的預測價值分析
林靜 鄭燕丹 李啟欣
廣東省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檢驗科 528000
髖關節置換術是當前是治療中老年髖關節骨折的有效方法之一,可重建髖關節功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1]。隨著醫學技術的提高,髖關節置換術的微創性越來越高,患者術后康復時間也越來越快,但是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在臨床上依然比較多見[2]。下肢DVT為一種深部血管阻塞性疾病,導致靜脈回流障礙,引起遠端靜脈高壓,臨床上主要表現為肢體腫脹、疼痛及淺靜脈擴張等,可造成不同程度的慢性深靜脈功能不全,嚴重時可致殘。此外,下肢深靜脈血栓可發現移位,嚴重者將發生急性肺、腦、腎的栓塞,導致患者發生猝死。靜脈造影是診斷下肢DVT的金標準,但是為有創性檢查,臨床上廣泛推廣的可行性比較差[3]。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下肢DVT比較方便,但是檢查結果的準確度及敏感度有所欠缺,存在滯后性,并且主觀性較強。現代研究表明纖維蛋白降解產物(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s,FDP)、D-二聚體(D-D)可作為DVT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兩者可反映體內凝血和纖溶過程的變化,都是血液發生血栓及血栓前狀態的凝血及纖溶系統活性改變的分子標志物,也是血栓形成或溶解的標志[4]。其中D-D是纖維蛋白的降解產物,診斷活動性纖溶較好的指標,對血栓形成性疾病如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DVT形成、腦血管疾病、肺栓塞、肝臟疾病、惡性腫瘤、外科手術后、急性心肌梗死等疾病均有重要的診斷價值。FDP是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主要反映纖維蛋白(原)的溶解功能。在纖維蛋白原大量被分解所引發的原發性纖溶亢進發生時,FDP含量明顯升高。在高凝狀態、肺栓塞、惡性腫瘤、靜脈血栓、溶栓治療等所致的繼發性纖維亢進時,FDP含量亦升高。FDP是反映纖溶亢進的敏感指標,是血栓已被溶解的直接證據[5-6]。本文探討與分析了血漿D-D和FDP的聯合檢測對髖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的預測價值,以明確兩者聯合使用的預測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完成髖關節置換術的患者113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順利完成髖關節置換術,術中無嚴重并發癥發生;符合髖關節骨折的診斷標準;所有患者手術均由同一組手術團隊完成;年齡55~75歲;單側手術;臨床資料完整;首次進行髖關節置換手術;術前1 d已經抽血檢查D-D和FDP。排除標準:既往有肢體靜脈血栓疾病史者;既往史中有血栓性疾病的患者;既往有精神疾病或意識不清的患者;合并嚴重頭顱外傷或急性脊髓損傷的患者;存在全身、局部或其他臟器器官急性感染患者;妊娠與哺乳期婦女。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了此次研究。
1.2 術后預防方法 術后留置引流管,術后夾閉引流管4 h,積極補充血容量。術后第1天開始小腿三頭肌、股四頭肌的等長收縮,促進血液循環;術后第2天開始鼓勵患者下床活動。術后開始給予患者5 000 IU低分子肝素鈣皮下注射。
1.3 血漿D-D和FDP檢測(1)所有患者在術前1 d、術后1 d、術后3 d、術后7 d抽取空腹外周靜脈血1.8 ml,采用藍色頭檸檬酸鈉抗凝管(1∶9)抗凝,充分混勻后1 500×g離心15 min分離乏血小板血漿,使用希森美康CS-5100全自動血凝分析儀進行檢測血漿D-D和FDP含量,所用試劑均為儀器廠家配套試劑。D-D和FDP正常參考區間:D-D 0~0.55 mg/L,FDP 0~5 mg/L。(2)在術后7 d進行彩色多普勒超聲,下肢DVT判斷標準:無血流或頻譜不隨呼吸變化,血栓段靜脈內完全無血流信號或僅探及少量血流信號,管腔內為低回聲或無回聲,靜脈管腔不能壓閉。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統一匯總數據庫,采用SPSS21.00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對比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百分比表示,對比采用χ2檢驗,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判斷預測價值,檢驗水準為α=0.05,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血漿D-D和FDP變化對比 所有患者術后1 d、術后3 d、術后7 d的血漿D-D和FDP值均高于術前1 d(均P<0.05),隨著術后時間的增加,血漿D-D和FDP值逐漸降低(均P<0.05),見表1。
表1 113例髖關節置換患者手術前后血漿D-D和FDP變化對比(mg/L,±s)

表1 113例髖關節置換患者手術前后血漿D-D和FDP變化對比(mg/L,±s)
注:D-D為D-二聚體,FDP為纖維蛋白降解產物
?
2.2 下肢DVT發生情況 在113例患者中,術后7 d發生下肢DVT 12例,發生率為10.6%。DVT組的性別、年齡、手術位置、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等與非DVT組對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髖關節置換患者一般資料對比
2.3 術前血漿D-D和FDP對比 DVT組術前1 d的血漿D-D和FDP值都高于非DVT組,其中FDP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髖關節置換患者術前1 d的血漿D-D和FDP對比(mg/L,±s)

表3 兩組髖關節置換患者術前1 d的血漿D-D和FDP對比(mg/L,±s)
注:DVT為深靜脈血栓,D-D為D-二聚體,FDP為纖維蛋白降解產物
?
2.4 預測價值 D-D、FDP預測髖關節置換術后患者下肢DVT的最佳閾值為1.045 mg/L和2.655 mg/L,兩者聯合預測下肢DVT的曲線下面積為0.927[95%可信區間(0.859~0.996)],見表4、圖1。

圖1 D-D、FDP及聯合檢測對113例髖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形成的ROC

表4 血漿D-D和FDP的聯合檢測對113例髖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的預測價值
3 討 論
下肢DVT是髖關節置換術后常見且嚴重的并發癥,嚴重情況下可導致患者死亡。現代研究表明DVT形成的因素包括高凝狀態、血小板增高及功能異常、紅細胞變形性下降、血液淤滯加重等[7]。特別是手術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損傷微小血管內皮,會導致血小板活化、凝血的啟動、血栓的形成[8]。同時術后長期制動可使得下肢處于被動體位,靜脈血流緩慢,使血液處于高凝狀態,這些原因均可導致下肢DVT的發生,嚴重者可繼發肺動脈栓塞而危及生命。本文研究了113例患者,術后7 d發生下肢DVT 12例,發生率為10.6%,比聶廣龍等[9]研究發現髖關節置換術后患者DVT發生率21.6%較低,可能與醫院髖關節置換術較年輕化和只統計了較短時間內的DVT發生結果有關。
國內研究者周斐[10]對骨科髖部骨折患者的預后做了跟蹤隨訪,發現術后1年內病死率約為7.77%,但其中死于肺栓塞的概率為28.75%。這表明骨科患者術后死因中肺栓塞所占比重很大,而術后導致的下肢DVT是肺栓塞發生的最重要危險因素之一。因此,尋找骨科手術中下肢DVT發生的敏感指標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主要研究血漿D-D和FDP兩個檢驗指標對髖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的預測價值。人體內的抗凝系統主要由纖維蛋白溶解系統調節凝血活性,阻止血栓的發生。D-D是交聯纖維蛋白經纖溶酶降解后生成的特異性降解產物,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血栓性疾病的病理生理變化。D-D增高反映機體高凝狀態和繼發性纖溶的增強,是反映凝血和纖溶的理想指標。相關研究認為:D-D在臨床上已被視為體內高凝狀態和纖溶亢進的分子標志物,其存在表明體內有血栓形成并溶解,但該指標并非血栓存在的金標準標志物[11-12]。而FDP是纖維蛋白/纖維蛋白原在纖溶酶的作用下所產生的各種降解產物的總稱,主要反映纖維蛋白(原)的溶解功能。在高凝狀態、肺栓塞、靜脈血栓、溶栓治療等所致的繼發性纖維亢進時,FDP含量亦升高[13-15]。本研究顯示DVT組術前1 d的血漿D-D和FDP值都高于非DVT組。從機制上分析,D-D和FDP值在血液中的濃度高低均能夠體現繼發性的纖溶活性,若濃度升高代表活性增加,表明體內出現了高凝狀態。而如果體內處于高凝固狀態,在手術一系列創傷和術后制動的因素下,更有可能導致下肢DVT的發生。另外,本研究顯示所有患者術后1 d、術后3 d、術后7 d的血漿D-D和FDP值均高于術前1 d(均P<0.05),隨著術后時間的增加,血漿D-D和FDP值逐漸降低(均P<0.05)。可見,血漿D-D和FDP雖然是骨科患者常規檢查項目,但都是反映纖溶亢進的敏感指示,可用于DVT篩查,血漿D-D和FDP的檢測對高凝狀態和血栓形成性疾病的早期診斷、療效觀察和預后判斷都具有重要意義。
檢測患者血漿D-D、FDP水平,對DVT篩查均有較大參考價值,本文的觀點和多位學者研究觀點一致[10,16]。不過單獨進行D-D與FDP檢測預測DVT的特異度容易受其他因素影響,單獨檢測D-D與FDP升高并不能說明一定有血栓存在。本研究顯示D-D、FDP預測髖關節置換術后患者下肢DVT的最佳閾值為1.045 mg/L和2.655 mg/L,兩者聯合預測下肢DVT的曲線下面積為0.927[95%可信區間(0.859~0.996)]。這表明D-D、FDP預測下肢DVT各具優勢,聯用兩個檢驗指標進行預測可以減少漏診、誤診風險。究其原因可能與D-D、FDP檢測在特異度與靈敏度方面各有不同有關,有研究表明D-D靈敏度較低,但特異度較高,而FDP的靈敏度較高,但缺乏特異度,兩者配合,可相互彌補兩者各自的不足[17]。不過本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研究的樣本較少,研究對象不具有普遍代表性,研究機制分析不夠深入,將在后續研究中進行深入分析。
綜上所述,髖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比較常見,也伴隨有血漿D-D和FDP升高,血漿D-D和FDP的聯合檢測能有效預測下肢DVT的發生。
利益沖突:作者已申明文章無相關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