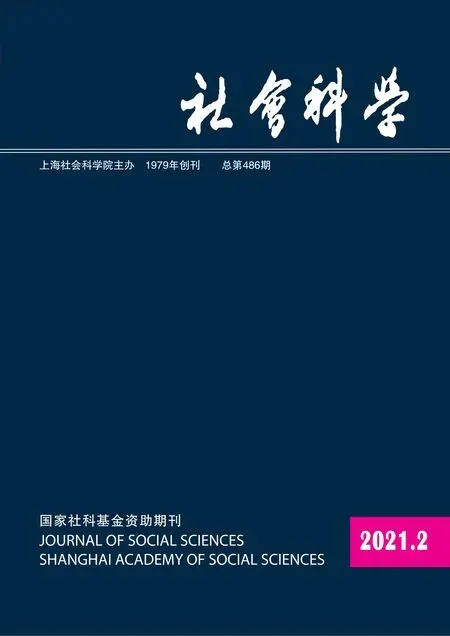“政治戰”視域下特朗普政府對華意識形態攻勢:特點、影響和內在機制
倪建平
自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將我國鎖定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的戰略界、安全界、政界、學界、思想庫和媒體便將注意力集中在與中國進行長期戰略競爭的“政治戰”上(1)CNAS Report, “Protracted Greatk-Power Wa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eb., 2020.。近三年來,特朗普總統無縫整合美國國家權力的多個要素(外交、信息、經貿、金融、情報、執法和軍事),推動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朝著“縱向升級”的遏制方向演變(2)CSBA Report, “Forging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2020.。其中,美國戰略界、安全界和智庫以中國“影響力行動”為主旨框架,先后發表了20余份研究報告,對中國十八大以來為提升國際影響力所做的各種努力橫加指責,發起了包括信息戰在內的愈演愈烈的意識形態攻勢。特別是2020年初以來,特朗普政府更以美國大選為契機,凸顯“政治戰”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重要作用,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5月20日,白宮公布了《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首次將“價值觀挑戰”與“經濟挑戰”“安全挑戰”并列為中國對美國的三大威脅,為對華全面戰略競爭展開進一步的政治動員(3)https://translations.state.gov/2020/05/20/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本文以美歐智庫聚焦中國影響力行動的研究報告為依據,以冷戰時期美國對蘇“政治戰”為研究出發點,闡述特朗普政府對華意識形態“政治戰”的特點、影響和內在機制,以期更深入地追蹤和研究日趨嚴重的中美意識形態沖突,有效應對美國對華的“政治戰”攻勢,努力改善我國在國際上的戰略處境和安全環境。
一、“政治戰”:冷戰史視角的基本涵義
近年來,隨著美國對華整體戰的逐步展開,“政治戰”也逐漸進入美中兩國智庫和學界的研究話語,并日益得到關注(4)唐健:《大國競爭背景下的美國政治戰》,《國際關系研究》2020年第5期;王鴻剛:《中國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政治戰》,http://www.crntt.com/doc/1059/1/8/3/105918322.html?docid=105918322; Seth G.Jones, “The Return of Political Warfare”,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turn-political-warfare; Rand Report, “Modern Political Warfare, Current Practice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772.html; Hal Brands and Toshi Yoshihara, “How to Wage Political Warfare”。。但是,這也難免會出現“誰也說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況,其概念的界定和涵蓋的現象比較寬泛和極不明確,帶來的問題是兩國政策層面以及學界對“政治戰”的討論趨于表面化和缺乏完整性。面對美國對華發起的日益咄咄逼人的“政治戰”攻勢,有必要充分把握“政治戰”的內涵和外延。冷戰時期美國“政治戰”計劃的歷史為我們理解什么是“政治戰”以及采取什么應對形式提供了例證,也指出了美國今天對華發動“政治戰”的可能手段。以史為鑒,厘清概念。中美有關冷戰史的研究成果更能啟迪我們對“政治戰”這一概念內涵的提煉和闡釋。
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實施了遠比人們想象的更加具有影響力和穿透力的“政治戰”。美國與蘇聯在政治、軍事、外交、思想和文化領域進行了除直接戰爭以外的全方位競爭,采取了向蘇聯集團廣播、秘密和準軍事行動、經濟脫鉤政策、人權運動等一系列措施,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遏制共產主義,推廣西方制度模式,竭力抵制和削弱蘇聯在歐洲和更廣泛的“第三世界”的意識形態輿論攻勢,在全世界范圍內支援與美國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權,作為防止蘇聯影響力擴張的途徑,對那些他們認為有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奪權的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干預。時任美國國務院第一位政策規劃司主任、美國遏制戰略的設計者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就大力倡導美國對蘇聯戰略中發揮“有組織的政治戰”的重要作用。他對“政治戰”的定義依然是目前最常引用的定義之一:
“政治戰”是克勞塞維茨的原則在和平時期的邏輯應用。從廣義的定義來說,“政治戰”是指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利用一國統領下的所有手段來實現其國家目標。“政治戰”的行動既公開又秘密,包括政治聯盟、經濟措施(如“馬歇爾計劃”)和“白色”宣傳之類的公開行動,還有秘密支持外國“友好”團體、針對敵對國家施行的“黑色”心理戰甚至鼓勵地下等隱蔽行動(5)CSBA, “Forging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2020.。它可以包括像公共廣播這樣的公開行動和像心理戰這樣的秘密行動,以及對地下抵抗組織的支持(6)George F.Kennan, “Organizing Political Warfare”,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April 30, 1948,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4320.pdf?v=944c40c2ed95dc52d2d6966ce7666f90.。
在這個意義上,信息戰也是一種“政治戰”,其目標包括一個民族國家的政府、軍隊、私營部門和普羅大眾。無論是為了影響輿論或迫使決策者采取某種行動而攻擊政府機構、政治領導或新聞媒體,信息戰的最終目標都是人的認知。因此,信息戰有時被稱為勸說或影響力行動,甚至是心理戰(7)CRS, “Information Warfare: Issues for Congress”, Mar.5, 2018.。單從字面上看,凱南的定義暗示了“政治戰”可以涵蓋廣泛的行動范圍。正如凱南在1949年指出的,“政治戰”的兩個目標是“凝結我們的自由世界,增加蘇聯集團的離心力”(8)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對他而言,“政治戰”在當時就是美國應該在冷戰中采用一切手段來保護自己免受熱戰一樣的危害,這也就難以區分和平時期作為整體的外交政策的內涵和外延了。因此,近期就有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專家學者對凱南的這一定義加以提煉,指出“政治戰,作為一種廣泛的競爭戰略的一部分,就是使用除戰爭以外的各種措施來增加自身的影響力,損害對手的國家利益,使其社會陷于動亂并嚴重削弱其競爭力”(9)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顯然,這個概念更清晰地強調了對特定對手或敵人施展的“政治戰”舉措是展開大國競爭的一部分,也排除了諸如人道主義干預、氣候變化外交以及普通的外交政策倡議等國家的外交戰略基本目標。當然,這些外交舉措絕不是當年凱南稱之為“政治戰”的組成部分。
實際上,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三位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對蘇聯的“政治戰”就反映了凱南提出的“有組織的政治戰”的內涵范圍,這一時期(1947年至1956年)也是美國“政治戰”勃興的第一階段。從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冷戰中期,這一時期見證了美國“政治戰”攻勢的相對衰退。美國“政治戰”勃興的第二階段是卡特和里根政府時期,特別是里根總統在冷戰的最后十年復興了美國的“政治戰”。1983年,里根總統頒布了《國家安全決策指令》(NSDD 77),把國際信息、國際政治和國際廣播活動重新整合到“公共外交”的概念中,強調實施針對蘇聯的“真相(宣傳)計劃”,要求動員美國社會全部力量,推動他國民主政治機制的構建和其他民主實踐,反擊蘇聯及其代理人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侵略性政治行動。1985年,里根又頒布了《國家安全決策指令》(NSDD)159號文件,要求使用包括秘密戰在內的所有適當手段來反擊敵對力量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10)于群、白玉平:《冷戰時期美國的心理戰和宣傳戰》,載沈志華等《冷戰啟示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頁。。這些手段包括宣傳,經濟政策,外交和政治援助、政治行動,準軍事活動和情報援助等在內的秘密行動,它是冷戰期間美國“政治戰”的關鍵要素和有效工具。
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發動了防御性的“政治戰”,旨在挫敗蘇聯的“政治戰”倡議,保護美國社會及其盟國免受“惡的影響”(Malign Influence)。早在1948年,美國就通過經濟援助,支持外國友好的政治家、工會和政黨,公共外交以及其它秘密行動,減少共產黨在意大利和法國上臺的可能性。“馬歇爾計劃”提供了130億美元以振興西歐經濟,這在當時是一項雄心勃勃的運用經濟政策以實現美國戰略目標的計劃,它成功制止了西歐國家親蘇政治力量的興起。依據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統計,“馬歇爾計劃”主要參與國家及份額為英國(24.7%)、法國(21%)、意大利(11.7%)、德國(10.8%)等。從援助的形式上看,主要包括美元援助、技術協助、擔保金以及對等基金等。科技上對蘇聯封鎖,遏制其經濟發展,也提升了美國防御性“政治戰”的成效。凱南認為,盡管蘇聯可以輸出意識形態,但卻無法形成有效的經濟出口。如果西方以足夠的資源和力量對蘇聯政權遏制10年到15年,將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1949年,美國召集17個西方發達國家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禁運和貿易限制。在美國,根據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相關規定,制訂了《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出口管理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武器出口控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AECA)《國際武器貿易條例》等法律法規,阻止蘇聯獲得西方高新技術和武器裝備,使其不斷喪失經濟活力和軍事優勢。值得指出的是里根總統在1980年代的對蘇政策中,也強調利用美國的非對稱經濟優勢,拒絕蘇聯獲得美國高新技術。隨著信息技術在冷戰期間的發展,這在當時成為美國越來越強大的“政治戰”工具。美國以蘇聯衛星國經濟為目標的種種制裁,以及拒絕修建跨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的做法,使得已經過度擴張的蘇聯經濟雪上加霜。里根政府“星球大戰計劃”的實施成了蘇聯經濟被徹底拖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防御性“政治戰”方面,美國隨著冷戰的發展還對蘇聯發起了信息戰攻勢。這主要是通過采取反情報措施和協調機制,政府跨部門全力應對蘇聯通過發布虛假信息來增強其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里根總統于1981年成立的積極措施工作小組(AMWG),幫助建立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即蘇聯虛假信息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威脅。這個跨部門的工作組包括中情局、美國新聞署、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局、國防部和司法部,致力于發現蘇聯的影響力行動,并將其向美國公眾公開。積極措施工作小組通過發表公開年度報告——《蘇聯影響力行動:對積極措施和宣傳的報告,1986-1987》,宣傳蘇聯的虛假信息活動,增加了蘇聯制作虛假信息的聲譽成本,并最終說服了時任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接受虛假信息對推進蘇聯目標難以奏效這一事實。當時,在美國自由規范的推動下,活躍的美歐國家的新聞界在無美國政府協調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公共外交的信息戰活動,著力揭露蘇聯意識形態的虛偽性、蘇聯政府控制的虛假言論和政治壓制。他們的高專業水準也證明了反對蘇聯虛假信息的壁壘,針對那些制造虛假故事的手段,“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11)CSBA, “Forging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2020.。
冷戰期間,美國還實施了旨在重創蘇聯的進攻性“政治戰”,通過顛覆蘇聯集團的統治政權、增加其發展經濟的成本以及其它方面,破壞其與美國競爭的能力。美國當時采取廣泛的手段來增加蘇聯集團的離心力,包括支持這些國家的秘密抵抗行動、信息戰、經濟脫鉤政策、人權外交以及其它的意識形態壓力。然而,美國當時切中蘇聯統治集團軟肋的進攻性“政治戰”倡議也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激烈反彈,致使蘇聯動輒鎮壓其勢力范圍內發生的反蘇政治動亂。1953年6月17日,當時的駐德蘇軍出動坦克上街,鎮壓了發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場工人運動。另外,在蘇聯的兩次軍事干預下,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發生在匈牙利的由群眾和平游行而引發的武裝暴動事件也被迅速平息。為此,即使處于冷戰高潮時期的1950年代,美國官方也決然排除那些可能導致沖突升級的選項,以免引發不必要的、難以收拾的流血沖突。美國冷戰后期發動的進攻性“政治戰”都不得不考慮其它的目的和力量因素(12)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
冷戰時期,在對蘇聯的進攻性“政治戰”中,美國通過秘密情報活動開展“黑色宣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幫助拆除了歐洲和“第三世界”的蘇聯政治聯盟。里根政府還通過秘密行動,成功侵蝕蘇聯的政治影響力,并將蘇聯的注意力分散在許多緊迫和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之間。例如,美國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動致使蘇聯的政治意愿和財政資源都大為削弱,這被證明是美國“政治戰”非常成功的工具。據不完全統計,美國高層批準的、主要由中央情報局實施的大型秘密行動,杜魯門政府有81項,艾森豪威爾政府有170項,肯尼迪政府有163項,約翰遜政府(截至1967年)有142項。到了約翰遜政府和尼克松政府時期,由于中情局被迫面對國會質詢,并對“政治戰”進行重新定位,一部分秘密行動項目被中止,一部分項目被打上“絕密”標簽,迄今沒有解密,還有一部分項目卻由秘密轉向公開。以中央情報局1951年在亞洲開始實施的代號為“DTPILLAR”的大型秘密行動項目為例,其主要目標就是在亞洲成立一個秘密機構,“團結亞洲‘自由’國家的人民,共同反擊共產主義對‘自由’以及其他人類基本價值觀的挑戰”。該項目實際上就是其后數十年間在亞洲文化和教育援助領域發揮巨大影響力的亞洲基金會(原名自由亞洲委員會)。亞洲數所大學(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建、數十個“現代”專業方向的發展、無數大學生和“青年領袖”的培養、十多個刊物的創建、數個影業公司的實際投資,還有亞洲各圖書館中難以計數的捐贈圖書,都與該機構有關。1967年,亞洲基金會是中央情報局前線機構的事實被美國媒體曝光后,其身份轉為公開并直接接受美國國會的撥款(13)于群、白玉平:《冷戰時期美國的心理戰和宣傳戰》,載沈志華等《冷戰啟示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101頁。。
美國對蘇聯的進攻性“政治戰”,采取“黑色宣傳”的秘密行動,還包括中情局利用美國的文化影響力在整個“第三世界”引發親美情緒。例如,1950年,中央情報局(當時的OPC)秘密組織并資助了文化自由大會(CCF),該大會召集了來自西方各地的知識分子來反對共產主義,鼎盛時期在35個國家/地區設有辦事處,雇傭了數十名人員,并出版了20多個著名雜志。它舉辦了藝術展覽,擁有新聞和專題報道服務,組織了備受矚目的國際會議,并向音樂家和藝術家提供獎勵。中情局還秘密實施了“學說宣傳項目”,對該項目的功能定位是發揮“沖鋒在前”的作用,對于所有相關行動都會給予優先支持。圖書出版則是中情局“學說宣傳項目”的一個重要領域。在中情局的策劃之下,美國總計向蘇聯和東歐國家發放了1000萬冊圖書和其他出版物,這項行動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由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作為項目負責人的《日瓦戈醫生》的出版以及之后帕斯捷爾納克迅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冷戰時期一場意識形態斗爭的風暴。在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文件中,曾經這樣評價中情局在圖書傳播方面的作用:這個項目在直接接觸專業技術精英方面十分有效,通過該項目,加強了對文化自由的態度和傾向,以及對獨裁的不滿。
冷戰時期,美國進攻性的“政治戰”也是以“白色宣傳”的公開信息戰來實施的。1946年3月5日,前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反蘇聯、反共產主義的“鐵幕”演說,正式開啟美蘇冷戰的序幕;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就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發表演說;1987年6月12日,里根總統站在柏林墻的西德一側發表被“視為冷戰的轉折點”的演說,呼吁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倒柏林墻。官方公開的、系統的破壞性宣傳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蘇聯開展信息戰的重頭戲。不同于三位前任總統尼克松、福特和卡特,里根總統的“政治戰”策略解除了緩和“蘇聯用來追求自己目標的單行道”,強化對蘇聯及其衛星國的意識形態攻勢。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開展公開的信息戰,除了美國之音連篇累牘地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問題,還有為了配合匈牙利的“自由運動”,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在東歐劇變期間充分利用富布萊特項目的運作機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20世紀80年代對波蘭團結工會和公民社團的支持,資助和推進這些國家的自由化運動項目。美國認為,在與莫斯科開展全球的意識形態競爭中,毫不畏懼地支持民主價值觀本身對蘇聯就是一種壓力,可以通過捍衛美國的外交傳統和價值觀來贏得競爭優勢。如果說“政治戰”的一個關鍵目標是要利用競爭者體制的軟肋,那么,公開或直接瞄準其最糟糕的發展趨勢就是非常強有力的,它們還有助于避免秘密倡議不斷陷于被揭露或公開,以及由此引發的負面效應(14)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
正如美國外交政策的大多數方面,美國“政治戰”一般都是由政府部門或準政府機構實施的,包括中情局、國務院和國家民主基金會。但美國進攻性的“政治戰”也得益于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的網絡,所有這些都有助于建立有利于美國目標的信息環境。冷戰期間,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等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通常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據透露,1963年至1966年間,美國向164家基金會共撥發700筆10000美金以上的款項(當時這是很大的數目),其中,至少有108筆完全或部分來自中央情報局。在這些基金會所有對國際活動的贊助中,有將近一半來自中央情報局(15)王紹光:《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讀書》2002年第5期。。卡特總統時期,1978年成立的赫爾辛基觀察組織(“人權觀察”非政府國際組織的前身)就是設在紐約的一個美國非政府組織,其成立是為了調查蘇聯對1975年簽署的確保歐洲國家自決權以及政治和領土主權的《赫爾辛基協定》的遵守情況。在冷戰的最后十年,美國勞聯-產聯積極支持和貫徹美國統治集團以反共和反蘇為核心的“政治戰”戰略,積極充當美國干涉別國內政和滲透、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最為著名的案例是勞聯-產聯選擇了波蘭“具有西方傾向”和“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團結工會,對其政治上大力支持,經濟上鼎力資助。勞聯-產聯還在美國政府資助的促進世界“民主化”的“全國爭取民主基金會”中起著主要作用,該基金會在五年時間里先后資助波蘭團結工會370萬美元。1989年1月,勞聯-產聯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特意邀請了波蘭、匈牙利、捷克和蘇聯“獨立工會”領導人,同加拿大、法國、奧地利、聯邦德國等國的工會代表一起參加大會。布什總統親臨大會,這是1971年以來第一個參加這種大會的共和黨總統。他對“這么多”社會主義國家獨立工會領導人第一次參加美國工會的全國代表大會“激動不已”(16)呂其昌:《美國勞聯-產聯是搞和平演變的急先鋒》,《國際研究參考》1990年第9期。。
以上有關美國在冷戰時期對蘇聯開展“政治戰”的經驗做法,有助于我們從三個方面來更好地理解美國“政治戰”的內涵,也有助于我們洞察美國對華施展“政治戰”的策略和手段。其一,對冷戰歷史的回顧表明,“政治戰”為美國政府提供了多種政策選擇,既可以補充也可以取代軍事行動,還可以適用于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以及進攻性和防御性戰略。美國對蘇聯“政治戰”的措施也是在不斷調整的,如積極措施工作小組只是在冷戰的最后階段才出現,旨在集中火力與蘇聯打一場同軍事和經濟競爭同等重要的“觀念戰爭”。這不僅是為了守住美國防御型“政治戰”的底線,也是對蘇聯集團進行極限施壓,是按照美國方式來結束冷戰的前奏。其二,信息戰是冷戰時期美國對蘇“政治戰”致使東歐轉型和蘇聯解體的重要推動力量。作為“政治戰”的一種形式,信息戰是美國實現戰略目標和推進外交政策目標的一種手段,更是最大限度追求對蘇競爭優勢的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充分發揮公共外交中信息戰的“意識形態攻勢”,并有意忽視或中斷雙方的文化交流。其三,在美國對蘇聯的緩慢絞殺過程中,經濟方面利用貿易管制、經濟制裁和拉攏盟友的方式,阻礙蘇聯貿易發展,斷絕其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技術領域,聯手西方國家實施限制高新技術轉讓的管制政策;此外,美國根據蘇聯是糧食進口大國以及對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點,有針對性地對蘇聯經濟貿易的痛點及弱點進行突破(17)葉楨:《以史為鑒:冷戰時期的大國經濟博弈》,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8-10-19/doc-ifxeuwws5864890.shtml。。但美國對蘇“經濟戰”措施被證明是有爭議的,無論是卡特政府還是里根政府,都很難采用“經濟戰”來對付蘇聯。當下所有主要經濟強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是與當今世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相接軌的,以至于這次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許多歐洲國家始終沒有與美國保持同步。這也是冷戰時期從未有過的。
二、特朗普政府對華“政治戰”的特點和影響
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政府通過2017年12月頒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8月通過的《2019年國防授權法》,逐漸確定了對華開展全面戰略競爭的基調和手段。過去兩年多來,除了貿易爭端成為中美關系的最大熱點,美國政府還動員和整合所有戰略資源(包括外交、經濟、情報、法律、文化和軍事),采用冷戰時期應對蘇聯戰略競爭的模板來塑造當前的對華競爭戰略,其行動、布局呈現越來越強烈的“有組織的政治戰”特征。在這場新一輪的對華“有組織的政治戰”中,特朗普不僅開啟了“史詩級”的中美貿易爭端,還糾集美國國內的建制派精英、反華極端派以及“五眼聯盟”的反華勢力,將對華實施地緣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斗爭等內容全面導入其中。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對華“政治戰”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意識形態攻勢成為特朗普政府對華“政治戰”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美國對華競爭戰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疫情打擊和經濟不振的情況下,意識形態對抗成為特朗普對華“政治戰”的重要戰略資產。2020年5月20日,白宮公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稱,“北京顯然自以為正與西方進行一場意識形態競爭”,并首次將“價值觀挑戰”與“經濟挑戰”“安全挑戰”并列為中國對美國的三大威脅。國務卿蓬佩奧還在該方針發表當天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這一事實”。7月23日,蓬佩奧又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黨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講,提到了美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根本不同,這不是他第一次強調美中在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自2019年以來,他就多次在公開演講中刻意區分“中共/中國政府”與“中國/中國人民”。這也是特朗普政府對華發起意識形態攻勢的一個特點。越來越多的美國政界人士強調,“美中沖突只是美國與中共的沖突”,宣揚西方社會制度的優越性,甚至還公開挑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在6月26日發表的有關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講話中也承認,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國之前沒有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指出,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已經呈現螺旋式上升的趨勢——一國的“防御型”意識形態努力被另一方視為“攻擊型”的意識形態行動(或是意識形態的輸出),從而觸發另一國的反應,導致競爭升級(18)VOA中文網,2020年7月24日。。
在這一輪對華意識形態攻勢中,美國政界、戰略界、思想界還刻意打造兩個妖魔化中國的標識性概念,即“國家資本主義”和“儒家重商威權主義”。這兩個概念的推出再次表明,中美戰略競爭已向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方向擴散和蔓延,這使中美戰略競爭有了越來越多的新冷戰涵義。近幾年來,美國戰略界認為,中國經濟運行的方式與美國和西方所奉行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完全不同,如果西方無法與這種模式抗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將在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競爭中敗北,最終就連西方信仰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都將受到顛覆(19)倪峰:《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若干特征》,http://www.cpifa.org/cms/item/view?table=book&id=135。。他們警告稱,“儒家重商威權主義”正在擊敗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中國早已對西方打響“經濟戰”,通過輸出過剩產能等方式摧毀西方國家的工業能力,導致美歐中產階層日益窮困。他們認為,現在美歐的民粹主義者已經覺醒,將從根本上改變面對中國時的軟弱和被動,他們還號召全世界的民粹主義者聯合起來對抗中國。曾在小布什政府擔任國防部中國事務官員的約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日前在《國會山報》(TheHill)撰文指出,“美中對抗的意識形態本質,最終使其成為一場關于生存的斗爭,因為兩位參賽者爭奪的是自我身份的認同。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在爭奪暫時的地緣政治優勢,而是兩種截然相反的世界觀、治理理念和價值體系在沖突中爭奪永久的文明優勢地位”(20)https://www.voachinese.com/a/defense-china-biden/5700496.html.。
第二,近年來,美國戰略界先后推出“全政府”和“全社會”的組織動員概念,以此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對華“政治戰”中凝聚起強烈的社會共識。美國戰略界通過研究認為,需要更新和提升西方國家的“政治戰”組織能力,尤其是政府能力,這樣才能應對中國的舉國體制。為此,他們從美國與蘇聯的冷戰經驗中提取出“全政府”這樣一個所謂的新概念,旨在改變過去出現的“政出多頭”亂象,整合打造官方各部門一致的對華戰略行動。這一概念已被特朗普政府采用,并正式寫入了《2019年國防授權法》。美國在2020年5月公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中,正式確立美中兩國的競爭關系,其結果是美國開始了一種動員“全政府”的對華戰略,并向更深更廣的全社會方向發展,對中國進行制衡,美國政府稱之為“全政府模式”(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該指針指出,特朗普政府對華采取“競爭性”的方針有兩大目標:一是“提升美國制度、聯盟和伙伴關系的應變能力,以期在面臨中國挑戰時占據優勢”;二是“迫使中國停止或減少從事損害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重大國家利益的行動”(21)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p.1.。
美國對華“全政府”戰略不僅體現在兩黨的反華共識、行政與立法機構的配合上,還體現在行政部門對“全政府”對華戰略的貫徹與執行上。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自2017年8月上任以來,始終將中國視為“美國全社會的威脅”。美國司法部長巴爾2020年7月16日在密西根州杰拉爾德·福特總統博物館的一場演講中呼吁,“自由世界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工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22)VOA中文網,2020年7月18日。。美國國務院利用各種外交場合,不斷攻擊抹黑中國。2019年2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出訪歐洲五國期間對這些國家施壓,阻撓其使用華為5G技術,聲稱“美國有義務警告其他國家用中國電信巨頭的設備建立網絡的危險”(23)侯海麗、倪峰:《美國“全政府-全社會”對華戰略探析》,《當代世界》2019年第7期。。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7月8日的演講中,也強調來自中共的威脅。他認為,中共“正在不擇手段地鉆我們開放制度的空子,同時利用它自己封閉制度的優勢”(24)VOA中文網,2020年7月24日。。雷還表示,“我們將中國的威脅視為全政府和全社會的威脅,應當采取全社會的策略來應對這種威脅”(25)Michal Kranz, “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and Americans must Step up as a Society to Defend Themselves”, https://www.thisisinsider.com/chinathreat-to-america-fbi-director-warns-2018-2.。受此影響,2018年,共有30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教授、學術機構負責人以及政府政策研究專家的訪美簽證被吊銷,或開始行政復審,其中包括知名學者(26)VOA中文網,2019年4月14日。。這給中美正常的學術交流蒙上了陰影。
第三,特朗普政府對華發起的意識形態攻勢正在形成國內輿論與國際盟友兩相夾攻的局面。美國戰略界認為,正如美國計劃者在冷戰時期所發現的那樣,發展和維持民眾對與中國長期競爭的支持至關重要,這種競爭既涉及和平時期,也涉及長期沖突的可能性,這樣的評估是基于考察美國和中國在競爭的社會維度上的優勢和劣勢。因此,首要任務應該是為美國人民確定一個合適的社會敘述(Narrative),以及旨在支持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的民眾支持的敘述。一方面,通過宣傳手段使美國民眾視政府的一切戰備與戰爭行為為遏制國際規則破壞者的正義行為,并力爭獲得首戰勝利,鼓舞國內士氣,堅定必勝信心。另一方面,美國爭取盟友國家民眾支持的重點是為了降低中國全面“政治戰”脅迫的風險,努力與世界各地盟友達成合作協議,共同結成信息戰的群體網絡。但是,西方國家采取適當的防御性和進攻性對策的組織障礙也相當高,美國和盟國必須充分加強政府機構之間卓有成效的協調,相關協調機構必須在打擊這種威脅方面發揮超常作用,即使這要求它們承擔額外負擔并在傳統責任領域之外進行運作(27)Thomas G.Mahnken, Ross Babbage and Toshi Yoshihara, “Countering Comprehensive Coercion o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gainst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Warfare”, CSBA Report, 2018,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Countering _Comprehensive _Coercion% 2C_May _2018.Pdf.。
第四,保守派思想庫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意識形態攻勢中發揮急先鋒的作用。特朗普上臺之后,在掀起中美貿易爭端的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華防范也在進一步增強,保守派思想庫繼續將中國視為首要挑戰者和競爭對手,將中國正常的對外交往行為貼上“銳實力”和“海外干涉”等標簽,積極推動美國在行政和立法層面展開行動,醞釀出臺多個反華措施。與特朗普白宮團隊核心成員納瓦羅有密切聯系的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于2018年6月出臺《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干涉行動: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應該如何應對》的報告,在梳理和分析中國共產黨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的“干涉行動”的基礎上,就全球民主國家如何予以反擊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包括:一是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應該牽頭成立“全政府”的項目來調查中共的干涉和影響情況,確定反情報和執法之間的界限,以及立法和公民社會倡議之間的界限;二是國會應該就此問題發布年度報告以增強透明度和公共監督,公民社會、智庫、中國問題學者和記者應該聯合起來,建立“統戰追蹤機制”;三是建立“國際民主國家統一戰線”,采取為全球媒體和教育以及中文研究和中國研究提供更多獨立資金來削弱孔子學院的吸引力等反制措施(28)Hudson Institute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June, 2018.。此后,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時就指出,“中國正在使用全政府的途徑,使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宣傳工具來提升自身影響力,獲取在美國的利益”。哈德遜的研究報告還認為,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行動”“模糊了傳統間諜、秘密行動和擴大影響力的界限,并以民主的脆弱之處作為攻擊目標,因此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危害”(29)Hudson Institute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June, 2018.。保守派思想庫的研究報告還無一例外地提出了反制中國海外“影響力行動”的建議,這些建議已經有相當大部分被美國政府特別是國會所接受,并在其他一些歐美國家引起了強烈共鳴,客觀上助推了美國對華的意識形態攻勢。
綜合2017年以來美國思想庫特別是保守派思想庫在特朗普總統上臺以來發布的一系列有關中國“影響力”的研究報告,根據他們的分析建議和對華強硬態度,以及與白宮的頻繁互動,不難發現,他們保守的對華政策主張對白宮對華關系方針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2018年以來中美關系的惡化,對中美關系的發展趨勢以及中國的國際環境變化起到了非常負面的影響。
第一,發達世界正在迅速且全面地形成一個反華陣線,在各方面支持和同情中國的重要國家正在顯著減少。自提出“印太戰略”以來,美國不斷推動完善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國協調機制,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推出“對印太地區經濟前景的構想”和安全合作倡議,與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在支持地區基礎設施、能源安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等方面采取聯動舉措,不斷加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力,推進構建“印太民主十國聯盟”,甚至是“印太十國軍事同盟”,同中國進行所謂較量,爭取阻絕或減少中國的意識形態影響。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海洋發達國家和歐洲大陸國家,在戰略和以高科技為內涵的高端經濟上,與美國的戰略保持高度一致,在如新冠肺炎疫情來源,香港、臺灣、邊疆問題,高科技脫鉤以及軍備控制等一系列問題上,也基本與美國一致,有些稍微保持一點距離(30)《對話時殷弘:近乎全面的西方聯合反華陣營正在浮現》,http://net.blogchina.com/blog/article/570578562。。2020年12月初,歐盟委員會在其發布的《全球變局下的歐美新議程》中也表示,歐盟已做好準備,在當選總統拜登提議的民主峰會中發揮充分作用,就打擊集權主義、侵犯人權和腐敗的抬頭作出共同承諾(31)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joint-communication-eu-us-agenda_en.pdf.。可以說,近乎全面的西方聯合反華陣營正在浮現。
第二,特朗普政府將對華人文、教育和衛生議題高度政治化,對中國在美媒體及文化機構的發展與合作進行更為嚴格的審查和壓制。這不僅惡化了中國文化和媒體機構在美歐國家的運營環境,也使得美中兩國的民眾對對方的負面看法均創下新高。2020年2月18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將五家中國主流官方媒體機構認定為“外國使團”;3月2日,又宣布對中國駐美五家官媒機構實行人員的限制;后又宣布拒絕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入境美國。在以上這番政治操弄下,兩國民眾對于對方觀感進一步走低。2020年7月30日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受調查的美國民眾對中國(中共)持“無好感”(Unfavourable)態度的比率上升到73%。這是皮尤中心2005年開展這項調查以來的最高點。該比率比中美2018年貿易爭端時猛升了26個百分點(32)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12月5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終止五項美中交流計劃,并指出這些計劃實際上是中國政府的對外宣傳工具。美國同時宣布制裁積極參與中共中央統戰部事務的官員及個人,拒絕他們申請入境簽證。被終止的五個美中交流計劃,包括“政策制定者中國行教育項目”“美中友好項目”“美中領導力交流項目”“美中跨太平洋交流項目”“香港教育文化項目”。這些計劃是根據美國1961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法》,容許美國政府雇員接受外國政府資助出行。此前一天,特朗普總統還發布了限制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家屬赴美旅行的規定,將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直系親屬B1/B2訪問簽證的最長有效期從10年縮短為一個月(33)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5206235.。甚至在抗疫這個需要國際合作的重要議題上,特朗普卻不斷“追責”中國造成大流行,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充當中國的牽線木偶,并以此轉移美國國內對疫情惡化和種族矛盾激化的視線,使得中美兩國幾乎沒有合作的可能。
第三,美國濫用“國家安全”概念,將經貿問題高度政治化,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為由,對中國在美企業發展和運營設置障礙和進行打壓。2020年2月以來,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相繼出臺多項措施應對“中共威脅”,包括特朗普總統11月頒布一項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投資被美國國防部認定為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企業,理由是這類投資會為中國的軍事野心提供資源,名單目前包含中國鐵建、中國中車、中芯國際、海康威視和華為等35家中國企業,另外,開展“干凈網絡”行動。12月15日,MSCI明晟指數也表示,從2021年1月15日起,將把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的七家中國公司的股票從其指數中剔除。納斯達克、標普和道瓊斯指數公司此前已宣布將采取類似行動。2020年6月底,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宣布,正式將華為和中興這兩家中國通訊設備企業列入國家安全威脅名單,禁止美國企業使用聯邦資金購買他們的設備和服務。此前,特朗普政府還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美國應用商店下架中國手機應用程序TikTok(抖音海外版)和WeChat(微信),并要求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剝離TikTok在美所有資產。2020年5月,美國商務部切斷了對中國華為公司的芯片供應,并擴大了對使用美國技術的限制,還宣布有意限制中國電信運營商和云服務供應商,限制中國開發商進入美國移動應用商店(34)https://www.voachinese.com/a/Who-is-abusing-national-security-20201216/5701648.html.。
三、美國實施“政治戰”的內在機制
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發動的進攻性“政治戰”是多層面的,能夠對蘇聯發動多線攻擊。1961年,肯尼迪(John Kennedy)總統提出“兩個半戰爭”理論,這一戰略目標雖然在冷戰結束后趨于“收縮”,但美國從未放棄過同時贏得兩場戰爭的實力和準備。美國攻防型“政治戰”也強調戰略的多邊性,盡可能利用與盟國和伙伴國之間的合作。美國還注重在總統的統一指揮下,由政府各部門協調實施,避免了過于刺激蘇聯而產生負面后果。總之,美國相對完善的“政治戰”內在運作機制,保證了其冷戰以來無論是遂行非常規的軍事行動,還是執行秘密政治行動,抑或是履行海外外交行動的長期性和有效性。
(一)美國“有組織的政治戰”擁有頂層設計的組織和立法保證
“政治戰”是冷戰時期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美國政府以及軍方著眼于戰爭需求,在“政治戰”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非常完備的決策程序。美國歷屆政府都成立了專門機構來負責“政治戰”的制定和實施,另有專門委員會考察、評估、提供政策指南和監督。1961年,美國國會頒布《教育及文化平等交流法》(又稱《富布萊特法》),成立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局,主管學術、文化、體育和專業等方面的國際交流,推進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利用可以鞏固美國國家安全和國際領導地位并為美國提供諸多利益的交流項目,率先開展國務院的公共外交外聯工作。1999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秘密的68號總統決策指令(PDD-68),它是國家安全決策指令(NSDD-77)的替代性指令,該總統令由國際公共信息委員會(IPI)負責,在于“誘導國外民眾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抵消美國敵人的宣傳”。直到今天,美國國務院還在繼續履行主管和統籌“政治戰”的職能,下轄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人權、民主、勞工辦公室,給美國民主基金會和美國和平隊等機構撥款。2008年9月11日,美國國務院負責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的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K.Glassman)在倫敦查塔姆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發表講話時透露,美國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部分是意識形態的較量——思想戰(Ideological Engagement),區別于用炸彈和子彈進行的戰爭。負責公共事務的副國務卿身兼兩職,除了負責屬于國務院的公共外交工作,他同時還按照總統的指令,主導整個政府范圍內有關思想戰的工作,包括統籌與國防部、情報界、其他政府機構和私營部門的協作(35)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08/September/20080912112648eaifas0.8478968.html.。
國會為美國應對中國“影響力行動”提供了立法保障、經費支持,并進行有效監督。2019年3月,美國眾議院通過《對抗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政治影響的行動法案》,該法案責成國務卿應與所有相關聯邦機構共同制定一項應對中國影響力的長期戰略,除了要加強與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臺灣地區和蒙古的合作與協調,有效對抗中國共產黨在全球和美國的“銳實力”政治影響力行動,還要確保美國公民、普通華裔美國人以及經常成為“惡勢力”政治影響行動的受害者和主要目標的華人受到保護。該法案還建議在國務院或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成立一個常設機構,監視和應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力行動”(36)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181.。此前2月13日,參議院也通過了《應對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影響力的法案》,該法案聚焦中國的“政治影響力行動”,認為中國“協調一致、經常隱蔽地運用虛假信息、操縱媒體、經濟脅迫、有針對性的投資、腐敗或學術審查。這種努力通常是為了脅迫和腐蝕美國的利益、價值觀、機構或個人,為了在美國培養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利益的態度、行為、決定或結果”,要求國務卿和國土安全部長協調聯邦相關機構來制定一項長期戰略,有效地對抗中國共產黨在全球和美國的“銳實力”政治影響力行動(37)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480.。2019年2月27日,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發布《中國對美教育系統影響》調查報告,認為孔子學院在美運營信息披露不公開,且美方類似教育機構在華未得到互惠待遇。2月28日,該小組委員會就該份調查報告舉行聽證會。會上,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代理主任賈森·拜爾(Jason Bair)在證詞中表示,與中國大學合作在華建立學位授予機構的美國大學強調學術自由,但面臨互聯網審查和自我審查等因素的約束。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首席副助理國務卿郭瑾(Jennifer Zimdahl Galt)在證詞中指出,與孔子學院相關的K-12教學問題叢生,在兩起查辦案件中,私營部門交流辦與領事事務局密切合作,合理撤銷了已進入美國教學但不是通過交流訪問者項目中教學類別指定的贊助商而獲取資格的中方交流訪問者的簽證(38)參見https://www.rollcall.com/2019/03/01/china-is-building-soft-power-in-u-s-schools-senate-report-warns以及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研究與參考》2019年第7期。。
(二)政府和民間機構緊密合作機制的有序運行
近幾年來,美國思想庫和非政府組織發布的有關信息戰報告和文件都強調,要加強與美國社會中私人機構的合作,特別是大學、基金會、政治團體和媒體。在公共外交領域,美國政府、私人基金會和大學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機制,各自責任明確,構筑了“三位一體”的行動網絡,甚至形成一種特殊關系下的利益共同體。美國非政府組織在這一輪對華意識形態攻勢中,更是與權力部門相互策應、密切配合。從2017年底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下屬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發布《銳實力:崛起的極權主義影響》研究報告,到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中國簡報》中陸續刊登了《中國共產黨在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影響力行動的初步調查》系列報告,再到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布《北京的全球揚聲器——2017年以來中共媒體影響力的擴張》報告,這些反華基金會不僅擔心中國威權“軟實力”所帶來的更復雜的挑戰,還分析民主社會中非自由主義精英的言論,并強調中國這樣的威權政權為了促進自身利益而試圖傳播的意識形態概念(39)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Jamestown Founda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CP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Japan, Singapore and Hong Kang”; Freedom House, “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隨著特朗普本人的玩忽職守加劇了美國國內的全國性混亂,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高潮和失業人口的疊加效應,他急于“甩鍋”世衛組織和中國,“中國責任論”在他的政綱及正式言論中占有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不少非政府組織也指責中國有關抗疫的宣傳報道為“虛假信息”,煽動西方民眾對中國政府的不滿。美國捍衛民主聯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負責人勞拉·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就在《外交事務》網站上撰文稱,“隨著疫情開始在本國境內得到控制,中國政府發起了一場強勢的外部信息宣傳活動,旨在引發全球對其應對疫情方式的討論。這場運動有著明確的目標:轉移對北京自身抗疫失敗的指責,并強調其他國家政府的失誤,同時把中國描繪成其他國家的榜樣和首要合作伙伴”(40)《外交事務》網站,2020年4月22日。。
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大多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美國政府也鼓勵非政府組織在從事自身活動的同時,能夠承擔政府不能夠開展的部分公共外交事務。美國國務院早在2006年12月公布的《對待非政府組織的指導原則》第六條中就規定,應允許非政府組織為從事和平活動而尋求、接受、管理和支配來自國內、國外和國際組織的財務支援。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投入數億美元用于公共外交,其中大部分文化教育交流項目的經費流入了非政府組織,由非政府組織出面提供經費及通過其它資助方式,借由文化交流來影響目標國國內有著重要社會影響的人士,包括教育工作者、新聞記者、婦女領袖、商界精英、工會領導、政治人物、科學家、軍界人士以及青年學生等。美國私人基金會基于非政府的角色,借助公共外交的“柔性介入”方式,不僅比較容易回避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還有利于扮演某種客觀、公正和中立的角色,從而使公共外交活動更具合法性的表象。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相互借重、各謀其利、互相依存而又保持距離,形成了一種微妙而特殊的關系。就政府間的文化外交而言,囿于意識形態差別及主權意識,美國官方對華帶有政治敏感性的公共外交很難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這些問題在基金會活動中卻可以適當避免,因為基金會往往不會像跨國公司那樣追求利潤,不涉及“賺錢”的問題,也不會大張旗鼓地宣傳某些價值觀念,因而給人以單純和公允的印象。這些獨特功能是美國任何官方機構推行對華外交時所無法企及的,私人基金會往往憑借自身優勢,能夠在政治敏感地區發揮特殊功能,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特別是美國的基金會能極方便地深入到中國民眾當中,這種草根化的表象使它們不僅容易取得普通民眾的支持,還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民眾的思想。另外,草根化的特點又使得它們在獲取第一手信息方面具有獨到的優勢。這些基金會能夠在一些政治環境不同的非西方教育機構如大學中開展工作,途徑之一就是在政治意識形態迥異的國家間推動各個層面的學者交流。
(三)“旋轉門”機制助推保守派思想庫發揮重要影響力
美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決策咨詢制度,尤其是“旋轉門”機制,為保守派思想庫設定美國對華政策議程、引領公眾討論并傳遞相關信息提供了充分條件。“旋轉門”提供了參與對華政策決策的雙行道:保守派思想庫專家成為官員后進入美國外交決策層的核心,成為對華政策的直接制定者;思想庫專家和政府官員角色的“旋轉”也增加了其在大眾媒體的曝光率,形成了對華議題強有力的公共傳播網絡。保守派思想庫通過與美國各種涉華政治機構、商界、非營利組織、學界以及媒體的溝通,實現特定議程設置;在某個涉華議題受到關注后,繼而引領相關討論,包括接觸特定的決策者(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商界領袖以及社會精英,在媒體發表美中關系的文章后,接受采訪并舉行主旨演講。這些保守派智庫還經常派專家去國會聽證會,提供中國問題的證詞。布什政府時期提出的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的對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和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遏制+接觸”的政策咨詢建議,他們主張,通過“接觸”保持與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促使中國融入現存國際體系,推動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合作性民主大國,同時利用“遏制”減緩中國崛起進程,預防中國崛起后挑戰美國國際地位和利益。
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后,保守派思想庫與特朗普鷹派團隊的成員一拍即合,頻繁互動,他們的研究實力和綜合影響力也得到了進一步提升。據報道,彭斯副總統2018年10月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講的講話稿,就是由特朗普的“權威中國通”顧問、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撰寫的。彭斯在演說中還特別提及白邦瑞的觀點,“中國反對美國政府的行動和目標。實際上,中國正在與美國的盟友和敵人建立關系,這與建立任何和平及高效的中美關系的意圖相矛盾”。這一觀點即出自于白邦瑞2015年出版的《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強國的秘密戰略》。白邦瑞本人新近擔任國防部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這一身份注定讓他不只是一位簡單的保守派思想庫中國問題專家,而是今后美國軍方對華戰略的謀劃者。美國保守派思想庫的很多專家學者有在政府任職的職業經驗,這也成為他們發揮影響力的一個重要途徑。據統計,保守派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有18名研究員先后進入奧巴馬政府任職,部分成員還直接進入美國外交決策的核心圈。例如,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任常務副國務卿、萊恩(Willam Lynn)任國防部副部長、蘇珊·賴斯(Susan Rice)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坎貝爾任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布萊爾(Dennis Blair)任國家情報總監等。這使得新美國安全中心異軍突起,成為華府地區一家影響著美國軍事發展戰略的頂尖智庫。
(四)“政治戰”的催化性策略和侵蝕性策略的靈活運用
美國在冷戰時期發動“政治戰”,最驚奇的策略固然是催化性的(Catalytic),用來引發一些戲劇性的近期變化。如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將有民主化進程的危地馬拉阿本斯政府視為蘇聯共產主義勢力在該國的擴張。1954年,美國通過兩次秘密行動,采取外交壓力和心理戰相結合的手段,最終推翻了危地馬拉的民選政府,這也成為美國后來在拉丁美洲干涉別國內政的一種模式和手段。這一行動是由中央情報局負責策劃和實施的。中央情報局自1947年成立之后,在世界范圍內的第一次“秘密行動”是1953年推翻伊朗摩薩臺的“阿賈克斯”(TPAJAX)行動,而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則是1954年推翻危地馬拉政權的“勝利”(PBSUCCESS)行動(41)賈力:《美國中情局在危地馬拉的心理戰》,《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4期。。此外,冷戰時期美國的宣傳計劃也具有同樣的動機。為了加強對蘇聯、東歐等國家的廣播宣傳,美國之音先后播出了“揭露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弱點和邪惡”的《政治的卡巴萊》、“揭露共產主義所標榜的更好的生活的虛假”的《共產主義伊甸樂園》和《鐵幕后的生活》,以及回顧蘇聯擴張的歷史,“使人們想起蘇聯政權想要抹掉或歪曲的事件和聲明”的《你——記得這些時刻嗎》等一系列專題節目。1953年,美國之音不斷廣播東德騷亂的報道,希望“推回”蘇聯的宣傳攻勢,鼓舞東德民眾抗議蘇聯的統治。中情局還向東歐廣播發表了赫魯曉夫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秘密講話,它后來確實引發了震動蘇聯集團的抗議活動。中情局局長杜勒斯稱之為“保持沸騰”的行動(42)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艾森豪威爾的第一任期是美國對蘇東國家冷戰宣傳發展的重要時期,將“全社會”的“心理因素”融合進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各個方面。不僅美國的政府官員,而且美國的民眾也卷入到國家的冷戰宣傳中去。美國冷戰宣傳政策、宣傳機構建制和具體的宣傳運動逐漸向長期、漸進和隱蔽的方式發展。在艾森豪威爾第二任期和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的冷戰宣傳發展到高峰,美國對蘇東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也邁向成熟(43)郭又新:《穿越“鐵幕”:美國對“蘇東國家”的冷戰宣傳(1945-1963)》,東北師范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
冷戰時期,美國最成功的“政治戰”更多地是侵蝕性的(Corrosive)。這些“政治戰”計劃聚焦推高蘇聯集團的對抗和競爭成本,而不是政權的徹底更迭。美國國際廣播在國內和全球聽眾面前,宣傳共產主義勢力的失敗,其目標就是促使蘇聯集團內部不滿的爆發,增加這些共產黨執政政府長期的壓力。此類經典案例就是自由歐洲和自由無線電臺,通過長期播送蘇聯集團內部的弊病和失敗,從而增加它們向更開放社會漸變的機會。成功的“政治戰”不必刺激徹底的反抗,它只需要追求逐漸地、累積地侵蝕根基并打擊敵對統治的競爭潛力(44)Hal Brands, “The Dark Art of Political Warfare: A Primer”, AEI Report, Feb., 2020.。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年中以來,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司法部長、聯邦調查局局長等美國政府重量級官員,分別就意識形態、經濟和間諜等議題發表涉華長篇主題演講,他們紛紛為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中心的“7·23演講”預熱。有美國的中國觀察家指出,由于美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處于螺旋式上升的狀態,中國對威權體制的支持確實會挑戰美國的意識形態理念——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對此,蓬佩奧的講話如同發表了新鐵幕宣言,開啟了一場類似于美蘇之間的新冷戰(45)VOA中文網,2020年7月24日。。
結 語
冷戰時期,美國曾利用多種方式對蘇聯發動“政治戰”,包括在蘇聯內部制造混亂、削弱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合法性、與蘇聯圍繞第三方展開競爭等。美國從未忘記強調與其對手之間意識形態差異的重要性。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一系列“顏色革命”,從中都能看到美國意識形態攻勢發揮的顛覆性作用。美國擁有長期積累的意識形態“政治戰”資源和經驗,不僅具有非常強大的優勢,并且這種優勢還將長期存在。特朗普總統自上臺以來,希圖恢復美國的競爭優勢,在美國國務院的統籌和協調下,再次把思想和價值觀的沖突放在對華關系的中心位置,對華意識形態攻勢愈演愈烈。中美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沖突呈加劇趨勢。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意識形態安全關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前途命運,更深刻地認識和把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及其變動在當今國際安全關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對于科學決策與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也需要我們對美國的“政治戰”策略有更深刻的把握。畢竟,中美兩個大國的長期戰略競爭,不僅是在地緣政治利益方面的角逐,更是對中國戰略能力、戰略經驗、戰略資源、戰略耐力、戰略定力的大檢驗。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我們無論如何既要增強自身的“四個自信”,又要有效應對美國的“政治戰”攻勢,努力改善我國在國際上的戰略處境和安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