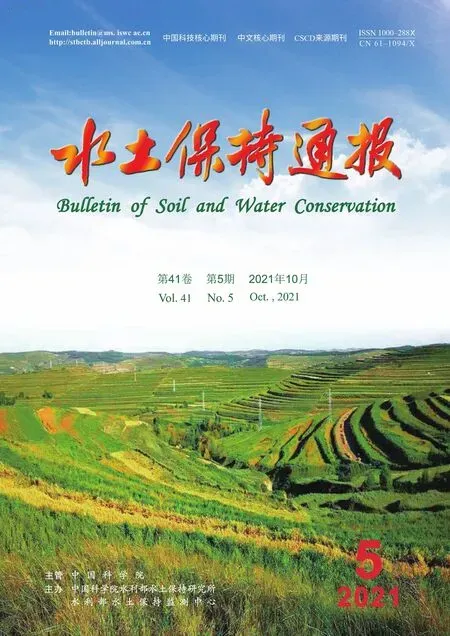植被恢復對青海省北川河流域水循環演變趨勢的影響
楊明楠, 劉景濤,2, 朱 亮,2, 周 冰,2, 溫得平
(1.中國地質科學院 水文地質環境地質研究所, 河北 石家莊 050061; 2.河北省中國地質調查局地下水污染機理與修復重點實驗室, 河北 石家莊 050061; 3.青海省水旱災害防御服務中心, 青海 西寧 810001)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國土綠化取得顯著成效,在水土保持和防風固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3]。與此同時,大規模植被恢復使下墊面格局發生劇烈變化,對流域水循環條件和水文過程產生深遠影響,尤其在缺水地區,局部植被恢復趨近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極限,出現了新的生態—水資源矛盾[4-5],植被恢復的水資源約束問題已成為干旱半干旱地區植被恢復過程中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大氣降水是陸地水循環的主要水分來源,從物質守恒上來看,植被恢復在消耗更多水資源的同時必然會對其他水循環環節水量分配產生影響[6-8]。受近幾十年來大規模退耕還林還草的影響,黃土高原深層土壤水分普遍存在土壤干層現象,且其分布范圍有不斷增大的趨勢[9-11];土壤水分變化進一步影響了大氣降水對地下水的補給,試驗尺度的觀測及模擬研究顯示,固原黃土區荒地轉耕地使地下水年補給量由100 mm減為50~55 mm[12],毛烏素沙地沙柳、檸條等植被覆蓋區的地下水降水入滲補給量是裸地的10%~67%[8];在流域尺度上,晉西南森林覆蓋小流域與無林小流域相比地表徑流衰減近80%左右[13],隨著森林面積的增加,在相同降雨量條件下,Abay河流域基流降低了4.4%[14]。植被恢復引起土壤水、地下水及地表徑流的變化將改變流域水循環條件,最終影響流域水資源形勢[15]。因此,研究大規模植被恢復作用下水循環演變趨勢,對科學認識干旱半干旱地區植被生態與水資源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內關于植被恢復對水循環的研究多以點尺度或坡面尺度的觀測試驗和模擬研究為主,且研究區主要集中在黃土高原地區,由于水熱條件的差異,青藏高原地區植被與水循環之間的相互作用與黃土高原地區存在顯著差別。北川河流域是黃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養區和國家生態環境建設的重點地區。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規模人工造林使流域植被覆蓋快速增加,流域生態環境水平及水源涵養能力顯著提高,但也出現了徑流系數衰減、水循環變異等問題。本文結合長序列氣象、水文資料及遙感數據分析流域尺度水循環要素演變趨勢,闡明植被恢復對關鍵水循環要素演變的影響作用,對科學認識黃河上游水源涵養區生態建設與水資源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區概況
北川河位于青海省東部,是湟水河一級支流,黃河二級支流,全長149 km,流域總面積3 371 km2,其中橋頭水文站以上流域面積2 774 km2;地貌類型上屬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接壤地帶,區內以高山、縱谷、盆地為主,地形上從西北向東南呈“C”字形;氣候上屬大陸性半干旱氣候,且具有典型的垂直分帶性,隨著海拔的升高,氣溫、蒸發量呈遞減趨勢,降水量呈遞增趨勢,年均氣溫從6.2 ℃降至-6 ℃,年均蒸發量從1 000 mm以上降至800 mm左右,年均降水量從350 mm左右增加至600 mm以上。
北川河大部分支流河谷區第四系沖洪積層厚度不大,賦水性較差,受構造沉降影響,從上游支流黑林河和寶庫河交匯處的干流河谷區開始第四系沖洪積層厚度陡然增大,河水開始大量滲漏補給地下水,在橋頭一帶,由于基底抬升明顯,河谷潛水幾乎全部溢出補給河水,因此北川河橋頭以上可視為一個閉合流域。從多年平均逐月降水量、徑流量分配過程可以看出,流域內連續最大4個月降水量出現在6—9月,占全年降水量的70.8%,連續最大4個月徑流量出現在7—10月,占全年徑流量的比例在71.4%,徑流與降水相比存在約為一個月的滯后周期,屬典型的降水—地下水補給型河流[16]。
2 研究數據與研究方法
2.1 植被覆蓋數據
植被覆蓋數據來源于landsat 5 TM,landsat 8 OLI及MODIS MOD16A2產品,其中landsat數據來源于美國地質勘探局官網(USGS),空間分辨率為30 m,重訪周期為16 d。本次研究選取了2000年和2019年6—9月數據,共8幅,對原始遙感影像進行圖像預處理后,獲取各月份NDVI值,利用ArcGIS 10.1軟件 cell Statistics工具實現最大值合成,利用 Landsat紅光和近紅外兩個通道的反射率數據,得到地表月度NDVI產品的合成,進一步使用像元二分模型計算植被覆蓋度,計算式如下:
fveg=(NDVI-NDVIsoil)/(NDVIveg-NDVIsoil)
式中:fveg為植被覆蓋度; NDVI為混合像元的植被指數值; NDVIveg為純植被像元的植被指數值; NDVIsoil為純土壤像元的植被指數值。參考高健健等[16]的估算方法,在NDVI頻率累積表上取頻率0.5%的值為NDVIsoil,取頻率99.5%的值為NDVIveg。
2.2 氣象水文數據
橋頭、黑林、衙門莊、牛場4個氣象站和橋頭水文站1956—2019年的降水量、徑流量數據來自“青海省第三次水資源評價數據集”,其中徑流數據是根據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狀況進行逐月還原的天然徑流量;1961—2019年風速數據來源于國家氣象科學數據中心(http:∥data.cma.cn/);橋頭氣象站1970—2019年的年水面蒸發量數據來源于大通縣氣象局,是根據E20蒸發皿測試結果換算的E601型蒸發器的蒸發值;根據水面蒸發量和降水量的比值(水面蒸發量/降水量)計算干旱指數,用以反映流域氣候干濕程度,其值越大說明氣候越干旱。
2.3 研究方法
一個閉合流域的水循環要素可概化為大氣降水、生態用水和徑流三部分,其中徑流由基流和地表產流組成,本文基于流域水循環模型分析大氣降水、生態用水、地表產流和基流之間的變化規律。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可表達為:
Q=R+S+Ug
(1)
R=P+G
(2)
式中:Q為大氣降水量;R為還原后的天然徑流量;S為生態用水量,主要包括流域蒸散發量以及土壤、植被蓄水等;Ug為地下水潛流量,在一個閉合流域內Ug為0;P,G分別為地表產流量和地下基流量,可以根據基流分割計算得到。
其中,S和R,P和G之間分配比例的變化能夠反映流域水資源時空分配的變化,因此,分別定義了降水分配系數(KQ)和徑流分配系數(KR)兩個指標:
KQ=S/R
(3)
KR=G/P
(4)
式中:KQ表示流域內部生態用水與流域外部徑流排泄之間的關系,反映了流域水資源在空間分配上的變化;KR表示基流和地表產流之間的關系,反映了流域水資源在時間上分配的變化,即大氣降水向流域外排泄周期的變化。
考慮到流域大部分區域包氣帶厚度較大,且大部分情況下一次降水不能對地下水形成有效補給,因此,采用直線分割法對月徑流過程線進行基流分割。在多年平均月徑流過程曲線上,從10月開始,受降水量減小的影響,徑流量快速衰減,從11月開始逐漸進入冰凍期,至12月地表基本完全凍結,降雪基本不會河水和地下水形成補給,12月至次年2月,徑流呈微弱的減小趨勢,從3月起,冰雪和地表凍結層逐漸開始融化補給河水,徑流開始逐漸增加。因此將2月和12月作為基流分割點。
3 結果與分析
3.1 流域植被覆蓋及水循環要素的變化特征
流域大規模植被恢復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近幾十年來,流域植被覆蓋率大幅度提高,其中在大通縣城兩側的丘陵山區,植被覆蓋率由7.2%上升至75%以上[17-18]。但由于受遙感數據源的限制,缺乏大規模植被恢復工程以前流域內的植被覆蓋狀況的具體數據,因此大規模植被恢復前后的植被覆蓋情況不能進行直觀對比。
根據北川河流域2000年和2019年兩個時期的植被覆蓋變化,可以得出北川河流域植被覆蓋的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特征。在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高強度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影響下,2000年以來,北川河流域植被覆蓋條件總體較好,流域植被覆蓋度以大于80%的區域為主(表1)。高植被覆蓋區主要分布在海拔2 600~3 500 m左右的中低山地區,這一區域幾乎不受人為開發的影響,具備有利于植被生長的良好自然條件。植被覆蓋小于50%的區域主要位于干流河谷區及海拔大于4 000 m的高山地區,河谷區城市建設及工業活動等對地表覆被的改變較大,高山地區冰雪覆蓋周期較長,在凍融侵蝕作用下大部分基巖風化嚴重,形成典型的高寒石漠化景觀。

表1 2000-2019年北川河流域植被覆蓋變化統計
2000—2019年,流域大部分區域植被覆蓋度增加,其中,覆蓋度大于80%的區域面積增加最大(表1)。在ArcGIS軟件中對2000年和2019年兩個時期的植被覆蓋度進行差值計算并對植被覆蓋變化圖(圖1)進行統計計算,結果顯示植被恢復(變化量>0)和退化(變化量<0)的區域分別占流域總面積的88%,12%。植被退化區主要分布在受人為開發影響最大的干流及部分支流河谷區,尤其是2000年以后,隨著青海省經濟的快速發展,河谷區的開發強度進一步增大,引起植被覆蓋退化,最大降幅為64.7%,平均降幅為11.56%;在河谷區兩側的大面積中高山和低山丘陵地區,植被覆蓋主要呈增加趨勢,最大增幅為52.2%,平均增幅為14.98%,其中,植被恢復強度最大的區域主要分布在大通縣城以南河谷兩岸的低山丘陵區,這一區域屬“西寧南北山綠化工程”的覆蓋范圍,植被恢復最為明顯。

圖1 2000-2019年北川河流域植被覆蓋度變化量
1956—2019年,橋頭站以上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572.47 mm,最大值為1961年769.9 mm,最小為1991年413.1 mm,極值比為1.86,降水量總體變化穩定;橋頭站多年平均徑流量6.27×108m3,平均徑流系數0.39,最大徑流量為1989年的1.08×109m3,最小為1991年的3.63×108m3,極值比為2.97,年徑流量總體呈下降趨勢,平均下降幅度為1.60×107m3/10 a(圖2)。

圖2 1956-2019年降水量和徑流量變化曲線
從1956—2019年降水量及天然徑流量累積距平變化曲線上可以看出,流域內降水量和徑流量總體呈現“豐—枯—豐—枯—豐”的波動變化特征,其中,20世紀 60年代初期、80年代末期及2015年左右為3個峰值期,20世紀80年代初和2000年左右為兩個低值期(圖3)。

圖3 1956-2019年北川河流域降水及天然徑流累積距平變化過程
根據1956—2019年基流分割結果計算,北川河橋頭以上流域多年平均基流量2.17×108m3,多年平均基流系數0.15。從基流量和地表產流量的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圖4),基流量的波動變化幅度小于地表產流量,兩者的變差系數分別為0.19,0.34。從長序列變化規律上來看,地表產流量和基流量均呈下降趨勢,其中,地表產流量和基流量的平均下降速率分別為1.38×107m3/10 a和2.70×106m3/10 a。

圖4 1956-2019年北川河流域基流量和地表產流量變化特征
結合閉合流域水平衡模型,根據公式(1)計算流域生態用水量。從生態用水量變化曲線上可以看出(圖5),1956年以來流域生態用水量呈波動上升趨勢,平均上升趨勢為2.80×107m3/10 a,多年平均生態用水量為9.60×108m3,占多年平均降水量的60.3%,最大生態用水量出現在2003年,為1.38×109m3,最小生態用水量出現在1991年,為7.80×108m3,生態用水是流域中最大的水資源消耗項。

圖5 1956-2019年北川河流域生態耗水量變化特征
3.2 植被恢復對流域水循環變化的影響
根據流域植被覆蓋變化情況,分別選擇1956—1970年和2000—2019年作為植被恢復前后的兩個典型時期進行對比分析,研究植被恢復對流域水循環變化的影響。
在不同年代降水量—生態用水量關系散點圖上(圖6a),1956—1970年的趨勢線位于2000—2019年的下方,這說明在相同的降水量條件下,2000—2019年的平均生態用水量高于1956—1970年,即隨著流域植被恢復,生態用水量具有明顯的增加趨勢。根據兩個時期降水量—生態用水量的趨勢關系計算得到,在多年平均降水量(572.47 mm)條件下,2000—2019年流域年均生態用水量比1956—1970年增加了1.33×108m3(39.93 mm),增加比率為15.3%。
在不同年代降水量—地表產流量和降水量—基流量關系散點圖(圖6b,6c)上可以看出,1956—1970年的趨勢線位于2000—2019年的上方位,這說明隨著流域植被恢復,在相同的降水量條件下,地表產流量和基流量具有明顯的降低趨勢,根據兩個時期降水量與地表產流量和基流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可以計算得到,在多年平均降水量條件下,2000—2019年地表產流量比1956—1970年降低了9.80×107m3(35.25 mm),降低比率為24.3%,基流量降低了7.60×107m3(27.33 mm),降低比率為25.6%。多年平均降水量條件下植被恢復前后主要水循環要素變化統計結果見表2。

圖6 1956-2019年北川河流域植被恢復前后生態用水量、地表產流量、基流量變化關系

表2 多年平均降水條件下植被恢復前后水循環要素變化統計
從1956—1970年和2000—2019年兩個時期降水量—生態用水量、降水量—地表產流量的變化趨勢上來看,當流域處于枯水年時,兩個時期的趨勢線近于相交,而當豐水年時,趨勢線的間距越來越大,這一變化趨勢說明,流域植被恢復后,對枯水年生態用水量和地表徑流量的影響不大,但在豐水期,這種影響變得十分明顯。也就是說,植被恢復對流域水循環的影響作用并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隨著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這一變化特征充分體現了植被恢復對流域水循環調節作用。
植被恢復引起流域水循環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單個水循環要素的變化上,而且也體現在流域水資源的時空變化及流域氣候變化上。根據公式(3)—(4)分別計算1956—2019年流域降水分配系數(KQ)和徑流分配系數(KR)。通過對比1956—1970年與2000—2019年兩個階段降水分配系數的變化可知,在相同降水量條件下,2000—2019年的年均降水分配系數是1956—1970年的1.42倍(圖7a),說明植被恢復后,產流條件發生了變化,更多的大氣降水供給流域內部的生態用水,而向下游的徑流減少。
通過對比1956—1970年與2000—2019年兩個階段徑流分配系數的變化可知,徑流分配系數隨降水量的增加而減小,這與大部分流域的產流規律是一致的,但在相同降水量條件下,2000—2019年的徑流分配系數略微高于1956—1970年(圖7b),這說明在植被恢復后,徑流中基流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地表產流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且這種變化隨降水量的增加而更加明顯。總體來看,植被恢復前后徑流分配系數的變化并不明顯,降水是引起徑流分配變化的敏感因素,而植被恢復的影響則相對微弱。

圖7 1956-2019年北川河流域植被恢復前后降水分配系數和徑流分配系數的變化關系
1970—2019年流域年水面蒸發量即年蒸散發能力(E0)呈波動降低趨勢,干旱指數與蒸散發能力之間存在相同的變化趨勢,統計結果顯示,2000—2019年干旱指數均值(1.58)比20世紀70年代(1.91)降低了21.4%(圖8a),這說明,受植被恢復的影響,流域的干旱程度有所降低。風速是影響水面蒸發的一個重要因素,1961—2019年最大風速和平均風速均呈下降趨勢(圖8b),尤其是2000年以前的下降速率最為明顯,相關研究表明,地表覆蓋對近地面風速具有顯著的減弱作用[18-19],因此,植被覆蓋恢復引起經地面風速降低可能是造成流域潛在蒸散發能力降低的因素之一。由此可見,流域植被恢復與氣候要素之間存在著良性的互饋機制,大規模植被恢復可以通過改善流域半干旱的氣候條件進而對流域水循環產生影響。

圖8 1956-2019年北川河流域干旱指數和地表風速的變化趨勢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 論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植被恢復后流域生態用水量呈增加趨勢,但水面蒸發反映出的流域蒸散發能力卻呈下降趨勢。在公式(1)所示的流域水循環模型中,生態用水量S存在兩種消耗形式,一是以陸面蒸散發的形式進入大氣,二是以土壤、植被蓄水的形式存儲在流域內。因此,植被恢復影響下蒸散發能力的降低也就意味著流域土壤、植被蓄水能力的增加[20]。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北川河流域的生態用水并未全部消耗于蒸散發,其中一部分以土壤、植被蓄水的形式存儲于流域內,這充分體現了黃河上游流域植被恢復的水源涵養價值。
植被蒸騰和土壤蒸發是構成半干旱地區陸面蒸散發的兩個主要要素[21]。植被恢復一方面帶來植被蒸騰耗水的增加,另一方面大規模植被帶來的遮陽、阻風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林下土壤水分蒸發量。彭煥華等[11]在相鄰的祁連山黑河上游地區的監測研究表明,青海云杉林內土壤蒸發量僅是林外土壤蒸發量的45.5%。因此,在考慮植被恢復對蒸散發量的影響時,不僅需要考慮植被生長的蒸騰量的變化,還需要充分考慮植被覆蓋帶來土壤水分蒸發量的變化。北川河流域植被恢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表層土壤水分蒸發量可能是引起流域蒸散發能力隨植被覆蓋增加而降低的一個重要作用因素。
4.2 結 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川河流域經歷了大規模的植被恢復。2000—2019年期間平均植被覆蓋率增加了5.01%,其中,干流河谷兩側廣大的低山丘陵及中高山地區是植被恢復程度最大的地區,最大增幅為52.2%,平均增幅為14.98%。大規模植被恢復在改變流域下墊面性質的同時,引起流域水循環條件發生了變化。
(1) 從流域降水量、徑流量、生態用水量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在降水量條件未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受大規模植被恢復的影響,流域水循環條件發生變化,直接表現為生態用水量增加和徑流量衰減。
(2) 植被恢復影響對大氣降水在流域內外的時空分配。在空間分配上,植被恢復使更多的大氣降水用于流域內部的生態所需,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對下游的水源供給量;在時間分配上,徑流中基流的占比有所增加,延長了降水向流域外的排泄周期,即流域內更多降水參與長周期的降水—土壤水—地下水循環過程,更多水資源從線狀水域系統向面狀陸域系統轉移。
(3) 植被恢復與流域氣候要素變化之間具有良性的互饋作用。大規模植被恢復后,流域地表風速、水面蒸發量、干旱指數及土壤蒸發量顯著降低,最終引起流域的蒸散發能力的降低和土壤蓄水量的增加,這些要素的變化對提高流域水源涵養能力和改善流域半干旱的氣候條件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