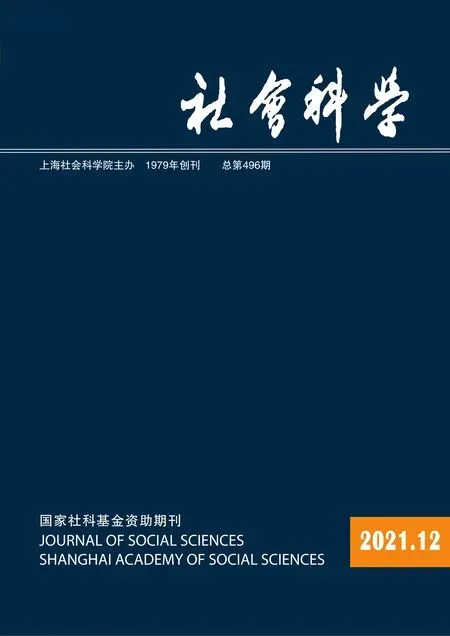多元與融合:風險社會中的危機致貧及治理框架建構
林 茂
一、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來,我國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方面,這是經(jīng)濟與社會成功轉(zhuǎn)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國家、市場、社會良性互動所致。然而,貧困治理絕對不是一勞永逸的事。貧困,從有形財富比較的角度來看,是一種既有的收入低下、溫飽問題突出的社會事實。(1)孫德超、周媛媛、胡燦美:《70年“中國式減貧”的基本經(jīng)驗、面臨挑戰(zhàn)及前景展望——基于主體-內(nèi)容-方式的三維視角》,《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但貧困問題不僅涉及絕對意義上、縱向維度(時間階段)最為基本的需求無法滿足,更涉及橫向維度(社會空間)基于先賦性社會資源存在狀況的差異比較,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資源占有的不均衡。貧困也從來都不只是個體生活困境問題,更是與之相關的環(huán)境、制度以及社會公平與公正問題。
在社會的復雜轉(zhuǎn)型中,貧困個體所面臨的往往是個體困境與社會危機疊加,尤其是在前現(xiàn)代向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進程中,現(xiàn)代性的風險和突發(fā)性危機導致的貧困或“返貧”是值得關注與預警的。舉例來說,根據(jù)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的統(tǒng)計,近些年來,全球各國在解決多維貧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自2019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這一進展倒退8至10年。(2)多維貧困指數(shù)(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是一種著眼于超越收入的指標,包括安全飲用水、教育、電力、食品和其他六項指標。參見《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新冠疫情或使世界解決多維貧困進展倒退8至10年》,聯(lián)合國新聞網(wǎng),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7/1062381,2020-07-16。突發(fā)性的公共危機,不僅帶來對各國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驗,同時也促進政治體制的完善和社會群體的博弈,創(chuàng)造出規(guī)則重組的機會。與傳統(tǒng)社會個體由于脆弱與饑餓而導致的貧困有所不同,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由突發(fā)性公共危機所導致的貧困,和不可抗力相聯(lián)系,呈現(xiàn)出一種不確定的、流動的與無邊界的狀態(tài)。
我們身處的現(xiàn)代社會或“后現(xiàn)代社會”,是正在經(jīng)歷第二次現(xiàn)代化的“風險社會”,是社會物質(zhì)極大豐富、科技高度發(fā)展的社會,其所面臨的“不可抗力貧困”卻伴隨著風險與危機無處不在。迅速的、激烈的、突發(fā)的社會危機,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加劇了對現(xiàn)代社會穩(wěn)定性的沖擊。(3)林茂:《危機社會治理中的“法律”及其屬性》,《求索》2021年第1期。一方面,長效穩(wěn)定的分配制度在應對危機事件時,其滯后性顯而易見。改善分配制度的程序合法性的建立以及新制度的實施,滯后于應對突發(fā)性危機所需的時效。另一方面,個體精神領域的貧困,無法簡單地通過科技進步與制度完善來解決。
精神領域貧困所導致的社會成員個體之間互動關系模式的改變、社會信任機制的破壞,以及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侵占,都促使既往累積的社會問題在突發(fā)公共危機中進一步強化,展現(xiàn)出社會個體精神與能力的雙重貧困狀態(tài)。如何在物質(zhì)資源豐富的情況下,解決風險社會中的危機致貧問題?這一問題不僅與社會整體收入、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分配制度高度相關,更與個體能力、權利維度高度相關。
危機致貧呈現(xiàn)出不確定性與流動的狀態(tài),個體困境演化早已超越生命周期的階段性(幼年期、老年期、哺乳期等弱勢階段)。基于多元融合視角,對危機致貧治理框架的建構,其前提就在于承認貧困的不確定性和多元化,承認彼此沖突的判斷貧困的價值原則的存在,如對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定義與判斷。價值原則的多元化使我們在認識貧困產(chǎn)生的機制及其后果上產(chǎn)生不同的“優(yōu)先性”(priorities)排序。本文試圖超越個體-社會兩極對立的格局,從人類共同體視角出發(fā),探尋和總結社會危機引發(fā)的貧困問題的內(nèi)涵、特征及其治理框架。只有聚焦于現(xiàn)實視角,才能促使我們更容易阻止真實存在的非正義,從而真正實現(xiàn)共同富裕。
二、危機致貧:不確定性、流動性與無邊界性
現(xiàn)代社會面臨著動蕩 (Volatility)、不確定 (Uncertainty)、復雜 (Complexity) 與模糊 (Ambiguity) 的風險。(4)應驗:《風險社會中的公共危機治理》,《中國治理評論》2021年第1期。“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與不可控性所招致的匱乏狀態(tài)與以往研究所發(fā)現(xiàn)的由物質(zhì)需求導致的貧困有所不同。(5)[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 新的現(xiàn)代性之路》,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 2 頁。在風險社會中,與公共危機相伴,貧困作為一種生活狀態(tài),具有不確定性、流動性與無邊界性的特征,且往往是兩種維度貧困混合的產(chǎn)物。(6)Robert Walker, The Shame of Prop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第一維度的貧困,即維持生存需要的最低物質(zhì)需求。這一維度的貧困高度同質(zhì)化且可量化,如貧困區(qū)域和低保收入的劃分多著眼于此。第二維度的貧困(多維貧困),則是精神、文化、法律、權利方面的貧困。(7)參見Sabina Alkire, Suman Seth,“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between 1999 and 2006: Where and How?”, World Development, Vol.72, 2015, pp.93-108。
危機致貧同樣涉及上述兩個維度,具體是指受制于現(xiàn)代性的整體風險而產(chǎn)生的公共危機,進而由這一危機所引發(fā)的物質(zhì)與精神上的雙重匱乏。這種匱乏或“闕如”的狀態(tài),伴隨著相對剝奪而產(chǎn)生,與社會正義高度相關。既往的研究中,多數(shù)反貧困研究以探尋完美正義的應然性為目標而建構理論框架,將抵抗貧困的結果正義看作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并試圖確立一種先驗性的完美正義制度的框架,從而實現(xiàn)按照“社會的基本結構分配某些基本物品”。(8)[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頁。這樣的理論框架對現(xiàn)實背景下個體或群體危機困境的判斷難有突破。原因在于,風險社會下的公共危機,以一種更為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加劇了基于制度的貧困,與社會選擇條件下對權利的剝奪有一定的相關性。
以被征地或拆遷的農(nóng)民為例,第一維度的貧困多是征地賠償款低于市場價格而導致的物質(zhì)貧困——農(nóng)民不能再購買住房,既往社會關系受到破壞而沒有得到補償?shù)取_@一維度的物質(zhì)貧困通過行動實現(xiàn)補償平等即可以解決。事實上,自2010年后,我國因被征地或拆遷引發(fā)的物質(zhì)貧困問題已經(jīng)基本得到解決,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二維度的貧困卻更加常態(tài)化。一些被征地或者被拆遷的農(nóng)民從事保安、清潔工等職業(yè),從農(nóng)民變成市民,部分人無業(yè),依靠房租生活。他們中的一些人就財富而言,或許已然豐裕,但其在能力及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等領域的匱乏狀態(tài)卻更加突出。換言之,解決民生問題,不等于獲取民生權利。在政治領域和精神領域,這一群體的部分人仍然處于貧困狀態(tài)。面對突發(fā)性的公共危機,如新冠肺炎疫情引發(fā)的危機,依靠租房、從事底層體力勞動的“市民化農(nóng)民”群體,其貧困的不確定性集中體現(xiàn)為抵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中的自然風險的能力不足以抵御社會風險,這些社會風險不斷累積就可能成為一種整體性社會危機。當疫情導致人口流動減少、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萎縮進而引發(fā)退租、失業(yè)等社會風險時,剛剛成為“食利者”的“市民化農(nóng)民”既有的生活經(jīng)驗中抵御自然風險的能力和技巧失去了應有價值。(9)張康之:《論風險社會中的危機意識》,《黨政研究》2020年第6期。
究其原因,“農(nóng)民市民化”后所擁有的重要權利仍是基于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但源自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驗的勞動力并不被城市社會需要,無法用于交換。農(nóng)民在市民化過程中,喪失了主體性能力,是“被制度化安排的市民”。(10)文軍:《“被市民化”及其問題——對城郊農(nóng)民市民化的再反思》,《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這一社會現(xiàn)象伴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推進而涌現(xiàn),并非新生事物。在工業(yè)革命發(fā)展初期,農(nóng)民由于土地有限而脫離土地,四處謀生,造就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城市。(11)[德] 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發(fā)生和心理發(fā)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頁。現(xiàn)代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將這一群體納入,為他們提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避免他們因勞動力無法在城市市場交換而淪為赤貧,但這僅僅是在常態(tài)穩(wěn)定的現(xiàn)代社會中的狀況。隨著公共危機與整體性風險的出現(xiàn),疊加在這部分群體身上的則是:稟賦權利不能充分發(fā)揮的貧困,(12)Yan-Yan Chen, Liu Hong and Robert Walker, “Reconstructing Poverty-Related Shame Among Urban Seniors in China: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Narrated Experiences and a Reflection on Anti-Poverty Intervention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Vol.12, 2020, pp.1-21.且交換權利由于公共危機無法得到滿足,進而導致突發(fā)性的、不確定性的窮困或“返貧”。這種貧困伴隨著公共危機而不斷流動、擴張,又呈現(xiàn)出無邊界性的特點。全球經(jīng)濟與社會的一體化,使得一國以內(nèi)的危機不再局限于某個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空間,如全國各地的“三和青年”們,(13)參見田豐、林凱玄:《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diào)查》,海豚出版社2020年版。流動性促使危機致貧不斷疊加與放大,由此所造就的貧困也成為全球范圍內(nèi)流動的貧困。
(一)相互疊加的匱乏狀態(tài)
風險社會中的危機致貧,從經(jīng)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是一種社會關系,(14)李小云:《消除貧困:中國扶貧新實踐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6期。更加準確地說是一種分配關系,是各種社會關系沖突在危機境況中,以疊加的方式呈現(xiàn)出的資源匱乏的狀態(tài)。因此我們需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有效防范和化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15)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 25 頁。針對疊加的匱乏,解決的辦法是提供底線保護,聚焦于不同群體對食物的支配/控制能力的權利差別關系。這樣一種疊加的匱乏狀態(tài),表現(xiàn)在權利領域,是象征職業(yè)群體能力的技術資格證及“稟賦權利”(土地、自身的勞動力)不再有價值,其“交換權利” (從事生產(chǎn)并與他人交換以獲得商品)不能實現(xiàn)。在現(xiàn)代社會中,當一個人基于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而處于貧困狀態(tài)時,這一狀態(tài)呈現(xiàn)出權利和能力被剝奪的局面是客觀存在而不可控的。(16)[美]阿瑪?shù)賮啞ど骸敦毨c饑荒——論權利與剝奪》,王宇、王文玉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8頁。突如其來的經(jīng)濟危機、行業(yè)蕭條與失業(yè)潮,進而引發(fā)的“房貸”“車貸”等各種借貸體系的崩潰,在美國的“次級債危機”中得到深刻的展現(xiàn)。疊加的匱乏狀態(tài)不僅體現(xiàn)在導致匱乏的負面原因?qū)訉盈B加,在呈現(xiàn)的后果上,其匱乏的類型與程度更是一場深刻的危機,即物質(zhì)、精神與權利的多重潰敗。其多重性表現(xiàn)在物質(zhì)領域,是基本物品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時,“特殊需要”更是不被滿足,如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愛與尊重的需要。這種多重性表現(xiàn)在權利-能力領域,則是個體無法獲得平等發(fā)展的機會。
面對這一多重匱乏的狀態(tài),古典的治理框架對基本物品的概念化與一般化,使得傳統(tǒng)的貧困治理成為一個同質(zhì)化的過程,難以解決這一貧困問題。根據(jù)對基本物品的獲得來判斷制度的優(yōu)劣以及正義的實現(xiàn)效果,只是考慮到貧困的單一中心發(fā)展模式中某一階段的物質(zhì)匱乏狀態(tài)。實際上,在風險社會中,一種復合的能力(capabilities)、權利與功能,及其所帶來的自由選擇,使得個體有可能實現(xiàn)各種功能n元組合, 其“復數(shù)能力”的自由建構才是解決匱乏狀態(tài)的關鍵。(17)[印] 阿瑪?shù)賮啞ど骸逗蠊u價與實踐理性》,應奇、劉訓練譯,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頁。從多元整合的角度來看,基于自由選擇發(fā)展自身能力的權利與保障多重能力,皆需法律與政策層面的支持,尤以底線保護為重。底線保護更為深刻的內(nèi)涵在于,底線所蘊含的物質(zhì)、精神與權利的基礎性資源平臺,表現(xiàn)在個體身上,則是通過選擇各種可能的能力與功能的組合,(18)[印] 阿瑪?shù)賮啞ど骸逗蠊u價與實踐理性》,第215頁。這是個體解決現(xiàn)代性不確定風險所導致的貧困問題的主要路徑。
就此而言,社會關系中的信任、人的自主性、人際間差異性,還包括受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福利制度等保障人的權利與能力,可用于理解危機與貧困之間的關聯(lián)。因此,在哲學層面增強個體“人”的情感、文化、道德等對規(guī)范和規(guī)則的作用,在社會學的層面將集體、行動看作建構以軟法/活法為代表的法律體系的重要元素,從多元主體參與的視角出發(fā)理解規(guī)則的形成和現(xiàn)代國家管理的轉(zhuǎn)型,是對危機致貧問題作為社會關系的最為基礎性的回應。
基于社會群體的異質(zhì)性,我們可將貧困進一步類型化,將其分作先賦性貧困、自致性貧困、制度性貧困等。但基于社會危機而引發(fā)的貧困,涵蓋且不限于上述類型。在多元整合發(fā)展的模式下,要將貧困的常態(tài)化與非常態(tài)化加以區(qū)分,因此,將需求決定論置于貧困研究之前就顯得尤為重要。面對風險社會的來臨及其挑戰(zhàn),強化危機意識,理解貧困問題中的多重疊加狀態(tài),或許將催生出風險國家 (risk state) 這樣一種新型的后行政國家的治理體系,(19)劉鵬:《風險社會與行政國家再造:一個行政學的闡釋框架》,《學海》2017 年第 3 期。從而從根本上提升個體的復合能力及其能力所蘊藏的社會功能。
(二)選擇及多重需求難以滿足的困境
上述所言“復數(shù)能力”的缺乏,與角色集的概念類似,并不是彼此互斥的缺乏狀態(tài),而是表現(xiàn)為整體性的多重能力及功能的缺乏。“復數(shù)能力”的缺乏并非簡單的各種單一能力所具有功能的無法實現(xiàn)或不完全實現(xiàn)的總和狀態(tài),而是對多重能力的選擇、重組與整合過程中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表現(xiàn)出的自由,以及日常生活實踐的邏輯與智慧的缺乏。這種缺乏首先是能力種類不足——做選擇的前提在于有多種選擇存在。其次,缺乏平等地進行多種選擇的機會。最后,在機會平等與選擇自由之間,個體即使擁有多重能力,仍缺乏實現(xiàn)多重能力所需的選擇的智識與自由。
現(xiàn)代社會帶來物質(zhì)的極大豐富,但并不意味著工業(yè)社會比農(nóng)業(yè)社會貧困現(xiàn)象大量減少。事實上,面對現(xiàn)代性所帶來的返貧風險,每一次都激發(fā)出社會學意義上對確定的、農(nóng)耕社會的懷念。這與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對宏觀社會結構的認識高度一致,即“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對貧困的定義,多是就同一類資源和實物占有的比例多少而言的。(20)梁樹廣、黃繼忠:《基于貧困含義及測定的演進視角看我國的貧困》,《云南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單一的、簡單的需求所帶來的穩(wěn)定性,在現(xiàn)代風險社會之下,已然改變。
風險社會中危機致貧的突發(fā)性、客觀性與邊界不可控緊密結合。從需求的角度來看,基于滿足生存的需要而對農(nóng)民與鄉(xiāng)土的珍視,呈現(xiàn)出單一的資源占主導的美好生活。然而,現(xiàn)代性的危機致貧,所要滿足的則是多重的需求與資源占有。所要求的能力-功能重組所創(chuàng)造的美好生活,是難以通過簡單的物質(zhì)需求滿足就可以實現(xiàn)的。這一重組打破了既往的對于貧困群體的簡單想象。
單一需求的貧困群體想象源于勞動分工所造就的專業(yè)化發(fā)展。長時間以來,專業(yè)化被認作現(xiàn)代社會穩(wěn)定的構成基礎,職業(yè)群體之間所具有的異質(zhì)性知識和能力,本不具有統(tǒng)一量化評比的可能性,因此也不具有基于評比結果而產(chǎn)生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普遍意義上某一群體相對于其他群體的貧困。然而,流行于各學科的馬斯洛需求等級所體現(xiàn)出的從物質(zhì)到精神的排序理論呈現(xiàn)出中心主義的霸權,忽視了貧困的整體性,即物質(zhì)需求的滿足所對應的能力,及這種能力所獲得的社會認同在常態(tài)社會中低于滿足精神追求的能力所獲得的社會認同。
農(nóng)民所掌握的四季生產(chǎn)的知識與制造芯片的科學家所掌握的微電子技術知識并無優(yōu)劣之分。從微觀的個體角度來看,閱讀識字的能力,與烹飪料理家務的能力皆是生活所必需,在風險社會中,面對存活和發(fā)展的需求,烹飪和家務能力的必要性甚至更強,但閱讀識字等作為滿足前者之后的“奢侈品”與“富余的愛好”則變?yōu)楸匦杵贰M话l(fā)性危機促使我們正視物質(zhì)、精神與權利的多重貧困和剝奪的匱乏狀態(tài)。
在此意義上,風險社會所帶來的危機致貧所呈現(xiàn)出來的對能力的需求打破了從物質(zhì)(低級)到精神(高級)這一中心主義的理論路線。風險社會的系統(tǒng)性,不同風險之間暗藏著的豐富內(nèi)在聯(lián)系,(21)[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 新的現(xiàn)代性之路》,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使得現(xiàn)代社會公共危機,通常以專業(yè)分工鏈條上某一環(huán)節(jié)的平衡被打破而呈現(xiàn),進而導致社會面臨全面的風險與多重需求無法同時滿足的狀態(tài)。
三、危機致貧的發(fā)生機制:分配與能力
現(xiàn)代社會中風險的非邊界性突出,全球化使得一國以內(nèi)的風險不再局限于某個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空間,風險的流動性促使基于突發(fā)性的公共危機也不斷疊加與放大,由此所造就的貧困也成為全球范圍內(nèi)流動的貧困。這一流動性使得現(xiàn)代危機致貧不僅是一種社會關系,還是受制于空間發(fā)展的社會關系集合。現(xiàn)代性危機使每個人都難以置身事外,整個社會乃至全球成為共同體。基于常態(tài)性的、全面性的風險而導致的突發(fā)性危機,也促使共同體內(nèi)資源發(fā)生變化。不同的社會和國家,在應對現(xiàn)代性的風險的過程中,基于危機而產(chǎn)生的貧困深受分配不均衡的影響。
對現(xiàn)代風險的控制需要整體思維,更需要區(qū)域合作和全球合作。合作通常建立在兩種方式之上:通過暴力或通過自愿、自發(fā)。(22)[英]赫伯特·斯賓塞:《社會學研究》,嚴復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88頁。局限于傳統(tǒng)行政區(qū)劃和民族國家范圍內(nèi)的風險控制難以應對流動的外生性風險。因此,個體的社會成員或國家居于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與自然環(huán)境中,常態(tài)化的分配方式,即基于既有稟賦差異的分配將進一步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無論處境最差的群體是否應該為自己的不利境地承擔責任,在資源共享層面,面對“無知之幕”,作為共同體的社會,富有者是否應當為稟賦差異負責而救濟貧困者都成為一個難題。(23)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Revisited”, Ethics, Vol.113, No.1, 2002, p.122.
事實上,在共同體之中,區(qū)分“選擇(分配)”和“環(huán)境”,排除由環(huán)境因素所帶來的不平等,個體應當為自己的選擇所帶來的貧困承擔責任。在一個社會內(nèi)部,如何解決由天賦不平等所導致的貧困?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旨在緩和自然資產(chǎn)的分配對貧困的影響。但是在尋找與確定處境最差者(最為貧困者)的指標時,這一特殊性的建構,暗含了主觀價值評判。(24)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4.從分配的角度來看,自然資源與天賦不應該被用來為個人謀利,而應該為社會全體成員所共享。共同的財富必須屬于共同的主體,將差別原則建立在共同體觀念的基礎上是一種路徑,而個人對其天賦是不應得的和不應擁有的,是否意味著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就對它們是應得的和應擁有的?依照對所擁有的天賦的不同看法,個體與其所對應的天賦之間,是所有權意義上的天賦的“擁有者”(獨占者與絕對支配者)還是為共同體所有的天賦的“監(jiān)護者”(使用者)?(25)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99.因此,在危機狀態(tài)下,由于分配而導致的貧困,這一問題本身與資源的先天分布不平等類似,是環(huán)境作用于個體或人類社會的結果。
(一)分配與再分配:總體性風險打破分配平衡
社會世界基于人的總體性智慧并通過征服自然所獲得的財富,卻在總體性的風險出現(xiàn)并成為危機后產(chǎn)生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不平衡。面對共同性的危機致貧,財富、權力的分配與貧窮之間的關系在亞洲文化中已經(jīng)建立起因果的認知。(26)張清:《貧困與自由:基于印度“不平等”的憲政分析》,《學習與探索》2010年第2期。在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過程中,避免分配不均而產(chǎn)生的危機成為常態(tài)化社會條件下生產(chǎn)關系變革的動機。(27)孫永平:《自然資源與經(jīng)濟増長關系的歷史考察——三次“中心-外圍”格局的形成及其轉(zhuǎn)換》,《經(jīng)濟評論》2011年第2期。在風險社會中,由社會本身運行規(guī)律所導致的全面風險,基于專業(yè)化的分工與科層制的發(fā)展,在一國內(nèi)部無法依托單一部門進行防范和控制。面對突發(fā)性的經(jīng)濟危機、公共衛(wèi)生危機、環(huán)境危機,既有的分配格局與資源供需平衡被打破,調(diào)整既有的分配制度所需要的統(tǒng)籌管理與時效,常常使得再分配的平衡具有滯后性。由此而產(chǎn)生的危機致貧深受分配制度影響,如“中產(chǎn)階級陷阱”,以一種突發(fā)事件出現(xiàn)在個體日常生活之中。
社會內(nèi)部的分配不平等所引發(fā)的貧富分化是穩(wěn)定社會的常態(tài),但現(xiàn)代性框架下的危機加劇了這一分配制度的不完美。如果我們運用斯賓塞的人格化的理論,將會發(fā)現(xiàn)不同國家先賦性資源的多少源自于對自然的掠奪,這本身存在貧困危機。但在整體性風險引發(fā)的突發(fā)性危機中,對風險的認知增強了所有行動主體的危機意識,這會導致這種資源占有量的分化更為明顯。因此,危機致貧,在相對意義上而言,還源自既有分配的靜態(tài)與慣性,無法滿足危機之下需求的增加。借由危機而必須進行的再分配,對既有的分配框架的改變,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對既有分配框架的習慣和安全感或再分配制度建立的滯后性,都可能產(chǎn)生新的貧困或加劇貧富分化。
既有的分配制度對處于弱勢地區(qū)和國家的資源掠奪,將進一步導致這部分群體處于全面危機與貧困之中。然而,不管是先賦性的差距(對自然的掠奪)還是分配的掠奪,兩條掠奪的路徑,從未有心甘情愿的臣服者。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引發(fā)的全球公共危機中,對新冠疫苗的爭奪,超越了原有的市場經(jīng)濟下商品交換的屬性,演變成為強勢國家與貧困國家的生存競爭,歐洲各國對美國疫苗預定的爭奪即屬此例。
在全球化過程中,多中心之間的經(jīng)濟、人口、商業(yè)的流動,讓一國內(nèi)部的危機在各大陸之間傳播“變異”,在認知領域強化了個體對風險與危機的認識。“人人自危”與對貧困者的放棄、掠奪,這是社會在戰(zhàn)勝貧困的道路上不得不面對的“自造的囚籠”。這一危機所帶來的貧困均基于進化論思維與中心化/同化邏輯,排除多樣性與多中心,這將可能導致全球陷入普遍性的危機致貧。
換言之,作為差異性存在方式的傳統(tǒng)貧困,對于阻隔危機(如新冠疫情)的公共性傳播或許反而是有積極意義的。如那些基于低需求而獨立于全球化以外的國家和地區(qū),由于缺乏流動性,也減少了對全球化的依賴,由此避免社會系統(tǒng)因過度滿足“偏頗性供給”的需求而發(fā)生危機致貧。類似前現(xiàn)代社會中,糧食自足而不依賴進出口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避免共同危機致貧。但一種以單一中心或單邊主義為主的社會發(fā)展模式,制造絕對的富有與絕對的貧困本身就是違背多元中心發(fā)展的壟斷模式,全球化危機致貧背后更深刻的卻是本身固有的特定區(qū)別,(28)[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7頁。在文明與非文明種族之間如此,在生命體之間也是如此。因此,在對抗危機致貧的過程中,基于差異而產(chǎn)生的整合分配再平衡就顯得尤為必要。
(二)個體能力無法通過常規(guī)分工與社會交換實現(xiàn)
在全球化進程中,突發(fā)性公共危機防控取得成效的核心技術往往成為治理危機問題的關鍵。如同前現(xiàn)代社會中農(nóng)耕制度作為核心因素可以緩解物質(zhì)貧困一樣,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能力和基于此而產(chǎn)生的技術是解決貧困的重要因素。技術為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提供了工具,而技術功能的實現(xiàn)則依賴于社會內(nèi)部成員間權利與社會整體權利的分配。
如前所述,基于危機的突發(fā)性與不確定性,在整體性危機到來的時刻,個體全面發(fā)展的權利難以通過常規(guī)的社會運轉(zhuǎn)鏈條和交換行為實現(xiàn)。個體多重能力不僅包含一個人利用各種能夠獲得的法定渠道以及所獲得的可供選擇的商品束的集合——對事物的所有權是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最基本的權利之一(29)Amartya Sen,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3, No.372, 1983, pp.745-762.——同時也包括對其所擁有的能力進行自由交換的權利。受制于突發(fā)性的社會危機,對貧困的定義不再是數(shù)字標準,而是具體的情景以及情景之下的行動限制。只有給予人們在行動上更大的自由、更多的選擇、更多的機會,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將危機致貧消除。(30)Amartya Sen,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3, No.372, 1983, pp.745-762.不僅如此,危機致貧也不再是不發(fā)達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一個區(qū)域性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是每一個國家,是整個人類世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權利視角”(Entitlement approach)下,造成饑荒的真正原因并不是食物短缺,而是由于個人所擁有的交換權利不斷下降。(31)[印]阿瑪?shù)賮啞ど骸兑宰杂煽创l(fā)展》,任賾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頁。在面對公共危機時,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數(shù)量緊缺,從社會的角度出發(fā),社會治理在危機環(huán)境中不僅應當提供基本的食物供應和保障,更應該制定可保護人民權利、發(fā)展可行性能力(capability)的措施,從而建構人們進行選擇和行動的“實質(zhì)性自由”。(32)[美]瑪莎·C.納斯鮑姆:《尋求有尊嚴的生活》,田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頁。
基于能力而產(chǎn)生的貧困的焦點不在于一個人事實上最后做了什么,而在于他實際能夠做什么,即能力所產(chǎn)生的功能實現(xiàn),而無論他們是否會選擇使用該機會。(33)[印]阿瑪?shù)賮啞ど骸顿Y源、價值與發(fā)展》(下) ,楊茂林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 271 頁。通過自由的選擇和發(fā)展,個體獲得一定的社會認同的功能與特性,利用這些功能和特性獲得成就、福利以及人的主體性,從而真正擺脫貧困。這是農(nóng)耕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轉(zhuǎn)型中,先賦性資源依賴降低后,人對自身自決性的體現(xiàn)。
在現(xiàn)代社會中,公共危機所導致的貧困狀態(tài),其內(nèi)涵和意義都發(fā)生了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向,在既有框架下定義貧困群體,不但要面臨本身所既有的能力、權利的缺陷以及功能的不可實現(xiàn),還必須承認面對“具體性的事物和問題,只有在其出現(xiàn)了某種端倪的時候,才能作出應對的選擇”(34)張康之:《論風險社會中的危機意識》,《黨政研究》2020年第6期。的無能。危機致貧的突發(fā)性、流動性與無邊界性,讓身處危機致貧中的行動主體無法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當風險以危機事件的形式出現(xiàn)的時候立即作出反應。
四、邁向多元融合的危機致貧治理模式
個體與整個社會皆有危機致貧的風險。回顧人類社會多線發(fā)展的艱難歷史、認識困境與應對困境,可以發(fā)現(xiàn)人類對貧困的認知體系的探索經(jīng)歷了差別化-多元化-一體化的不同階段。差別化階段,主張尊重主觀先賦性因素的異質(zhì)性與個人選擇的自由;多元化階段則強調(diào)在差別中去中心化發(fā)展,通過分配制度上減小貧富差距,尊重多樣化發(fā)展,避免霸權主義與同質(zhì)化;一體化階段,在保留多元的基礎上,強調(diào)實現(xiàn)以人類共同體為基礎的“共同善”以對抗未來的不確定性,而不是鏟除過去的先天性的差異性。這里的一元概念指的是同質(zhì)性、單一中心的貧困(治理)模式;多元則指的是異質(zhì)性、多中心的貧困(治理)模式。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面臨一元和多元并存,強調(diào)多元一體、多元融合,而不是單邊主義或同質(zhì)化,其目的在于回應和尊重多樣性與人類總體價值。
我國的多元化發(fā)展不僅包含兼容并蓄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還包括在生產(chǎn)技術領域中不同技術間打破壁壘與界限,相互融合,提高生產(chǎn)力從而走向繁榮和富強。相比于海洋文化與殖民者開拓精神,我國本土的有關利益的、宗教的、對生命本身的理解等多種狀態(tài)綜合成一種對世界整體干預狀態(tài)。我國在發(fā)展路徑與治理模式上多中心、多元融合的發(fā)展模式,植根于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兼容并蓄與相互轉(zhuǎn)化的辯證思維,歷久彌新,為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相對于西方二元且對立的發(fā)展模式,在社會理論層面,我國社會治理的多元化特征與優(yōu)越性,值得學界進行多方面、全方位的討論。
建構多元化的發(fā)展路徑本身在于通過多元化消解不同單元的界限和排斥,從而減少面對整體性危機時的機會不平等。“強調(diào)以多樣和統(tǒng)一辯證的觀念觀察世界,既強調(diào)世界多樣、道路多樣、文明多樣,具有多樣性,也注重共同性,它反對‘西方中心論’‘霸權主義’‘單邊主義’,是主張國家平等、文明互鑒、包容發(fā)展、互利普惠的文明”。(35)韓慶祥:《深刻把握“中國式現(xiàn)代化新道路”豐富內(nèi)涵》,《學習時報》2021年8月30日。只有通過制度建設實現(xiàn)多元之間的融合,才能讓那些原本有可能憑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變經(jīng)濟狀況的群體平等地獲得重要的對抗危機致貧的機會。
(一)個體基于自由發(fā)展的可行能力塑造與實現(xiàn)
可行能力的多元化是亟須被正視的解決危機致貧的重要因素。通常而言,個體受教育越多、知識水平越高,他們的見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們贊同某種價值等級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基于個體差異性,貧困問題面臨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向,對貧困的認識更多聚焦于交換權利的不可實現(xiàn),而非稟賦權利的不可獲得。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中,我們可能將面對更多多元化發(fā)展帶來的挑戰(zhàn)與不確定性。其結果必然是:如果我們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觀念,就必須降格到道德和知識標準比較低級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與趣味占統(tǒng)治地位。(36)[奧]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鄧正來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16頁。面對疫情疊加衰退,社會呼喚多邊反危機協(xié)調(diào)新模式以建立底線保護。(37)雷達、武京閩:《疫情疊加衰退:呼喚多邊反危機-協(xié)調(diào)新模式》,《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4期。
從整體論意義上看,解決危機致貧,能力、權利與自由均涉及個體內(nèi)在的自主性,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同義反復。在能力與功能實現(xiàn)之間,受到三組“轉(zhuǎn)換因素”(conversion factors)的影響。第一,個人轉(zhuǎn)換因素(如新陳代謝、身體狀況、性別、閱讀能力、智力),影響一個人怎樣將商品的特性轉(zhuǎn)換為一項功能。第二,社會轉(zhuǎn)換因素(如公共政策、社會規(guī)范、歧視性行動、性別角色、社會階級、權力關系)。 第三,環(huán)境轉(zhuǎn)換因素(如氣候、地理位置),在從物品特性轉(zhuǎn)換為個人功能的過程中產(chǎn)生影響。(38)Ingrid Robeyn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 Theoretical Survey”,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6, No.1, 2005, pp.93-114.從能力-功能的角度解決貧困問題,超越了個體層面的能力建構,強調(diào)應當更多地著力于公共政策層面能力的獲得與基本需求相結合,使基本能力(basic capacity)在解決危機致貧問題時更具效力。(39)鄭智航:《全球正義視角下免于貧困權利的實現(xiàn)》,《法商研究》2015 年第1期。即,在單一中心模式下,極端的貧困問題的解決只需要通過獲得相應的基本能力,進而占有維持生命活動必需的食物和住所。在其他語境下,包括經(jīng)濟發(fā)展的更為一般的問題,這個基本能力的構成清單可能很長而且更不相同,(40)[印] 阿瑪?shù)賮啞ど美] 瑪莎·努斯鮑姆主編:《生活質(zhì)量》,龔群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7 頁。類似于亞里士多德所言,人的功能是獲得幸福生活(Eudaminia)的能力。自由和主體性成為能力的本質(zhì)體現(xiàn),這一觀點如前所述,深受亞里士多德傳統(tǒng)的影響。(41)[印]阿瑪?shù)賮啞ど骸墩x的理念》,王磊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頁。解決危機致貧問題,從個人優(yōu)勢視角來看,對能力的研究探求的結果歸結為“自由”,一個人能否自由地做他有理由珍視的事情,這一情形比擁有“基本善”更能體現(xiàn)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優(yōu)勢。(42)[印] 阿瑪?shù)賮啞ど美] 瑪莎·努斯鮑姆主編:《生活質(zhì)量》,龔群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1頁。
發(fā)展多重能力的自由、自主選擇并整合能力,成為應對風險疊加的現(xiàn)代社會中危機致貧的一種設想。如對于貧困村與鄉(xiāng)村貧困家庭,我們國家扶貧的思路也發(fā)生了從“為生存而生產(chǎn)”向“為市場而生產(chǎn)”的轉(zhuǎn)型。(43)王春光、單麗卿:《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中的“小農(nóng)境地”與國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貧困村產(chǎn)業(yè)扶貧實踐的社會學分析》,《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扶貧政策也聚焦“服務轉(zhuǎn)向”,通過建構自下而上的農(nóng)民賦權的維度,呈現(xiàn)出基于農(nóng)民主體的差異性為主的多元化的扶貧方式。(44)李小云、徐進:《消除貧困:中國扶貧新實踐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6期。危機致貧是社會關系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的產(chǎn)物,減少或消除貧困必然涉及到社會關系的變化,而減少或消除貧困的機制也表現(xiàn)在扶貧政策與社會系統(tǒng)的互動上。(45)王浦劬、湯彬:《當代中國治理的黨政結構與功能機制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 9 期。從社會學角度看,復合型治理結構決定了政治與行政之間的系統(tǒng)性、整體性和協(xié)調(diào)性。(46)王春光《中國社會發(fā)展中的社會文化主體性——以 40 年農(nóng)村發(fā)展和減貧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 11 期。
同時,個體自由發(fā)展可行能力在現(xiàn)實領域,得到一定的實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福利制度應確保個人在所擁有的交換權利不斷下降時,能使用合法的分配方式掌控事物所有權的能力,這一權利再分配的體系與國家權力高度相關。國家應提供再教育和培訓資源,提供就業(yè)機會,使得農(nóng)民能力復合化、多元化以應對現(xiàn)代化專業(yè)分工所帶來的生存危機,從而實現(xiàn)在城市中再就業(yè)。促成社會群體能力多元化的過程,在群體性結果的層面,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發(fā)展模式,即專業(yè)化的多中心、個體的多重能力、地理空間的多中心發(fā)展。這一發(fā)展模式,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在運轉(zhuǎn),政治、經(jīng)濟、文化領域都呈現(xiàn)出多元化發(fā)展的特征。
(二)國家-社會系統(tǒng)內(nèi)部:差別化原則與多元融合
上述個體能力的建設,是從微觀行動角度出發(fā),建構危機致貧的治理框架。從宏觀結構角度看,在多元中心模式下,如何在一國內(nèi)部應對危機、建設個體成員多重能力?差別原則應用于現(xiàn)代化過程中發(fā)達地區(qū)對欠發(fā)達地區(qū)的援助似乎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這一行為本身在方法論上的可能性討論并不是重點,面對突發(fā)性危機,基于分配方式而造成的貧困及非正義討論才是爭議的焦點。富裕地區(qū)的居民是否有基于正義幫助危機致貧地區(qū)的義務?基于先驗主義視角既定的自然資源分布不均的現(xiàn)實與建設多重能力而選擇的資源再分配原則,實現(xiàn)正義的過程和以正義為目的的行動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分離,“每一個人對總體可利用資源的一份都有一種平等的顯見要求權”。(47)[美]查爾斯·貝茲:《政治理論與國際關系》,叢占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頁。如果能夠踐行資源再分配原則,資源較為貧乏地區(qū)的居民獲得發(fā)展能力所需要的經(jīng)濟條件保障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這一合法性從人類整體的利益來看,常常導致以正義為目的的行動產(chǎn)生非正義的行動過程,如為搶奪疫苗而忽視既有貧困地區(qū)群體的生存狀況。為解決先賦性因素的不平等采取再分配行動而實現(xiàn)結果平等,是不能忽略過程平等的。
基于分配制度而引起的貧困受制于人的主觀能動性,“決定一個國家經(jīng)歷、進展如何的關鍵因素是其政治文化”。(48)[美]約翰·羅爾斯:《萬民法》,陳肖生譯,吉林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157頁。即使我們承認基于自然資源的分布而導致的傳統(tǒng)貧困是一個事實,但是分配制度對自然資源分布的處理方式,就關涉到國際制度的正義與否。(49)高景柱:《評約翰·羅爾斯與查爾斯·貝茲的國際正義之爭》,《世界哲學》2014年第4期。
因此,在制度體系框架下談論貧困以及非正義的解決方法,多元中心的模式除了考慮到自然資源的分布屬于先賦性的既定因素,還應考慮到基于道德上的任意性與人的自由選擇等因素。正是由于這兩個因素,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xié)調(diào)配套的基礎性制度,(50)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承認貧困的先賦性與客觀性,由此而實行的公共行為與制度建設應該維持多重能力建設的目標,避免公共危機加劇傳統(tǒng)貧困群體的貧困,進而實現(xiàn)人類共同體意義上的協(xié)同發(fā)展。在多中心發(fā)展模式下,為了減少危機致貧,基于系統(tǒng)外部力量的援助義務致力于滿足需求,使個體成為一個合乎情理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是再分配性援助義務的目標。(51)[美]約翰·羅爾斯:《萬民法》,第160頁。
(三)協(xié)同合作框架下打造多中心人類共同體
除多中心下的差別化發(fā)展以外,多元融合的模式建構還應考慮差別化所帶來的分歧如何解決。基于社會選擇以及社會分層的結果所展現(xiàn)出的等級與區(qū)隔,應將貧困治理的目標縮減為減小差距與去“等級化”,由此而衍生出針對貧困治理的備選方案。如果將相關群體實際生活評估體系的價值原則進行排序,我們會發(fā)現(xiàn),貧困治理在執(zhí)行層面以實現(xiàn)統(tǒng)一標準的需求滿足為基礎,將會忽略價值多元與利用局部排序的整合過程。(52)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Penguin Books, 2009, pp.2-7.正是基于更高層次的預防和消除危機致貧,貧困治理模式可能發(fā)展出多元融合的方案。
在理論建構層面,用社群主義來對抗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53)姚大志:《評桑德爾的分配正義觀》,《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建立起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zhàn)勝公共危機最有力的武器。(54)習近平: 《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zhàn)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人民網(wǎng),http://hi.people.com.cn/n2/2020/0416/c231187-33952040.html,2020-04-16。尊重差別原則,在承認差別的基礎上實現(xiàn)團結合作,對解決危機致貧問題的結果有個體化與整體化之分,從多元一體的角度來看旨在建立以社群主義為核心的聯(lián)合的善,或者說共同的善。(55)[美]約翰·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第170-172頁。這有別于單個的個體與民族國家的善,即一個國家/民族根據(jù)審慎的合理性而樂于從最高級的計劃中選的那項合理生活計劃所決定。”(56)[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第426頁。相對于整體性的危機致貧,聯(lián)合的善、基本善或者“天賦權利”意味著一個不能以任何其他善的目標來換取的前提性價值。(57)李偉:《正義與公共善孰為優(yōu)先——論桑德爾與羅爾斯政治觀的分歧》,《蘇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共同的善是對人類共同體共有價值的追求,表現(xiàn)在危機致貧問題上,它要求限制個人選擇與追逐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基于共同善進行援助與再分配。在多元中心模式下,強調(diào)社會有機體整體建設與個體成員發(fā)展并重。將貧困看作全人類共同的困境——不僅看作某一個體基于先賦性或自致性因素的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待貧困、弱者以及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的態(tài)度。
對抗危機中的困境,中國本土化中的文化自覺與多元包容,將客觀與主觀結合,實現(xiàn)了授人以漁、助人自助的解決貧困問題,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承認人際間差異性,進而在差異的基礎上實現(xiàn)資源整合。危機致貧的多維度衡量所產(chǎn)生的解決貧困的能力也是復數(shù)的。應對貧困多元一體化的態(tài)度,體現(xiàn)在我們國家當前,則是重視貧困的多樣性并采取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發(fā)展路徑。面對不確定性,具有理解風險、接受風險和采取措施的意愿和能力,解決自身危機致貧問題,并進一步確認多中心的秩序,強調(diào)參與者的互動過程和能動地創(chuàng)立治理規(guī)則、治理形態(tài),這也是我國戰(zhàn)勝社會整體性風險與危機致貧的挑戰(zhàn)所取得的成功經(jīng)驗。
五、討論與反思
多元融合下的危機與貧困,不僅需要判斷既有的制度和規(guī)則的完善情況,更需要從歷時性與共時性二元互動的角度判斷社會本身所處的時代及其轉(zhuǎn)型。在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所造就的社會公共危機中,我國脫貧攻堅仍能夠取得全面的勝利,并經(jīng)歷了資源分配的不同模式的轉(zhuǎn)換與融合。從管理向治理、服務的發(fā)展,這是國家應對危機致貧問題與現(xiàn)代化建設所積累的成功經(jīng)驗。危機致貧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的社會關系,但以家庭為單位的,以血緣、地緣關系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并未消失。相反,隨著人口遷徙,這樣的社會關系在危機致貧的背景下,在大都市社區(qū)治理中日漸發(fā)揮作用。
多元融合作為更為深層次的文化結構,在政府主導的脫貧工作中表現(xiàn)為不斷吸納符合現(xiàn)代化專業(yè)分工的倫理要素,構成了家庭、國家和社會同向性的互動模式,從而使得個體層面與社會整體層面得到統(tǒng)一穩(wěn)定的發(fā)展。治理危機致貧的主題并不僅是試圖建構完美的正義社會或制度,而是建構現(xiàn)實可行的多元化的分配方式,以減少導致非正義產(chǎn)生的條件,在個體層面發(fā)展多元復合能力。同時,進一步賦權個體,強化通識教育,促進選擇自由將復合能力轉(zhuǎn)化為功能,實現(xiàn)多元到整合的過程,進而阻止人類共同體意義上的貧困及非正義。
強調(diào)人類共同體的發(fā)展與社會的共同富裕,正是對抗危機致貧所帶來的異質(zhì)性與不確定性的重要路徑。在多元一體的共同體利益基礎上,建立起發(fā)展個體的多重復合能力的社會分配制度,以激勵人們根據(jù)自己的選擇、依從那些決定著其日常行為的動機而盡可能地為滿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貢獻出自己的力量。(58)[匈]卡爾·波蘭尼:《大轉(zhuǎn)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jīng)濟起源》,馮剛、劉陽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面對個體與社會、一元與多元、同質(zhì)性與異質(zhì)性、本土化與全球化,身處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中,不拋棄對立,但調(diào)和對立、解除對立,建構多元融合的知識體系,在認識危機致貧的理論道路上,才能避免通往被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