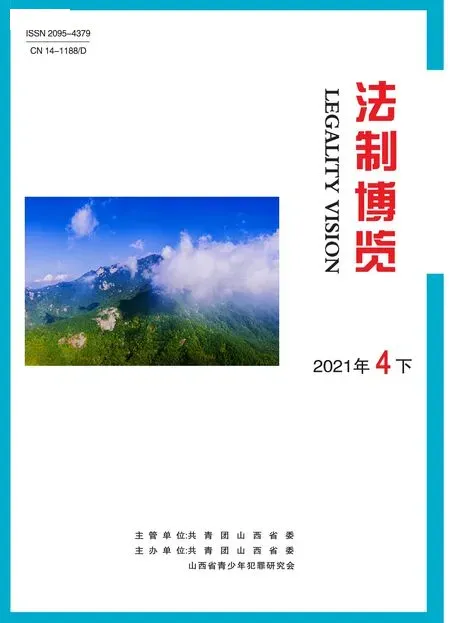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最后陳述權
曹 熙
(內蒙古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一、被告人最后陳述權的內涵及功能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審判長在宣布辯論終結后,被告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從這條法條中我們不難發現,首先,被告人最后陳述權是被法律所規定的專屬于被告人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剝奪和干涉。其次,在刑事訴訟的一系列活動中,被告人一直處于弱勢地位。在公訴案件中,控方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行使的是國家權力,而被告人行使的是屬于當事人的辯護權,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的私權利。兩者的力量和地位有明顯懸殊,此時如果不給予被告人一些特殊的救濟權利,很難改變被告人的不利情勢,而被告人最后陳述的設立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被告人最后陳述權主要有以下幾點功能:(一)保障被告人人權,釋放被告人負面情緒,增強司法裁判的公信力。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與法官的裁判息息相關,即使是最有說服力的律師也不會比被告人本人更渴望自身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只有讓被告人自己將積蓄已久的想法充分表達出來,才能有效釋放其在訴訟過程中一直壓抑的精神情緒。同時,被告人在參加庭審的過程中直面了解了法官的審理理念和定罪依據,對于大部分被告人而言,他們認同法官的判決結果,因而在最后陳述中他們會積極認罪,懺悔道歉。這樣不僅有利于消除他們自身“報復、詛咒、怨恨”的負面情緒,也撫慰了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心理創傷,使雙方都能在心里接受判決結果,增強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二)有利于發現案件事實真相,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被告人最后陳述增加了被告人自我救濟的機會,他可以就刑事訴訟的偵查、起訴及庭審過程中的程序問題提出異議,也可以就案件提出新的證據和事實。法官通過被告人的陳述,很有可能發現新的裁判依據,這就有可能實現案情的反轉,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從被告人做出最后陳述的語氣和狀態中,法官可以辨識出被告人內心是否真正的認罪認罰,并以此作為量刑的依據。(三)警示教育功能。被告人最后陳述是被告人的現身說法,對于旁聽的民眾來說,雖然這些陳述可能與案件的認定沒有很強的聯系,但是相比庭審其他環節這更能觸動他們的內心,這樣就起到了良好的教育警示作用,有效預防了犯罪的發生。
二、被告人最后陳述權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被告人自身文化水平限制
與庭審的其他環節相比,被告人文化水平對最后陳述的影響最大。因為在庭審的其他環節,被告人往往是被動的回答,而在最后陳述中被告人需要完全自己組織發言,這就需要被告人有較好的事實歸納能力、判斷分析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對于文化程度較低的被告人來說,他們甚至都不能理解最后陳述對他們的重要意義,很容易致使最后陳述變成了簡單的“一句話陳述”。
(二)權利的不合理使用
首先,被告人消極行使權利的現象普遍。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導,被告人只能憑借僅有的認識,做出最后的陳述。這導致在實踐中,被告人對最后陳述的熱情并不高,多數被告人放棄陳述,即使是行使最后陳述的被告人中相當一部分也傾向于以一句話陳述了事,甚至在無罪辯護時也無不同[1]。在許多案件中,被告在判決前一直持不認罪的態度,但在最后陳述時卻對此絕口不提,有的被告甚至直接選擇沉默,還有的被告則做出與無罪辯護相矛盾的“希望從輕或減輕處理”的陳述。
其次,不合理陳述屢屢出現[2]。被告人在作最后陳述時,所述內容更多為感性的內容,缺乏對定罪量刑有實質性作用的陳述,這樣的陳述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意義,自然也就不會對定罪量刑產生任何影響。還有的被告人在最后陳述時慷慨陳詞,痛斥社會現狀,質疑法制現狀。更有甚者甚至對審判人員、公訴人員發表輕蔑、威脅言論。這些言論都是被告人語權失當的表現,這樣的話語又怎能幫助被告人爭取合法權益,達到獲得被告人諒解減輕刑罰的目的。
再次,權利的表達缺乏文本體現[3]。一些法院對被告人最后陳述缺乏重視,許多案件庭審筆錄中直接省略了最后陳述的內容。在量刑展示時,裁判文書中大多以“被告人認罪、悔罪態度較好”這樣一句簡單的話來代替被告人的陳述。
最后,放任自流,不加引導的做法。法官在開庭審理中對被告人損害國家、他人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的發言,以及漫無邊際破壞庭審的發言不加制止和訓誡,嚴重破壞了庭審活動的公正性、嚴肅性,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導致被告人陳述權失去真正的意義。
(三)法官對最后陳述的不當限制
任何權利的行使都必將受到一定的限制,被告人最后陳述權在司法實踐中也不例外,許多法官會以陳述時間過長為由打斷或取消被告人的最后陳述,還有一些被告人會因為語氣不當被法官打斷發言,這些行為都侵害了被告人的最后陳述權。
(四)最后陳述對審判結果無實質影響
在案件審理前的整個過程中,法官完全沒有參與到偵查活動中。在審理案件前,他首先接觸到的是由公訴機關移交的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的證據材料,這很容易使得法官對被告人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在法庭審理階段,通過對控辯雙方各自陳述事實及證據審核后,法官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是否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早已有了答案。因此,即使被告人在最后陳述階段表現出最誠懇的悔罪態度,法庭在定罪量刑時一般也不會受被告人最后陳述的影響。
三、對完善被告人陳述權的建議
我國的法律雖然有對被告人最后陳述權的規定,但相比于某些其他國家的規定,則顯得太過簡單。同時,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最后陳述權并沒有得到真正的重視。作為被告人的一項重要權利,如何使其在司法實踐中切實有效的實施對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保障司法公正,以及我國刑法的正確實施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如下建議:
第一,強化律師的幫助。由于被告人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致使被告人行使辯護權的能力參差不齊,能夠理解、掌握、運用法律的被告人少之又少。所以,在最后陳述時因為錯誤判斷這項權利的重要性而做出沉默和一句話辯護的被告人比比皆是。而辯護律師一般有著豐富的法律知識、職業經驗和辯護技巧,不僅能有效的指導被告人以更具法律邏輯的方式進行陳述,而且能引導被告人做出更易被法官接受的陳述。相對比下,一個專業人員的介入顯然對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更有利。因此要強化律師的幫助,無論是辯護律師還是法律援助律師,都應該在庭前與被告人進行有效的溝通,核實相關證據事實,幫助被告人理解最后陳述權,提前為庭審做好準備。或者結合案件證據、事實引導被告人做出有利于量刑、減刑的陳述內容,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由辯護人和被告人共同進行最后陳述,切實保障最后陳訴權的真正實現。
第二,對被告人最后陳述的相關事宜明確立法。如,最后陳訴不得受到任何人的干擾,法官只有在必要時才能對被告人不當的陳述進行限制。被告人陳述的內容應當記錄在庭審筆錄中。對內容進行明確規定,最后陳述的內容除涉及被告人犯罪的原因、對犯罪的認識及悔罪態度以外,還可以在辯護律師的幫助引導下,從案件的事實、證據、法律適用和司法程序方面進行陳述,既可以總結在庭審階段提出的辯護意見、突出本方的辯護要點,也可以就案件提出新的證據和事實,只要宗旨不偏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即可。
第三,加強對被告人最后陳述權行使的監督。監督的主體主要是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內部以及公眾輿論。監督的內容有兩方面,其一是對人民法院審判時妨礙和侵害被告人最后陳述權利的行為的監督。其二是對被告人行使最后陳述權時的監督,防止其濫用權力,妨害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
第四,明確法官的釋明義務。在最后陳述中明確法官釋明義務的合理性在于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由于最后陳述主體的特殊性,在法庭上由法官對報告人進行幫助最為適宜。對于法官釋明的內容,首先,應當向被告人闡明最后陳述的法律規定,尤其要告知被告人不可為的行為。其次,法官可以對最后陳述的內容進行舉例,如當下內心的想法、對行為的認知、對定罪量刑的意見等,但不得在內容上有法律明確規定之外的限制,不得要求被告人作“簡要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