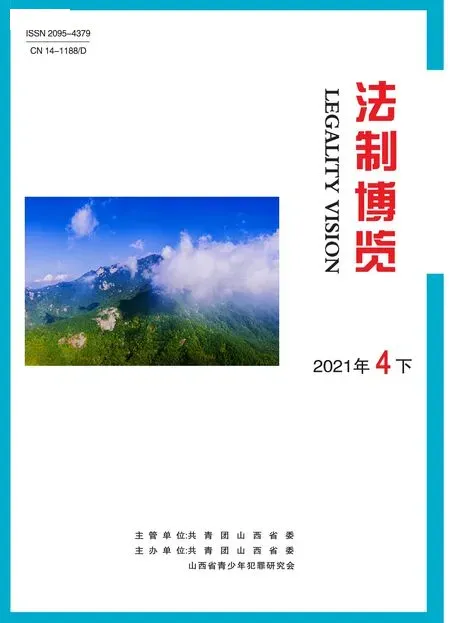我國榮譽權的認知和適用
翟凱鋒
(吉首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湘西 416000)
榮譽權自從在《民法通則》之中首次立法確認以來就引起廣泛關注和研究,這種爭議一直延續至今,這也導致了學者們對于《民法典》背景下榮譽權的性質、機制等討論方興未艾,隨著《民法典》的施行,關于榮譽權的相關實踐問題必然成為新的重點。通過剖析榮譽權立法中長久存在的一定問題,結合一些理論總結以及對于榮譽權的相關認知,提煉出一些促進榮譽權實踐運用和體系完善的建議,使榮譽權的定位更加明晰,在具體實務中的作用更加規范。
一、榮譽與榮譽權
事實上,榮譽和榮譽權是兩個概念,在《辭海》解釋中,榮譽指的是某些個人或者某個團體所獲得的公允的贊許和獎勵,一般是出于其出色履行義務或進行了奉獻,與之相對應的還有主觀上獲得的肯定感受。是客觀評價和主觀感受的雙重統一,隨著歷史的進步和社會階段的不斷變化,表現出不同形態。在我國榮譽一詞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晉朝,在葛洪的《抱樸子· 行品》中就出現了榮譽一詞,語義詞義上并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1],使用的方式大致也一致,成為我國源遠流長傳統文化中關于道德評價的重要組成。關于法律意義上的榮譽缺乏一個規范的定義,各個學者之間的分歧很大,楊立新教授就在其著作中總結了當前學界存在的幾種關于榮譽的學說,學說各有千秋,大體上可以分為“評價說”和“獎勵說”兩種流派,不論是正面評價還是特殊獎勵,兩種學說都肯定了榮譽所具有的積極性,當前學界占主流的是評價說,即個人或者團體在社會勞動期間或者科研活動期間表現優秀,成績斐然,而由政府機關或者一些權威組織對于其的一種正式的積極的評價[2]。
與之相對應的是,榮譽權的定義也存在幾種不同的理解,例如認為榮譽權是對自己已經獲得的榮譽支配并從其中獲得利益的人格權[3]等,這些對于榮譽權的定義也體現出不同學者對于榮譽等問題的不同認知,但都基本圍繞著保護維護的權益和相關利益的維持等基點來構建的。所以筆者認為,榮譽權是當事人對于其合法獲得的榮譽所產生的保有、維持、支配和就相關利益進行收益的權利。
二、榮譽權相關問題
我國法律規定中的榮譽權是不包含榮譽獲得權的,即便是在符合相關的榮譽授予條件下而由于一些惡意行為不能獲得榮譽也不在榮譽權保護范圍之內,并且法院是不能夠替行政機關做決定的,這種問題如果行政訴訟都不能解決,民事訴訟就更加無能為力了。這主要是因為法院所依據民事法律對于榮譽權進行保護,但并不能逾越公私法之間的界限而做出行政行為,法院出于民事的角度考慮進行規制,但由于一個更加強力的行政權力存在,法院是無法承擔這樣的職責的,那么當當事人的榮譽稱號被無理剝奪時,法院是無法通過民事立法的規則來對于這種情況進行保護的,法院對于榮譽受到侵害的救濟能力大打折扣,榮譽權條文的效力以及適用面都大大減少。一旦上升到公法領域,民事權利所設置的救濟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由此又可以衍生出一個問題,如果榮譽的救濟并不能通過現有獨立的條文進行,那么將榮譽權獨立出來進行保護的意義何在?正當性何在?和名譽權相比,那么榮譽權的獨立性的理由是如何?如果在當前《民法典》出臺的背景下不能改變,或是在短時間內不能改變,那么如何能將榮譽權的認知和救濟發揮最大的效果?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關于榮譽權是否存在獨立的正當性的問題上,學界存在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學說,否定說認為,我國法律的設置是遠超于理論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來自于對于蘇聯法律的繼受,事實上,蘇聯法之中的所謂的“榮譽權”就是名譽權,只是在移植過程中發生了認識的錯誤[1]。而相類似的,在國外的相關立法之中都沒有關于榮譽權的設置[4],且榮譽權的相關規制和名譽權的調整如出一轍,沒有獨立出來的必要,對于行政權力授予的榮譽,更多的屬于行政事項,這種事項通過民事立法來進行普遍性的規制效力低下,且沒有理論支撐[5]。所以很多學者認為其并沒有獨立存在的正當性[6]。不過更多學者支持獨立,主要是從我國法律的設置出發的,首先,雖然學界研究并不透徹,但《民法典》并不是沒有發展而刻板地照抄,經過了這么多年的研究和修改,榮譽權都是以其獨立的面貌出現在法律體系中,在司法解釋和法規規章之中都存在關于榮譽權的相關法條,榮譽權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民法典》之中。同時國外關于榮譽權的立法較少,但是并不能由此否認我國存在的價值。所以,榮譽權仍然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對于榮譽權獨立出來之后的性質問題,仍然存在爭議,包括人格權說、身份權說和雙重屬性說三種學說。人格權說主要根據榮譽權所具有的對世屬性,和其他的身份權相比并沒有任何共同屬性,將其歸入身份權是不合理的[3];身份權學說也是我國學者大部分同意的觀點,認為榮譽權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具有一定身份之后才能獲得,而所有的個人和團隊都應具有人格權,所以應當歸于身份權[7];雙重屬性說是指榮譽權包含雙重屬性,是二者結合的折衷觀點,也得到部分學者支持。
三、如何解決榮譽權的問題
(一)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論研究。當前學界爭議不斷,一大原因是理論研究不足,各種學說之間的割裂有余而合作不足,尤其是在面對榮譽的內涵、榮譽權的性質、榮譽權救濟的理論途徑等問題時研究嚴重缺乏,尤其是在當前《民法典》的視角下,豐富榮譽權的救濟理論,對于榮譽的取得、喪失和撤銷等問題進行完善的研究,明確界定榮譽和榮譽權的概念,對于榮譽權本身理論的結構要素進行深入分析,將榮譽權拆分為比較細致的組成部分并對其進行完善,對其主觀和客觀方面都樹立一定的標準和內涵,力求在表述基礎概念時完善而適合實務。
(二)在立法方面進行深入完善。我國榮譽權立法雖然走得是立法先行的道路,但是在具體規定上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完善榮譽權的救濟制度,為榮譽權的施行的各個方面都進行細致規定,尤其是在榮譽權的撤銷和恢復這些以前存在較大漏洞的方面加強立法。通過立法將榮譽權的救濟途徑確定下來,明確救濟方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運用保障名譽權的途徑。例如可以包括恢復榮譽、停止侵害、賠禮道歉等,在一些特定的場合,還可以要求賠償精神損害賠償金,發揮出榮譽權自身特有的實用的權利保障機制。
(三)夯實榮譽權的社會外部基礎。榮譽權建立在榮譽之上,而榮譽有著豐富的群眾和社會基礎,要解決榮譽權的問題,就必須切實加強每個人對于榮譽和榮譽權的認知,結合我國法規以及理論體系,進行必要的社會宣傳,避免出現認知不清的問題,尤其是加強執法人員的學習,這些人員既是保護榮譽權的中堅力量,事實上也是侵害他人榮譽權的主要人群,所以必須提高這一批人的認知水平,形成保護榮譽的良好社會風氣。
四、結語
對于榮譽權這一概念來講,其背后的概念研究比較單薄,所以體現出了理論和立法、實踐和立法的雙重割裂,這些問題的發生更加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對實踐的總結。法律是治世之科學,脫離了實踐的立法并沒有意義,但單薄的立法也更需要實踐來完善,我國《民法典》的施行必然會引起新的實踐背景,在此背景下進行更有價值的研究和完善,才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良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