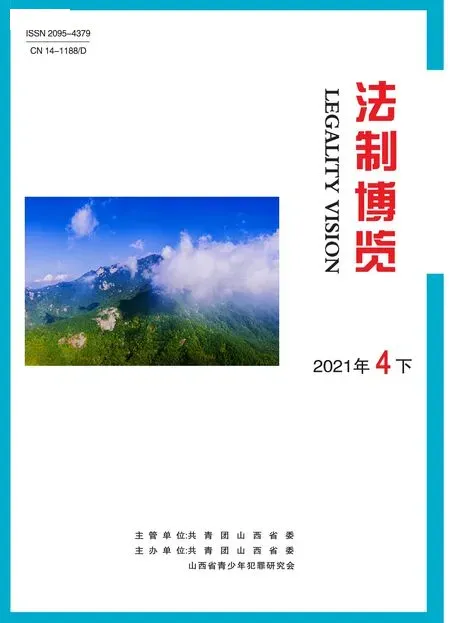網絡監督中對個人信息的保護
胡云寶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0)
網絡監督是人民群眾通過網絡了解國家、社會事務,自由的發表意見、建議,進行褒貶、評價的過程。監督主體是全體網民,大家可以在互聯網上對眾多熱點事件發帖、跟帖、討論、熱議,進而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2003年至今,網絡監督所顯示的巨大能量得到了充分體現,但網絡言論自由的濫用也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
一、個人信息保護的現狀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民法典》,第四編第六章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備受矚目,既回應了大眾期待,又完善了民法典自身建設,是國家法治進步的表現。
(一)個人信息的認定范圍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規定: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有的觀點認為與公民個人存在關聯,可以識別特定個人的信息,均可定義為個人信息[1]。
(二)網絡暴力的基本內容
網絡暴力主要是直接或間接傷害他人名譽、隱私,不需要拳腳相加,但威力巨大,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1.網民針對已經證實或尚未證實的網絡事件,在網上實名或匿名公開發表具有煽動性、攻擊性、侮辱性的言論,造成當事人名譽受損。2.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網上公開當事人個人隱私。3.對當事人的正常生活進行言論干擾、行動侵擾,致使其人身權利受到侵害[2]。
二、網絡監督中的利益相關者
網絡監督能揭露、批判丑惡、不法現象,群體發出正義之聲,督促社會大眾崇法、敬法、畏法、守法。但有人的地方就難免有利益糾葛,當流量、粉絲、點擊率可以轉化為金錢時,網絡水軍應運而生[3]。
(一)網絡水軍、大V、主播和其他“鍵盤俠”
這并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而是分工明確的團隊,主體是針對特定內容持續搜集、發布特定信息的網民和被雇傭的網絡寫手。這股力量,用于社會公益,效果事半功倍;用于網絡暴力,同樣是事半功倍。在“人肉搜索”過程中,網絡水軍是“收人錢財,替人消災”,大量網民并不一定清楚事情原委,憑個人好惡將當事人個人信息發布到互聯網上[4]。如:2015年,“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中,雙方當事人都僅僅是個人的一時沖動,屬于民事糾紛、治安處罰的范疇。但進入網絡熱搜后,事態急轉直下,與事件本身并無關系的當事人電話、照片、單位、家庭情況等信息先后公之于眾,連女司機的生理期這樣的個人隱私都被發到網上,侮辱性詞匯鋪天蓋地而來,禍及家人。
(二)當事人
以“XX照片事件”為例,當事人僅僅是在朋友圈里調侃了一句“照片拍得丑”,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是女同志,這個無可厚非。事情本身很小,又與公共利益無關,但網友在熱議、爭論時,部分“鍵盤俠”在網上誤導輿論等言論就明顯具有攻擊、謾罵意味,1條普普通通的朋友圈,竟能招來如此“網絡暴力”,這能起到何種正面作用?當事人還是正在成長期的優秀律師,面對網絡暴力也無可奈何。
(三)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
凡是權利皆受限制,無不受限制的權利,言論自由也不能例外。在熱點事件被網絡炒作過程中,國家機關既負有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侵犯,抑制網絡暴力的職責,又應當依法公平公正處理違法違紀問題;既要回應社會關切,還要防止被不法之徒當槍使;既要保護好個人信息本身,也要保護信息所承載的人格獨立、言論自由、私人財產權等基本權利,實現公正司法與保護個人信息、抑制網絡暴力相得益彰。
三、網絡監督存在的主要問題
網絡監督是一把雙刃劍,在推進熱點事件有效解決,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遇到一些問題與挑戰。
(一)虛假消息泛濫成災
帶有明顯傾向性的言論層出不窮,引導整體輿論偏離主流軌道,滋生出各式各樣的謠言。一些不負責任的“標題黨”博主、媒體省略關鍵信息,用一部分看似客觀的語言,將謠言偽裝成事實,吸引受眾的眼球,誤導網民的思維。以“XX幼兒園虐童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后,喂白色藥片、XX團群體猥褻兒童等文章極具吸引力,瞬間被高度關注。但事后查明,全是子虛烏有。
(二)網絡暴力恣意妄為
網絡暴力的受害人有名有姓,但施暴群體過于龐大,很難精準定位到具體施暴者,多數人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恣意妄為。很多網絡事件的起因往往并不是關系國計民生、危害國家安全的大事,高鐵讓座、狗咬人、人打狗等小事居多,后果并不嚴重,應當以思想教育為主,或借助“楓橋經驗”民間調解,一旦被網絡炒作,就會有無數網民自封“道德法官”,匿名開展“道德審判”,上升為現實暴力,造成巨大的精神、物質傷害幾年都無法抹平。
四、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考量
網絡監督的背后是言論自由、公共監督和個人信息保護之間的沖突,無論是言論自由還是個人信息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都不可偏廢,要雙管齊下,保護好個人信息。
(一)制定完善的個人信息保護法
應該平衡好個人信息保護與言論自由的關系,個人的私生活不受非法干涉,是構成人格尊嚴、人格獨立的基本要件,法律法規不僅要懲處違法違紀行為,而且要依法保護無辜當事人的個人信息、基本權益,使他們免受不當追究。目前,這類侵權行為依靠司法途徑圓滿解決的少之又少。互聯網的無國界性、分散性、匿名性,使得調查、取證非常困難,大多數受害者找不到幕后黑手。要想從根本上規范網絡使用,凈化監督環境,還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靠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因此,制定完善的、操作性強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勢在必行。
(二)權威回應民眾關切
網絡終端人人在手,社交平臺時時在線,信息傳播的速度非常快,有關政府部門要敢于直面敏感事項,正面回應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將各個謠言予以逐個擊破。2018年8月27日晚,發生的“昆山寶馬男砍人被‘反殺’案”中,警方的處理就非常及時。8月28日,昆山市公安局便發布《警情通報》,通報案情基本情況,提醒廣大網民不要發布和輕信未經警方證實的信息,也不要傳播涉及相關當事人的照片和視頻。網民后期的討論也是圍繞“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開展,完全在維護公共利益的范疇之內,昆山市檢察院又及時作出回應,廓清了網民思想迷霧,“正當防衛”深入人心,民眾的法治意識進一步增強。
(三)警示懲處和事后救濟
網絡監督可分為兩個階段:1.信息搜集、發布階段。該階段信息是否無中生有,是否斷章取義有待考證。2.公開批判懲罰階段。信息搜集、發布階段跟個人信息密切相關。前者類似于公開審判,法官卻是全體網民,當事人基本沒有辯護權。后者更像是古代的恥辱刑,極易讓當事人焦慮、抑郁,產生精神、心理疾病。
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因此,對于非經許可,擅自獲取、收集、使用、加工他人個人信息,惡意侮辱、誹謗他人的行為應當進行嚴厲處罰,并保證個人信息事后救濟權。經要求刪除而拒絕刪除的,應當被認定為侵權;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使用個人信息的,進行非法活動的,應當受到刑法的制裁,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承擔民事賠償和刑事處罰責任。
五、結論與建議
如何全面保護個人信息,遏制網絡暴力,是值得認真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研究結論如下:1.使用個人信息,應當具有目的和程序正當性,即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依申請,經批準后使用。2.制定操作性強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國家機關和非國家機關對個人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利用的程序,權限及侵權后的法律責任。3.搞好輿論引導,從道德層面減少惡意侵權。4.對違法違規使用個人信息,實施網絡暴力的主要責任人,應當追究民事、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