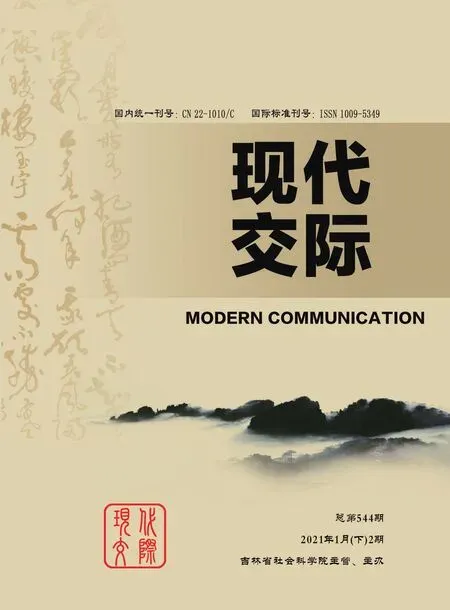先秦儒家人性論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藍燕燕
(福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先秦儒家人性論在古代人性論中占據重要地位。僅在儒家內部而言,據王充《論衡?本性》記載,除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之外,言人性者,還有世碩、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的影響最為深遠。關注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起點,這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著重大啟發作用。
一、先秦儒家人性論產生的背景
任何一種思想觀念的產生,都既與提出者的家庭有關,也離不開社會的影響,人性論的產生也是如此。
1.家庭背景
家庭環境對人的思想的形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孔子的先祖為宋國(河南山丘)貴族,孔氏傳家的好家風千年不墜,經久不衰,不為任何朝代的更迭或政治變化所動,這樣的良好的家風對孔子提出人性論思想有著重要影響。孟子先祖為魯國貴族孟孫氏,其母親極度重視孟子的教育,為了給孟子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曾有“孟母三遷”和“孟母斷織”等家喻戶曉的故事。在良好的教育下,孟子從小就學儒習禮,在潛移默化中悟出仁義禮智的道理,為其性善論的提出埋下伏筆。此外,由于孟母重視教育,孟子十五歲就寄學于孔子的孫子子思門下。受子思門人的影響,那時孟子對孔子的儒家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以孔子為人生典范,并立志繼承和發展孔子的思想,特別是在人性論上做了獨特的發揮,提出了性善論。史料對荀子的家境背景記載很少,荀子十五歲游學于齊國的稷下學宮,稷下學宮中各學派都有自己的主張,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對荀子產生了一定影響,為他后來批判地繼承孟子“性善論”,提出“性惡論”提供了一定依據。總的來說,人性論的提出,離不開提出者家庭帶來的生命體悟。
2.社會背景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提出離不開當時的社會背景。
第一,從政治方面說,禮崩樂壞的政治局面,導致“人人爭富,交相利”的社會現狀,引起人們對道德問題的思考。其一,從政治格局的轉變來說,由于以“血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禮樂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引起了社會動蕩,這無疑給社會思想意識帶來巨大沖擊,自然也會給社會道德生活和倫理觀念帶來深刻的影響。人與人之間關系由穩定到緊張,道德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道德的主體是人,思想家對道德問題的思考首先從人的本性開始。其二,從政治環境來說,“禮崩樂壞”的局面使舊的社會秩序被打破,階級分化之后出現新的階級,各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地位,不得不寬松政治環境,任人唯賢,使更多的思想觀念廣泛傳播。人性論的觀點,容易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產生。
第二,從經濟方面說,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的轉變,經濟貧富差距的拉大,以及觀念的轉換、交往的日益頻繁,都引發了對人性的思考。一方面,就貧富懸殊而言,錢是萬惡之源,貧富兩極分化必然會引起人們心理不平衡,進而產生嫉妒、憤恨、不滿等情緒,后者就是“惡”的表現。因此,人們會不擇手段地獲得財富,必然會激發各種社會矛盾,引起社會動蕩混亂。另一方面,就觀念的轉換和交往的日益頻繁來說,土地的自由買賣,使人們的商品意識逐漸增強,人們開始思考如何賺取利潤的問題,用已有的商品去換取想要的商品,人們的交往日漸頻繁,各種惡端日漸突出。由此,人們開始關注交往中的公平、誠信、道德等問題,引發人們對善惡問題的思考,人性問題逐漸地引起了人們的反思。
第三,從文化方面說。其一,西周之后,人們憂患意識開始覺醒,把禮樂看作宗教的儀典形式,宗教觀念開始淡化,逐漸形成了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先秦學者繼承并發展了這種人文精神,用理性的態度分析這種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把人的自身價值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引起了人們對“人”的思考。其二,中國古人非常注重道德的作用。在西周,就有“修德配命”的說法,認為只有“修德”才能取得政權。到后來把宗法道德和個人品德也概括為“德”,以及任人唯賢,使道德成為鑒別人才和招賢納士的標準。這都說明崇尚道德的風氣日盛,而道德的主體是人,必然會引起人們對“人”的思考。其三,《周易》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周易》中含有許多關于道德修養、道德價值、理想人格的培養及環境對人格的塑造的問題。簡而言之,人文精神的產生、崇尚道德的風氣、《周易》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為人們對人性的思考提供了一定的文化背景。
二、先秦儒家人性論的邏輯脈絡
孟子提出的“性善論”和荀子提出的“性惡論”,對人性作了價值判斷,由此開始,更多的學者對人性論展開了系統的論述。
1.孔子的性近習遠論
孔子對人性問題論述得比較少,他對人性到底是善的還是惡的沒有明確表態,僅提到了“性相近,習相遠”。從“性相近”來說,孔子認為人的本質屬性是相差無幾的,自然屬性是相近的,是天賦予人的性情、道德情懷;從“習相遠”來說,“習”有兩層含義,其一可以理解為后天的練習及實踐養成,其二可以理解為環境的習染,人們可以通過后天實踐和環境拉開差距,這說明人的社會屬性是可變的。總的來說,人性是可塑的,引導受教育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經過實踐養成,是可不斷進步的。
2.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以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為基礎,提出了自己性善論思想,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善”是人的基本屬性。孟子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忍之心”,他舉例,倘若我們看到一個孩子落入井中,我們會第一時間救助,對于孩子的救助并非源于外力和功利動機,而是人內心的“善”自然的流露,孟子肯定了人“性善”的基本屬性。
第二,“人性”先天固有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屬性。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人具有向善的本心,人有內在道德的知、情、意,這是人固有的道德屬性,是與動物的區別所在。人性之所以為“人”,因為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即所謂的“仁、義、禮、智”的四端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人類共性。
第三,人性“四心”是先天的,但也是可失的。孟子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意思是說人內的同情心、正義感、羞恥感和道德是非的鑒別、判斷是人內在固有的,不是外力強加的。孟子將其稱之為“良知”“良能”,即合稱之為“良心”。即便如此,孟子又認為“善”是可失的。人后天之所以會喪失“善”的本性,是由于人們不善于保養,由此孟子提出了“求放心”,要求人們通過擴充,從而達到善的本質。
3.荀子的性惡論
荀子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論,提出了性惡論,從而進一步深化了對人性論的理解。理解荀子的“性惡論”,一方面,從“性偽之分”深刻理解人性之惡。在荀子看來,“性”并不是人的本質屬性、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是“不可學”“不可事”的。通過后天習得的是“偽”,即是“人為”的。比如說禮儀道德,就是通過人后天習得的,是經過人反復思慮形成的行為規范。因此,從“性偽之分”出發,荀子對人的自然本性進行了道德評價,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是“性惡”的。另一方面,從“化性起偽”中理解棄惡從善的必要性及途徑。正因為人性是惡的,更需要“性偽合一”。雖說人性之“惡”,但卻可以“化”,通過后天的學習和改造,人是可以為善的。如果不對人性進行禮義制度的教化,人性就不能自然變善。因此,正因人性是惡的,需要后天的禮樂教化,從而改變人之惡本質,引導其向善,達到“性偽合一”。
總之,孔、孟、荀的人性論雖存歧義,實則殊途同歸,說明了人性是可塑的。人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實踐養成而服務于社會的。
三、先秦儒家人性論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人性到底是善還是惡,至今還有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是可塑的。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道德滑坡事件屢見不鮮,這引起了人們的反思,這顯然也會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絆腳石。由此,“立德樹人”成了高校的靈魂和使命。從先秦儒家人性論來看,人性是可塑的,人是可以通過引導棄惡從善,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因此,要狠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先秦儒家人性論對于當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定啟發作用。
1.發揮主觀能動性,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
人性是可塑的,只有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自我修養、自我完善、自我凈化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也如此,注重教育與自我教育相結合。學為主,教為導,理論知識固然重要,實踐素養也不可缺,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引導受教育者將學習的基本理論注入實踐,讓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人的生活,讓學生不再只學習抽象的理論,這需要引導學生發揮主觀能動性,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主動了解與實踐相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以指導自己的實踐。
一直以來,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填鴨式的灌輸。隨著經濟、科技的進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方法也應該創新,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雙向互動性,要從單純的說教轉為主動解決實際問題,積極引導受教者發揮主觀能動性,挖掘自身的需要,將被動接受轉化為主動學習,進而從主動感悟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品質,實現自我教育。
2.重視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氛圍
孔孟荀三人對人性的看法略有不同,但都肯定了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注重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通過創造良好的環境,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我們需辯證地看待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辯證地看待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挖掘校本資源,創建良好的校園環境。同時,也不能忽視人對環境的改造,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自覺抵制不良的環境因素,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校園環境。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網絡時代的到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如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動搖,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逐漸淡化,家國情懷淡薄,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一些不良的腐朽文化思想、黃色暴力等層出不窮,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了阻礙;因此,要及時正確引導學生,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
3.加強法制教育,堅持法制和德治教化并重
荀子的“性惡論”注重外在約束力,他認為僅僅依靠德育的教化,不足以維護社會秩序,還要注重“刑法”,用外在約束力制約自己。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將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結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樣才能創造更好的環境,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
一些高校大學生法制意識淡薄,法制知識欠缺,特別是剛步入大學的大學生,思想不夠成熟,僅靠道德的教化是遠遠不夠的,需加強法制意識和法律知識的學習,將法制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將德治和法治相結合,心中的道德律與外在的約束力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用。
總之,先秦儒家人性論有其合理因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定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