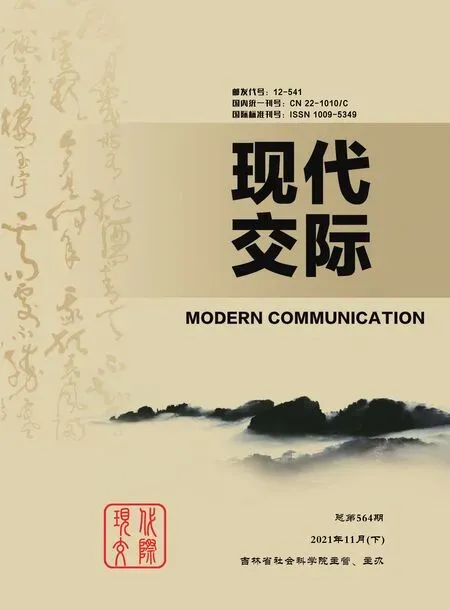善的存在論
——消解現代性困境的可能方式
王 鵬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吉林 長春 130031)
現代性困境給人類帶來了疑問與困擾,人在反思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與虛無主義遭遇,在現代道德語境中,碎片化成為顯著特征而缺少了一種整體的終極價值的關懷。同時,工具理性的泛濫導致形上理性的扭曲與消解。在缺少整體依據與根本價值而陷入虛無的現代道德境遇下,人們的追求是盲目而零散的,把囚困自身的欲望指向當作選擇的方向導致人類的生活遭遇漫無目的的空虛。對善的追本溯源是必要的,把善作為一種理念與目的,并居于最高地位是解決現代性困境的一種可能的途徑。
一、形上性失落的虛無主義困境
在哲學史及整個人類文明發展轉向近代的十字路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興起,自然科學的極大進步,都在某種層面上逐步吞噬形而上學的領地,把人類自身拋進一個客體世界,與虛無遭遇。[1]在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家及以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中世紀神學家那里,理性是曠遠而無邊際的,大自然是完全向上帝敞開的;而在以康德為代表的19世紀哲學家這里,理性的范圍被畫上了一道嚴格的邊界,以至于宗教傳統中對自然的神圣崇拜導致的符號化投影被逐漸從大自然中排除出去,形上理性在宗教改革中逐漸被非理性因素排擠到邊緣,人類對超驗形上世界的體驗與聯系被人為割裂,這樣的割裂尤其體現在現代存在主義視域中,形上式的信仰缺失體現在人類不斷的自我選擇困境中。首先,最高“善”作為一種純然的目的性指向已然被現代世界碎片化為“公正”“應當”“原則”“快樂”這類細微的詞語,而這些詞語背后卻失去了其應有的真正根據。碎片化正是現代性困境中的一個重要現象,“ought to be”在現代性語境中是一個極其常用的短語,它指向一切作為預設前提的細小原則,但我們究其根本來探究為何要設置這些前提的時候卻發現它們缺少了一種根本目的,一種最高的形上理念式的原因。其次,在缺失形上理性這樣一重維度所導致的現代性問題中,理性逐漸被扭曲并降低到工具理性的層面上,就像在功利主義中,所謂“最大幸福”對幸福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一樣,作為目的論核心的善被功利性肢解。工具化、手段化成為人們的生存向度,生存手段遠遠超越生存本身。在這樣的道德困境中我們該如何選擇?如果說現代性困境是一片充滿虛無的泥淖,那么選擇置身其中所試圖做的一切掙扎將是徒勞的,此時我們需要的是用一種反思的、回歸的方式來尋找缺失的終極關懷,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那里尋找一種最終目的與根本價值。回歸并非一種逃避問題的態度,而是一種通過追本溯源的方式來找尋現代人破碎的最根本之“善”,以及丟失信仰的靈魂。
二、善作為Ιδ?α
善并非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倫理學概念,對善的理解基于柏拉圖認識論中關于的理論。的翻譯十分復雜困難,無論是將其理解為本質、在雜多中尋找“一”,抑或是尋求普遍定義或概念,在本意上都只能說接近或部分符合其原貌,但并未達到對的全面而真正的理解。
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理念論進入我們的視線,即理念的層級,這是涉及作為理念的最高善的重要而根本的問題。首先柏拉圖使善與理念的關系成為一個問題。在柏拉圖、蘇格拉底之前,哲學是自然性的,是以一種知性的視角來審視自然界,因為沒有善的維度,這樣一幅自然運動的圖景顯得機械而死板。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薩戈拉引入了愛與恨的力量用來解釋自然世界運動的原動力,但最終卻把愛與恨歸結成了同樣機械的具有本體性的必然性力量。在《國家篇》的對話中,蘇格拉底提出善與理念的關系就像太陽與萬物的關系。蘇格拉底說,“太陽跟視覺和可見事物的關系,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關系一樣”[2]266,“太陽不僅使看見的對象能被看見,并且還使它們產生、成長和得到營養,雖然太陽本身不是產生”[2]267。太陽喻表明善與理念的關系正如太陽使得萬物能夠被看見并且生長,善使得理念得以顯現并最終導向最高的善,并且善本身即是一種理念,而此種理念與其他理念形成了層級,理念既指向最高善,又因之而顯現。善對蘇格拉底的影響是其對話中的一條隱線索,蘇格拉底的諸多對話背后則隱秘地藏著預設的善。“what is it”的問句中預設了善作為前提,“be”的回答中又導向一種善的目的論指向。如果沒有了善,那么勇敢、虔敬、節制等并不能成為問題,它們本身也成為盲目的無源之水。對善本身的理解非常重要,由于中文翻譯的原因,需要把它與日常用語中的“善良”區別開來,善良只是世俗社會中一種對人類行為的道德判斷,善良的行為或品格也只是最高善之下善事物的一種。而“good”一詞相比較而言更接近善,但同樣作為世俗社會中的一個常用詞匯,也只是對善的一種模糊概括,因為首先在人們使用“good”時并沒有對它進行嚴格的定義,人們自己并不清楚什么是“good”,而一旦要對其進行定義就必然要上升到理念論的高度。對最高理念之善的剖析必然會帶有神性的色彩,因為柏拉圖的理念并不是通俗意義上的概念、本質,它作為一種最高存在已經進入超驗的神的領域。或許是受當時希臘社會對來自希臘神話奧林匹斯神的崇拜的宗教影響。因此,最高善本身也必然具有神性。
三、善的目的論解讀
柏拉圖的理念論把人們帶入一個對超驗至善的信仰境地,善不但成為神圣理念,也同時具有了一種終極指向性的目的論色彩,這種目的論在柏拉圖那里并未作重點論證,而是作為一種隱而未顯的前提,但這個問題卻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解答。
某種善是人們活動和選擇中的目的,這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習慣的表述方式,在這樣一種表述中,亞里士多德預設了一種具有目的性的善。目的論的合理性是將善作為目的的重要前提。亞里士多德在《物理學》中對目的因做出過詳細論證,首先他在論述事物本因時說,目的因“是終結,是目的。例如健康是散步的原因。他為什么散步?我們說‘為了健康’。說了這句話我們就認為已經指出了原因”[3]。對于設置目的因,亞里士多德也明確做出提問“為什么一件自然的事情就不可以不是為了目的,也不是因為這樣比較好些,恰如天下雨不是為了谷物生長,而只是由于必然呢?”這是一個涉及目的因合法性的問題。其次,自然中的許多事件具有偶然性,偶然性如何成為目的?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樣的問題和推理并不成立,他在接下來對自然目的論的表述中闡述了這樣一種邏輯:只有目的性才會產生必然性,無目的的必然性造就的是不斷的偶然性巧合所拼湊形成的結果,就像亞里士多德敘述的“人的牙齒必然長得門齒鋒利,適于撕咬,而臼齒寬大,適于咀嚼”,如果沒有一種目的性在其中,那么人的牙齒只是一種在偶然的自然選擇中恰巧適合,然后保留下來,否則就會滅亡。如上述所言,無數的偶然性導致的結果就是完全開放的無限制的可能性,但事物并未因偶然性而造成漫無邊際的、無法想象的結果,那么在偶然性與目的性之間具有目的指向性是一種可能的理解方式。其次,在所有具有連續性的事物發生過程當中,一切階段都指向終結,某個事物無論是由自然決定還是人為的決定,它的過程與指向都是一樣的。因此,沒有目的因的存在,“必然性”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而只能成為偶然。這也是亞里士多德實體哲學中潛能存在與現實存在中所具有的目的論關系。
亞里士多德的論證把萬物引向了目的論。當純粹的機械性運動找不到根本原因時,一種自然心靈意志就會被作為僅有的可以相信的力量,這就是早期希臘以阿那克薩戈拉為代表的哲學家引入“努斯”的原因。“努斯”最早意指秩序,后來由畢達哥拉斯學派將其闡釋為“心靈”。“努斯”的引入是被作為具有指向性的動因來看待的,一切變化因此有了方向性,他們認為自然的意志就如人類的意志,天然地存在著某種目的。因此,動因與目的指向在這里具有相同的含義。阿那克薩戈拉對目的論做出了卓著貢獻,但他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他找到了某種動因,但其指向卻是模糊不清的,心靈可以解釋世界的運動,但并不能解釋世界為何運動得如此和諧完美,心靈是思維著的,而作為目的的心靈自身也是有其思維原則的,因此更根本的問題在于怎樣的原則使得心靈成為目的,并展現出如此的思維樣態。《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論述宇宙動因時說道“事物所由成其善美的原因,正是事物所由始變動的原因”[4]。換言之,也即事物的變動最終指向善,他在這一點上與柏拉圖保持一致。不難看出,阿那克薩戈拉的理論缺陷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這里得到補充,“善”正是心靈的原則。按《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說法,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活動、技藝與知識,每種技藝與知識都對應其目的[5],那么為何從眾多目的中選擇善作為最高目的就是善作為目的論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個問題首先在柏拉圖那里得到論述,蘇格拉底的太陽喻將善納入理念層級之中,善不只是理念,更是一切理念的原因。相比較于正義等范疇,善具有更高的地位,如柏拉圖所言,沒有善,正義等都是無用且無益的,我們如果不清楚正義是如何成為善的,也就不會認識正義自身。蘇格拉底所做的是倫理學范圍內的探討,在柏拉圖看來,善更是認識論和存在論中的最高范疇。靈魂都是趨向善的,我們可以從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中看到,知識是先天存在于靈魂之中的,需要被引導出來,前提在于我們靈魂的認知可能性與知識的對象的被認知可能性均來自善的理念,雖然善的理念并不產生靈魂與知識本身。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在倫理學和認識論的層級性上具有相似性,但區別在于柏拉圖把善作為一個整全而龐大的單一理念,居于一切理念的最高層級;而亞里士多德則把善也做了分類并予以等級區別,對應不同層級的目的,在這種層級關系中,有的目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追求,其余的目的皆因之而存在,至善就是這樣一種目的,因為自然和人類一切和諧而規律的運動皆指向一個更好的樣態、一種最高的好。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至善高于其他的善,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至善是幸福,它賦予了至善以屬人的性質,與柏拉圖外在于人的善相區別,但卻具有相同的終極價值。幸福既是倫理學概念又是一種實踐哲學,它是人的每種活動的最完善的終結,最終又指向人類整體意義上的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