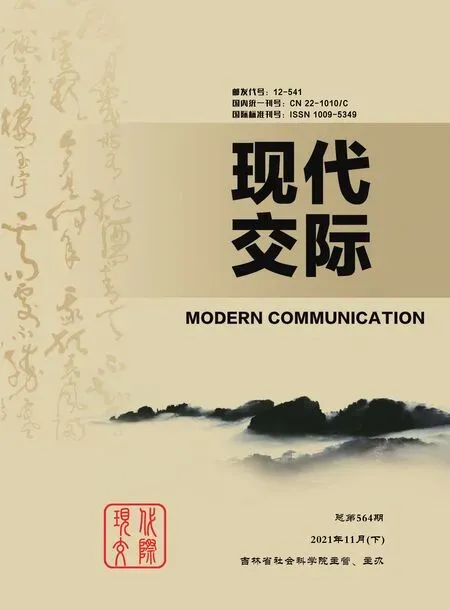自媒體背景下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
劉 鑫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吉林 長春 130033)
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為代表的信息數字化能力不斷提升,移動互聯網產業的蓬勃發展,自媒體產業也呈現井噴式增長。根據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底,我國新建5G基站超60萬個,全部已開通5G基站超過71.8萬個,5G基礎設施網絡覆蓋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及重點縣市,同時移動互聯網用戶多達13.5億。[1]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不僅帶來網速的提升,同時也推動流量單位成本下降,“提速降費”讓視頻服務類APP的用戶量和活躍度不斷增加。
自媒體APP是互聯網人與人交流的社交軟件和平臺,作者和用戶都有自主的話語權,每個人的身份、目的、訴求卻又各不相同。在一些敏感問題上,有些用戶積極討論參與互動,有些用戶單純圍觀,也有些用戶借此到達自己的利益需求,這部分用戶捕風捉影,使網絡環境問題層出不窮。
一、自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特點
自媒體的興起和發展已經影響到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很多自媒體軟件通過各自的技術手段占領用戶群,通過研究傳播方法、功能使用、個人使用習慣等信息,逐漸改變用戶使用習慣,與傳統媒體傳播方式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海量信息覆蓋傳統媒體
傳統的新聞傳播由報紙、電視、廣播構成,其特點是在固定的時間、固定的板塊發布相對固定的內容。電視臺及廣播電臺每天基本只有30分的新聞類節目,各大報紙發布的內容量受時間和版面的限制,內容容量固定,且不能將突發事件的內容第一時間呈現出來,造成信息堵塞,不能更及時地發揮輿論引導的作用。目前,自媒體借助現代網絡技術和通信工具的數字力量蓬勃發展,各類信息通過數以億計的自媒體人通過自媒體平臺24小時不間斷發布,形成了海量的以圖片、文字、音頻、短視頻的信息平臺,這是傳統媒體所無法做到。自媒體平臺形式多樣,內容廣泛,連續銜接性強,是吸引受眾的重要基礎。
2.技術推送——“算法”
自媒體成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網絡技術,各個自媒體平臺通過自己技術團隊運用技術“算法”分類信息,分類受眾群體,把二者有效聯系,通過跨越傳統傳播方式的技術革命,把受眾“喜歡”的內容和相關的上下游內容通過技術手段推送給群體。“算法”最早是為商業類型網站服務(淘寶、京東、拼多多等),客戶只要安裝了相關軟件,就會隱藏式強制獲取使用人的個人信息;更有甚者,在你沒有使用該軟件期間,也會監聽使用人日常聊天內容,根據你聊天內容和購買及瀏覽信息推送給使用人相關商品。自媒體興起后也借鑒了這一技術手段推廣相關聯內容,篩選并推送用戶感興趣的內容,不僅提高了信息分發的效率,也呈現出分眾化的特點。同時,自媒體平臺通過該項技術達到了擴大影響、延長使用時間、普及推廣的目的。不同的人打開同一個軟件,看到的內容是不同的,這就是“算法”技術。
3.“去中心”自我設置
“去中心”是與“算法”相伴共生的另一用戶選擇的功能。自媒體時代給予用戶更多的選擇權,不再以“灌輸”方式接收信息流,而是通過軟件提供的功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這種逆向的脫離傳統傳播方式的“去中心”化,受到廣大用戶的推崇。通過選擇權,把不喜歡的內容忽略掉,甚至也可以把“算法”屏蔽,活在自己是“社交圈”內,也可能屏蔽一切信息,變成“社交孤僻”。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媒體平臺發布自己“去中心”的想法和觀點,同時也能通過平臺轉發和評論功能與陌生人交流,用戶設置的議題在不同平臺不同群體之間討論傳播,形成一個話題,一種思想,當該話題積攢的能量到達峰值時,就能引起全網的重視和關注,引起傳統媒體的重視。
4.主題權下放
自媒體環境下,平臺和作者為了搶占頭條位置,提高時效性,降低核實成本,作品往往缺乏事實依據,這是自媒體的一個眾所周知的缺點。很多自媒體平臺沒有充分的審核機制和審核人員,只能由作品傳播發酵,直到得到傳統的主流媒體關注核實,才加以處理。主題權下放是自媒體的一個特色,優點是內容更加貼近公眾的思想,真實地體現基層百姓的生活和想法;弊端是受管制約束弱,給有用心的作者有可乘之機,發布不實言論,造成社會恐慌,激化矛盾。由此可見,伴隨各種網絡技術的進步,自媒體通過技術手段控制的內容傳播方式和方法愈發難以控制。
二、自媒體行業中存在的問題
1.虛假內容伴生,混淆視聽
自媒體創作者通過自媒體平臺發布作品,很多作品摻雜著部分虛假內容。微博、微信、QQ和短視頻APP等社交軟件和自媒體平臺擁有大量的作者和用戶,部分作者為了博取眼球,增加流量,主觀臆造、捏造事實,助推謠言升級。讀者通過評論跟帖點評等方式,助推事件升級,甚至用大量的“事實”佐證謠言的真實性。
2.庸俗和網暴作品盛行
網絡時代,人人都是傳播者,很多人沒有受過正規的新聞和媒體工作教育,作者素質參差不齊,導致庸俗內容和網暴事件頻發,降低了自媒體作品的品質。快餐式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導致傳播內容庸俗是必然的,同平臺不同層次的作者,基于學歷、閱歷、分析力的不同,對同一個事件會有不同角度和觀點,更不用說自媒體平臺數量眾多,庸俗作品層出不窮,攀比、拜金、炫富、網暴事件頻頻出現。
3.法律意識淡薄,侵權問題激增
自媒體除了公司經營的賬號外,絕大多數自媒體人法律常識不足,法律意識淡薄,這也是自媒體內容出現問題的原因,抄襲、炒作等問題頻出。2019年“馮提莫侵權”事件,大家一定以為馮提莫是主要的責任者,結果卻是斗魚賠錢,緣由是馮提莫于2000年2月份在直播間播放了張超的歌曲《戀人心》,并且將直播過程做成了1分多鐘的小視頻發布到了平臺上,因為該歌曲版權屬于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所以才會出現音著協將斗魚告上法庭的事件。
三、建立完備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自媒體新業態的出現和快速發展,帶來了新的社會矛盾,增加了公共危機事件,加快了信息的公開概率和傳播速度。以利益為驅動的部分網民,為增加點擊率和曝光量,歪曲事實,斷章取義,臆斷遐想,利用互聯網和自媒體平臺發布的不實和沒有根據的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作品,導致虛假事件過度發酵,造成公眾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和混亂的認知。落實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夠及時、準確、全面地還原事件真相,保障公眾在此類事件發生時的知情權,遏制各類不實信息進一步擴散和蔓延,消除公眾疑慮和焦慮,進一步提高媒體的公信力,消除自媒體作品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危機。
1.建立新聞發言人“辦公室”
目前,通過自媒體發布的信息數量越來越多,公共事件的種類和性質也千差萬別,涵蓋的知識領域千奇百怪,新聞發言人要從紛繁蕪雜的信息中發現、分析、整理、提取出重要的信息,不是一個個體能夠完成的,需要一個團隊的支撐和分工協作,這需要設立專門的新聞發言人“辦公室”,協調和溝通相關的部門。同時,“辦公室”成員的知識結構應是多專業、多領域、多層級的,成員也要有媒體工作背景或相關工作經驗。通過團隊的協作才能確保新聞發布的嚴謹、高效、專業。
2.設立專職新聞發言人
2016年,中辦、國辦聯合發布的《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提出主要負責領導要當好“第一新聞發言人”。[2]目前,絕大多數新聞發言人都是兼職,中央層面多為辦公廳、宣傳部、政策研究部門的廳局級領導;省、市級多為秘書長、副秘書長、宣傳部部長、辦公廳主任等。[3]新聞發言人多是他們的兼職工作,不會把主要精力投入其中,工作沒有連貫性,達不到傳播效果。迄今為止,中國新聞發言人還未進入到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正式職業名稱序列。新聞發言人目前只是一項工作,還不是一種職業,更缺乏系統的制度保障。
3.建立健全完備的新聞發言人培訓制度
1983年,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中共中央宣傳部聯合下發《關于實施<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其中要求“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行新聞發布會,讓新聞發布會成為外宣工作的新常態、新慣例”。2012年,國新辦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突發事件新聞發布工作的意見》指出,要進一步加強新聞發言人培訓工作,把對新聞發言人系統化、科學化、專業化的培訓,作為加強和改進新聞發布工作的一項重要工作。同年,國新辦聯合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舉辦了全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并將其作為新任政府新聞發言人崗前培訓的固定平臺。目前,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培訓工作能夠做到制度化、規范化,但是常態化卻不夠。各地區各部門的培訓工作差異化比較大,對自媒體時代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新聞發言人培訓尚需加強。
4.充分授予權力
雖然各級政府按照相關制度和規定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和制定了相關制度,但在工作中的安排多半為副職兼任,職級上的差別決定了新聞發言人在發言時的顧慮較多。新聞發言人接收信息的渠道也不暢通,在重大事件上,新聞發言人得到信息也僅是結果性的,對事件的前因后果不甚了解,無法充分發揮作用。新聞發言人可能無法參加新聞發布會前的重大決策會議,信息堵塞是授權不足的結果。充分授權給新聞發言人,才能第一時間回應網絡事件,有效應對網絡輿論壓力,提前化解矛盾在評論區。
四、結語
自媒體時代的新聞發言人已經不是一個具體個體,而是在以新聞發言人制度保障下,由一個團隊或是多個機構支撐起新聞發布體系。在大眾視野下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輿論事件的裁判,在日漸公開透明的社會環境中架起政府與公眾的橋梁,擔負起新聞發布、輿論引導、政務公開、危機公關等多種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