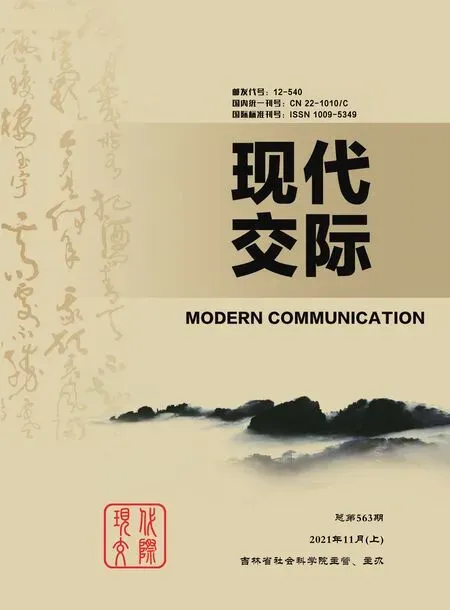高校資助型社團育人實效性研究
——以鹽城師范學院伯藜學社為例
謝莉俐
(鹽城師范學院 江蘇 鹽城 224007)
高校的資助工作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因為其不僅反映了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更代表著社會溫度,關系社會和諧。信息時代的到來,快速的新聞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高校資助虛假化、表面化,不僅無法使真正需要幫助的學生得到資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其造成了負面影響。基于上述問題,對高校資助型社團育人所能產生的實效進行研究。
一、簡述高校資助型社團所存在的問題
1.精神資助流于形式
高校資助型社團屬于學生資助模式,在中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直至現在,經歷了較為漫長的發展過程,并形成了具有一定指導性的輔助理論。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故高校資助型社團相較于成立初期,不僅在理論與成熟度上有了進步,而且有了良好的外部經濟條件;但是,即便如此,其依舊存在一些問題,而最明顯的問題是精神資助流于形式。當下高校資助工作在精神關注層面存在不足,主要是因為相關人員將資助活動定義為物質資助,認為對貧困學生予以一定的物質資助,便能為其解決就學問題,從而達到高校資助的真正目的。而調查顯示,貧困學生由于生活條件差,不得不接受外界幫扶時,心理上承受了很大壓力,自卑感更強,這無疑是高校資助型社團在工作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因此,高校的資助助人應該向資助育人方面發展,在給予貧困學生物質支持的同時,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使其在物質上有保障,在精神上有尊嚴,讓貧困學生真正融入集體生活,充分體現高校資助型社團的積極作用。[1]
2.全面發展力度不足
工作的全面發展力度不足是高校資助型社團存在的問題之一。真正的扶貧應該讓貧困學生與貧困家庭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而不是被遺棄在社會的冰冷角落。然而高校扶貧工作仍存在學生與教師謊報扶貧資格、貪污扶貧物資的情況。而該問題的產生,同當前扶貧全面發展力度不足有直接關系。所謂全面發展,不僅是在扶貧名額上惠及全體貧困學生與貧困家庭,更是在規章制度與獎懲形式上確保扶貧工作能夠走進真正需要的家庭,對覬覦扶貧物資的無恥之徒給予嚴格的懲處。只有這樣扶貧工作才能真正全面覆蓋社會,使經濟問題不再成為阻礙我國人才發展的桎梏。[2]
二、高校建立資助型社團的必要性
目前,高校資助活動的主要問題在于對學生心理的關注不足,管理形式存在一定的問題,高校可以通過建立資助型社團加以解決。
1.資助型社團的形式是以學生為主體,并以學生作為相關負責人來策劃相應活動
這種學生性質的社團資助活動,相較于其他形式的資助與扶貧活動,更容易走進貧困學生的內心,使其在接受物質幫扶時心態更加平和輕松。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資助型社團成員與受資助學生朝夕相處,了解貧困學生的內心,可使資助活動更具親和性,有利于資助育人理念的實施。[3]
2.資助型社團在管理與監督方面有天然優勢
學生在學校學習過程中,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較小,針對資助的貪污問題,能夠嚴肅、公正處理。由學生組織領導的資助型社團更了解貧困學生的生活狀況,能夠準確識別貧困學生,從而使每一筆資助都能準確投放,對貧困學生起到幫助作用,杜絕資助物資貪污的情況。[4]
3.資助型社團可幫助學生進行心理建設
對在學習生活上需要資助的學生而言,“貧困”是最敏感的標簽;在生活中,物質條件差便會使其無法體會社會的精彩之處,而在接受資助時,會再一次被“貧困”喚醒心中的脆弱,因此,很多資助活動,在未意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情況下,使貧困生逐漸與團體之間的關系出現裂痕,甚至變得更加孤僻冷漠、自我否定、缺乏自信。貧困生不想一次次被資助活動貼上標簽,但是又迫于生活壓力不得不接受幫助。因此,貧困學生只有擁有較為強大的心理素質,才能保證不被資助活動壓彎了腰。而資助型社團的出現很好地解決了上述問題。資助型社團,使貧困學生在群體中消除了心理負擔,融入群體,社團幫助貧困學生更好地進行心理建設。
三、伯藜學社簡介
伯藜學社創始人為陶欣伯老先生,他在2002年著手籌備新的基金會,名為“江蘇陶欣伯助學基金會”,2006年經江蘇省民政廳批準成立。助學基金會設立在南京,屬于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非公募基金會,所頒發的助學金稱為“伯藜助學金”,接受助學金的學子也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陶學子”。基金會專注高校資助育人工作,“伯藜助學金”的資助政策為每人每年五千元,“一助四年”。為使更多學子獲得幫助,自2007年起,基金會陸續與東南大學、淮陰工學院、淮陰師范學院、江蘇大學等22所學校建立合作關系。至2019年,基金會累計資助人數8,707人,累計捐贈金額共10.7億元。由于在資助學子方面取得了較為優異的成績,“伯藜助學金”項目先后榮獲江蘇省第二屆慈善大會“最具影響力慈善項目”、第二屆“中華慈善獎突出貢獻(項目)獎”、“2014年度十佳公益慈善項目獎”與2019年度“江蘇最美資助人”提名獎。[5]
伯藜學社是當下最典型的資助型大學社團,在資助人陶欣伯的組織與領導下,該社團已經漸漸發展出屬于自身的成長軌跡,不僅建立了完善的助學體制,還在社會與網絡上引起了良好的反響。伯藜學社對貧困學生的幫助不僅是物質上,更是心靈上的。有關調查顯示,目前伯藜學社出現的“反哺”現象正在逐年上升,很多曾經接受過伯藜學社資助的學生畢業后,都會選擇通過自身力量為伯藜學社提供一定的物質支持。這一現象說明,在伯藜學社的資助下,學生不但能夠順利完成學業,還建立起健全、高尚的品格,是非常成功的助學案例,值得當下所有社會慈善工作向其學習。
四、高校資助型社團育人實效——以鹽城師范學院伯藜學社為例
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高校資助型社團的育人實效,本文以江蘇鹽城師范學院伯藜學社為例,分析學生在參與伯藜學社后,所取得的顯性與隱性進步。
1.顯性進步
學生在學習上的進步最明顯的研究指標即是學習成績,故本文收集了鹽城師范學院伯藜學社的學生掛科率及獎學金獲取率,分析伯藜學社在促進學生學習上的顯性成效。
首先,伯藜學社相較于其他類型的資助活動最明顯的優勢是對學生實現長期的鼓勵與督促,而不是對學生進行資助后便不予理睬,他們繼續為學生提供關懷,并建立較為溫馨的學習生活環境。例如,鹽城師范學院的伯藜學社會在為加入社團的學生提供費用支持,還通過學校教師與管理層建立伯藜學社學習部,意在鼓勵貧困學生補上高中階段的學習不足,更好地適應大學學習氛圍與學習強度。這種做法給了貧困學生極大的信心與歸屬感,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相聚在伯藜學社的學習部,給予彼此心靈上的慰藉,還激發了學習與生活熱情。故伯藜學社不僅為學生提供了最為基礎的物質保障,還在氛圍營造、心理建設方面考慮得較為周到。而對學生2020—2021年的掛科率統計后發現,2020年初伯藜學社的掛科率為39%,但是到了2021年末伯藜學社的掛科率下降至9.01%。這說明,入學初的貧困學生由于文化基礎差距較大而掛科率偏高問題,在伯藜學社的氛圍影響下掛科率明顯減少。在獎學金獲取方面,2021年相較于2020年除特殊的單項獎學金沒有變化外,其余一、二、三等獎學金的獲得率明顯提升。這也說明加入伯藜學社的學生通過一學年的努力,不僅學習成績得到提高,而且獲得獎助學金,改善了生活,伯藜學社的育人實效非常明顯,也說明資助型社團具有相對明顯的育人優勢。[6]
2.隱性進步
除學習成績外,伯藜學社所創辦的校園活動也在更多的隱性方面幫助學生全面成長。鹽城師范學院伯藜學社的特色在于為學生創辦了“第二課堂”,第二課堂使學生心理更健康、綜合素質更強。伯藜學社創辦的第二課堂,能最大程度地照顧有經濟問題的學生,為社團內學生量體裁衣,使其盡可能少地付出獲取更全面的校園生活體驗與社會生活體驗。
鹽城師范學院伯藜學社非常重視榜樣力量,并善于挖掘校園中勵志典型,為學生提供充足的精神養料。伯藜學社在學校的支持下選拔“勵志之星”參加江蘇省甚至是全國范圍內的評選,并將活動結果以校報、微博、公眾號等形式進行宣傳與報道,意在通過該活動讓更多的學生感受榜樣的力量,從而在心靈上給予學生慰藉,讓學生在心底涌現出“看不見”的隱性力量,更好、更自豪地生活在大學校園內。
伯藜學社非常重視組織學生參加志愿服務活動。對內,志愿服務活動的對象大多是伯藜學社本身,這不僅能夠降低活動費用,也能夠讓學生加強溝通,敞開心扉,更好地發揮伯藜學社的作用。而對外,伯藜學社所組織的志愿服務活動會深入云南、甘肅等貧困山區,支教幫扶,目的是讓伯藜學社的學生切身感受作為貧困生不僅僅只能等待被資助,也能在社會上發光發熱,去資助那些更需要幫助的孩子。這種活動不僅能夠幫助學生建立自信,更能激發其奮斗與前進的動力,并懂得感恩的重要性。
此外,伯藜學社在創始人陶欣伯的建議下,鼓勵該社團學生創新創業,他認為青年的夢想需要被托起。在陶欣伯基金會的支持下,伯藜學社會積極同國內外高校、社會創業組織等交流,并舉辦相應的創業訓練與比賽。陶欣伯先生之所以這樣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被他資助的學生在未來可以通過創業取得成功,并延續他的想法,為更多貧困學生帶來幫助。這無疑是非常高尚的,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每一個伯藜學社的學生。
五、結語
伯藜學社不僅在育人實效上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成績,還在精神層面上影響著每一位學社中的學生,真正意義上將資助助人變成了資助育人。高校資助型社團育人需借鑒伯藜學社經驗,并在其基礎上開枝散葉,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進步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