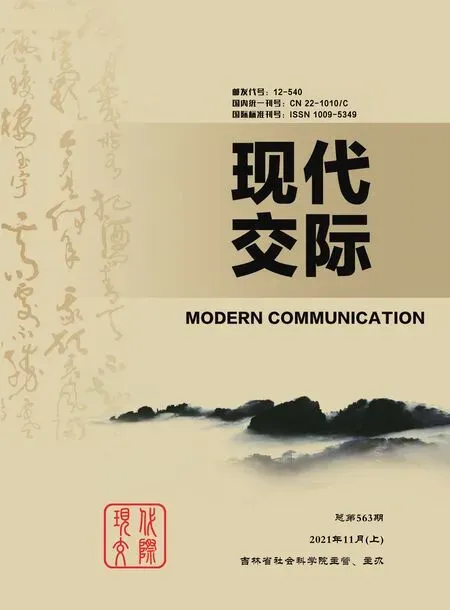中醫藥譯介及“走出去”與“走進去”問題研究
段紅梅
(四川文理學院 四川 達州 635002)
關于中醫藥的翻譯及其對外傳播的研究,不少學者已經展開了多方面的論述,但主要研究內容還是集中于對某一具體中醫方法內容的翻譯,或對語言文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的討論,輔之以中醫藥典籍的譯介論證。[1]這些研究為中醫藥外譯提供了切實參考,但放眼整個中醫藥對外傳播的過程,語言轉換只是其中的一個基本環節,而譯介內容的擇取、譯入語環境、譯介價值效果等才是更值得探討的問題。謝天振先生提出完整的譯介活動還包括在譯作基礎上展開對影響、接受、傳播等文學關系和文化交流問題的考察、分析[2]9-10,文本所討論的譯介之路就是經譯者翻譯處理后在譯入語環境里的傳播發展之路。本文將從譯介學的視角去探討中醫藥在本國的翻譯之路及在國外的發展之路,即中醫藥譯介的“走出去”與“走進去”之路,以期突出研究中醫藥傳播過程中的關注盲點,分析癥結所在,推動中醫學與中醫文化的對外傳播。
一、中醫藥外譯的“走出去”與“走進去”問題
(一)中醫藥外譯的“走出去”問題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下,中醫藥及其文化相關作品的外譯迫在眉睫。目前,我國傳統醫藥作品翻譯數量較少。學者朱文曉、童林等從數量、期刊、研究對象和類別方面對我國醫藥翻譯研究進行分析發現,其局限于中醫藥翻譯原則、策略、方法、技巧、教學、術語等技法的討論層面。中醫藥的翻譯數量和中醫藥翻譯研究視野的單一,使中醫藥事業難以向更寬廣與更深入的領域發展。
除了譯本翻譯研究,原文本選擇及翻譯主體選擇在中醫藥外譯的“走出去”任務中也至關重要。談及中醫藥文本,市面上大多集中于中醫藥典籍、中醫學史、文學作品中的中醫藥元素,但這種太過專業的文本對于普通大眾來說難免會產生一種“疏遠感”,甚至讓沒有相關知識的人產生“畏難”而放棄的心理。此外,目前,中醫藥翻譯的主體是從事醫藥工作的專業人員及相關方面的研究專家、醫科院校出身的教員和在讀學生。雖然國家層面在積極倡導中醫文化外譯,但大部分譯者反應較為冷淡或“愛莫能助”,一是因為其對中醫藥及其文化發展認識不全面,認為只有古代的醫藥典籍著作或高深的專論研究才能展示中醫藥的魅力,二是譯者對中醫哲學文化的認可、自信與熱愛尚不夠強烈,難以驅動其對醫藥翻譯的鉆研精神,難以擔當起弘揚傳統中國文化的責任與使命。
(二)中醫藥文化的“走進去”問題
中醫藥譯作的成功是其對外傳播的最重要一步,但傳播的成功還取決于譯作能否走進譯入語環境,為譯入語讀者與譯入語文化所接受。中西方語言、文化及觀念差異是譯介傳播應考慮的基本因素,尤其是中醫藥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代表,其內在的傳統哲學思想彰顯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其在西方的融入之路既光明又坎坷。
1.讀者對中西文化的了解存在時長與范圍上的差距
由于經濟發展、政治局勢等原因,中國在國際上曾一度處于相對的弱勢地位,文化交流上,我們更多的是引進而較少輸出,因此中國文化的“逆向流動”十分艱難。雖然現在情況有了改善,但西方接觸中國文化的時間較短,缺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認知,對傳統中醫藥的醫學文學價值認識更是不足。
2.西方讀者對中醫的興趣和價值需求欠缺
中國文化全面輸出,需要西方主動引入的配合,這取決于西方讀者對中醫的興趣和價值需求。對國人而言,經典的傳統中醫著作如《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毋庸置疑是中醫價值和中國文化韻味的集大成者,其文化負載詞極為豐富,融合了中華民族的傳統哲學觀、科學觀和自然觀念。但西方讀者,對接受與其語境固有觀念不同的理念會產生排斥的心理,且這可能會讓自以為是文化引領者的西方人錯誤或惡意地宣揚“中醫無用論”。此外,即使對中醫文化感興趣的人,在了解了這“天書”般的作品需要極大的知識儲備才能理解時,也免不了產生放棄的念頭,即使再成功的中醫藥譯作對于他們而言,也只是一堆帶有中國特色的符號,而難以認識其實用價值或引起興趣。
3.中西方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
中西方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使一些西方國家惡意污化中國文化形象,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地位,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土壤中的認可度。因此,中醫藥譯作傳播仍然任重而道遠。
二、譯介學理論與中醫藥翻譯
譯介學是謝天振先生從比較文學視域提出的文學作品翻譯研究理論,其主要關注文學翻譯、翻譯文學(譯作)、譯者的主體性與創造性叛逆及翻譯中文化信息與文化形象的失落等問題。“譯”可以理解成為翻譯,“介”為傳播,“譯介”即探討(文學)翻譯過程中的現象、問題及譯本的交流、傳播、接受和價值等。譯介學這個概念自提出以來一直受文學界和翻譯界人士關注與討論,因為它是“翻譯研究轉型的重要推動力量,拓展翻譯研究的學術空間”[3],使學者對文化和翻譯的研究從語言信息層面轉向了視域更為開闊的文化環境層面,即除了原文或譯文文本本身是值得關注的焦點之外,譯入語文化環境相關因素等都應納入考慮范圍,以此才能從更深層次意義上完成翻譯。
中醫藥文化作品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探討其文化譯介“走出去”與“走進去”問題就是在探討中醫藥領域的譯介內容、譯介主體、譯介接受環境和受眾價值問題。正如謝天振先生在《譯介學導論》自序中指出的:“近十余年來,我們國家舉國上下正在關注一件事,即如何讓中國文學、文化切實有效地‘走出去’,走進世界各國,而譯介學理論所揭示的文學譯介、文化交際的規律無疑將為這一宏大的文化使命做出它的貢獻。”[4]從譯介學的規律來看,中國醫藥文化批量外譯的時機已經成熟:一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話語權越來越受到重視,二是中國在近兩年國內外疫情局勢影響下,高效預防舉措和高度的醫學意識加深了西方民眾對中國醫藥文化和中國形象的好感。借助譯介學規律,進一步完善中醫藥譯介傳播,以更好抓住時機,高效推動中醫藥文化作品對外傳播,使中醫藥學在國際社區實現價值最大化。
三、譯介學對中醫藥譯介及文化傳播的啟迪
從譯介學的視角來看,要擴大中醫藥譯介內容的廣度,加深譯介在國際上的影響深度,應著眼于探討中醫藥譯介內容、譯介主體、譯介接受環境和受眾價值方面的重要性。
(一)中醫藥譯介類型多樣化和內容實用性
中醫藥譯介,一方面要注重傳統醫學文化的傳播,推廣中華優秀文化;另一方面要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和中醫藥在國際醫學上的作用,讓其醫學研究價值促進醫學的完善和長遠發展,讓中醫藥真正造福于人類。在選擇中醫藥譯介材料時,翻譯發起人要綜合考慮源語言環境、譯入語文化環境及大時代背景下的翻譯需求、目的和價值,選取多種類型的中醫藥文本,以實現多方面效果。中醫藥譯介內容應綜合考慮原文本的實用價值,即進入另一個語言環境時應讓讀者易懂,使讀者能感受到其實際效用。因此,除了“晦澀高深”的醫學著作之外,一些語言難度介于專業性與大眾性之間,又實用的如中醫藥病例診斷書、中醫口述診斷記錄、中醫學交流一手資料、中醫學教材、中醫藥著作的副文本等集專業性與通俗性、科學性與經驗性、嚴謹性與簡潔性于一體,對中西方患者或醫者,專業中醫學習者或業余愛好者,甚至醫學研討會和學校單位,都可作為有效的學習參考資源。
(二)中醫藥譯介主體的專業素養和文化使命感
譯介主體的價值作用極為重要,傳統翻譯研究者“是連接不同語言文化的橋梁”,譯介學認為它“是翻譯文學的創作者”。中醫藥作品外譯時,其譯介主體不僅要著眼于語言差異問題,更應考慮譯入語讀者的理解與接受的問題。中醫藥文本中的傳統哲學思想常用四字表達結構或晦澀的古漢語表達,且語言又涵蓋復雜的知識體系。這種文本特點對于西方讀者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不利于中醫藥文化“走進”讀者的視野。譯者應憑借翻譯素養和技能,使中醫藥譯作從“陌生化”變身成為“熟悉化”,考慮讀者的閱讀習慣與文本專業性之間做到平衡,減少讀者接受難度和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畏懼感,滿足英語讀者其“既實際有效,又具有異域藝術之感”的期待。更為重要的是,譯介主體要對中醫藥學科知識和博大的中醫藥文化發自內心地認同與熱愛,有強大的中國文化自信,這樣才能意識到中醫藥譯介的文化藝術價值,才能立足于國家文化傳承與傳播的需求,肩負起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使命。
(三)中醫藥譯介傳播與接受環境的營造
在討論傳播中醫藥譯介和讓其為譯入語環境所接受前,我們應認清“譯入”與“譯出”的差別。“譯入”活動是一個民族文化對他者文化養分的主動汲取,譯者只需考慮讀者應汲取哪種文化和如何汲取的問題;而“譯出”活動作為本民族向外推介自己文化的任務,要著重考慮對方接受的意愿與需求。若譯入方對譯介文化尚未產生強烈的內在需求,則難以形成比較成熟的接受群體和環境。[2]9-10因而中醫藥譯介及其文化的傳播需要大力激發西方讀者對中醫文化的興趣和內在需求。這一方面需要在譯入語環境中發起中國傳統文化宣傳和中醫知識普及活動,增加文化產業中的中醫文化元素,如《刮痧》《推拿》等帶有中醫文化元素的影視作品出現國際視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西方接受群體的戒備懷疑心理,有利于培養壯大西方漢文化愛好群體。此外,在國際慈善救助活動、醫學交流中可適當加入中醫方法和思維,鼓勵利用現代科技、借助發達的媒體軟件對中醫知識進行普及。同時,在譯介傳播的過程中,也要注重文化本身傳播與發展的規律,分階段對中醫藥譯介進行推廣,循序漸進地引導譯入語環境和讀者在觀念心理上對中醫哲學的接納。
四、結語
現今我國中醫藥外譯與傳播事業受到高度重視,從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倡議到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任務中都少不了中醫藥文化。中醫藥的國際化、中國傳統文化的走向世界,有助于增強我國文化自信。讓中醫藥譯介及其文化“走出去”,走進西方讀者的視野與內心,走進國際醫學體系與國際文化領域,譯者們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