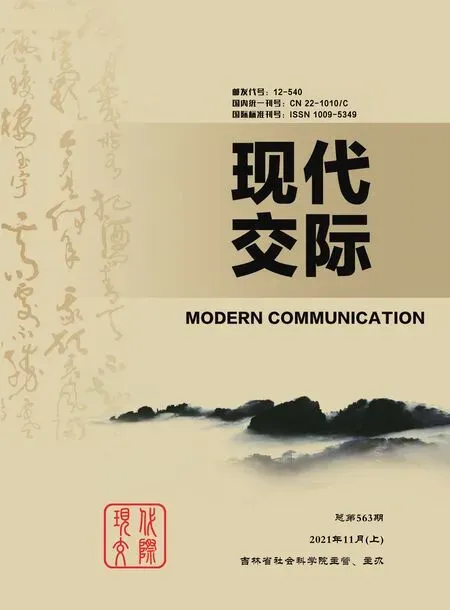《論語》俄譯本的翻譯研究及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對比
陳禹霖
(吉林師范大學(xué) 吉林 四平 136000)
儒家經(jīng)典著作《論語》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詔令之下,儒家學(xué)派達到空前鼎盛時期,至宋朝已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16世紀末17世紀初,《論語》開始向歐洲傳播,最初經(jīng)由傳教士之手,在翻譯過程中被裹挾上了宗教的味道,“孔夫子”的形象也沾染了基督教文化的氣息。
一、《論語》俄譯本翻譯研究歷程
在西歐“漢學(xué)”潮流影響下俄羅斯開啟了對中國經(jīng)典的探究。自18世紀初至今,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里,《論語》在俄羅斯的譯作已有十余冊。《論語》的翻譯與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沙俄時期、蘇聯(lián)時期、俄羅斯時期。
沙俄時期是漢學(xué)研究的萌芽時期,《論語》俄譯本最早出現(xiàn)在俄羅斯文學(xué)奠基人之一比丘林翻譯的《四書》中,因其年代久遠無法考證其譯文。在19世紀下半葉,“漢學(xué)風(fēng)”在俄羅斯帝國迎來第一個高潮。80年代末,漢學(xué)家瓦·巴·瓦西里耶夫完成了《論語》的俄譯,并將此納入《中國文學(xué)》的編撰。巴·斯·波波夫受其老師瓦西里耶夫的影響,加入《論語》的研究,并于1910年出版了俄羅斯?jié)h學(xué)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論語》俄譯本。隨后,1917年,俄國爆發(fā)十月革命,國內(nèi)局勢動蕩,受中國五四運動新思想的影響,在此后的十幾年中蘇聯(lián)學(xué)術(shù)界經(jīng)歷重新“洗牌”的重創(chuàng),中國傳統(tǒng)國學(xué)備受冷落、停滯不前。1949年,中蘇建交,蘇聯(lián)重拾對漢學(xué)的思考與研究,漢學(xué)研究出現(xiàn)第二個高潮。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guān)系發(fā)生變化,儒學(xué)研究在蘇聯(lián)也隨之沒落。70年代后期,蘇聯(lián)國內(nèi)的儒學(xué)研究再次走入人們的視野,直至蘇聯(lián)解體,俄國進入新時代,漢學(xué)研究迎來前所未有的高潮。這一時期,《論語》譯本層出不窮,其中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列·謝·貝列羅莫夫于1998年出版的《孔夫子與論語》,被稱為俄羅斯史上最完整、最系統(tǒng)的譯本。
現(xiàn)如今,《論語》的翻譯已從為統(tǒng)治者、宗教服務(wù)的枷鎖中走出來,突破了逐字逐句的對應(yīng)翻譯,不再固執(zhí)堅守“信”“達”,更加注重“雅”,逐步轉(zhuǎn)向從“音譯”到“意譯”,從修辭、韻律、語體的角度出發(fā),真實傳達儒家精神內(nèi)涵、哲學(xué)思想。
二、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對比
1980年,許國璋教授第一次提出“文化負載詞”概念并對其闡釋。[1]隨后,廖七一、包惠南教授進一步解釋“文化負載詞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承載和反應(yīng)民族文化特征的語言,它反映了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思想特征和生活方式”[2]。“文化負載詞又稱詞匯空缺,是指源詞匯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沒有對應(yīng)語。”[3]中國傳統(tǒng)文化自古以來以儒家思想為“底色”,以宗法家族為核心,而西方則崇尚平等、自由,以基督教的道德標準為準則。因而《論語》想要被俄羅斯人民所接受,不可避免地要平衡兩種語言相互轉(zhuǎn)換時的不對等的表達。
1.“仁”的翻譯對比
《論語》中,“仁”字涉及58章,計出現(xiàn)109處,可見“仁”在其學(xué)說中的核心地位。在《論語》中,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在孔子眼中“仁”最基本的核心便是“愛人”,但孔子并未明確解釋“仁”的具體內(nèi)涵,孝親之愛是“仁”,“泛愛眾”是“仁”。“克己復(fù)禮”為仁,“剛、毅、木、訥近仁”(《子路》)。“仁”的內(nèi)涵無法簡單用一詞一句概括,“仁”的這種特性為翻譯提供多種可能性,也帶來困擾。
2.“義”的翻譯對比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內(nèi),“仁”是最高道德要求和道德準則,“義”屬于“仁”的范疇,是實現(xiàn)“仁”、踐行“仁”的行為規(guī)范。“義”的范圍很廣,《論語》中,“義”指道義,即必須履行的道德義務(wù),另外“義”通“宜”,有適宜、正當之意,指人的行為應(yīng)當符合道德準則。《里仁》第十六章講道:“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也成了“君子”立身的標準。對于“君子”而言,“義”是自身所追求的高尚節(jié)操,“君子義以為上”(《陽貨》)。于國家而言,“義”是統(tǒng)治者的道德規(guī)范,“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子路》),統(tǒng)治者維護道義、正義才能獲得百姓擁護。
在眾多俄譯本中,大多將“義”譯為“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或其同根詞“долг”及其相關(guān)詞組。例如:“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第四)。
3.“禮”的翻譯對比
孔子重“禮”。在《說文解字》中“禮”為“禮”,“禮,履也,所以事鬼神之福也。”原意指原始社會對鬼神、祖先舉行的祭祀儀禮,后來逐步演變?yōu)榧s定俗成的禮節(jié),社會秩序。《論語》中孔子曾與宰我討論三年之喪的問題,《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時孔子所說的“禮”則是“儀式禮節(jié)”之意,可譯為“”。另外,“禮”的內(nèi)涵也非常豐富、復(fù)雜,俄譯過程中,譯者也采用了靈活的翻譯方式。例如: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學(xué)而》)
4.“信”的翻譯對比
“信”在《論語》中出現(xiàn)三十余次,“信”與其他文化負載詞不同,它有實詞、虛詞之分。作為虛詞,“信”無實際意義,不需翻譯;作為實詞,“信”又有名詞與動詞的區(qū)別。
例1:“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當“信”表示真誠、信實、誠懇的意思時,波波夫則以淺顯易懂的語言譯為“”及其名詞形式“”;謝緬年科在其譯本中,除上述譯法還“信”譯成了“。謝緬年科認為強調(diào)了誠實、坦白的態(tài)度,他將《子路》中的“言必信”譯為“”。貝列羅莫夫用”來表達“信”的誠心誠意、正直的含義,如“悾悾而不信”譯為“。
例2:“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述而》)
三、結(jié)語
《論語》的俄譯本經(jīng)歷了翻譯主體、譯本形式、翻譯途徑的轉(zhuǎn)變。每一部《論語》譯作都有獨到之處,但也存在著對原文闡釋不足的地方,這與他們所參照的注釋和譯本有很大關(guān)系。與我國大多數(shù)經(jīng)典作品一樣,《論語》的傳播多依賴于目的語國的翻譯力量,而中國學(xué)者更多地參與了《論語》的英譯,而很少關(guān)注《論語》的俄譯。作為本民族文化的傳承人,我們有必要肩負起為文化“塔橋”的重任——研究經(jīng)典,傳播經(jīng)典。做好傳播中華文明的“中間人”,講好中國故事,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