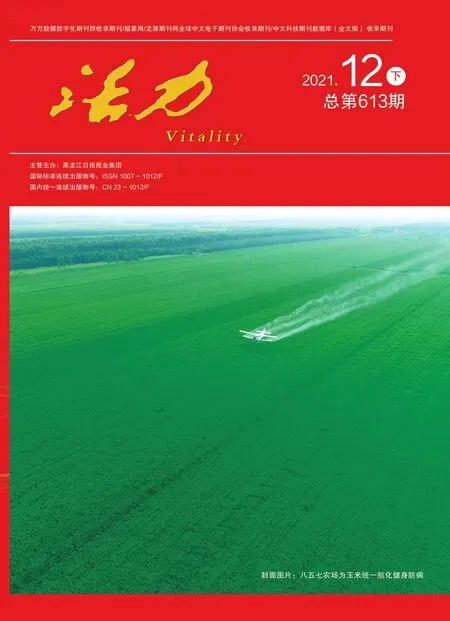百年政黨的淬火歷程:革命、發展與改革
毛 博
(延安大學政法學院,延安 716000)
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大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從民族獨立解放到社會化大生產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成就。當前,我國國際地位的確立與民族復興進入了不可逆的進程。只有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才能確保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行穩致遠,并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順利實現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
首先,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場徹底的政治革命。這場深刻的革命圍繞政治權力與階級利益展開,但同時由于近代中國歷史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導致中國的革命充滿了血雨腥風和艱難坎坷。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就已經昭告了這一現實:“工人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擺脫困境,但他們卻像今天處于嚴重失業時期的工人一樣赤手空拳。”在當時資產階級政權、地方豪紳權貴乃至軍閥占主導地位的復雜的國內環境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是極為困難的,中國在20世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與俄國1905年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和列寧的判斷類似,中國共產黨沒有陷入像早期德國空想社會主義或托洛茨基主義那般不切實際的構想,最終借鑒俄國蘇維埃的革命經驗使中國的革命理想成為現實而非停留在理論層面上。
其次,社會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政治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前提,不改變舊有制度的上層建筑就無法改變落后的生產關系,共產黨革命根據地被解放農民的革命熱情高漲正是因為由政治革命引發的社會革命導致舊有的落后的生產關系的改變,促進了無產者生產力的發展。農村地區逐漸成熟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廣大無產階級對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自下而上的廣泛支持,美國學者西達?斯考切波將這種模式稱為“大眾動員型政黨”。相比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對于中國共產黨是更根本、更徹底的革命,不僅如此,社會革命要求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的條件下進行,以政治權力為依托確立并保護新的生產關系。社會革命不像政治革命一樣簡單消滅階級和敵人即可,它涉及整個社會組織架構的重構和國家財富的再積累,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依然經歷了多個復雜的時期才發展到當今的新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為此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最后,中國共產黨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政黨獨有的,以此才能確保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無論是遵義會議、延安整風、改革開放和反腐敗斗爭等,在不同階段、不同時代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勇氣與魄力。自我革命要求刀尖向內,敢于直面問題,自我革命的精神有效地遏制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本本主義和形式主義,能夠起到自我凈化的作用。這一點對于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尤其重要,歷史證明自我革命在多次歷史關頭挽救中國共產黨于危難之中,這是保持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具體表現,也從根本上避免了黨陷入“歷史周期律”的悲劇。
二、發展為第一要務
首先,經濟發展是一切發展的基礎。歷史地來看,歐洲資本主義深入發展相應地帶來其政治上的進步與蛻變直至取代君主制使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因為“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已將經濟增長和民生福祉作為政治保證,在全球化的今天這更關系到執政黨的合法性,這一點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適用,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同樣適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對于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政權至關重要。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得到大力發展是對廣大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的真正維護,只有社會主義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才能為社會主義的廣泛上層建筑服務,這是最根本和最持久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功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日趨成熟的綜合領導力。
其次,政治發展服務于經濟發展和國家政權。政治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經濟發展同樣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政治發展作為后盾,中國的政治發展邏輯基于經濟發展和國家政權。一方面,政治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既相互統一,又有其各自獨立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和階段,相應的政治發展可能超前于當下社會經濟發展,也可能滯后于當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國民經濟發展進程中以計劃經濟調控手段分別進行短期和長期規劃使得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方向保持一致,這一點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就深刻闡述并揭示了政治權力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演進的規律。另一方面,國家政權是政治發展的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取得政權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頓具體分析了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在政治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共產主義運動為現代政治做出了貢獻,即組建和創造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并填補了權威真空。新的政治制度與政權的建立為其政治發展提供了支撐并引導政治發展的方向。同樣,無產階級政治發展的最高追求和理想也需要無產階級統治以國家政權的形式來保障,實現中國政治發展的正確方向需要堅持黨的絕對領導。
最后,實現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最終目的。無論怎樣發展,若不能實現生產關系和雇傭勞動制的徹底變革就不能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偉大飛躍,也就不能實現人類的最終徹底解放。不進行徹底而深刻的變革就只能如馬克思所形容的“游擊式搏擊”。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帶領廣大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進行的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打破了舊有的生產關系,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并為實現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制度保障。集體自由和解放的前提就是個人的自由和解放,這些都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在準確把握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之間的發展規律的同時明確了人的發展才是最終的目的。
三、勇立潮頭的改革精神
中國共產黨自1976年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改革開放政策上贏得了普遍的黨內支持和民意基礎,但最初的改革方案面臨極大阻礙,面對改革困境和阻力,黨中央不斷強調這場改革是一場革命。
最初的產權改革主要涉及農村和國有企業改革。1980年鄧小平肯定了農村部分地區實行的“包產到戶”,并認為這一情況并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至于國有企業,在吸取了部分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改革方面的重要經驗后,引入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概念,主動擴大了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權。
我國市場經濟與對外開放進程幾乎是同一時間協同發展的。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建立適應其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統籌協調好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合力大發展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標志,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更是成功實踐和偉大跨越。改革的另一重要舉措即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曾經的發展困境主要來源于資金的極度短缺與先進管理技術和經驗的匱乏,因此適時地引入外資并公派留學、出訪調研成為解決這些困難的重要抓手,這些舉措也為中國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政黨是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應的代表政治上層建筑的有機載體,中國共產黨從戰爭洗禮到社會革命,從改革開放到現代化治理,經歷了從革命型政黨向現代化政黨的轉型。一方面,政黨轉型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其是鞏固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根基。
中國共產黨作為革命性政黨肩負著領導革命和保存革命成果的重任,作為執政黨也有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責任,隨著黨的治理經驗和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首先實現了政府職能的轉變。改革開放后的政府治理從過去對市場化的單一的、片面的治理轉向了多維度的、科學化的治理。黨政分工是中國共產黨實現政黨轉型的關鍵舉措,實現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與明確政府職能不是也不應當是矛盾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黨政分工符合政治性和科學性的統一的制度化安排,它既確保了黨的領導也解決了以黨代政的弊端。總體來講,黨政分工要求政府更多地負擔經濟、社會和行政事務,這一概念自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后對我國在政府職能的轉變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現代國家治理從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上來講更趨向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相應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制度層面或政策層面可操作性的變革,那么中國共產黨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觀念的和價值評價的更高層次的追求。實行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必要且迫切的,尤其是在當下我國經濟繁榮和物質基礎雄厚的大時代背景下,因為“經濟富裕不僅不能代替民主訴求,相反,它為民主訴求的產生提供了條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確保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生活的具體體現,只有繼續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發展。
結 語
黨的百年歷史與輝煌成就波瀾壯闊。“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革命黨,只要革命最高理想還未實現,就不能停止革命的步伐,同時通過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抓鐵有痕的決心推進改革開放,實現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革命、發展與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從一個艱苦奮斗的革命黨蛻變為成熟穩健的執政黨在三個不同維度的整體概括,三者之間既不是簡單的遞進關系也不是邏輯推理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百年政黨的發展歷程與蛻變正如含有雜質的鋼鐵經過一道道淬火工藝得到淬煉最終百煉成鋼。人間正道是滄桑,只有客觀地認識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成功領導革命、為什么能夠實現社會生產力大發展,以及為什么能夠推進改革進程,才能統一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齊心協力為第二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