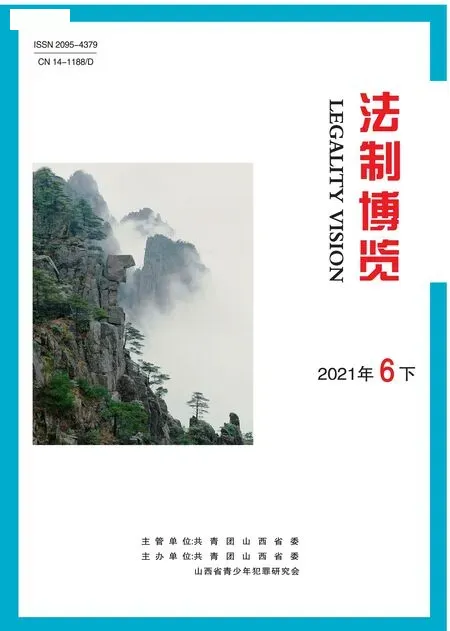法院在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功能定位
周 詩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上海 201700)
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作為我國糾紛解決的重要方式,不僅可以緩解法院辦案壓力,還能減少雙方當事人的抵觸情緒,社會效果較訴訟更為明顯。法院的訴前調解制度也成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機制體現了司法能動性和法院承擔的社會責任,通過非訴的方式,可以有效緩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避免在法庭上的針鋒相對,對于修復社會關系,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這種優勢在民事案件中尤其明顯,不僅促進了糾紛化解,而且有助于敦促當事人自覺自愿地履行,這種從法院強制到主動履行的變化,不僅緩解了法院工作壓力,而且還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真正實現案結事了。
一、人民法院的基本職能及其延伸
設立人民法院的初衷是為了化解糾紛,具體而言,在刑事案件中懲罰犯罪以保障人權,而在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的主要作用是定分止爭。因此解決糾紛是法院工作的重要任務,而實現這項任務的具體方式,就是審判。
審判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權力,但是卻不是人民法院社會影響力的唯一表現。我國法律賦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就是審判權的重要延展,并最終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頒布出來。從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條可以看出,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最終目的是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任何工作都應該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力也不例外。因此除了審判業務之外,人民法院還承載著司法公開和普法教育的任務,并最終服務于社會主義法治事業。
二、我國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之現狀
(一)非訴糾紛解決的方式
首先,2010年8月28日我國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從第一條和第七條規定可以看出,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行為是一種訴前的非訴糾紛解決方式。調解制度作為糾紛的解決方式的一種,可以依靠社會力量,通過“老娘舅”式的說理,往往比訴訟更能讓當事人接受,而且還能產生有效的督促作用,甚至達到向社會大眾宣傳正能量的效果。
其次,仲裁也是非訴糾紛解決方式的一種。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勞動仲裁被定位為處理勞動爭議的主要方式,是勞動爭議處理體系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環節。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領域拓展,勞動關系展現出多樣性復雜性態勢,表現形式對以往而言進一步程式化、復雜化。[1]
最后,刑事和解制度,即在刑事案件發生之后,被害人對加害人達成諒解,最終導致檢察機關不起訴的結果。在刑事案件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情況下,在當事人達成和解后,往往最終能達到積極的效果。[2]這樣,一方面被害人獲得了應有的賠償,以彌補刑事違法行為對其造成的損害,另一方面,被告人也得到了教育,從內心真實悔過,實現了法律教育的作用。
(二)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的短板
首先,非訴方式沒有強制執行力,在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議的情況下,當事人無法強制要求對方履行,而必須采取訴訟方式。正是因為沒有強制力加以保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訟累。
其次,當事人對于非訴方式存在誤解,認為是法院在有意拖延時間。由于訴前調解程序是設立在立案之前,當案件調解失敗需要轉入訴訟程序時,會引起當事人對訴前調解的質疑,當事人往往會認為訴前調解就是法院在拖延審理期限,從而對于法院產生錯誤印象,對于調解產生抵觸情緒,最終將不利于法院后續訴訟工作的進行。
三、法院在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之定位
(一)糾紛的終結者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由此可見,訴前并不是調解的唯一階段,調解也可以作為法院審理過程中解決糾紛的一種方式。法院通過審判來維護糾紛當事人的權利,保證糾紛處理的相對公平性。而且由法院居中的調解更容易讓當事人信服,因為法官在調解中往往會釋明雙方各自的法律風險,在有了一定心理預期的情況下,更容易達成調解方案。
(二)履行的督促者
不同于調解委員會調解,法院介入之后作出的裁判文書具有強制效力。通過法院制作具有司法效力的裁判文書,可以彌補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協議不具備強制執行力的缺陷,以此來提升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用。相反,在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的情況下,若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另一方當事人往往還是需要通過訴訟的方式,借助于法院的強制執行力來確保權利實現。
四、人民法院在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困境
(一)社會糾紛解決依賴法院
一直以來,法院作為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群眾常常把訴訟作為解決糾紛的唯一途徑,認為只有通過訴訟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權利才能得到保護,對于其他解決糾紛的方式往往了解不多,甚至忽視了其他社會群體在解決糾紛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在法院經過審理形成最終判決之后,一方當事人對于審理結果不甚滿意,進而上訴的情況也十分常見,案件經過一審、二審,無疑增加了當事人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形成訟累,調解的難度加大,當事人之間的積怨加深。而當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后出現的執行難問題,更是加劇了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矛盾,認為法院執行不到位。與此同時,由于當事人選擇訴訟的比例上升,其他糾紛解決機制被忽視,導致其應有的解決糾紛的功能得不到發揮,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3]
(二)訴與非訴機制銜接不暢
由于在普通群眾心中,一直忽視非訴的解紛方式,而正是由于觀念的缺乏導致非訴機制工作的開展存在困難,一直都難以得到公眾的支持。在長期非訴解紛方式缺位的情況下,訴訟與非訴之間的銜接勢必無法有效形成。非訴并不是一個強制的訴訟前置程序,在普通群眾拒絕非訴的情況下,訴訟是唯一的解紛方式。同時,根據法律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仍然可以組織當事人進行調解,在調解不成的情況下進行判決。因此當事人普遍認為,即使在訴訟程序中,調解也是必經程序,因而無須訴前就進行調解,況且,訴訟在一定程度下可以給對方造成壓力,更有利于達成調解。
五、人民法院糾紛解決功能之合理延伸
為應對新階段非訴糾紛解決機制亟待解決之困境,人民法院應該圍繞審判這一工作重心,在合理范圍內拓展自己的職能。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法院應該對當事人進行一定的引導,提供釋法明理的渠道,告知雙方當事人訴訟中存在的風險,即原告訴請未必能得到支持或者被告將會收到法律制裁。法院應該明確自身審判的職能,從而鼓勵當事人運用非訴的方式來解決糾紛。
在當事人選擇非訴方式來解決糾紛的情況,由于是當事人出于真實意思表示從而處分自身權利的行為,因此無法得到與法院訴訟同樣的保障,即法院強制執行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法院可以對于非訴解紛方式提供最終的司法保護,這樣才能真正維護多元化解紛機制的順利進行,保障多元解紛機制的穩定性。因此,對于發揮法院的監督功能,就是要以讓法院成為確保非訴解紛機制發揮功能的。
六、總結
在多元化解紛機制中,法院首先要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維護司法的公信力,這毋庸置疑。與此同時,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解紛責任,保障非訴與訴的順利銜接。在憲法規定的法院職能范圍內進行一定延伸,創新解紛方式,促進非訴解紛方式的發展,這不僅僅有助于修復破壞的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同時對于法院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功能定位也有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這樣才能使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更為順暢。通過訴訟和非訴兩種方式的共同作用,使矛盾得到徹底化解,也能達到對社會大眾法律宣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