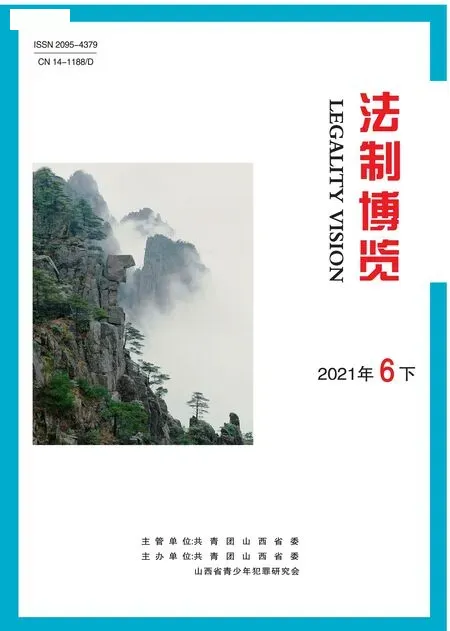我國法官職業保障的發展
馬旭杰
(山東政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我國法官職業保障的發展歷程
法官職業保障制度是指為實現法官的職業化而建立的有關法官權力、地位、收入、安全、教育、監督的一系列保障機制。我國早在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下稱《法官法》)中就對法官職業保障作出了相關規定,之后最高法于2002年、2005年、2017年發布的《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依法保障法官權利的若干規定》《人民法院落實<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的實施辦法》等文件,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于2016年聯合發布的《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都對法官的職業保障進行了落實[1]。2019年頒布的新《法官法》,專門設立“法官的職業保障”一章來調整和規范法官職業保障,使得我國法官職業保障在制度層面實現了質的跨越[2]。
二、我國法官職業保障制度的現狀與缺憾
(一)法官職業保障法律體系有待完善
我國涉及法官職業保障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數量雖在不斷增加,但是從其性質來看,除《法官法》外的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多為法院系統內部或行政機關的行政指令。這些指令雖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由于其自身法律位階的限制,其對法官職業的保障力度相對有限。其次,從內容上看,這些規范中大多數是準用性或委任性規則,而確定性規則較少,以《法官法》為例,在“法官的職業保障”一章的14個條文中,確定性規則僅有4條,其余均為準用性或委任性規則。這就使得法律規范過于籠統模糊,執行難度較大,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指引作用。
(二)法官職業壓力較大
“案多人少”問題一直較為嚴重,在法官員額制改革之后這一問題更加突出[3]。以L市D縣人民法院民一庭為例,該庭共有員額法官8人,2020年新收案件為2833件,與舊存案件總計達3230件,結案件數為2762件,人均結案件數有345件之多,其工作強度可見一斑。其原因在于:首先,員額制改革后,辦案法官人數銳減。以該院為例,在員額制改革前,該院法官人數為81人,改革后員額法官人數為53人,減少了28人。其次,法院的領導干部人數在入額法官中占據一定比例,而這些入額的領導干部由于黨務行政工作繁重,使得其工作重心難以放在案件審判上,這也造成實際辦案法官人數減少,從而增加了一線辦案人員的工作壓力。
(三)法官職業收入有待改善
首先,法官收入與其高負荷的工作強度不相匹配。以L市D縣人民法院為例,按照往年慣例,該院平均每年加班天數約為150天,去年受到疫情影響,該院加班天數達200余天。但由于受到財政經費的限制,無論加班時間長短,只能象征性地給予三五百元補貼,顯然資不對等。其次,我國法官收入未能與其他職業的收入拉開差距,無法體現法官的職業特性,難以維持其職業尊榮。仍以該縣法院為例,該院員額法官的收入主要包括職務工資、績效工資以及各項津貼三大板塊,年收入約為16萬元。而通過筆者對該縣中學教師、律師、個體經營戶、工人、從事銷售和普通崗位的企業員工、服務員,六個不同職業的30多名從業者的走訪來看,他們的平均綜合年收入分別約為15.5萬元、28萬元、19萬元、7.5萬元、20萬元與11萬元、6萬元。結合法官的工作特性和準入門檻,不難看出,法官收入在該地的競爭力處于劣勢。
(四)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存在漏洞
法官作為矛盾糾紛的裁判者,不可避免地會觸及案件當事人的利益,難免有些欠缺法律意識和道德理性的當事人會對法官進行報復。根據有關學者的不完全統計,2000-2019年間發生在我國的法官受害案件數在131件以上,平均每年法官受害案件至少在6起以上[4]。這充分地暴露出,當前我國在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上存在一定漏洞。首先,相較于法官職業保障制度相對健全的國家,我國對法官人身安全的保護區域和保護對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沒有將法官的近親屬納為保護對象,而且對法官的人身保護區域僅限于法院內特定區域與法官的住所,對法院周邊地區和其他法官經常出入的場所缺乏必要保護[5]。其次,受到人身傷害的法官獲得的物質救濟有限。盡管在法官傷害案件中會判處不法分子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但是這種人身損害賠償通常難以得到兌現,而由國家提供的救濟補償,例如工傷保險賠償等,又不足以維持法官與其整個家庭的原有生活水平。對此尷尬局面,我國目前并未形成有效途徑予以應對。
三、法官職業保障制度完善措施的探索
(一)立法先行,構建完備的法官職業保障法律制度
法者,治之端也。我國法官職業保障制度的完善,究其根本在于完善相關法律規范,發展其應盡的制度作用。因此,必須堅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統領,以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為契機,將新《法官法》中有關法官職業保障的原則性規定,結合實踐中已經被驗證且行之有效的機制,通過立法加以明確化,從而為法官職業保障的實施提供具體指引。同時,對當前涉及法官職業保障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進行必要的法律整理,統一有關概念、標準,將行政法規、部門意見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借鑒到立法中,提高其法律位階,形成完備的法官職業保障法律制度,從而發揮其規范作用。
(二)增強員額彈性,完善員額制度,緩解“案多人少”困局
法官員額制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對審判資源配置的優化與司法責任制的落實,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應因其當前出現了一些“不良反應”,就加以否定,而是應當吸收經驗,彌補不足。首先,增強員額法官的數量彈性,不以39%的員額比例一刀切。在確定員額數量時,引入大數據技術,對法院的收案數量與其轄區內發案因素進行統計和抓取,從而預測該區域在一定時間內的案件數量,然后根據預測推定員額法官的周期性數額,同時結合實際立案數量在一定區域內調配法官。其次,減少領導干部的入額比例,但對其福利待遇水平加以維持,以此保障行政管理人員能夠專注其職,員額法官能夠專注辦案。最后,明確員額法官入選和退出的標準和程序,細化法官的退出和入選考量措施,實現員額法官隊伍的精英化和專業化。
(三)立足實際,統籌兼顧提升法官的物質保障
首先,對法官的薪資進一步細化,既注重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因地制宜地提升入額法官和未入額人員的薪資水平,避免片面追求均衡和忽略地區消費水平差異的收入分配狀況出現。同時兼顧薪資漲幅,防止明升暗降的現象出現,使得法官的勞動付出與勞動所得相匹配。其次,借鑒法官物質保障發展完善國家的經驗,結合我國當前實踐,兼顧法官職業的特殊性和自治性,探索法院經費獨立和法官薪資獨立管理的方案,以切實保障法官的物質待遇,提升法官的職業尊榮和吸引力。
(四)消除潛在威脅,完善法官的人身保障措施
首先,對當前法官人身保障存在的漏洞,針對性地強化法院安保力量,探索可行的外聘安保人員方案,以緩解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人手不足的局面,形成兼顧院內院外區域、法官和法官近親屬的全方位保護。其次,加強法官對突發性人身傷害的應對技能培訓,通過定期培訓來提升法官對針對性威脅、危害的防范意識和防范技能。同時在法院內建立安全、有效的當事人——法官判決后溝通機制與場所,從而將當事人的憤懣通過可控、平緩的方式化解,在源頭上消除針對法官的人身安全危害。最后,探索建立法官人身保險制度,從而在法官人身損害發生后但損害賠償難以兌現時,提供有效快速的物質救濟[6]。
四、結語
法官職業保障制度的建設與完善作為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應有之義,關乎法官能否得以生存、能否更好地化解矛盾糾紛,更關乎法治目標的實現。因此,必須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通過各方共同努力來不斷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