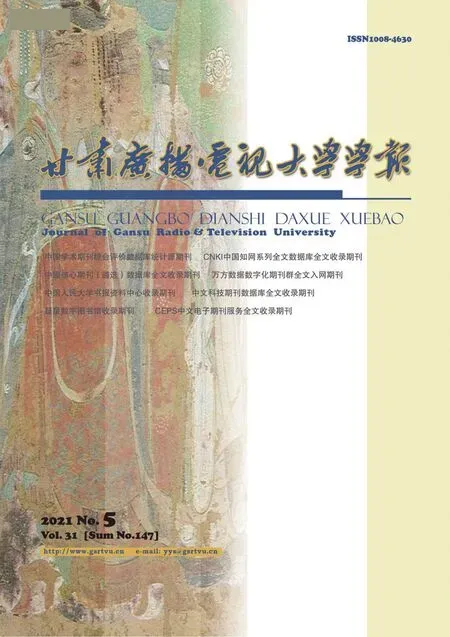許淵沖“中國學派文學翻譯理論”的建構與發展研究
姜 燕
(蘭州財經大學 外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20)
一、引言
在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的歷史上,許淵沖的翻譯理論不僅在翻譯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在整個人文社科研究領域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和參考價值。他的身上體現了中國翻譯研究者們“敢為天下先、務實進取、勇攀高峰”的精神,他的翻譯思想對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學翻譯理論、推動世界譯論的多元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他不僅為中國人文學者樹立了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榜樣,更為中國特色翻譯理論研究扛起了“走出去”的大旗。
許淵沖的翻譯理論自發軔之初發展至今,如亭亭玉立之小樹長成參天大樹,枝蔓繁茂,根系牢固,縱橫捭闔,圓潤通達。通過對許淵沖翻譯思想體系的建構與發展之研究,可以管窺我國建國以來,翻譯理論與實踐發展之脈絡與特色,或可以對我國譯學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參考意義。
二、許淵沖翻譯思想體系的建構歷程
許淵沖曾詼諧地比照但丁《神曲》的分法,將自己的翻譯生涯分為三個階段:“青春”(1921—1950)、“煉獄”(1951—1980)和“新生”(1980—)三部曲。“50年代以前,基本是學習繼承時期,同時注意前人的弱點,準備超越。80年代以前是改造時期,浪費了我生命中的黃金時代。1980年以后才開始我的超越時期,成了‘書銷中外百余本,詩譯英法唯一人’”[1]。依據許淵沖翻譯理論與實踐在發展與形成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所體現出的特點,其思想體系從發軔、成長,到蛻變與成熟,可以分為四個主要階段:理論萌發期、理論探索期、理論成熟期與理論超越期。
1.理論萌發期(1921—1950):發現自我
理論源于實踐,許淵沖先生的豐碩的理論成果與他早期的翻譯實踐的積累是分不開的。人生的第一個三十年里,許淵沖不斷地嘗試、探索、發現自我,確立了自己終身的愛好與奮斗目標。許淵沖自八歲開始學習英語,起初并不覺得有趣,但是在高二時背誦了30篇英文短文后,他的英語考試成績躍居全班第二。在上大學一年級時(1939年),許淵沖翻譯并發表了林徽因的詩《別丟掉》,開始了他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探索;大二時,他的歐洲文學史、俄文、法文考試成績都在班上名列前茅,許淵沖開始逐漸認識到自己學習中的長處與優勢。1941年,他為美國援華志愿航空隊擔任翻譯期間,將“三民主義”翻譯成“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并得到好評[2]325。此后直至1950年,許淵沖輾轉于國內外的知名大學,潛心研讀,為他日后的外語教學及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知識與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他所說,“50年代以前,基本是學習繼承時期,同時注意前人的弱點,準備超越”[1]。
2.理論探索期(1951年—1980年):實踐出真知
“80年代以前是改造時期,浪費了我生命中的黃金時代。”許淵沖人生的第二個三十年既是其經驗積累期,也是理論探索期。該時期的代表作有譯著《一切為了愛情》(1956)、《哥拉·布勒尼翁》(1958);專著《論法譯漢》;論文《意美、音美、形美》(1979)、《翻譯的標準》、《直譯與意譯》、《忠實與通順》、《翻譯中的矛盾論》等,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許淵沖翻譯理論探索期的理論概述
如果說理論萌發期是許淵沖翻譯實踐經驗的積累期和翻譯理論的孕育期,那么第二時期則是其依據實踐形成早期理論的關鍵時期。許淵沖該時期的翻譯理論更多關注翻譯的哲學思考與描述,如對翻譯的基礎、翻譯的方法與翻譯的原則的探討。
“三美論”則是許淵沖最能見諸翻譯實踐的理論,比如他對《詩經·邶風·擊鼓》中詩句的翻譯。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Meet or part,love or die.We’ve made oath,you and I.
Give me your hand I’ll hold!And live with me till old.[3]23-24
譯詩中首先實現了“形美”的再現,原詩中“死”與“生”、“契”與“闊”的對偶修辭形式被譯為“meet or part,love or die”;“與子……與子……”處理為“you and I,your hand I’ll hold”;其次,實現了音美再現。原詩“闊”與“說”的押韻處理為/a?/的尾韻(die與I),“手”與“老”的押韻處理為/??ld/(hold與old)的尾韻。最后,通過“meet or part,love or die”“made oath”“live with me till old”等表意形式生動地再現了原詩的意美。可以說是對“三美論”的經典演繹。
3.理論成熟期(1981年—1999年):碩果累累
在這第三個將近三十年的實踐與研究中,許淵沖筆耕不輟,憑著豐富的翻譯經驗,結合自身翻譯實踐的感悟與心得體悟,總結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論:①三美論:從“音美、意美、形美”三個角度討論文學翻譯[2]95;②三化論:即深化、淺化、等化。深化是指特殊化、具體化,譯文內容比原文內容更深刻了,而淺化正好相反,是指一般化、抽象化,把深奧難懂的原文化為淺顯易懂的譯文;等化是指形似的譯文,包括對等、等值、等效[2]104;③三之論:“知之、好之、樂之”[2]119;④藝術論:“從心所欲,不逾矩”是翻譯藝術的成熟境界[2]188;⑤創譯論:譯作可以和原作競賽,看譯者能否發揮譯語優勢,用譯語最好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作的內容;看新譯能否超越舊譯,甚至超越原作[4]5;⑥優勢論:翻譯中要充分認識不同語言的特點,發揮各自語言的優勢[4]5;⑦三似論:為了傳達詩詞的“意美、音美、形美”,譯文“意似、音似、形似”的程度是可以變更的[2]130;⑧競賽論: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競賽,文學翻譯更是兩種文化的競賽[4]5;總結起來就是“美化之藝術,創優似競賽”(如圖1所示)。此外,許淵沖還提出了譯詩六論:“譯者一也、譯者藝也、譯者異也、譯者依也、譯者怡也、譯者易也”[5];翻譯的哲學,即翻譯哲學的認識論、目的論和方法論問題[2]189;翻譯實踐論:即“文學翻譯理論來自文學翻譯實踐,又要受到實踐的檢驗。因此,沒有兩種文字互譯的實踐,不可能提出解決兩種文字互譯問題的理論。理論如與實踐不符,應該改變的是理論而不是實踐”[6];文學翻譯與翻譯文學的辯證關系等[2]198。在后來的著述中,許淵沖結合實踐經驗,不斷深化之前提出的諸多理論,如將“矛盾論”進一步解釋為:文學翻譯理論解決真與美的矛盾,或科學與藝術的矛盾。因此求真是文學翻譯的低標準,求美是文學翻譯的高標準。矛盾統一的結果是提高。這一系列翻譯實踐與理論不間斷的互動與探索,引發了學者們的熱烈討論,也為許淵沖最終提出膾炙人口的翻譯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期間他還出版了幾部譯著:《毛澤東詩詞(譯本)》(1981)、《蘇東坡詩詞新譯》(1982)。

圖1 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所包含的內容
許淵沖的諸多理論見諸翻譯實踐,如《小雅·采薇》中的詩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When I left here,willow sheds tear.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
Long,long the way;hard,hard the day;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My griefover flows,who knows,who knows?[3]107-108
原詩中的形美體現為對仗、押韻、重復等修辭手法的運用。對賬如“昔”與“今”,“往”與“來”,“楊柳”與“雨雪”相對。音美體現為押尾韻“矣”—“依”—“思”—“遲”—“饑”、“霏—悲”。許淵沖的譯文,不但實現了尾韻的再現,如“here-tear”“now-bough”“way-day”“overflows-knows”,還使用了英語獨有的頭韻的修辭手段,如“when”與“willow”;此外,“行道遲遲,載渴載饑”一句中的“遲遲”屬于漢語獨有的疊音現象,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詞法現象。而兩個“載”字屬于重復手法。許淵沖巧妙使用重復的手法,將二者合二為一翻譯成了“long,long the way,hard,hard the day”既再現了原文的疊音與重復,又達到了對仗、工整的效果。同時,將“雨雪霏霏”的意境之美再現為“snow bends the bough”的具體景象,將“載渴載饑”的意義深化為“hard,hard the day”的深層體悟,符合譯語讀者的審美期待與審美想象,實為“創優”的翻譯。
又如唐朝詩人杜牧的《過華清宮》的譯文。
過華清宮
The Summer Palace
長安回望繡成堆,
Viewed from afar,the hills paved with brocades in piles,
山頂千門次第開。
The palace doors on hilltops opened one by one.
一騎紅塵妃子笑,
A steed raising red dust won the fair mistress’smiles.
無人知是荔枝來。
How many steeds bringing her fruit died on the run.[3]38
對詩名中的“華清宮”,許淵沖沒有遵循慣常的地名“音譯”的方法,而是譯為“The Summer Palace”,會令譯語讀者聯想到頤和園,從而對“華清宮”的指代意義產生恰當的聯想。原詩中的地名“長安”在譯文中也被省略;同時,“妃子”只是被譯作“mistress”,“荔枝”只用“fruit”簡單帶過。作為原詩作者,這些具體的名詞具有指代和象征意義,即唐玄宗為博楊貴妃的“妃子一笑”,勞民傷財的昏庸統治,同時表達了對當時朝政的不滿與憤慨。但是作為譯語讀者,沒有相關的歷史文化背景是無法了解這些象征意義的。若是采用直譯加注的翻譯方法又容易破壞原詩的形式美,弱化原詩的意境與意義之美。因而作為譯者,若想不損失原詩風韻,又能使原作者的意圖躍然紙上,就需要打破其文字壁壘,為譯語讀者重建語境與意義。因此,最后一句“無人知是荔枝來”的翻譯沒有采用直譯,或者簡單的意義再現的方法。而是改用了“how many steeds bringing her fruit died on the run”的感嘆句式,一語道破原詩作者的深層意圖,實為點睛之筆。也再次印證了許淵沖提倡的“美化之藝術,創優似競賽”的翻譯理論。
在許淵沖的譯詩中,這樣的經典翻譯可謂比比皆是,不再贅述。需要了解到的是,許淵沖“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的建構,就是如此基于廣泛的翻譯實踐基礎之上,形成理論,又將理論反過來觀照到翻譯實踐,依此反復循環,螺旋式上升,從而不斷驗證、修正翻譯理論,使之發展成為日益成熟、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4.理論超越期(2000年—):從心所欲不逾矩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邁上了新臺階,許淵沖的翻譯理論也步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界,該時期是他的特色文論期。許淵沖將自己的理論體系化整合,他的理論探索不再局限于翻譯的方法、原則或是對譯作優劣的論述,視野更為宏大,立意更為深遠。從翻譯理論的哲學研究到翻譯理論的文化溯源,以及我國翻譯研究的歷史站位,無所不及。早在1999年,許淵沖就曾指出,“面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翻譯事業首先要克服自卑心理,譯學要敢為天下先”[7]4-9。他先后在《翻譯的藝術》《文學翻譯談》《文學與翻譯》《譯筆生花》四本書中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此外,他還從中國文化的視角,在《中國學派的古典詩詞翻譯理論》[8]、《再談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9]、《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化夢》[10]12-18、《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翻譯理論》[11]中,逐步深入地解讀了中國文學翻譯理論;討論了創建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的諸多議題。在之后的《怎樣的翻譯才能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12]、《新時代:中國詩詞如何走出去》[13]等論述中結合世界局勢及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身份轉變,高瞻遠矚地提出翻譯研究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進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許淵沖翻譯思想對中國特色翻譯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啟示
縱觀許淵沖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成長之路,不難看出其清晰的研究脈絡與特色。許淵沖翻譯思想帶給中國學者的更是一種立足于本國實際,永不止息的奮斗精神,一種始終如一的愛國熱情和中國氣魄。他的思想建構歷程體現出如下特點。
1.始終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活水源頭
許淵沖理論思想的萌發時期,西方的大量文學、歷史、政治類譯著正在中國遍地開花,是翻譯文學發展的高峰期。許淵沖在歐洲游學過程中接觸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如果以西方譯論為研究對象,對于其來說,可為近水樓臺,怕是早已“功成名就”了。但是,尋遍許淵沖所有翻譯論著,我們發現沒有一篇文章是專為討論西方譯論而作的,相反,許淵沖的所有理論著述都集中在對我國璀璨的傳統文論的翻譯討論中。他總結的“美化之藝術,創優似競賽”,雖只有十個字,卻字字珠璣,可見他對祖國的傳統文化的深厚興趣與熱忱。
2.始終以推動中國譯學發展為己任
近代中國,受盡霸凌的中國人處處自覺不如人,事事以西方為鑒。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作為一名翻譯工作者,許淵沖深知我國譯學博大精深,不輸于西方譯學分毫,立誓要改變這種“不如人的心理”,喚醒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與熱愛。他呼吁“首先就要克服自卑心理,譯學要敢為天下先”,他站在了文化與時代的前沿,將個人夢想與家國理想高度統一,將“中國學派翻譯理論”視為中國學者的共同“夢想”,扛起中國翻譯復興之大旗,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翻譯家的膽識與有擔當[7]4-9。許淵沖在翻譯實踐中提取理論,用理論反觀并指導實踐。他一路走來,且譯且行,提出的翻譯理論與主張無不引起學界的熱烈討論與關注。在贊譽之聲與質疑之音中,理越辨越明,“中國學派翻譯理論”已成為國內翻譯學界的共識,許淵沖的翻譯理論已經成為我國翻譯理論的風向標,尤其是在中國特色、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語境下,在文化話語權成為大國競爭之利器的前提之下。許淵沖的中國特色文學翻譯理論無疑為中國學者吹響了號角,為中國學者打了一劑強心針。
3.始終以戰略眼光創新發展理論
無論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將三民主義翻譯成“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還是跟隨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所撰的《翻譯中的十大關系》,以及后來從毛澤東思想中的實踐論、矛盾論提煉出的“翻譯中的實踐論與矛盾論”,及至今天新時代背景下對“中國文化夢”的注解:“我國要建設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我看來,這就是要實現中國文化夢。要實現中國文化夢,對于一個文學翻譯工作者來說,一方面要把外國優秀的文學作品譯成中文,另一方面又要把中國優秀的文學作品譯成外文,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輝燦爛。由此可見,文學翻譯對實現中國文化夢的重要性。”[10]12-18許淵沖的學術思想高瞻遠矚、立意深遠,始終將翻譯研究與文化傳統、社會發展緊密關聯,與民族命運關聯,使我國的翻譯研究成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從而在世界文化體系中,如常青藤一般,青春永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