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學與梁啟超啟蒙思想的塑造
張文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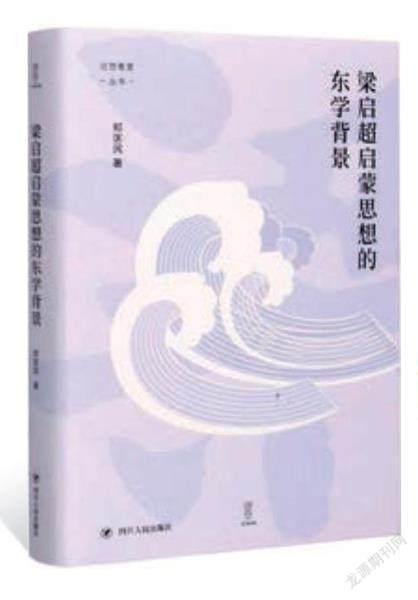
《梁啟超啟蒙思想的
東學背景》
鄭匡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2月
在梁啟超波瀾壯闊的一生中,1898年到1912年流亡日本的14年至關重要。這一時期梁啟超以日本思想界為跳板深入學習西方,深刻認識到啟蒙國人塑造“新民”的重要性,借助他“常帶感情”的妙筆推動了近代中國思想的轉型。要深入理解日本時期梁啟超的思想世界,必須弄清楚他從日本思想界所導入的歐美思想中接受了什么?又拒絕了什么?他讀過哪些書?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但難度很大的研究課題,要求研究者對梁啟超置身其中的中日兩國思想、政治背景有深入了解,對他最終攝取的西學有足夠的認識。
學界迄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國內學界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鄭匡民先生為代表,海外學界以日本京都學派狹間直樹先生為代表。他們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方法相對接近,均注重對西學、東學和梁啟超新學的文本異同比較,揭示中日兩國接受西學過程中的共性與區別,尤其是接受西學過程中基于各自國情的創造性。《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是鄭匡民先生的代表著作。
“半開化文明”國家的壓力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敗于“蕞爾三島”的日本,師夷長技30余年的洋務運動宣告失敗。中國思想界不得不將眼光投向學習西方更有成效的日本,日本化的西學即“東學”也進一步成為國人學習、效法的對象。梁啟超自不例外,他在康有為源出公羊學的春秋三世說指導下重新理解日本的崛起與列強環伺的世界。1898年9月26日,戊戌變法失敗后的梁啟超在日人幫助下逃上日艦大島號,開啟他14年的日本流亡生涯。以明治維新后日本為橋梁,借助“東學”深入探索、宣傳啟蒙救國之路,這14年在梁啟超一生中最為濃墨重彩。
在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等人影響下,深入理解中日兩國學習西方的共性、區別及成效,成為梁啟超維新事業的新起點。福澤諭吉等人的思想給予梁啟超莫大刺激。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認為人類歷史從野蠻到文明不斷發展,發展的過程有野蠻、半開化和文明三個階段。他認為在當時世界各國中,歐美諸國是文明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是半開化文明國家,非洲、澳大利亞等是野蠻國家。歐美國家對于亞洲國家而言,自然是應被效法的文明。不過,福澤諭吉文明觀同時也認為文明是無限的,歐美諸國的文明也未達到盡善盡美,也不應滿足于此。訴諸明治時期日本歷史,不得不承認這是日本人的真實心態,向歐美先進文明學習謀求與其并駕齊驅,乃至趕英超美越乎其上。
梁啟超心悅誠服地接受福澤諭吉的三階段論文明觀,視其為“世界人民所公認的進化公理”。梁啟超也從明治維新的成功實踐中看到巨大希望,他在《文野三界之別》一文中聲稱“吾中國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興矣”。可見梁啟超在接受福澤諭吉的文明三段論理論后趕超西洋文明的急切情緒。但是,梁啟超還是過于樂觀,他明顯忽略了福澤諭吉文明觀中的負面因素。福澤諭吉本人就曾明確認為“文明既有先進和落后,那么先進者自然就要壓制落后者,而落后者自然要被先進者所壓制”。鄭匡民先生就據此敏銳指出,福澤諭吉的這種理論客觀上已在為“先進文明”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行為辯護。
側重于“國權”的思想啟蒙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國人學習西方救國有三大步驟,即從學習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在典型意義上,這三個層次又分別對應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新文化運動。但是,較少有人知道的是,這三個層次的劃分源出于梁啟超1922年所寫《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這種劃分基本上是大體而言。梁啟超在日本14年活動是在反思戊戌變法的基礎上展開的。赴日之初,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呼吁日本政府營救光緒帝處處碰壁,戊戌變法本身也被日本朝野批判為操之過急。在此背景下,梁啟超開始借鏡明治日本思想界,在反思戊戌變法失敗的基礎上謀求救國之道,這就是思想啟蒙的形成與展開。
戊戌變法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梁啟超當時就已認識到日本變法“先其本”,中國變法“務其末”,兩者“事雖同,而效果乃大異”。到日本之后,在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思想家影響下,梁啟超對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區別的認識慢慢清晰。福澤諭吉將文明分為“內在文明”和“外在文明”,前者指衣食住行等外在的西洋化,后者指西洋區別于他處的內在“文明之精神”,兩者之中后者才是根本所在。梁啟超完全接受福澤諭吉的觀點,認為“外在文明”只是文明的形質層面、非本質,真正要學習西方就要學習其“文明之精神”。福澤諭吉主張攝取西洋文明的精神,通過思想啟蒙使每個日本國民能“獨立自尊”,從而達到日本救亡的目的。對此,梁啟超深以為然,按照“先改革人心,其次才能波及政令,最后方至有形之物”做法,在“新民”的口號下開始民眾啟蒙之路。對此,他在《新民說》中堅定地寫道:“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民眾啟蒙是明治時期思想家的共識。中村正直的思想也同樣推進了梁啟超的“新民”之路。和福澤諭吉等一致,中村正直也認為向西方學習的根本不是“政體之一新”,而是教育等問題上入手先使“人民一新”,在人的素質上縮小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做到人的現代化。
梁啟超對日本啟蒙思想并非照單全收。他就明顯拒絕中村正直所謂西洋文明精神的核心在基督教認識,凡此種種所在多有。但是,需要指出,當時不少關鍵問題無從論其優劣,只能從后世的眼光回顧反思。梁啟超流亡日本時期對“國權”和“民權”關系的認識是為關鍵,直接影響到他啟蒙思想的基調。這一問題不僅影響日本近代化的根本,也同樣是影響近代中國變動的關鍵,兩國在此問題上的異同深刻體現彼此的特質。大體以1903年梁啟超訪美為界,此前他更為注重“民權”,其后則側重“國權”。梁啟超在“國權”與“民權”問題上,主張中國完全效法日本,以“國權”為重。這當然并非是政治理想所致,而是近代化后發國家建立民族國家優先性的客觀需要。梁啟超清楚地認識到日本民權不及歐美,但他對日本能趕上歐美的民權水平充滿信心。這自然也表現了他的樂觀天性。
在啟蒙民眾的訴求中“國權”具有優先性,當然是近代中日兩國啟蒙思想的一致之處。套用福澤諭吉的說法,這是近代化過程中后發國家所面臨“現實中西洋”威脅,在學習“理念上西洋”過程中的自然選擇。但是,就“國權”壓倒“民權”的性質和結果而論,近代中日兩國卻根本不同。日本正是在“國家主義”等思想影響下走向“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對外侵略道路,但是同樣受到這些思想影響的近代中國卻主要以此思想作為捍衛國家生存的武器。從理想角度講,“國權”和“民權”應該是一致的,這是留給中日等學習西方卻結果有異國家的共同課題,其間的經驗和教訓都很重要。
“知人論世”與“論世知人”
鄭匡民先生留學日本八九年,他本人上佳的東學素養是本書成功的關鍵。這不僅體現在他對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全面而準確的把握,也體現在寫作此書的方法論。日本學界素以方法論見長,作者深諳其道受其影響,本書無疑給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帶來方法論的啟示。眾多周知,思想史的靈魂在于思辨,但思辨本身需要有效研究方法的支撐。本書在這一點上惠人良多,全書方法一致、一以貫之,首述日本相關學者身世、師承、生平和學術,后在文本比對中把握對梁啟超的具體影響。就對日本思想家本身思想的討論,則在漢學、蘭學進而直接對話西學的框架中論其思想脈絡,再從思想家與明治時期日本國情的深刻互動中把握彼此的異同。
對于本書的研究方法,耿云志先生在序言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論述:“盡量搜集到當時影響到梁啟超的日本思想家的著作和他們所刊行的雜志,認真解讀它們,然后再與梁氏發表的大量相關論著加以比較,從中發現構成梁氏思想的材料來源,及其在理解和表達方式上,在怎樣的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想家的影響。”這自然是高明而實用的思想史方法,其結果不僅是本書厘清和析出了梁啟超接受和宣傳西學中的日本成分,更讓讀者對近代面對西方強勢文明時中日兩國學習借鑒中的異同,尤其是日本轉手歐美的所謂“東學”在國人思想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多了幾分理解。
本書以“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為名恰如其分。“東學”作為日本化的西學確實在清末民初國人的思想世界中扮演過關鍵角色,但客觀講也只是近代中國轉型的思想資源之一。國人的確將日本視為學習西方的榜樣,但是隨著中日關系的惡化和國人對日本認識的加深,“東學”對于國人的吸引力和正面價值逐漸下降。梁啟超本人的態度就是明證。1915年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的行徑就讓梁啟超看到日本文明的迅速退化,其后“護國戰爭”中的經歷則更讓他從“覺日人之可愛可敬”到“驚訝發現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 “知人論世”“論世知人”,本書在充分肯定“東學”在梁啟超啟蒙思想塑造中所起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深刻反思乃至批判了“東學”的局限性。近代日本“東學”所包含的“極負面的思想因子”,其根本之處在于日本在亞洲的優越性和主導權思想最終導致侵略他國,也造成自身悲劇。如果將此書和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比照,我們似乎可以說,對國人而言作為思想“背景”的“東學”是客觀存在,但以此為基礎的“近代東亞文明”卻顯得渺茫。
(編輯: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