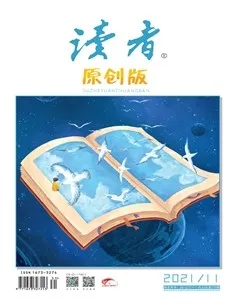鯽魚湯
張悅芊
一
蘭州倚居黃河,菜場里的魚販每天總有新鮮貨叫賣。我家有一半南方血統(tǒng),于是魚也成了童年回憶里的一道常見菜。
二
當時我們一家四口里包括一只名叫“丟丟”的貓。這只貓是寒冬臘月從自行車棚里跟著母親回家的,沒有做過絕育,沒用過豆腐貓砂,沒吃過凍干零食和進口貓糧,如今看來完全站在科學喂養(yǎng)的反面。但丟丟活得安然健康,平日里胃口很好,愛吃玉米和魚湯。于是,我媽下班帶回來的食材里,常常又加上“魚雜”。
魚肚、魚子,以及魚販們棄之不用、隨便丟在一旁的其他內(nèi)臟,都是丟丟的美食,于是與我媽相熟的魚販時常半賣半送地給我媽留一點。西北人常吃羊雜,但“魚雜”似乎鮮少聽過,大約是腥重肉少的緣故。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魚雜也從貓碗里被搬上了我們的餐桌。烹飪方式比白煮再精細些,加姜蔥紅燒,我倒是很喜歡——魚肚爽滑彈嫩,魚子飽滿味足,也算是平常人家豐富菜單的新鮮嘗試吧。
三
讀大學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了一道心頭好:烤魚。我人生的前18年從未見過或聽說過烤魚,而校門口的那家蜀味烤魚,極了解大學生愛辣、愛咸、食量大、愛花樣的特性,一整條草魚或花鰱烤得吱吱作響,再潑上一層青紅椒,最后可加別的蔬菜燜至入味。我印象最深的配菜是薯條,第一次見朋友點單時心中驚愕不已,總覺得薯條就該配上番茄醬,在窗明幾凈的肯德基里吃。但浸了紅辣魚湯的薯條外酥里嫩,入口的確驚艷。
多年后我和男友一起做咖喱食物,家里的土豆用完了,正當我愁眉苦臉時,男友得意揚揚地從冰箱里拿出凍薯條,咣咣地往高壓鍋里倒,出鍋后的口味和當年看似違和實則相得益彰的薯條辣魚湯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
我18歲離家,快10年了,燒菜的手藝仍然只可勉強稱為“制作食物”,食材加鹽弄熟,最多加一點兒生抽,就這樣搪塞過許多下定決心省錢做飯的時光。
我同齡的朋友大多如此,唯有一位同事不同,他看起來大大咧咧的,沒想到在廚房里卻極為細致,爆香、潑油、慢燉、提香,一步不落。
我在北京工作那年快活得很,和同樣剛畢業(yè)就入職的那些同事一起,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周末仍然有精神聚在一起做飯、唱歌。
有個周末,隔壁辦公室的同事剛搬了新家,邀請我們?nèi)プ隹汀S谑俏覀円恍形辶巳ゲ耸袌鲑I了食材,暖房兼娛樂。那天,“廚神”同事的風采在菜市場已經(jīng)初露端倪,他和攤主你來我往交換了幾句“黑話”,然后指揮我們選食材。
回到家,其他幾人炒了青菜、拍了黃瓜,很快完事,而他先是切了蔥姜絲、給魚劃了花刀,又翻出蒸鍋這種高級廚具,最后瀟灑地將花椒丟在油里燒出煙來,刺啦一聲,筆直地潑在水汽裊裊的清蒸魚上。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潑油”這種高級而復雜的烹飪工藝。對于那時的我,這種既需要掌控溫度又需要調(diào)味的危險手段離我太過遙遠,只覺得這位平日里看起來平平無奇的同事,在端出魚的剎那自帶光環(huán)。自那之后,我好像再也沒吃過那么好吃的魚了。
五
在美國讀博士時,我來到一所有很多中國人的學校,那里中餐極發(fā)達,學校旁有家川菜館,甚至令我來自成都的朋友都流連忘返。而這里的中國超市,也終于有了一些完整的食材——當然和國內(nèi)熙熙攘攘的菜市場還是不能比的。我踐行教條主義,嚴格復制了一些菜品,效果差強人意,又在多次重復中習得一些可以偷懶且結局不會太差的技巧,終于有膽量看一些復雜的食譜了。
有次看一個雙語菜譜時,我忽然發(fā)現(xiàn),美國常見的tilapia(羅非魚,又稱非洲鯽魚)竟然能夠替代可以熬出奶白色魚湯的鯽魚。于是第二天,我立刻在超市里買了兩條回家。這非洲鯽魚和我印象中細小窄長的鯽魚不同,但我仍然胸有成竹地將魚下鍋,小心地將雙面煎成金黃色,然后下料酒和蔥姜,再用滾燙的開水澆上去,下豆腐,大火煮開10分鐘,撒蔥花上桌。
湯雖然不是菜譜里牛奶般的濃白,但和我記憶里的鯽魚湯很像了。我小時候愛吃湯泡飯,正常吃飯吃不下半碗,兌了湯呼嚕呼嚕一大碗也不在話下。面前的魚比記憶里的結實,橫在鍋里呆頭呆腦,多少有點兒水土不服。
我依舊像小時候那樣把湯舀到米飯里,撇去蔥花,再盛豆腐。小時候,長輩說魚不能在湯里弄散,如今沒有人管我了,可以就著鍋對著一整條魚大快朵頤。胡椒灑多了,但魚肉剛剛好,沒有記憶里那么細嫩,但這場景忽然將我?guī)У绞畮啄昵跋∷善匠5耐盹垥r光——外公是湖南人,周末時家人吃飯,總會燒一大鍋魚湯,他和我媽總會有一個人說:“趕到洞庭湖里去了。”
轉眼外公已經(jīng)去世10年,而我已經(jīng)整整4年沒回家了。但那句調(diào)笑的話說了很多年也不倦,像是這碗差強人意的鯽魚湯,氤氳里看出一些家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