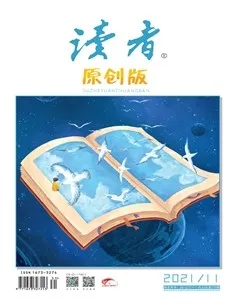說不盡飲食男女,吃不完家庭至味
小肥蝦
一
我的書架上有一排關(guān)于飲食的書籍,有些是隔段時間就要拿出來看一會兒的,《國宴與家宴》就是其中之一。
《國宴與家宴》的作者是作家王宣一,她的丈夫是作家兼出版人詹宏志。2015年,王宣一去世,詹宏志為了紀念愛妻,復刻了妻子做過的那些拿手菜。他說,我們本來把宣一的做菜本事視為理所當然,等到《國宴與家宴》定稿,我們才意識到這是一種文化傳承。王宣一秉承自己“認真請客”的傳統(tǒng),也有母親許聞龢的影響。
王宣一的廚藝來自她的母親。因為在報紙上發(fā)表了一篇懷念母親的長文,王宣一意外地接到了一連串的電話,這些電話的內(nèi)容不盡相同,有的是出版社打來的,問她要不要出版飲食相關(guān)的書籍;有的是讀者打來的,向她詢問某道菜品的詳細做法;更多的是老友打來的,向她“討食”,責怪她好久沒有做好吃的招待大家了。于是,王宣一又寫了幾篇關(guān)于母親、關(guān)于飲食以及逝去之味的文章,最終組成了這本《國宴與家宴》。
王宣一的母親許聞龢生于浙江海寧的名門世家,與金庸的查家、徐志摩的徐家都有世交或姻親關(guān)系。雄厚的家族背景和高等教育的熏陶,加上輾轉(zhuǎn)杭州、上海、臺北等城市,老太太見聞頗廣。許老太太在生活尤其是日常飲食上極為講究。王宣一自己也說,小時候會把干貝當零食吃,雖然這種“奢侈”讓朋友覺得不可思議,但這就是其家族的作風,比較“海派”。
老太太會吃,且擅長下廚,常年在家里招待許多親朋好友。賓客分為兩種,一種比較正式,氣氛較為嚴肅,兒女們把它稱為“國宴”;一種是親朋好友的年節(jié)聚會,比較輕松,兒女們稱其為“家宴”。
許聞龢老太太最拿手的是江浙菜,再細分一下,揚州菜、蘇州菜、無錫菜、杭州菜、上海菜、紹興菜和寧波菜都能挑出來幾道像樣的。從餐桌上一眼望去,醬油色是最主要的代表色,碗多、盤子多也是江浙菜的特點之一。
王宣一寫《國宴與家宴》,里面飽含對母親的思念,這種情緒的載體便是母親在世時精心制作的一桌桌家宴、一道道美味。王宣一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用最日常的方式懷念母親——下廚料理母親生前的拿手菜,圍坐在一張桌子前吃飯。
上一輩的味道飄散至今,也許某一天它會被淡忘,但是,關(guān)于家庭和母親的美好回憶,以及對傳統(tǒng)飲食和逝去味道的懷念一定會留傳下來。
二
2020年2月29日這天,我才看了李安導演的經(jīng)典電影《飲食男女》。
最初被開頭這段蒙太奇式的下廚場景吸引:
為了準備一頓豐盛的家庭晚宴,郎雄扮演的退休大廚老朱在廚房里忙活著。老朱先從裝滿清水的大缸里抓出來一條大魚,用一雙筷子插進魚的嘴里,便于去鱗片,去鱗后,把魚剖成長條,裹面,過油炸。
案板上也不耽誤。魷魚平鋪于砧板上,老朱細致地改花刀;雞胗要一點一點地去除外皮;紅椒滾刀切,皮和瓤完美分離;咸肉切片,泛著油光;蘿卜切片,轉(zhuǎn)而鋪平切絲。砧板與菜刀碰撞,噔噔噔,鏘鏘鏘,美妙的節(jié)奏在廚房上空縈繞。
肉塊過油炸后放入冰水里增其彈性,然后切片,放蒸籠里蒸糯之后反扣在盤子中央,澆芡汁,又是一道誘人的美味。
隨后,老朱走出房間,在雞圈里逮了兩只老母雞,一只用來燉湯,一只用來做茶香雞。老母雞煲的湯倒進茶香雞的容器里,茶葉油炸之后撒在雞肉表面,隔著屏幕,似乎也聞得到香味。
最后做主食。剁肉餡,當當作響;摔肉餡,噼里啪啦;搟面皮,圓潤柔和;包包子,百轉(zhuǎn)千回。
看得人心曠神怡,食欲倍增。
《禮記·禮運》里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整部電影由美味始,而劇中家庭的種種沖突也自美味徐徐展開。老父親做出來的一桌好菜只是擺設(shè)——不但女兒們個個食不知味,連老朱自己也喪失了味覺。家里人人都有自己的問題,感情上的、工作上的、為人處世上的,他們彼此之間也存著隔膜。
后來,三個女兒因為各自的事業(yè)或婚事要搬出去住,老朱也要和家珍的同學錦榮結(jié)婚,原來的家庭就此解體,分崩離析,連老宅也被賣掉。大姐和小妹選擇離去,二女兒家倩買下了老宅子,選擇了留守。
影片的最后,家倩和老朱父女倆吃了頓家倩親手做的晚宴,老朱的味覺恢復了,家倩也體會到父親的良苦用心,他們實現(xiàn)了彼此的理解與溝通。
三
“味不全不成席,人不齊不成宴”,說的是中國傳統(tǒng)大年三十的年夜飯。如今,我們身處時刻變化著的城市生活中,日常繁忙的工作與理想中悠閑的生活之間,矛盾不可調(diào)和。聚餐與組局的場合常有,一頓飯有時候不重要,快餐便可解決;有時候格外重要,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但吃得多了,吃得膩了,似乎在消解著人們對家宴的眷戀。
然而,因為有了鄉(xiāng)愁和親情,我們骨子里的傳統(tǒng)意識在不斷堅持和捍衛(wèi)著,舊時的烹飪和禮俗,并非是人們的某種陳舊認知或習慣。年節(jié)里的飯菜是我們揪心思念的味道,味全便成席,人齊則成宴,一句“回家吃飯”,拉回來的是我們漸行漸遠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