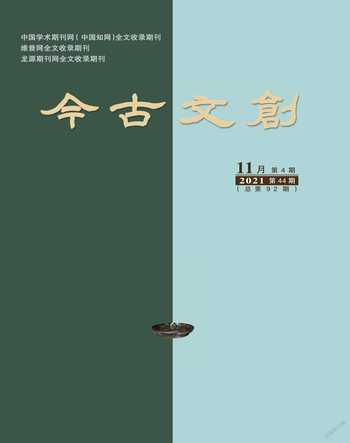“ 天地君親師 ”信仰的近代衍變
陳嫣然
【摘要】 “天地君親師”信仰在中國千年文化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到了近代,因封建王朝的終結,人們發現它與社會環境不再匹配,于是衍變出種種變體,分別以“國”“軍”“圣”填補以往核心“君”缺位后的空白。本文旨在厘清其近代所衍變的三種變體的出處與發展,為“天地君親師”在近代的創造性轉化奠定基礎。
【關鍵詞】 “天地君親師”;“天地國親師”;“天地軍親師”;“天地圣親師”
【中圖分類號】B22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44-0053-02
在中國千年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里,“天地君親師”信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為儒家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練,它是文化“大傳統”的一部分,作為民間信仰,它是文化“小傳統”的一部分,“一般地說,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一方面固然相互獨立,另一方面也不斷地相互交流。所以大傳統中的偉大思想或優美詩歌往往起于民間,而大傳統既形成之后也通過種種渠道再回到民間,并且在意義上發生種種始料不及的改變。” ①
自誕生到上升為文化“大傳統”的過程中,“天地君親師”信仰構建了一個以君權為核心的環環相扣的堅實結構,君王作為“天子”是天人交媾的產兒,生來與眾不同,他“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立于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 ②,受命于天、奉天承運在人間實行自己的統治。除此之外,君王兼具了“親”與“師”的功能,所謂“民之父母” ③,“母能生之,能事之;父能教之,能誨之。圣王曲僃之者也,能生之,能事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養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 ④故臣子、子民,人們要對君父、君師又忠又孝又敬。到明末清初時期,這一“大傳統”下沉至民間,成為家家戶戶祭拜的對象,即“小傳統”的一部分,并在雍正時期被上諭欽定,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從而推廣至全國各地。
到了近代,中國文化的“大傳統”因激變的國際局勢和社會環境而漸趨瓦解,“天地君親師”信仰也不可避免受到沖擊,其中最直觀的便是辛亥革命后,其核心“君”被推翻了。文化“大傳統”的變化對“小傳統”的影響具有一定的遲滯性,民間對于“天地君親師”的祭拜并沒有因為“大傳統”中對傳統文化普遍的反對與批判而完全消失,甚至直至今日民間依舊存在這種祭拜習俗,但人們意識到往日祭拜的“天地君親師”與當下的社會環境不再完全匹配,可同時人們并不想立即訴諸行動去改變一種延續數百年的傳統習俗,因此“天地君親師”在近代衍變出了不同的變體,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種。
一、“天地國親師”
在種種變體中,“天地國親師”出現最早、使用范圍最廣、持續時間最長。中國各地的地方志中都有關于當地祭祀、信仰、喪葬相關的內容,在提及祭拜“天地國親師”位傳統的地方志中往往會以“民國后”或是“辛亥革命后”這樣的字眼將這一變遷發生的時間一筆帶過,故很難確定這一變體產生的具體時間。徐梓先生在《“天地君親師”源流考》一文中提到了一種“天地國親師”表述始于湖北十堰的說法⑤,但徐梓先生的論文中沒有出示具體網址,加之十六年來網站信息的更迭,故筆者并未在十堰市人民政府網站(www.shiyan.gov.cn)上查詢到十六年前的《市情知識問答之市情概略》,而關于《十堰人良好的道德習俗傳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一文則在湖北日報(荊楚網)上尋得⑥,但原文旨在闡釋十堰人民的道德習俗傳統,并不是專業的學術文章,故沒有列出具體的證據。然而,若是將目光從兩湖地區放寬,《申報》1912年2月10日刊中有一則相關報道,稱蕪湖地區的中華民生黨在清朝既倒之際制“天地國親師”位發賣⑦。這一報道相較于各地方志中語焉不詳的“辛亥革命后”等字眼,有了更為確切的時間,且這一日期甚至早于《清帝退位詔書》的頒布,比前文的“湖北十堰說”更具可信度。
二、“天地軍親師”
與“天地國親師”幾乎同時期出現的還有“天地軍親師”這一變體。最早提出這一變體的是《時報》1912年3月4日刊《天地君親師改天地軍親師》一文,署名不羽鵬的作者答《時報》1912年2月28日刊《滑稽增減》一文所提出的“天地君親師”應當如何更改這一問題 ⑧,稱應將“天地君親師”改為“天地軍親師”,“音同而義且合也”,“軍者,竭盡畢生之力保衛國家。國之強也,軍力為之;其弱也,軍力致之。國強則民受其幸福,國弱則民得其慘禍”,與“天地”“親”“師”三者同為“神圣不可侵犯者” ⑨。不羽鵬提出這一方案十年后,《大公報天津版》1922年9月27日刊中《改良牌位》一文稱自己的友人將家中供奉的神位改為“天絲軍親師”位以免糟兵災 ⑩,此中涵義大為不同。上世紀二十年代四川省甘洛地區也有與之類似的案例,當地彝漢兩族因偶然事件產生糾紛,官府以土司辦事不力為由派遣地方軍閥劉濟南前去處理,劉濟南見斯補土司家勢衰弱,就以“改土歸流”之名實施民族壓迫,其措施就包含了當地彝人須供神位、貼對聯,并制“天地軍親師”“劉氏堂上歷代宗親”的神位賣給彝人?。“天地軍親師”這一變體的使用案例都有著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離開這種環境后便銷聲匿跡了。
三、“天地圣親師”
出現時間最晚的“天地圣親師”這一變體由“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先生提出,據蔡仁厚先生的解讀,它兼含天地、祖先、圣賢,“其中‘圣’字指歷代圣賢,‘親’字指歷代祖先,‘師’字指各行業之先師以及個人自己之業師。或曰師亦指萬世師表之孔子” ?。最早使用這一變體的記載是同為新儒家學者的蔡仁厚先生《生命的本質:天地、祖先、圣賢》一文?,蔡仁厚先生自己也在家中安置了祖先牌位和“天地圣親師”的神位,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郭齊勇也提倡在家中設置“天地圣親師”牌位?。提倡“天地圣親師”是一種力圖以“小傳統”的形式改變“大傳統”的嘗試,然而它的受眾基本局限于研究儒學的學者之間,至今推廣范圍不大。
四、結語
“天地君親師”信仰在近代衍變的過程是一個由“大傳統”下沉至“小傳統”的過程,千年封建統治終結后,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以新的政權填補這一空缺,然而人們并沒有選擇“總統”這一更為具體的“統治者”形象,這也是受到了“大傳統”變革的影響,近代以來,人們意識到國家不再是與自己無關的一家一姓之天下,一國之中可以無君,所謂民國總統,也是“不得謂之君,召之來則來,揮之去則去” ?,國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國家之盛衰強弱,必視國民之愛力為衡” ?,“天地國親師”這一變體體現的便是當時中國國民性的覺醒。
“天地軍親師”這一變體出現的時間與“天地國親師”接近,最早被提出的時候也蘊含了一部分“大傳統”的文化涵義。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大傳統”的色彩早已褪去,人們對“天地軍親師”位的祭拜與對五顯、蝗神的祭拜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生怕自己的不敬招來不幸,甚至在甘洛地區的案例中,地方軍閥自制牌位刻上自己的大名與勢力,妄圖做一個甘洛地區的土皇帝。“天地軍親師”這一變體在實際使用中既沒有教化作用,又不完全是出于祖先崇拜的目的,只是身處于亂世之中的民眾對于自身安全的期望。
“天地圣親師”這一變體出現的時候,五四運動都已過去近百年,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偏激地視作導致百年悲苦遭遇的誘因之一,不論是“大傳統”還是“小傳統”都遭到過激烈的抵制。新儒學學者們重拾這一信仰體系實則是站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反思近代對傳統文化的偏激觀念,并嘗試以祭拜“天地圣親師”位這樣的“小傳統”反哺百年來遭受沖擊的“大傳統”,在新的社會、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方式中創設一套新的禮儀規范,“使一家大小,朝夕之間都能和天地、祖先、圣賢、相感相親;使人的生命由小我轉化為大我;使只供住宿的家,轉化為與祖先同在,與天地圣賢同在的安身立命之所。使我們的家人、子弟、兒孫,隨時可以獲得天地生德的流注,獲得祖先恩澤的滋潤,獲得圣賢慧命的啟發” ?。
將“天地君親師”信仰作為封建迷信的符號全盤否定是有失偏頗的,雖然它在發展過程中構建了一套以君權為核心的無法反抗的體系,但其中包含的敬天地、愛祖國、孝父母、敬師長的內涵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精華,也是各個時代國人立足的文化坐標。另一方面,現代化的生活使人們逐漸放棄了許多傳統習俗,而正是這些習俗將中國文化的行為規范、道德倫理滲透進人們的生活,故當下可以嘗試對“天地君親師”信仰進行創造性轉化,例如使用“天地國親師”“天地圣親師”等變體,從這樣一種“小傳統”的形式出發,反哺我們備受沖擊的文化“大傳統”。
注釋:
①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馮國超主編:《春秋繁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李民、王健撰:《尚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④(漢)伏勝撰、(漢)鄭玄注:《尚書大傳》。
⑤徐梓:《“天地君親師”源流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⑥http://focus.cnhubei.com/local/200806/t342917.shtml
⑦《民生黨制造新牌》,《申報》第13403期。
⑧《滑稽增減》,《時報》第2764期。
⑨《天地君親師改天地軍親師》,《時報》第2769期。
⑩《改良牌位》,《大公報天津版》第33881期。
?嶺光電:《憶往昔 一個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蔡仁厚:《從儒家“以禮為體,以法為用”說到“儒家之禮與憲政”》,《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
??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學的反思與開展》,吉林出版社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
?郭齊勇:《道不遠人 郭齊勇說儒》,孔學堂書局2014年版。
?《說國民》,《國民報》第2期。
?《論國民不可無政治思想》,《東方雜志》第3卷第4期。
參考文獻:
[1]徐梓.“天地君親師”源流考[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2):99-106.
[2]蔡利民.天地君親師的命運 從文化哲學視野看中國人的終極關懷[M].北京:中國書店,2013.
[3]劉澤華.王權思想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03.
[4]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 儒學的反思與開展[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