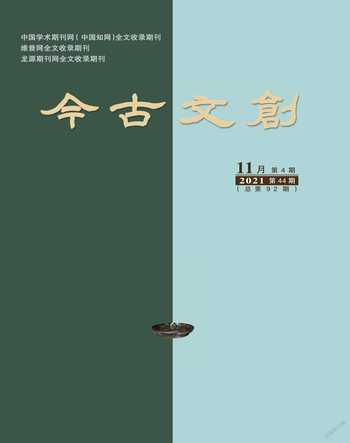短視頻中 “ 心形符號 ” 意義分析
任淑君 薛瀟換
【摘要】 新媒體時代,短視頻充斥著網絡世界,人們通常以點亮虛擬的心形符號表達贊賞之意,由此心形符號便成了人際交往的一種虛擬介質。“心形符號”作為一種非語言符號在信息傳播與人際交往中起著獨特的作用,霍爾在索緒爾與皮爾斯符號學基礎上對意義做出新的闡釋并探尋其背后規則建構與權力運行。
【關鍵詞】 符號;短視頻;意義;規則
【中圖分類號】G2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44-0105-02
符號學家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①人生活在符號世界中,創造并使用其作為意義表達的工具進行人際交往或闡釋世界。媒介不斷進行自我探索,并通過各種各樣的符號建構了一個與現實相對應的虛擬空間。在短視頻App中拍攝者與用戶以點贊形式進行著交流與互動。其中“心形符號”作為一種非語言符號在信息傳播與人際交往中起著獨特的作用。人們沉溺網絡符號空間并將這種認知與意念與現實生活相聯系,現實世界便趨于媒介主導構建的各種意義符號的虛擬仿真世界。
一、心形符號作為語言
符號作為虛擬網絡空間唯一能進行意義聯結的工具,承載了人際交流與傳播的功能。語言是一套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②,具有物理性質的存在物通過語言轉變為一個具有認知潛力,能夠推斷和解釋的符號。其中強調“當成”的意義,即物被放到主觀意愿中,接受者以此探索世界。那么語言也就囊括了話語、文學藝術作品、音樂、色彩、網絡符號等等。所以短視頻中心形符號首先是作為語言存在于虛擬網絡空間起到意義傳遞的作用。語言符號是在大腦中產生聯系的兩個要素之間的結合,或是概念和聽覺形象之間的結合。③隨后便以“能指”與“所指”來表述“概念”與“聽覺形象”。首先心形符號與大眾用戶頭腦中的“好、優秀”等概念相聯系,使抽象的情感依附于具體存在的事物,形成虛擬符號形象。其中符號任意性作為根本屬性貫穿整個過程,也就是“好、優秀”等概念并非心形符號的本質屬性,只是人為認定的,那么完全可以以正方形、圓形置于其中表示“好”的概念。當然也存在完全任意性與相對任意性,以任意性程度看符號的相對有理據性。④此過程中指出符號能指的并非所指本質,意義產生于其中的差異性,即贊賞與認同并不是心形符號的本質,而是在網絡大語境中,用戶點與不點之間顯示出贊賞的意義。
由于語言語意的編碼體系,即把語言當作一個信息傳遞的過程,由概念到接收解碼的循環模型本身存在不足。如果說索緒爾將語言看為“形式”(能指)和“對象”(所指)的一體兩面從而導致符號二元論的產生,那么皮爾斯在符號研究中則加入了解釋項表示對象的意義來探討語言的三元構成。對象真實存在與否,所指是真實的還是偽造的導致符號產生不同的解釋,并以此為動力推動整個符號意義產生,也成就了符號的無限衍意。由此作為語言的心形符號在被用戶接受時,絕大部分人理解其“點贊”的意義,但也正因為解釋項的差異,有理解就會存在誤解。這也就涉及了文化環境與網絡語境的問題。“文化”經常被定義為“共享的意義(概念圖)”,那么符號語言能夠傳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人們共享解釋語言符號的同一種方法。霍爾提出“共享信碼”的概念,即意義是由信碼建構的,作為是社會慣例的產物在文化中達成契約,從而完成自然人向社會人的轉化。那么,心形符號中承載“好”的概念事實上已在社會文化中被普遍認知,心形符號也作為共享信碼進入網絡語境中。
二、心形符號意指實踐
作為符號學接續研究者,霍爾將意義看作一個實踐的過程并將文化研究引入符號研究領域。在其著作《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中提出意義表征的“一種意指實踐”與“兩種表征構成”,以構成主義視角審視符號意義的生成,多主體在意義構建中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將世界與符號語言相聯系參與、完成意義構建。在表征構成中霍爾借鑒羅蘭巴特分析“能指”“所指”如何產生意義,借鑒福柯從語言轉向話語并關注其背后時代話語、知識與權力對“客觀事實”的構建。這就離不開媒介這一意義構建場與高速發展的傳播技術手段。
當把“點贊”整個過程行為看作一個新的能指時,其所指在于點亮心形符號行為中產生的各種現實意義,而此現實意義是生產者、應用者和接受者三方協商的結果。短視頻設計之初,軟件開發商基于大眾語境下人們普遍對心形象征“愛、喜歡”等因素的認知將此符號放置于視頻一側代表贊賞、欣賞等積極意義。“產品的意義不是簡單地由生產者送出和消費者收下的,而永遠是在使用中產生的” ⑤,霍爾借鑒馬克思生產理論對文化符號意義生產做出闡釋。當心形符號正式進入用戶視野,其意義也就開始發生飄移。符號真正的意義便在產品“使用”與“交換”中產生。在霍爾早期文化研究中提到文化傳播中符號“編碼”“解碼”理論,此前20世紀40年代美國文化傳播主要認同“信源—信息—接受者”這一模式,在此基礎之上霍爾將所有元素看作一個相關聯的整體從社會意義生產出發對此術語進行重新塑造,并將此看作一個話語意義生成的實踐過程,提出編碼與解碼沒有一致的必然性。符碼的意義總是在被不完全地傳達、中斷或扭曲。⑥這顯然受到巴特“可寫的文本”思想影響。由此為達到有效的交流與信息傳播中,心形符號最開始編入的贊賞意義的能指必須通過接受者解碼。當視頻創作者即符號使用者在作品中發出諸如點贊送紅包等對用戶做出點贊要求的信號時,心形符號自然被賦予新意義。此外用戶看到類似某些尷尬瞬間記錄的視頻時,點贊往往含有調侃之意。或好友間點贊以示關注之意時,原本的贊賞意義也蕩然無存。其實此符號本也就與贊賞無關,在復雜虛擬的網絡世界符號編碼解碼過程中意義被重新塑造與闡釋,故不再局限于創造或使用者想傳達的意義概念,而是更加清晰地表達現實的多樣化。整個過程中生產者、使用者和接受者三方都對該符號做出自己的意義構建,并在各種語境中進行著意義爭奪。但仍然受制于網絡語境與社會文化話語規則,如作為接受者自行賦予心形符號厭惡之意,并看到一個極其反感的視頻時,點亮愛心以表達內心的不悅。該作者在收到此信號時無法感知對方意圖,那么整個點亮行為也成了無效表達。
由此,軟件開發者基于網絡語境與大眾文化將心形符號編入贊賞意義,此虛擬的網絡符號又在實際應用者和使用者、接受者互動實踐中產生了普遍認同意義從而回歸大眾文化成為社會文化、網絡文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在下一次符號模仿與使用中也就開始了新生意義的循環和另一個意義建構的開始。在用意義來解釋文化時,也就不單是一種現象、一組事物而更多指向一個實踐的過程并看中語言實踐的結果。
三、心形符號背后的“點贊”效果
自新媒體進入生活之日起,就在不斷塑造甚至取代生活,仿佛新媒體就是生活,即在媒介化生存的時代現實生活與符號生活更加緊密相連。通過網絡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符號,人們愈加遠離真實的生活本身,也深陷社交媒體制造的符號景觀中。
一方面人們利用心形符號并發揮其訊息傳播功能,通過點贊行為尋找接觸媒介的認同需求和存在感表達,精準的算法推送促使點贊文化產生,從社會心理看簡單的點贊行為作為一種文化表達體現著人際交往。通過表達“認可”維系社會關系,點贊也成為一種文化氛圍。其中也不乏大量“點贊狂魔”,將其行為看作使命或是無意識地跟風展現自我存在價值。由于雙方信息不對稱性以及符號應用中實際意義的產生,無意識“點贊”也帶來虛偽交流。點亮行為在交流上也成了無意義表達,快餐式的視頻與植入式的心形符號和真正的人際交往產生的效果也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符號潛在影響人的思考與選擇。在對世界進行符號化表征時,實際上是在符號層面對世界進行了一種人為切分,把一個視頻作品判定為“好”與“壞”時,無非是在接受者一方對其進行不同角度審視,那么其判定標準往往與“點贊”量有直接關系。于接受者而言,往往對點贊量高的視頻產生一種天然地好感從而更容易對視頻內容產生認同。例如網絡輿情作為符號編織的結果,輿論的爆發往往充斥著符號的狂歡,空洞的點贊與表面上簡單的關注引起圍觀效果也正是無限量堆積帶來的巨大傳播力量。同時,流量帶來的關注焦點問題重新定義了事物的價值。這也就為符號的操縱提供了可能性。以往傳統微視頻或微電影流通中常以經典標準來判定,現如今網絡短視頻只要有足夠多的點贊數量,能夠引流,就認為其具有了文化意義和經濟價值。這也帶動了諸多社會現象,如 “網紅”“網紅城市”“網紅店”“網紅制作”等等。“網紅”也從一開始針對人發展到生活的衣食住行,從而支撐起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網紅經濟。此外資本的介入也使得點贊帶來了巨大收益,在某種意義上擁有點亮愛心的行為也成了使用者對用戶以及流量帶來的話語權的爭奪。
在網絡符號構建的虛擬世界中,“網絡空間”也成為突破人心理防線的符號化世界,在刷視頻點亮心形符號之際也關注其符號意義生成與構建問題。看到“心形符號”與“點贊”行為在充當大眾傳媒間人際交往媒介的同時,理應保持冷靜思考以警惕大數據大流量的信息同化。
注釋:
①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②③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5頁,第66頁。
④張紹杰:《語言符號任意性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⑤陳靜:《論斯圖亞特·霍爾的文化“表征”理論及其理論實踐》,廣西師范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第46-47頁。
⑥武桂杰:《霍爾與文化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頁。
作者簡介:
任淑君,第一作者,女,漢族,河北滄州人, 碩士,河北師范大學,藝術學理論專業,研究方向:藝術創意與傳播。
薛瀟換,女,漢族,河北邯鄲人,碩士,河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專業,研究方向:應用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