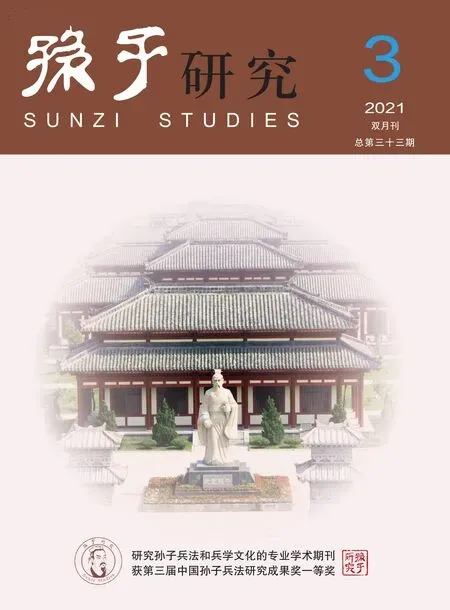田單復國后的軍事實踐及其軍事思想
趙 玲
田單,戰國末期齊國臨淄人,齊閔王時曾在臨淄擔任市掾,是市場管理機構中的一般屬官,當時并不為人所知,也沒有什么影響。即墨之戰和田單復國,使田單一舉聞名。但由于齊國國內政治生態的惡化,田單在齊國并沒有過多的政治、軍事活動,可知的主要有攻狄、破聊城和援趙三事。田單雖不像孫武、孫臏、吳子那樣有兵學著作流傳于世,但依據文獻記載,仍可對田單軍事思想進行梳理。由于田單并非職業軍人,是因特殊情況而被推上了軍事舞臺,因此其軍事思想有獨自的特征。
一、田單復國及復國后的政治生態
齊國在宣王、閔王時期,政治混亂和腐敗日漸嚴重。而這時,合縱、連橫的形勢十分復雜,各國彼此間因利益的需要時合時分。本來,在蘇秦的游說下,齊、燕、趙、韓、魏五國達成了合縱攻秦的共識,但是,齊國又出兵伐宋,滅掉宋國。這時,合縱五國便放棄攻秦,反而與齊爭奪宋國的土地,并謀劃聯秦伐齊,在燕將樂毅的努力下,最終達成了聯合攻齊的意向。
齊閔王十七年(前284),燕、趙、秦、魏、韓五國聯合攻齊,齊舉國相拒,戰于濟西,齊軍大敗。五國攻齊取得了重大勝利。五國破齊后,秦、韓軍隊回國,魏軍忙于爭奪宋地,趙軍忙于收取河間,燕軍則在樂毅的統帥下,準備一舉攻滅齊國。樂毅認為:“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1〕樂毅不失時機,率燕軍長驅入齊,直逼齊都臨淄。齊閔王急忙出逃,幾經轉折,最后逃到莒(今山東莒縣),才得以在莒茍延殘喘。
燕軍聽說齊王在莒,舉兵攻莒。由于莒地人的頑強抵抗,數攻不下。燕軍轉攻即墨,即墨大夫出兵應戰,戰敗而死。城中無主,一片混亂,人們認為田單能率族人從安平順利抵達即墨,可能通曉兵法,便共同推舉田單為將軍,以拒燕軍。田單采取堅壁清野的辦法,據城死守。燕軍也數次攻城,皆無功而退。在田單的主持下,即墨成為齊國軍民抵御燕軍的一個中心。
燕軍久攻即墨、莒不下,形成對峙狀態。這時兩國都發生了大的政治波動。
齊閔王得以據莒,是受到楚國的援助。可楚將淖齒為齊相后,自恃功高,不把齊王放在眼里,甚至殺齊王于鼓里。淖齒殺閔王,激起了齊人的憤怒,閔王之臣王孫賈招集眾人殺死了淖齒,并擁立齊閔王的兒子法章為王,是為齊襄王。齊襄王即位,給齊國帶來了復國的希望。這時燕國也發生了政治變動。燕昭王卒后, 燕惠王立。惠王做太子時與樂毅發生過矛盾,他即位后對樂毅擁兵在外十分不安。燕惠王擔心樂毅在外擁兵自重,便使騎劫替代樂毅為攻齊的主帥。騎劫為了樹立威信,不斷改變樂毅對齊作戰的方針,對齊國降兵濫施劓刑,還挖掘城外的墳墓,焚燒尸體。即墨守城軍民見燕軍挖掘齊人的墳墓。無不痛哭流涕,悲憤交加,紛紛要求出城與燕軍決一死戰。
田單見人心可鼓,與燕軍決戰的時機已經到來,遂積極進行戰前準備。“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史記·田單列傳》)又讓青年士卒埋伏起來,讓老弱女子登城守衛,以麻痹敵人。最終采取“火牛陣”的方式進攻燕軍,只見“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史記·田單列傳》)。燕軍驚慌失措,急忙退軍。燕軍主帥騎劫也被亂軍所殺,齊軍大獲全勝。
田單乘勝追擊,迅速收復了大多數齊國故地,田單又將齊襄王從莒地迎接到臨淄,齊襄王封田單為安平君并擔任齊相,以褒獎其復國之功。
田單功高,引起了齊襄王的猜忌。有一次,田單護送齊襄王過淄水,有一位老人不勝水寒,上岸后坐在沙灘上不能行走。田單讓人從隨行車上拿件衣服給老人,車上沒有,田單就脫下自己的裘皮大衣披在老人身上。齊襄王認為田單在收買人心,很不高興,不由自言自語地說:“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后之。”齊襄王見左右只有一個叫貫珠的人,問貫珠說:“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齊襄王又說:“女以為何若。”貫珠擔心齊襄王對田單的誤會導致君臣不和,靈機一動,向齊襄王說:“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矣。”齊襄王認為言之有理,壓抑住心中的不樂,向田單賜酒,并稱贊他做得對。數日后,貫珠又對齊襄王說:“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谷之。”齊襄王依計而行,又派人到各地探聽這件事的反映,老百姓都說:“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戰國策·齊策六》)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齊襄王對田單存有戒心,并有意樹立自己的威信,抑制田單的地位。
當時有一位叫貂勃的人四處宣揚田單是小人,田單聽說后,設酒宴請貂勃說:“單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見譽于朝。”貂勃說:“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斗,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戰國策·齊策六》)第二天,田單便將貂勃推薦給齊襄王。齊襄王身邊有九位寵信的大臣,他們嫉妒田單功高,讒毀田單說:“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于民,外懷戎狄,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杰,其志欲有為也,愿王之察之!”(《戰國策·齊策六》)齊襄王是一位沒主見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君主地位,于次日召見田單,田單不知何故,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罪。五天后,齊襄王又表示田單無罪過,召見田單只是為了顯示他和田單之間的君臣之禮罷了。
自此以后,齊襄王處處以君主自居,高高在上。有一次,齊襄王在眾臣面前直呼田單的名字。貂勃說這是“亡國之言”,并對齊襄王說:“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辟,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于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于道,歸之于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戰國策·齊策六》)齊襄王始恍然大悟,殺掉九位讒毀田單的大臣,益封田單“夜邑萬戶”〔2〕。但是,田單并未得到重用,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逐漸銷聲匿跡了。
二、田單復國后的軍事活動
田單復國后,受到齊襄王的猜忌,在齊國的政治、軍事活動并不多,可知的主要有攻狄、破聊城和援趙三事。
(一)攻狄。狄,地名,春秋時長狄所居,故名,古城在今天山東高青。田單攻狄見于《戰國策·齊策六》。田單攻狄前,將自己的打算告訴了魯仲連。魯仲連是齊國名士,他對田單說:“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不以為然,說:“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說罷,揚長而去。田單攻狄,果然三個月未能克城。齊國國內有童謠諷刺田單說:“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大意是:“頭戴高高的帽子,手持上等的寶劍,連續攻狄三月不下,士卒的尸骨卻壘成山丘一樣高。”田單十分懼怕,又向魯仲連請教說:“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說:“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能勝者也。”(《戰國策·齊策六》)田單對魯仲連的分析十分敬佩,于次日,親臨前線,勉勵士卒,擊鼓攻敵。齊國士兵見田單冒著生命危險指揮攻城,人人自奮,一舉攻下狄城。
(二)破聊城。事見《史記·魯仲連列傳》和《戰國策·齊策六》。聊城古城在今山東聊城市西,位于齊、燕的交界處。有一位燕國將領率軍攻下齊聊城,卻遭到國內權臣的讒毀,燕將不敢歸國,便擁城自居。田單攻聊城,一年多未能攻下,折將損兵,十分嚴重。于是,魯仲連給聊城守將寫了一封信,綁在箭頭上,射到聊城內。信中說:“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期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后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愿公詳計而無與俗同。……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于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于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愿公詳計而審處一焉。”(《史記·魯仲連列傳》)燕將看到魯仲連的信,連哭三天,猶豫不能決。欲回歸燕國,又怕燕王不諒解而被誅。欲投降齊國,又覺得從前殺死眾多齊人不為齊人諒解而受辱,喟然而嘆說:“與刃刃我,寧自刃。”(《史記·魯仲連列傳》)說畢,自殺身亡。燕將死后,城中無主,亂成一團,田單乘勢攻破聊城。
(三)援趙。事見《史記·趙世家》。齊襄王十九年(前265),趙孝成王即位。秦伐趙,連破三城。當時,趙王新立,惠文后用事,在秦王的猛烈攻擊下,趙向齊王求救。齊提出以惠文后的小兒子長安君為人質,才肯出兵。太后疼愛長安君,未答應齊國的要求。群臣強諫,太后竟大發雷霆,說:“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史記·趙世家》)最后在左師觸龍的勸說下,惠文后終于以大局為重,同意長安君入齊為質。
長安君入質于齊,趙舉國上下產生了很大的震動,趙國名士子義聽說惠文后讓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冒著生命危險入質于齊,對眾人說:“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于予乎?”(《史記·趙世家》)長安君入質于齊后,齊國果然派田單援趙。秦軍見齊、趙聯合,遂退軍。
不久,燕封宋人榮蚠為高陽君,率軍攻趙。趙孝成王割濟東三城給齊國,請齊國派田單為將救趙。趙奢反對請田單救趙,并主動請求率軍攻燕,他對平原君說:“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與敵國戰,復軍殺將之所取,割地與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戰國策·趙策四》)趙奢還認為田單不會真心實意救趙,因為一個強大的趙國是齊國稱霸的障礙,如果將趙國的軍隊交由田單指揮,后果不堪設想。但是,趙奢的意見未被采納。田單率趙軍攻破燕的中陽。又攻韓,奪取注人城。孝成王二年(前264),惠文后卒,田單為趙相。
田單相趙后,對趙國名將趙奢說:“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挽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戰國策·趙策三》)趙奢不同意田單的意見,他認為形勢今古不同,用兵數量自然不能一樣,他說:“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兩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戰國策·趙策三》)田單喟然而嘆,說自己沒有考慮到這些。
田單、趙奢論兵的時間,《戰國策·趙策三》記為趙惠文王三十年。據《史記·趙世家》,田單相趙在趙孝成王二年(前264)。故《戰國策》的時間有誤,田、趙論兵當在趙孝成王二年以后。
三、田單的軍事思想
田單不像孫武、孫臏、吳子那樣有兵學著作流傳于世,因此對其軍事思想的研究只能依據《史記》《戰國策》《資治通鑒》等古籍對田單事跡的記述來梳理。田單雖是齊國名將,但畢竟不是職業軍人,是在特殊情況下才被推上軍事指揮舞臺的,因此其軍事思想有獨自的特征。
其一,注重心理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樂毅攻齊,所以能順利攻取七十余城,除軍事力量強大外,他采取的籠絡齊國民心的措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前,齊閔王為政苛暴,“百姓不附”“大臣不親”(《戰國策·齊策六》)。樂毅攻破臨淄后,為了在思想上征服齊人,“修整燕軍,禁止侵略,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3〕,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面對這種局面,田單只有從心理上激起齊人復國的強烈意識,才有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恰巧,騎劫取代樂毅為將后,為了樹立威信,改變了樂毅對齊作戰的方針,對齊國降兵濫施劓刑,還挖掘城外的墳墓,焚燒尸體。田單為了提高士氣和迷惑燕軍,散布謠言說齊軍最害怕燕軍把割去鼻子的齊國俘虜放在前排與之作戰,騎劫聽說后,果然中計,將割去鼻子的齊國俘虜放在軍陣的前排。即墨城內的守軍看到俘虜都被割去鼻子,決心誓死守城,以免被俘,士氣大大提高了。田單利用燕人割俘虜鼻子的暴行,打消了齊軍投降的心理意念。利用燕人挖掘齊人墳墓的行為,激起了齊國軍民對燕軍的仇恨。使即墨軍民在思想上空前一致,形成了強烈的反燕復國意識,從而加強了守城軍民的凝聚力。
騎劫替代樂毅為將后,心高意驕,田單又以假降為手段,使燕軍從心理上放松了對即墨的警惕和戒備,只等著入城受降。最后,面對即墨軍民的突然襲擊,燕軍措手不及,倉皇敗退。
其二,重視戰前準備和積極利用客觀條件。“戰備”為歷代兵家所重視,田單在戰前準備方面有其獨到的一面。在燕軍攻齊時,田單及其族人逃到安平(今山東青州境內)。安平位于臨淄東九十里,田單認為此地會很快被燕軍攻占,便讓族人做好逃離的準備,將車軸的兩端鋸短,并包裹上鐵皮,以備車輛相行時車軸相碰撞。果不出田單所料,當燕軍攻破安平城時,齊國臣民紛紛而逃,道路上擁滿了拉人載貨的車輛,車軸相互碰撞,許多車子的車軸被撞壞,車子的主人因車壞而被燕軍俘虜,由于田單家族早有準備,車子未受到損傷,才得以逃到即墨。
在即墨之戰前,田單積極訓練士卒,儲備糧食,加強城防,他還親自參加修城墻,他的妻妾也編制在隊伍之間,積極進行戰前準備,“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史記·田單列傳》)。他又讓青年士卒埋伏起來,讓老弱女子登城守衛,以麻痹敵人。與此同時,田單遣使與燕軍約期假裝投降。為了進一步麻痹敵人,又讓城中富豪給燕軍送去金銀珠寶,假裝請他們入城受降時保護其家中老小及資產。燕軍將領大喜,由此放松了對即墨的警惕。
當時即墨城內部隊不足,田單充分利用客觀條件,讓老弱女子登城守衛,以麻痹敵人。即墨城長期為燕軍所困,物資極端貧乏,百姓在避難時房產、物資都不好帶,只好將各自的耕牛也帶到城內,田單便在耕牛上做文章,大擺火牛陣,一舉擊敗燕軍。
其三,以奇制勝。司馬遷在評價田單時說:“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后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史記·田單列傳》)司馬遷所以稱田單“以奇勝”,主要是指他出人不意,以火牛陣破敵。將動物用于戰爭,并非始于田單。魯定公四年(前506),吳、楚戰于柏舉,楚軍敗,“(楚)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左傳·定公四年》)。杜預注曰:“燒火燧系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楚王將火把縛在大象的尾巴上,使其沖入吳軍,以抵擋吳軍的追擊。晉文公五年(前632)春,晉、楚戰于城濮,晉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即胥臣在馬身上蒙上虎皮出擊楚軍。田單的火牛陣,是將楚王的“執燧象”和晉將的“蒙馬以虎皮”結合起來,并進一步發展。
田單在即墨城內征集了一千多頭牛,給牛裹上畫有五顏六色圖案的棉布,在牛角上綁扎上尖刀,在牛尾捆綁上灌了油脂的蘆葦,又在城墻上挖掘數十個洞口,夜幕降臨后,將牛從洞口內趕出,五千名士兵緊隨其后。點燃牛尾上的蘆葦,牛受驚嚇,拼命向前方的燕軍軍營奔跑。燕軍毫無準備,只見“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史記·田單列傳》)跟在牛群后面的齊軍,奮勇殺敵。即墨城中戰鼓震天,老弱婦女也齊聲吶喊,以助軍威。燕軍驚慌失措,急忙退軍。燕軍主帥騎劫也被亂軍所殺,齊軍大獲全勝。
在千余頭牛身上“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史記·田單列傳》)。田單在前人用動物作戰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發展,大擺火牛陣,是以“奇”制勝的典范。
【注釋】
〔1〕《資治通鑒》四《周紀四》,周赧王三十一年。
〔2〕夜邑,今山東萊州。
〔3〕《資治通鑒》四《周紀四》,周赧王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