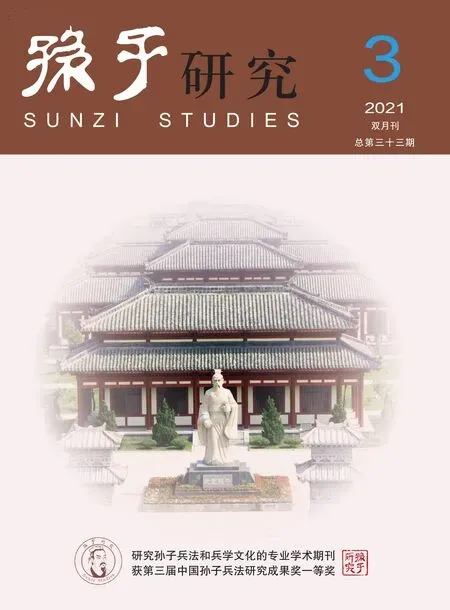論《孫子兵法》的正確閱讀
胡曉文
唐代杜牧在《注孫子序》中寫道:“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幾千載,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dāng)。猶印圈模刻,一無差跌。”哪怕是當(dāng)代社會(huì),《孫子兵法》也深為無數(shù)軍事家所膜拜。
一、戰(zhàn)略之讀大于戰(zhàn)術(shù)之讀
自古戰(zhàn)爭(zhēng)之思想便有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shù)的存在,單從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角度分析,眾多軍事家皆認(rèn)為《孫子兵法》是一部戰(zhàn)略兵書。《孫子兵法》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認(rèn)識(shí)是以“謀”作為定天下的最佳方式,崇尚“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謀攻篇》)的觀點(diǎn)。它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考慮充滿著理性化,講究“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fù);不知彼不知己,每戰(zhàn)必?cái) 保ā秾O子兵法·謀攻篇》);“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zhàn),勝之半也”(《孫子兵法·地形篇》)。強(qiáng)調(diào)“夫未戰(zhàn)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zhàn)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fù)見矣”(《孫子兵法·始計(jì)篇》)。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更是保持謹(jǐn)慎的態(tài)度,“兵者,國(guó)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始計(jì)篇》),“非利不動(dòng),非得不用,非危不戰(zhàn)。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zhàn);合于利而動(dòng),不合于利而止” (《孫子兵法·火攻篇》)。相對(duì)于戰(zhàn)術(shù)而言,這些謹(jǐn)慎、理性的兵家觀點(diǎn)完美演繹著中國(guó)兵家戰(zhàn)略文化的精髓,講究廟堂之算多于戰(zhàn)場(chǎng)之算。深入了解《孫子兵法》,更能明白《孫子兵法》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認(rèn)識(shí)不僅僅是戰(zhàn)爭(zhēng),更有天、地、人三者的考慮。通觀《孫子兵法》十三篇,可以概括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一至三篇構(gòu)成的戰(zhàn)略運(yùn)籌;第二部分是由四至六篇構(gòu)成的作戰(zhàn)指揮;第三部分是由七至九篇構(gòu)成的戰(zhàn)場(chǎng)機(jī)變;第四部分是由十至十一篇構(gòu)成的軍事地理;第五部分是由十二至十三篇構(gòu)成的特殊戰(zhàn)法。這五大部分可以說構(gòu)成了一個(gè)完整的戰(zhàn)場(chǎng),戰(zhàn)場(chǎng)中出現(xiàn)的因素?zé)o論是常規(guī)還是特殊,都被包含在內(nèi)。所以明代兵書《投筆膚談》就認(rèn)為:“《七書》之中,唯《孫子》純粹,書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備。”
由此可見,從戰(zhàn)略角度去讀更易理解和接受其中的觀點(diǎn),也更容易讀出其中的韻味,讀出中華兵學(xué)的博大精深。
二、哲學(xué)之讀勝于計(jì)謀之讀
《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充滿著系統(tǒng)理論的哲學(xué)體系:唯物主義和辯證方法。孫子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考量是“故經(jīng)之以五事,校之以計(jì),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孫子兵法·始計(jì)篇》)。春秋時(shí)期的戰(zhàn)爭(zhēng)主要是一種以“天命觀指導(dǎo)戰(zhàn)爭(zhēng)為中心”的軍事思想,那個(gè)時(shí)代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往往都是以“違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為號(hào)召,以占卜或神明的旨意驅(qū)使士兵戰(zhàn)斗。而孫子所說的“天”并非所謂的神明或者天神,而是指:“天者,陰陽,寒暑,時(shí)制也。” (《孫子兵法·始計(jì)篇》)孫武認(rèn)為天氣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勝負(fù)起著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孫武除了以氣候的客觀因素代替了之前的“神明”主觀因素外,還認(rèn)為地形也是戰(zhàn)爭(zhēng)中勝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光是對(duì)于地形的描述,孫武便以“地形篇”和“九地篇”兩篇來進(jìn)行總結(jié)和闡述,根據(jù)地形的情況來做出謀劃的判斷,以地形的判斷來決定投入兵力的數(shù)量,也因地形來決定勝敗的重要條件。戰(zhàn)爭(zhēng)的物資消耗也在孫武的考量?jī)?nèi),《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nèi)外之費(fèi),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fèi)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 (《孫子兵法·作戰(zhàn)篇》)由此可見,《孫子兵法》內(nèi)的戰(zhàn)爭(zhēng)理論是充滿唯物性的,是不以神明為主的,但里面的唯物主義也不是狹隘的,也注重人為因素的主觀能動(dòng)性,在《用間篇》中提道:“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yàn)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在這里,孫武認(rèn)為了解敵情是戰(zhàn)爭(zhēng)勝利的重要因素,而了解敵情必不可缺的條件就是人為因素。
孫武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認(rèn)識(shí)不僅僅體現(xiàn)在客觀的因素,還有不斷運(yùn)動(dòng)變化的辯證思維。在《孫子兵法·兵勢(shì)篇》中提道:“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孫武認(rèn)為戰(zhàn)爭(zhēng)的發(fā)展過程應(yīng)該是奇正并用,如同音律一般,有規(guī)律的起伏不平才能演奏出優(yōu)美的音律。孫武還認(rèn)為因?yàn)閼?zhàn)爭(zhēng)的基礎(chǔ)雖是客觀的,但發(fā)展的過程確是人為的,人的思想本無限制,所以戰(zhàn)爭(zhēng)的發(fā)展形勢(shì)也是無窮的,正如《孫子兵法·兵勢(shì)篇》所提到的:“奇正相生,如循環(huán)制之無端,孰能窮之?”
哲學(xué)上的辯證就是矛盾的雙方相互對(duì)立又相互聯(lián)系,在《孫子兵法·虛實(shí)篇》中的“虛”與“實(shí)”貫穿著矛盾即對(duì)立統(tǒng)一的原理。“虛”即為虛假,“實(shí)”則為真實(shí),孫武把“虛實(shí)”的哲學(xué)原理應(yīng)用在軍事上是為了掌握戰(zhàn)爭(zhēng)的主動(dòng)權(quán),在《虛實(shí)篇》的首段便提及:“凡先處戰(zhàn)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zhàn)地而趨戰(zhàn)者勞。”孫武提出要全面認(rèn)識(shí)和把握“虛實(shí)”的對(duì)立而又統(tǒng)一的原理,“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從中掌握自身的優(yōu)勢(shì)來打擊對(duì)方,達(dá)到“致人而不致人”的效果,“避實(shí)擊虛”的新型戰(zhàn)術(shù)便因此而誕生。
可見,《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是唯物而辯證的統(tǒng)一,深思其哲理,足可升華自身的思想與氣度,如此閱讀才更勝于謀略之讀。
三、武學(xué)之讀亦可文學(xué)之讀
《孫子兵法》是一部?jī)?yōu)秀的軍事著作,但同時(shí)也是一部具有極大文學(xué)價(jià)值的文學(xué)作品。南朝梁文論家劉勰說過:“孫武兵經(jīng),辭如珠玉,豈以習(xí)武而不曉文也。”(《文心雕龍》)由此而知,《孫子兵法》有屬于自身的文學(xué)藝術(shù)風(fēng)格。縱觀全文,《孫子兵法》的語言精確嚴(yán)謹(jǐn),簡(jiǎn)潔凝練,而且并無過多的語言雕飾,全文充斥著平實(shí)樸素和嚴(yán)謹(jǐn)縝密,雖與《論語》的語約義豐和《墨子》說理的邏輯嚴(yán)密相比還略顯不足,但其平實(shí)嚴(yán)謹(jǐn)?shù)恼Z句,暗含著戰(zhàn)爭(zhēng)變化無常的規(guī)律。
《孫子兵法》十分重視百姓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重要性,民本思想可以說貫穿著全文。他主張關(guān)心民生,爭(zhēng)取民心,在《孫子兵法·始計(jì)篇》中便提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在《謀攻篇》也提道:“上下同欲者勝。”《形篇》的“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和《地形篇》的“進(jìn)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等都體現(xiàn)了民本思想。
《孫子兵法》中許多的軍事思想都是對(duì)老子思想的繼承和演變。老子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的看法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孫武繼承這一思想,提出了“上兵伐謀”和“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用兵原則。從中可以看出孫武雖然是軍事家,但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亦認(rèn)為能不發(fā)動(dòng)就不發(fā)動(dòng),因?yàn)閼?zhàn)爭(zhēng)會(huì)給勝敗的雙方都帶來巨大的物力和人力損失,只不過勝者少一些而已。孫武在《孫子兵法·虛實(shí)篇》說道:“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shí)而擊虛。”孫武把戰(zhàn)場(chǎng)上的形勢(shì)發(fā)展比喻成水流,意在說明戰(zhàn)爭(zhēng)形勢(shì)的變化莫測(cè)。這一軍事思想無疑是跟《道德經(jīng)》中的“上善若水”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jiān)強(qiáng)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qiáng),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相契合的。史書對(duì)于一代兵圣孫武的結(jié)局并沒有詳細(xì)記載,但筆者認(rèn)為孫武最終的結(jié)局是功成身退,世莫知其所蹤。孫武有明知不可為而不為的處世之道,同時(shí)孫武對(duì)于自身的認(rèn)知也是十分看重的,在《謀攻篇》寫道:“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fù);不知彼不知己,每戰(zhàn)必?cái) !庇纱丝梢姡瑢O武在“知彼”和“知己”之間是更為傾向后者。孫武的“明知不可為而不為”和“知彼”的處世之道也是對(duì)老子的“道常無為而不為”和“自知者明”的繼承和演變。
《文心雕龍》寫道:“傍及萬品,動(dòng)植皆文。”既然連動(dòng)植物都蘊(yùn)含文采,更何況為人所著的《孫子兵法》呢。中國(guó)古代的兵家著作不僅可以作為軍事理論,也是能與時(shí)俱進(jìn)的文學(xué)作品,賦予了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未曾有的文學(xué)風(fēng)貌,因此《孫子兵法》也當(dāng)為優(yōu)秀的文學(xué)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