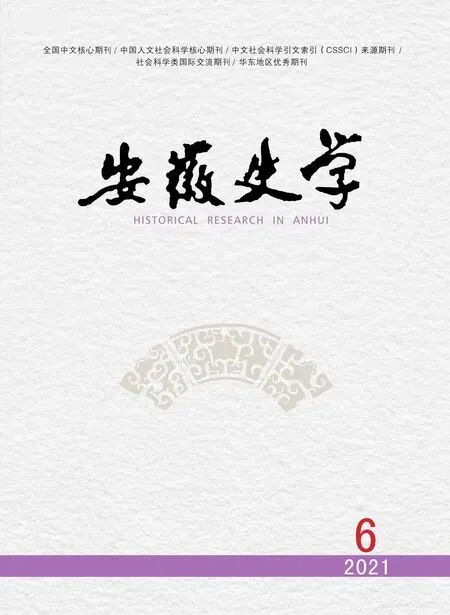近現(xiàn)代法國學(xué)界對(duì)高盧祖先說的構(gòu)建
曾曉陽
(中山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275)
“我們的祖先高盧人”這句話開始進(jìn)入并植根于法國人的集體記憶,是在相當(dāng)晚近的19世紀(jì)末。法國大革命激發(fā)了法國學(xué)界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的熱忱,其后,歷代學(xué)者又不斷加以豐富和發(fā)展。凱撒的《高盧戰(zhàn)記》是有關(guān)高盧歷史的唯一見證性文本,但其中對(duì)高盧居民的記敘僅寥寥數(shù)語。學(xué)界依憑的主要還是古代希臘和羅馬作家的著述,但它們的科學(xué)性與客觀性難以判定。在19世紀(jì),語言學(xué)、考古學(xué)、顱相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學(xué)的發(fā)展,也為學(xué)界提供了參考,但這些學(xué)科或尚處在起步階段,或未掌握有價(jià)值的材料,或成果模棱兩可甚至相互矛盾,均難以真正解釋高盧族群的起源與構(gòu)成。(1)Camille Jullian,Histoire de la Gaule T.I,Paris:Hachette,1920,pp.79-80.近現(xiàn)代法國學(xué)界對(duì)高盧祖先的構(gòu)建可謂從一開始便是一種歷史想象。
當(dāng)代法國學(xué)界對(duì)于近現(xiàn)代以來的高盧祖先敘事,已有相當(dāng)深入的研究。記憶史學(xué)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便指出,求索“起源”能為世俗化的民族社會(huì)帶來其所需要的意義和神圣性。(2)[法]皮埃爾·諾拉著、黃艷紅譯:《記憶與歷史之間:場(chǎng)所問題》,[法]皮埃爾·諾拉主編、黃艷紅等譯:《記憶之場(chǎng)》,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頁。后大革命時(shí)期,法國社會(huì)政治動(dòng)蕩,建構(gòu)法國與高盧之間的關(guān)系,成為時(shí)人為民主共和的法國奠定歷史合法性的一個(gè)重要手段。法國共和制度與共和政權(quán)象征研究的代表人物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認(rèn)為,19世紀(jì)法國學(xué)界致力于建構(gòu)高盧和法國之間的延續(xù)關(guān)系,是力圖為法國探尋一個(gè)具有進(jìn)步意義的起源神話。(3)Maurice Agulhon,“Le mythe gaulois”,Ethnologie fran?aise,nouvelle série,1998(3):pp.296-302.1980年召開的“我們的祖先高盧人”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議題涉及歷史、政治、文學(xué)、藝術(shù)、教育等多學(xué)科,反映出高盧祖先在法國集體記憶中的重要地位。(4)Paul Viallaneix and Jean Ehrard,eds.,Nos ancêtres,les Gaulois,Clermont-Ferrand:Association des publication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e Clermont-Ferrand,1982.會(huì)后,法國大革命史和教育史學(xué)家莫娜·奧祖夫(Mona Ozouf)撰文指出,大革命和普法戰(zhàn)爭(zhēng)是高盧祖先說確立的兩個(gè)最重要的時(shí)期,社會(huì)變革促使學(xué)人試圖給法國歷史確定一個(gè)獨(dú)特且專屬的起點(diǎn)。(5)Mona Ozouf,“Les Gaulois à Clermont-Ferrand”, Le Débat,1980 (6):pp.93-103.奇茲斯托弗·波米昂(Krzysztof Pomian)(6)Krzysztof Pomian,“Francs et Gaulois”,in Pierre Nora,ed.,Les lieux de mémoires T.II,Paris:Gallimard,1997,pp.2245-2300.和安德烈·布爾日也爾(André Burgière)(7)André Burgière,“L’Historiographie des origines de la France.Genèse d’un imaginaire national”,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2003(1):pp.4-62.也肯定起源主題的政治功能,強(qiáng)調(diào)“高盧祖先”與“法蘭克祖先”之爭(zhēng)牽涉到民族觀、社會(huì)等級(jí)觀和階級(jí)斗爭(zhēng)觀。法國政治思想和制度史學(xué)家克洛德·尼科萊(Claude Nicolet)指出,法德問題是法蘭西民族史構(gòu)建中的一個(gè)中心問題。(8)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aris:Perrin,2006.尼科萊對(duì)法德民族“宿敵”觀的強(qiáng)調(diào),提醒我們應(yīng)重視法國學(xué)界對(duì)祖先之爭(zhēng)的歷史緣由與政治動(dòng)機(jī)的探討,以窺探高盧祖先“戰(zhàn)勝”抑或“吸納”了法蘭克祖先的深層原因。法國政治史和種族史學(xué)家卡洛爾·雷諾—帕里戈(Carole Reynaud-Paligot)的研究體現(xiàn)了起源研究的一個(gè)主要方向,她更關(guān)注政治民族主義理論的發(fā)展為起源研究注入的新內(nèi)容,認(rèn)為起源傳統(tǒng)能夠植根于民族集體記憶得益于時(shí)人對(duì)民族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和身份認(rèn)同的不懈建構(gòu)。(9)Carole Reynaud-Paligot,De l’identité nationale.Science,Race et politique en Europe et aux Etats-Unis.XIXe-XXe siècles,Paris:PUF,2011.
在我國,法國的高盧起源也是一個(gè)普遍性知識(shí),學(xué)界亦重視研究高盧族群。沈堅(jiān)探討了凱爾特人的族群特征、文化及其在西歐的活動(dòng)。(10)沈堅(jiān):《凱爾特人在西歐的播遷》,《史林》1999年第1期;沈堅(jiān):《古凱爾特人初探》,《歷史研究》1999年第6期。陳文海指出,法蘭克人與高盧人的“同宗意識(shí)”,促進(jìn)了法蘭克—高盧的社會(huì)重組與族群融合,推動(dòng)了法蘭西民族國家的形成。(11)陳文海:《法蘭克族源敘事及其社會(huì)文化情境》,《學(xué)術(shù)研究》2014年第10期;陳文海:《共同先祖的虛擬與民族國家的初造——中世紀(jì)中、后期法蘭西人的“同宗意識(shí)”芻論》,《世界民族》2002年第2期。陳玉瑤從國家認(rèn)同角度討論了高盧人和法蘭克人的關(guān)系。(12)陳玉瑤:《從高盧人到法蘭克人——淺談促成族群對(duì)國家認(rèn)同的原因》,《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陳玉瑤:《國民團(tuán)結(jié):法國的理念與實(shí)踐》,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9年版。湯曉燕在18世紀(jì)法國思想界對(duì)法蘭克時(shí)期政治體制的反思中,看到民族起源問題的作用。(13)湯曉燕:《十八世紀(jì)法國思想界關(guān)于法蘭克時(shí)期政體的論戰(zhàn)》,《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18第4期。總體來看,我國學(xué)界對(duì)高盧祖先說構(gòu)建的系統(tǒng)梳理和研究仍相當(dāng)匱乏,這對(duì)我們深入理解和把握法蘭西民族特性和精神造成一定障礙。
本文力圖從社會(huì)政治變遷的視角出發(fā),對(duì)近現(xiàn)代法國學(xué)界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的重要著述做較為詳盡的梳理,聚焦高盧祖先說確立的社會(huì)政治動(dòng)因,考察社會(huì)政治的變遷如何促使學(xué)界不斷重新思考民族起源問題,為高盧祖先說注入新的內(nèi)容。本文也試圖基于這些文獻(xiàn)梳理,對(duì)近現(xiàn)代法國學(xué)界通過建構(gòu)民族祖先以應(yīng)對(duì)當(dāng)下社會(huì)政治問題的考量,以及高盧祖先說與法國政治民族主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進(jìn)行一些探討,以期豐富我國學(xué)界對(duì)法蘭西民族起源問題與政治民族特性的研究。
一、法蘭克征服者說:高盧祖先說構(gòu)建的緣起
19世紀(jì)法國學(xué)界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的起因,可追溯到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級(jí)以及部分開明教士和貴族對(duì)貴族特權(quán)合理性的質(zhì)疑。質(zhì)疑者試圖通過回答法蘭西民族主體是貴族還是第三等級(jí)這一問題,來評(píng)判貴族特權(quán)是否合理。這便牽涉到民族起源問題。于是,自視為高盧人后裔的第三等級(jí)與自視為法蘭克人后裔的貴族之間的政治沖突帶上強(qiáng)烈的種族沖突色彩,雙方的對(duì)立愈發(fā)尖銳,進(jìn)而引爆大革命。要理解時(shí)人為何將高盧人與法蘭克人的種族對(duì)立作為切入點(diǎn),來思考法蘭西民族主體和起源問題,進(jìn)而討論社會(huì)政治權(quán)利分配問題,需要再上溯至18世紀(jì)早期貴族和王權(quán)圍繞貴族權(quán)利問題展開的一場(chǎng)論戰(zhàn),雙方都試圖從貴族的起源出發(fā),來肯定或否定貴族的政治決定權(quán),這同樣牽涉到法蘭克人與高盧人的關(guān)系問題。這場(chǎng)論戰(zhàn)嚴(yán)重動(dòng)搖了此前流行的法蘭克人與高盧人同宗說。(14)12—15世紀(jì),圣德尼修道院修士編撰《法國大編年史》,指出高盧人和法蘭克人是先后抵達(dá)高盧的兩批特洛伊戰(zhàn)爭(zhēng)流亡者的后裔。參見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1370-1375。16世紀(jì)初,讓-勒梅爾·德·貝爾日則將高盧歷史上溯至圣經(jīng)時(shí)期,認(rèn)為諾亞在高盧的后代中有一支流亡小亞細(xì)亞,他們建立了特洛伊城。在特洛伊戰(zhàn)爭(zhēng)后,這支高盧人的后裔輾轉(zhuǎn)從日耳曼地區(qū)返回高盧,于是被稱為法蘭克人。參見Jean Lemaire de Belges,Les Illustrations de Gaule et singularités de Troye T.I,Paris:Imprimerie de J.Lefever,1882,pp.17-28;pp.93-107。自16世紀(jì)末起,法國王權(quán)開始強(qiáng)調(diào)王室的法蘭克起源,高盧人和法蘭克人同宗說出現(xiàn)微妙變化,但雙方并未被視為對(duì)立的異族,民族同源觀依然盛行。弗朗索瓦·霍特曼便認(rèn)為日耳曼人和高盧人是結(jié)盟的兄弟民族,日耳曼人是應(yīng)邀來到高盧解放了受羅馬帝國壓迫的高盧兄弟。參見Fran?ois Hotman,La Gaule francoise,Cologne:Hieromg Bertulphe,1574,pp.1-7。
貴族派代表亨利·德·布蘭維里耶伯爵(Henri de Boulainvilliers)便否定法蘭克民族起源于特洛伊的說法,認(rèn)為法蘭克王朝始于克洛維時(shí)期,法蘭克人通過征服高盧而奠定了法蘭克國家的基礎(chǔ)。布氏指出,法蘭克人相互之間是“伙伴”關(guān)系,當(dāng)今國王和貴族是克洛維及其戰(zhàn)友的后裔,共同繼承征服戰(zhàn)果,高盧人則是“奴仆”。他批評(píng)后世國王冊(cè)封貴族的做法讓許多農(nóng)奴得以提升身份,分享原本僅屬征服者的權(quán)利和榮譽(yù)。(15)Henri de Boulainvilliers,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Avec XIV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ts ou Etats-Généraux T.I,La Haye et Amsterdam:Aux dépends de la Compagnie,1727,p.15;pp.24-29;pp.35-39;pp.245-249;pp.306-319.
布氏區(qū)分法蘭克征服者和高盧被征服者,意在以古日耳曼貴族議政傳統(tǒng),來抗擊王權(quán)對(duì)貴族政治權(quán)利的侵奪,而無意制造種族對(duì)立,更無意將高盧人排除出法蘭西民族。相反,他將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時(shí)期等級(jí)分化的社會(huì),描繪為一個(gè)征服者憑戰(zhàn)功、奴仆們靠勞作、人人“理智地”各居其位的幸福和睦的社會(huì)。(16)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Avec XIV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ts ou Etats-Généraux,T.I,p.48;p.39.他還承認(rèn)法蘭克人和高盧人長(zhǎng)期通婚,其后完全融合在“同一個(gè)國民團(tuán)體”中。(17)Henri de Boulainvilliers,Essai sur la noblesse,Amsterdam,1732,pp.66-67.但他堅(jiān)稱法蘭克人才是“真正的貴族”,且是“唯一有權(quán)成為貴族的群體”,高盧人的財(cái)產(chǎn)要“按征服者的意愿受到限制”。(18)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Avec XIV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ts ou Etats-Généraux,T.I,p.48;p.39.這體現(xiàn)出他也希望通過強(qiáng)調(diào)征服者的高貴血統(tǒng),來打壓財(cái)富和政治地位日益上升的穿袍貴族和第三等級(jí)。(19)米歇爾·福柯認(rèn)為,布氏的征服者說體現(xiàn)出法國貴族是雙線作戰(zhàn),既對(duì)抗君主侵蝕其政治權(quán)力,又抵制第三等級(jí)蠶食其經(jīng)濟(jì)和政治權(quán)力。參見[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譯:《必須保衛(wèi)社會(hu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頁。從這個(gè)角度來看,布氏將貴族、王權(quán)和第三等級(jí)視為組成法蘭克國家的幾個(gè)等級(jí)不同的集團(tuán),并視等級(jí)制度為社會(huì)穩(wěn)定與民族統(tǒng)一的一種保障。他區(qū)分不同種族的政治身份和社會(huì)地位的主旨,是要證明貴族集團(tuán)憑借“征服”而成為法蘭西民族的主人抑或主體,理當(dāng)獨(dú)享政治權(quán)利。布氏是以“貴族即民族”說來對(duì)抗“朕即民族”說,但他從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血統(tǒng)之別出發(fā),去討論貴族、國王和人民在國家政權(quán)中的關(guān)系,其論證邏輯充滿種族色彩。
王權(quán)派思想家代表讓-巴蒂斯特·迪博修士(L'abbé Jean-Baptiste Dubos)則批駁布氏的征服說純屬“臆想”。迪博認(rèn)為高盧人和法蘭克人都是羅馬人。他指出法蘭克諸王從3世紀(jì)起便接受羅馬皇帝冊(cè)封,為帝國御邊,是帝國“理所當(dāng)然的臣民”。克洛維是獲封執(zhí)政官而合法取得高盧的管轄權(quán)(20)Jean-Baptiste Dubos,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 dans les Gaules T.I,Paris:La Veuve Ganeau,1734,p.3;p.8;p.12;p.39.,高盧人則是“自愿臣服”于獲封為高盧執(zhí)政官的法蘭克國王。(21)Jean-Baptiste Dubos,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 dans les Gaules,T.III,Amsterdam:J.Wetstein and G.Smith,1735,p.2;p.437.迪博的邏輯是,高盧人和法蘭克人都是帝國的臣民,因此都是羅馬人,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別。他認(rèn)為是貴族在10世紀(jì)時(shí)“侵奪”了君主的權(quán)力,建立了封建領(lǐng)主制度,才在高盧制造出一種如同外族入侵的后果。(22)Jean-Baptiste Dubos,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 dans les Gaules,T.III,Amsterdam:J.Wetstein and G.Smith,1735,p.2;p.437.顯然,迪博將貴族和第三等級(jí)之間的等級(jí)沖突視為一種社會(huì)沖突。(23)Krzysztof Pomian,“Francs et Gaulois”,p.2271.
不過,布氏意在肯定貴族權(quán)利的正當(dāng)性,迪博旨在為王權(quán)辯護(hù),雙方論戰(zhàn)的中心問題并非高盧人和法蘭克人的關(guān)系,他們也不關(guān)心民族起源問題。大革命前夕,貴族為了維護(hù)自己的特權(quán),支持制約王權(quán)、召開三級(jí)會(huì)議的主張,但拒絕給予第三等級(jí)雙倍代表名額。貴族因此徹底將自己推向第三等級(jí)的對(duì)立面,其自恃種族高貴性,更是為第三等級(jí)提供了將這些“法蘭克人后裔”清除出法蘭西民族的種族依據(jù)。
埃馬紐埃爾-約瑟夫·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正是將布氏的種族論反轉(zhuǎn),于1788年11月和1789年1月先后發(fā)表《論特權(quán)》和《第三等級(jí)是什么?》,質(zhì)疑特權(quán)等級(jí)在法蘭西民族中存在的合理性。西耶斯特地轉(zhuǎn)錄了1614年三級(jí)會(huì)議期間,貴族等級(jí)主席德·色內(nèi)塞男爵(M.de Senecey)因第三等級(jí)將法國比作由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jí)“三兄弟組成的家庭”,而感到“遭受侮辱”的言論,揭露是貴族主動(dòng)自視為“另一類人”。他以另一種種族歧視回敬這些“另一類人”,直斥這些外族“野蠻人”是國族的“負(fù)擔(dān)”,其“原則和目的”與法蘭西國族“格格不入”。西耶斯呼吁獨(dú)力承擔(dān)了保證國族“生存下去并繁榮昌盛”的“個(gè)人勞動(dòng)和公共職能”的第三等級(jí),展開民族“清洗”運(yùn)動(dòng),把“征服者種族的后裔”“一律送回法蘭克人居住的森林中”。(24)[法]西耶斯著、馮棠譯:《論特權(quán):第三等級(jí)是什么?》,商務(wù)印書館2019年版,第18、7、21—25頁。西耶斯頻繁使用nation一詞。在法語中,nation涵義豐富,但無一不將“人群 ”作為第一要素。馮棠將nation譯為“國家”“國民”或“民族”,本文根據(jù)1789年法文第三版(Sieyès,Qu’est-ce que le Tiers-Etat?Troisième Edition,Paris,1789),略微調(diào)整了馮棠的譯文,在nation分別突出族裔文化、公民政治聯(lián)合體或人民群體這三層涵義時(shí),相應(yīng)地譯為“民族”“國族”和“國民”。
西耶斯的主旨顯然也非探尋法蘭西民族起源,而是從政治層面去思考民族主體以及民族成員之間的關(guān)系,以定義一種國家民族概念。他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一群數(shù)量相當(dāng)多的孤立個(gè)人想要聚集起來”,“他們即已形成為一個(gè)國族”,他也同意向放棄特權(quán)者敞開國族之門。(25)[法]西耶斯著、馮棠譯:《論特權(quán):第三等級(jí)是什么?》,第25、87、58頁。西耶斯以人民的意愿以及民族成員與國家之間的政治關(guān)系來定義國族,其國族定義堪稱法國政治民族主義的先聲。隨著西耶斯對(duì)第三等級(jí)權(quán)利論證的推進(jìn),他所要求進(jìn)行的民族“清洗”行動(dòng)的真正對(duì)象即固執(zhí)于特權(quán)的群體,逐漸顯現(xiàn)。可以說,西耶斯是有意識(shí)地從貴族的論調(diào)中借用了種族斗爭(zhēng)話語,以令其戰(zhàn)斗檄文更具沖擊力,但隨后又迅速褪去種族話語外殼,展現(xiàn)出階級(jí)斗爭(zhēng)的實(shí)質(zhì)。《第三等級(jí)是什么?》本質(zhì)上是一篇階級(jí)斗爭(zhēng)宣言。諾拉指出,西耶斯“提前合法化了內(nèi)戰(zhàn)”,把國族的劃分線劃在了國族共同體之內(nèi),把主要矛頭對(duì)準(zhǔn)了國族“內(nèi)部的敵人”。(26)Pierre Nora,“Nation”,in Fran?ois Furet and Mona Ozouf,eds.,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Flammarion,1988,p.803.從西耶斯對(duì)國族的定義——“第三等級(jí)即國族”來看,他將國族建立在階級(jí)基礎(chǔ)上,建構(gòu)起第三等級(jí)與國家以及法蘭西民族的同一關(guān)系。這樣一個(gè)具有高度階級(jí)同質(zhì)性的、嶄新的國族政治共同體,完全否定了貴族和王權(quán)的民族說,革命已箭在弦上。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jí)代表組成國民議會(huì),以意愿而非種族來界定國族,先后接納了大部分教士等級(jí)代表和持自由主義觀點(diǎn)的貴族等級(jí)代表以及以愛國名義來參加議會(huì)的全體特權(quán)等級(jí)代表。7月27日,三個(gè)等級(jí)首次匯成一個(gè)等級(jí)共商國是,主席巴依(Bailly)激動(dòng)地宣布“家庭齊全了”。(27)Augustin Thierry,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Etat,Paris:Furne,1853,p.IX.巴依無疑言之過早,以高盧人后裔自居的共和派和以法蘭克人后裔自居的君主派之間的政體之爭(zhēng),直至19世紀(jì)末才塵埃落定,“兩個(gè)法國”也才在理論上融合為“一個(gè)法國”。
無論是“朕即民族”說、“貴族即民族”說,還是“第三等級(jí)即國族”說,時(shí)人對(duì)民族起源的追溯和民族主體的判定,無不帶有強(qiáng)烈的政治用意,旨在肯定并確立本族群或階級(jí)的政治權(quán)利的正當(dāng)性。大革命與舊制度的決裂為19世紀(jì)法國學(xué)界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提供了動(dòng)力源。同時(shí),19世紀(jì)法國國內(nèi)外的重大政治沖突,也在不斷刺激著法蘭西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宿敵”情緒。高盧人與法蘭克人的關(guān)系問題遂成為法國學(xué)界在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時(shí),首先且必須理清的問題。法國學(xué)界雖然基本認(rèn)同法蘭西民族由多個(gè)種族融合而成,但在高盧人和法蘭克人的關(guān)系以及蠻族入侵事件的影響上,出現(xiàn)很大的認(rèn)知差異。種族、地理、歷史、政治、社會(huì)等因素在高盧祖先說的構(gòu)建過程中此消彼長(zhǎng),與時(shí)政的變遷關(guān)聯(lián)緊密。
二、種族論與階級(jí)論視域下的高盧祖先說
1814年4月,波旁王朝復(fù)辟。貴族史家重彈法蘭克征服者說老調(diào),其代表穆特羅茲耶伯爵(Le Comte de Moutlosier)既堅(jiān)稱法蘭克征服者是高盧的主人,高盧人是“被奴役的種族”,也強(qiáng)調(diào)佩劍貴族與穿袍貴族的出身區(qū)別。(28)Le Comte de Montlosier,De la Monarchie fran?aise depuis son établissement jusqu’à nos jours,T.I,Paris:H.Nicolle,1814,p.18;p.41;pp.80-88.自由主義史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和奧古斯丁·梯葉里(Augustin Thierry)則接過西耶斯的階級(jí)斗爭(zhēng)論,但與西耶斯從憲政建構(gòu)角度來分析法國社會(huì)階級(jí)沖突不同的是,基佐和梯葉里是從歷史視角去解讀階級(jí)沖突,兩人也更多地關(guān)注到種族因素,但對(duì)種族沖突與階級(jí)沖突根源的看法存在較大分歧。
身為七月王朝重臣的基佐對(duì)法國社會(huì)的動(dòng)蕩深感憂慮。他既放棄種族斗爭(zhēng)視角,也不支持階級(jí)斗爭(zhēng)持續(xù)論,而更著力尋求國民的和解。他雖將法國歷史概括為法蘭克“戰(zhàn)勝者”和高盧“戰(zhàn)敗者”兩個(gè)國民群體之間的斗爭(zhēng)史,但明確表示以“社會(huì)境遇”之別來區(qū)分這兩個(gè)國民群體(29)Fran?ois Guizot,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Paris:Ladvocat,1820,p.III,p.V,p.1;pp.9-11;p.2.,肯定法蘭克人和高盧人的種族區(qū)分早已不復(fù)存在,而“特權(quán)等級(jí)”則存續(xù)至今。(30)Fran?ois Guizot,Supplément aux deux premières éditions 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Paris:Ladvocat,1820,p.16;pp.20-21.他還指出,法蘭克人征服高盧后產(chǎn)生的等級(jí)劃分并不純粹基于種族因素,構(gòu)成貴族等級(jí)的是上層的法蘭克人和高盧—羅馬人所組成的國王的“近臣階級(jí)”,而非“法蘭克階級(jí)”,落魄的法蘭克人也淪為隸農(nóng)和農(nóng)奴。(31)Fran?ois Guizot,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Paris:Ladrange Libraire,1836,pp.208-211.
基佐肯定第三等級(jí)是一個(gè)“真正新生的國族”,由沒有任何政治權(quán)利,處于奴役狀態(tài)的城鄉(xiāng)民眾組成。(32)Fran?ois Guizot,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Paris:Ladvocat,1820,p.III,p.V,p.1;pp.9-11;p.2.這一階級(jí)性定義與西耶斯的定義相當(dāng)貼合。不過,不同于希望與舊制度做徹底切割的西耶斯,基佐更希望看到階級(jí)的和解。他認(rèn)為法國歷史的一大教訓(xùn)就是貴族和資產(chǎn)者熱衷“彼此侵軋或排斥”,把自己和法國都投入了“革命的漩渦”。(33)[法]基佐著,沅芷、伊信譯:《法國文明史》第1卷,商務(wù)印書館2016年版,第3,279、195頁。而遠(yuǎn)在大革命前,法蘭克人和高盧人、貴族和平民,“全都有一個(gè)共同的名字即法國人,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祖國即法國”。(34)Fran?ois Guizot,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Paris:Ladvocat,1820,p.III,p.V,p.1;pp.9-11;p.2.他強(qiáng)調(diào)新生的法國要求“不再有戰(zhàn)勝者和戰(zhàn)敗者之分”,并將放棄特權(quán)而融入國族的決定權(quán)留給貴族。(35)Fran?ois Guizot,Supplément aux deux premières éditions 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Paris:Ladvocat,1820,p.16;pp.20-21.他因而也從歷史進(jìn)步論的視角評(píng)述蠻族入侵事件,認(rèn)為法蘭克人雖未改變高盧的社會(huì)政治制度,但給已然腐朽的羅馬世界注入了新鮮血液,帶來了“個(gè)人自由的精神”以及“對(duì)獨(dú)立和個(gè)性的需要和熱愛”。(36)[法]基佐著,沅芷、伊信譯:《法國文明史》第1卷,商務(wù)印書館2016年版,第3,279、195頁。
梯葉里則少了些政治家的考量,而完全從種族斗爭(zhēng)的角度來觀察法國社會(huì)階級(jí)斗爭(zhēng)。他批評(píng)將法國史等同于法蘭克民族史的論調(diào),并十分關(guān)注法蘭克人征服高盧后與高盧人之間的社會(huì)政治關(guān)系。他強(qiáng)調(diào)法蘭克入侵者對(duì)高盧—羅馬人充滿“刻骨的民族、宗教仇恨”,后者也極其反感法蘭克人建立的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他甚至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從法蘭西民族史上去除這兩個(gè)并未真正統(tǒng)一整個(gè)高盧而純屬“野蠻人的王朝”,而將888年撒克遜血統(tǒng)的厄德(Ode)當(dāng)選西法蘭克國王視為法國歷史的真正開端,因?yàn)楦弑R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的民族融合在此之后才真正開始。(37)[法]奧古斯丁·梯葉里著、許樾譯:《法國史信札》,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5、25、53、90、125頁。
馬克思曾將梯葉里比作法國歷史編纂學(xué)中的“階級(jí)斗爭(zhēng)之父”(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0頁。,梯葉里的階級(jí)斗爭(zhēng)觀其實(shí)有著濃郁的西耶斯的底色,但他比西耶斯更堅(jiān)定地把法國社會(huì)階級(jí)斗爭(zhēng)建立在種族斗爭(zhēng)之上。他在《第三等級(jí)的形成和發(fā)展史概論》中,從第三等級(jí)的視角來書寫法國歷史,把第三等級(jí)塑造為法國歷史的主要推動(dòng)力,認(rèn)為第三等級(jí)不斷通過社會(huì)革命來爭(zhēng)取權(quán)利的歷史,就是法國“國民關(guān)系發(fā)展和進(jìn)步的歷史”。他肯定第三等級(jí)在1789年以“同一個(gè)民族”“一部人人平等的法律”和“一個(gè)自由主權(quán)的民族”,取代“主人和奴隸”“戰(zhàn)勝者和戰(zhàn)敗者”“領(lǐng)主和農(nóng)奴”等不合理的區(qū)分,以國民議會(huì)取代三級(jí)會(huì)議之時(shí),便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39)Augustin Thierry,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Etat,pp.1-2.
然而,貴族史家繼續(xù)鼓吹征服者說,令梯葉里意識(shí)到第三等級(jí)并未真正完成其結(jié)束國民之間的等級(jí)分裂,建立一個(gè)平等、統(tǒng)一的國民團(tuán)體的使命。他揭露法國存在一個(gè)“可悲可怕的真相”,即法蘭克人和高盧人這“兩個(gè)敵對(duì)的陣營”,這兩個(gè)“在記憶上相互敵對(duì)”并“在未來計(jì)劃上不可調(diào)和”的民族,一直存在且“始終是兩個(gè)不同的部分”。他宣稱當(dāng)代法國人是“第三等級(jí)之子”,呼吁學(xué)習(xí)美國人,趕走自詡為“主人”的外族,奪回自由。(40)Augustin Thierry,“Sur l’antipathie de race qui divise la nation fran?aise”,in Augustin Thierry,Dix ans d’études historiques,Paris:Juste Tessier,1859,pp.292-297.梯葉里將法國社會(huì)階級(jí)沖突的根源完全歸結(jié)于法蘭克戰(zhàn)勝者和高盧戰(zhàn)敗者之間的種族沖突,其階級(jí)斗爭(zhēng)觀呈現(xiàn)出極其強(qiáng)烈的種族斗爭(zhēng)色彩。福柯曾指出,布蘭維里耶一脈的貴族史家是以征服者的名義講述法國歷史并要求占有權(quán)利(41)[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譯:《必須保衛(wèi)社會(huì)》,第295頁。,梯葉里恰恰是反向而行,以被征服者的名義講述法國歷史并要求奪回被占的權(quán)利,塑造出一個(gè)繼承了高盧祖先反抗種族與階級(jí)壓迫精神的第三等級(jí)形象。
奧古斯丁·梯葉里的弟弟阿梅德·梯葉里(Amédée Thierry)撰寫的《高盧人史:從最遠(yuǎn)古時(shí)期至高盧完全服從羅馬統(tǒng)治》被視為19世紀(jì)最重要的高盧史著。阿梅德持種族純潔主義觀,強(qiáng)調(diào)高盧種族血統(tǒng)的純潔性。他肯定當(dāng)今19/20的法國人源自高盧種族,認(rèn)為在高盧土著居民中,只有凱爾特人和基姆利人才擁有高盧血統(tǒng),是真正的高盧人。(42)Amédée Thierry,Histoire des Gauloi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à l’entière soumission de la Gaule à la domination romaine T.I,Paris:A.Sautelet,1828,p.II;pp.XXII-XL.阿梅德尤其突出高盧種族特性的恒定性,認(rèn)為羅馬征服高盧僅終結(jié)了獨(dú)立的高盧民族,但高盧種族仍在,而且在經(jīng)歷了羅馬人和日耳曼人的征服以及人種混雜后,高盧特性依然“容易辨識(shí)”并留存至今。他還頌揚(yáng)高盧人的獨(dú)立和反侵略精神,指出高盧人在被征服后仍不斷反抗,極大延緩了高盧被羅馬同化的進(jìn)程。阿梅德雖然僅寥寥數(shù)言提及日耳曼人入侵事件,但他強(qiáng)調(diào)人種永遠(yuǎn)不會(huì)因?yàn)檎鞣?zhàn)爭(zhēng)而消失,明確表達(dá)了對(duì)外族入侵的批判態(tài)度。(43)Amédée Thierry,Histoire des Gauloi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à l’entière soumission de la Gaule à la domination romaine T.III,Paris:A.Sautelet,1828,p.528;p.509.
基佐和梯葉里兄弟對(duì)蠻族入侵的看法對(duì)法國學(xué)界影響深刻,學(xué)界從此分持蠻族入侵有益論和無益論兩種觀點(diǎn)。總體上看,后大革命時(shí)期,新舊制度交鋒激烈,學(xué)界也在這一動(dòng)蕩的歷史分野背景下,思考法國何去何從的問題,重新解讀法蘭克“征服者”和高盧“被征服者”的關(guān)系,嘗試從中尋覓法國過去和當(dāng)下的社會(huì)政治矛盾的癥結(jié)。這一時(shí)期學(xué)界塑造的高盧祖先身上因而交織著強(qiáng)烈的種族性和階級(jí)性。
三、政治民族視角下的高盧祖先說
在19世紀(jì),尤其自下半葉起,更多的學(xué)者并不主張將法蘭西民族史建立在極具分裂性的種族斗爭(zhēng)和階級(jí)斗爭(zhēng)之上,而是著力建構(gòu)團(tuán)結(jié)、統(tǒng)一的民族觀,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法國國內(nèi)外政治局勢(shì)相關(guān)。大革命后,法國社會(huì)政治動(dòng)蕩,民族分裂危機(jī)嚴(yán)重。此外,普法戰(zhàn)爭(zhēng)也令時(shí)人深切感受到外族強(qiáng)敵對(duì)法蘭西民族共同體的巨大威脅。學(xué)人憂心民族和國家前途,期盼加強(qiáng)民族內(nèi)部的團(tuán)結(jié)和統(tǒng)一,以助力民族復(fù)興和國家崛起,因此在民族史的構(gòu)建上,更著意突出團(tuán)結(jié)因素。
茹爾·米什萊(Jules Michelet)就發(fā)出“不統(tǒng)一,必滅亡”的呼號(hào),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下法蘭西民族最重要的時(shí)代使命,就是建構(gòu)“一個(gè)民族、一個(gè)祖國、一個(gè)法國”。(44)Jules Michelet,Le peuple,Paris:Calmann Lévy,1877,p.XXXV.米什萊被學(xué)界視為地理決定論的重要代表,他指出地理環(huán)境對(duì)民族形成的影響十分重要,“歷史首先完全是地理”。(45)Jules Michelet,Tableau de la France:Géographie physique,politique et morale de la France,Paris:Librairie internationale,1875,p.2.但他也明確指出,自然地理和種族因素僅在最原始的時(shí)期起過重要作用,終將“讓位于社會(huì)和政治行動(dòng)”。米什萊提出“人種疊加”的觀點(diǎn),肯定高盧最早的居民是凱爾特人,其后基姆利人、布洛格人、伊比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和日耳曼人也相繼到來,他們都是組成法蘭西民族的“必要且充滿活力”的“材料”和“成分”。是法國通過“內(nèi)在的作用”將各種族黏結(jié)、糅合、塑造為一個(gè)實(shí)體,進(jìn)而造就了法國。(46)Jules Michelet,Histoire de France T.1,Paris:Librairie internationale,1876,p.33;p.82;pp.142-143.這一“內(nèi)在的作用”,就是世代相傳的共同的生活與戰(zhàn)斗經(jīng)歷所凝成的“共同精神”和“愛國情感”。(47)Jules Michelet,La France devant l’Europe,Paris:Achille Faure,1871,pp.113-114.米什萊的歷史觀對(duì)法國學(xué)界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地理、歷史、政治、社會(huì)因素從此成為法國學(xué)界論述民族起源和形成問題時(shí)必提的因素。從某個(gè)角度來看,米什萊的歷史觀為法國政治民族主義在19世紀(jì)下半葉的確立作了思想鋪墊,而普法戰(zhàn)爭(zhēng)引發(fā)的法蘭西民族空前的危機(jī)以及法德洶涌的民族“宿敵”情緒,推動(dòng)法國學(xué)界深刻反思民族的內(nèi)涵,對(duì)大革命時(shí)期萌發(fā)的政治民族意識(shí)進(jìn)行學(xué)理建構(gòu)。
普法戰(zhàn)爭(zhēng)期間,法德學(xué)界圍繞阿爾薩斯與洛林地區(qū)和人民的國家歸屬與民族歸屬問題,展開激烈論戰(zhàn)。德國學(xué)者大衛(wèi)·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和迪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等秉持文化民族觀,從語言、種族和歷史淵源出發(fā),論證德國兼并阿爾薩斯和洛林是“收回”曾屬于德國的土地。法國學(xué)者厄內(nèi)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弗斯戴爾·德·庫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和奧古斯特·熱弗瓦(Auguste Geffroy)等則以政治民族原則予以反擊。勒南強(qiáng)調(diào)人民“當(dāng)下的贊同”和“共同生活的意愿”才是構(gòu)成民族的“更明顯的東西”,阿爾薩斯“不希望屬于德國:這就解決了問題”。他進(jìn)一步批評(píng)德國的民族觀易于挑起民族沖突和戰(zhàn)爭(zhēng)(48)Ernest Renan,Qu’est-ce qu’une nation ? et autres écrits politiques,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96,pp.211-212;p.199.,先見性地警告了德國人注意血統(tǒng)論的荒謬和危險(xiǎn)。(49)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271.庫朗日則完全否定種族等因素對(duì)建構(gòu)民族和民族國家的作用,認(rèn)為是“適宜的地理因素”以及“共同的思想、利益、情感、記憶和希望”,造就了民族。他尤其重視民族自決權(quán),并以“斯特拉斯堡不是屬于我們,它是和我們站在一起”一言,抨擊德國的侵占行為。(50)Fustel de Coulanges,L’Alsace est-elle allemande ou fran?aise ? Réponse à M.Mommsen,Paris:Dentu,1870,p.8;p.10;pp.15-16.熱弗瓦也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當(dāng)由阿爾薩斯和洛林人民投票決定其民族國家歸屬。(51)Auguste Geffroy,“un manifeste prussien”,La Revue des Deux Mondes,1870 (90):p.135.三位法國學(xué)者的觀點(diǎn)集中體現(xiàn)了法國學(xué)界的政治民族觀,他們重視民族的政治屬性,視政治意愿為界定民族歸屬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
普法戰(zhàn)爭(zhēng)后,勒南并未停止對(duì)政治民族概念的思考。1882年3月11日,他在《國族是什么?》的演講中,重申人民的“政治意愿”是界定其國族歸屬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指出種族不能與國族混為一談,種族研究不能應(yīng)用于政治領(lǐng)域,肯定凱爾特人、伊比利亞人和日耳曼人都已在法蘭西國族大熔爐中融為一體。勒南以“國族的存在,就是日復(fù)一日的公民投票”一言,高度概括了法國政治民族主義的思想內(nèi)核。(52)Ernest Renan,Qu’est-ce qu’une nation ? et autres écrits politiques,pp.223-243.勒南視角下的高盧祖先顯然是一個(gè)歷史學(xué)和政治學(xué)意義上的集體祖先。他與同代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公民的政治意愿而非國族的階級(jí)屬性,他們的政治民族共同體是向外而建的,把國族的劃分線劃在國族共同體之外,呈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內(nèi)部團(tuán)結(jié)意識(shí),回應(yīng)了普法戰(zhàn)爭(zhēng)后法國對(duì)國族團(tuán)結(jié)與統(tǒng)一的時(shí)代需求。
庫朗日則將自己的研究對(duì)象從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宗法制度轉(zhuǎn)移到古代法國政治制度上,他表示自己將研究起點(diǎn)定在高盧—羅馬時(shí)期,原因在于羅馬征服高盧是“第一個(gè)改變了我們國家并定下國運(yùn)方向的事件”。(53)Fustel de Coulanges,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La Gaule romaine,Paris:Hachette,1901,p.XIII.庫朗日此言及其改變研究對(duì)象的決定反映出他期翼通過溯源法國政治思想和制度,來觀察并思考國家的發(fā)展趨勢(shì)。庫朗日重新思考了蠻族入侵事件。他雖然沿用“入侵”一詞,但否認(rèn)存在“入侵”事實(shí),認(rèn)為進(jìn)入高盧的日耳曼人是被古日耳曼國家的其他族群驅(qū)逐或打敗而逃亡至高盧。他們對(duì)高盧—羅馬人并無種族仇恨,反而視其他日耳曼族群為“宿敵”,克洛維正是戰(zhàn)勝了其他日耳曼首領(lǐng)而“征服”高盧的。庫朗日批評(píng)部分史家和民眾出于階級(jí)對(duì)立和仇恨,臆想出一種法蘭克人對(duì)高盧人的“原征服”,將法國人民分為兩個(gè)不平等的種族,而社會(huì)階級(jí)對(duì)立的加劇又令兩個(gè)種族之間的“仇恨”不斷升溫并延續(xù)至今。他尤其批評(píng)部分史家夸大蠻族“入侵”的重要性,指出進(jìn)入高盧的日耳曼人為數(shù)甚少且均為行武之人, “沒有以日耳曼特性和精神取代高盧—羅馬特性和精神”,他們的“入侵”不是“一個(gè)民族或一種新思想的勝利”,只是打亂了高盧社會(huì)的運(yùn)行。(54)Fustel de Coulanges,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L’invasion germanique et la fin de l’Empire,Paris:Hachette,1904,pp.319-322;p.498;pp.531-533;p.558.
庫朗日顯然力圖通過論證日耳曼人對(duì)高盧社會(huì)政治制度以及血統(tǒng)和民族特性均無影響,來對(duì)法蘭西民族史進(jìn)行某種“去日耳曼化”的處理。在這一點(diǎn)上,他與奧古斯丁·梯葉里的想法一致。但是,梯葉里持種族排斥觀,庫朗日則一以貫之地反對(duì)種族論,肯定法蘭克人和高盧人經(jīng)過長(zhǎng)期混居和聯(lián)姻后,已無純粹的高盧血統(tǒng)者或日耳曼血統(tǒng)者。(55)Fustel de Coulanges,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L’invasion germanique et la fin de l’Empire,p.504.然而,他受普法戰(zhàn)爭(zhēng)的影響,仍然力圖從文化、政治和血統(tǒng)等方面,降低日耳曼人在法蘭西民族歷史中的地位,以突出法蘭西民族特性。
哲學(xué)家阿爾費(fèi)德·傅耶(Alfred Fouillée)則大量借鑒歐洲種族人類學(xué)尤其是顱相學(xué)的研究成果,指出高盧人由與伊比利亞人有親緣關(guān)系的古長(zhǎng)頭型人,以及之后抵達(dá)高盧的短頭型利古里亞人、凱爾特人、北方長(zhǎng)頭型人混合而成,其后,羅馬人也加入其中。但他并不贊同人類學(xué)者按人種劃分歐洲民族的做法,認(rèn)為歐洲各民族均由金發(fā)長(zhǎng)頭型人、棕發(fā)長(zhǎng)頭型人和棕發(fā)短頭型人混合而成,但各民族中不同人種的占比對(duì)民族心理特性有影響。他批評(píng)庫朗日忽視了法蘭克人在與高盧人長(zhǎng)期融合過程中,對(duì)高盧人的體質(zhì)和性格產(chǎn)生了一些生物性影響。不過,傅耶并不因此認(rèn)為種族因素對(duì)民族形成起決定作用,他尤其批評(píng)德國學(xué)界以及梯葉里兄弟等法國學(xué)者混淆民族特性研究和種族研究,宣揚(yáng)歷史宿命論,將社會(huì)階級(jí)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轉(zhuǎn)變?yōu)榉N族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將國家之間的政治與經(jīng)濟(jì)競(jìng)爭(zhēng)轉(zhuǎn)變成血統(tǒng)仇恨,致使戰(zhàn)火難熄。他明確提出應(yīng)當(dāng)將生物意義上的種族和政治意義上的種族區(qū)分開來,后者是由生活在同一個(gè)國家、遵循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信仰的不同種族所組成的一個(gè)混合種族。(56)Alfred Fouillée,Psychologie du peuple fran?ais,Paris:Félix Alcan,1903,p.95;p.170;pp.77-84;pp.174-176;pp.I-II;p.27.傅耶所言的這一“政治種族”顯然就是政治民族主義視角下的國族。
庫朗日的學(xué)生卡米耶·于里安(Camille Jullian)是19世紀(jì)和20世紀(jì)之交高盧史研究的重要代表,其8卷本《高盧史》被視為20世紀(jì)法國最重要的高盧史著。于里安坦承自己研究高盧意在展示高盧命運(yùn)與法國命運(yùn)的關(guān)聯(lián)(57)Camille Jullian,Gallia,Tableau sommaire de la Gaule sous la domination romaine,Paris:Hachette,1902,p.VII;p.323.,他的多部高盧史著都洋溢著一種“高盧愛國主義”,頌揚(yáng)高盧人民的自由、獨(dú)立和反侵略精神。
于里安和阿梅德·梯葉里一樣,也十分強(qiáng)調(diào)高盧特性的恒定性,認(rèn)為征服并未改變高盧人的血統(tǒng)和民族特性。(58)Camille Jullian,Gallia,Tableau sommaire de la Gaule sous la domination romaine,Paris:Hachette,1902,p.VII;p.323.不過,于里安不贊同梯葉里的種族觀。他認(rèn)為古人并無人種觀念,而是從政治、語言或地理角度來稱呼不同人群。(59)Camille Jullian, Histoire de la Gaule.T.I,Paris:Hachette,1920,pp.119-120.利古里亞人、高盧人、羅馬人以及法蘭克人和其后的法蘭西人都是指代不同“政治形勢(shì)”的名詞,他們相繼戰(zhàn)勝先前居于高盧的群體,但他們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不是種族、宗教和語言的勝利,而是戰(zhàn)勝者群體的首領(lǐng)迫使當(dāng)?shù)孛癖姺钠浣y(tǒng)治,后者也逐漸習(xí)慣并接受了戰(zhàn)勝者群體的名稱。于里安還對(duì)米什萊的“人種疊加”觀點(diǎn)進(jìn)行了闡發(fā),表示自己更愿意使用“群體”“歷史名詞”“語言”等詞而非“人種”一詞。他同樣肯定所有“群體”都為建構(gòu)法國出過力,“我們的祖先先后曾是利古里亞人和高盧人,他們經(jīng)歷了這一個(gè)個(gè)階段,幫助我們變成了法國人。”(60)Camille Jullian, De la Gaule à la France.Nos origines historiques,Paris:Hachette,1922,p.82;p.123;p.83.相較于前代學(xué)者,于里安對(duì)種族因素的拋棄可謂更徹底,他從民族起源之初便否定種族因素的存在,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政治民族內(nèi)涵。
同時(shí),于里安對(duì)法國歷史上遭遇的外族入侵事件的否定態(tài)度也更徹底。他不但否定蠻族入侵有益論,而且還否定19世紀(jì)大部分史學(xué)家均認(rèn)同的羅馬入侵高盧而將高盧帶入文明世界的觀點(diǎn)。(61)Camille Jullian,De la Gaule à la France.Nos origines historiques,pp.193-203;pp.172-175;pp.185-189.于里安時(shí)期,困擾法國一個(gè)世紀(jì)之久的政體之爭(zhēng)已經(jīng)平息,高盧人和法蘭克人不再被視為新舊制度的象征。于里安也不再如同前代學(xué)者般,從一個(gè)國家內(nèi)部的兩個(gè)民族爭(zhēng)奪政權(quán)的角度,來探討蠻族入侵問題。他反而深切體味到法國在普法戰(zhàn)爭(zhēng)中又一次敗給日耳曼人的恥辱,他的關(guān)注點(diǎn)因此集中在外族對(duì)法蘭西民族的入侵上,從民族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角度,來思考蠻族以及羅馬人入侵高盧的問題。
縱觀米什萊以來法國學(xué)界對(duì)高盧祖先說的構(gòu)建,可以發(fā)現(xiàn),一方面法國學(xué)界越來越少動(dòng)員種族因素,而是更強(qiáng)調(diào)地理和社會(huì)政治因素,突出民族的政治屬性。另一方面,法國學(xué)界也逐漸放棄了種族斗爭(zhēng)和階級(jí)斗爭(zhēng)史觀,而強(qiáng)調(diào)民族融合與共同發(fā)展的思想。雖然在普法戰(zhàn)爭(zhēng)后,出現(xiàn)對(duì)法蘭西民族史進(jìn)行去日耳曼化處理,以強(qiáng)調(diào)“高盧人”和“高盧民族”身份的傾向,但這已不再是受民族內(nèi)部階級(jí)斗爭(zhēng)觀念的驅(qū)使,而是出于面對(duì)強(qiáng)鄰,樹立民族自信,加強(qiáng)國家和民族內(nèi)聚力的需要。
余 論
近現(xiàn)代法國一直存在兩種“民族危機(jī)”。一種是內(nèi)源型的,源自法國國民內(nèi)部?jī)蓚€(gè)陣營之間的沖突與競(jìng)爭(zhēng);一種是外源型的,源自法蘭西民族與他族之間的沖突與競(jìng)爭(zhēng)。普法戰(zhàn)爭(zhēng)后,明顯出現(xiàn)從內(nèi)源型民族危機(jī)向以外源型為主的民族危機(jī)過渡的現(xiàn)象。但無論是何種民族危機(jī),法蘭西民族的“宿敵”始終是日耳曼民族。高盧人與法蘭克人的關(guān)系因此成為法國學(xué)界在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時(shí),必須首先處理的一個(gè)中心問題。高盧祖先說于是相繼與種族觀、階級(jí)觀和國族觀的誕生與演變發(fā)生密切關(guān)聯(lián)。時(shí)人構(gòu)建民族祖先,不僅僅是在探尋法蘭西民族從何處來,更是在思考法蘭西民族和民族國家將往何處去。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成為時(shí)人構(gòu)建新的民族國家政治體,并加強(qiáng)其內(nèi)部團(tuán)結(jié)的一個(gè)重要手段。
自西耶斯以來,尊奉高盧祖先,成為認(rèn)同并奠定新政治制度的一個(gè)重要的政治手段。追溯高盧歷史,發(fā)掘高盧命運(yùn)與法國命運(yùn)的關(guān)聯(lián),也成為法國學(xué)界在民族起源問題上一個(gè)共同的研究旨趣。在第三等級(jí)與特權(quán)等級(jí)以及民主共和思想與專制王政思想的斗爭(zhēng)中,在階級(jí)意識(shí)、民族意識(shí)和國家意識(shí)的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在法蘭西和日耳曼兩個(gè)民族國家的沖突與競(jìng)爭(zhēng)中,高盧祖先意識(shí)不斷得到加強(qiáng),高盧祖先內(nèi)涵也在不斷調(diào)整。可以說,近現(xiàn)代法國學(xué)界構(gòu)建高盧祖先說,是在致力從民族的起源和歷史中,尋求就國內(nèi)而言,本階級(jí)或集團(tuán)相對(duì)于另一階級(jí)或集團(tuán)在政治權(quán)利上的歷史正當(dāng)性依據(jù),就國際而言,本民族相對(duì)于他民族在國族權(quán)利上的歷史正當(dāng)性依據(jù)。高盧祖先說于是先后被賦予了促進(jìn)政治覺醒、階級(jí)覺醒、國族覺醒的功用,成為一種有意識(shí)的構(gòu)建,映照出法蘭西民族從王政走向共和,從族裔民族走向政治民族共同體的過程。
進(jìn)入20世紀(jì),法國社會(huì)的移民成分已經(jīng)相當(dāng)繁雜,從狹義的民族主義視角去想象“高盧祖先”已不合時(shí)宜,高盧祖先逐漸演變?yōu)榉ㄌm西民族團(tuán)結(jié)的一個(gè)集體象征。1985年9月17日,法國前總統(tǒng)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在演講中肯定,高盧人不是所有法國人的祖先,但所有法國人都應(yīng)追尋“國民團(tuán)結(jié)之路”。(62)Fran?ois Mitterrand,“Allocution à l’occasion de l’inauguration du site archéologique au Mont Beuvray,Bibracte”,https://www.elysee.fr/francois-mitterrand/1985/09/17/allocution-de-m-francois-mitterrand-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occasion-de-linauguration-du-site-archeologique-au-mont-beuvray-bibracte-mardi-17-septembre-1985,2020年10月7日。密特朗基于政治民族的意愿核心觀,從共同的未來計(jì)劃角度,為“我們的祖先高盧人”注入了新的時(shí)代內(nèi)涵。不過,盡管法蘭西政治民族主義思想在理論上清除了國族概念中的種族元素,但由于歷史、宗教、意識(shí)形態(tài)等各方面原因,種族問題仍是當(dāng)今法國揮之不去的一個(g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