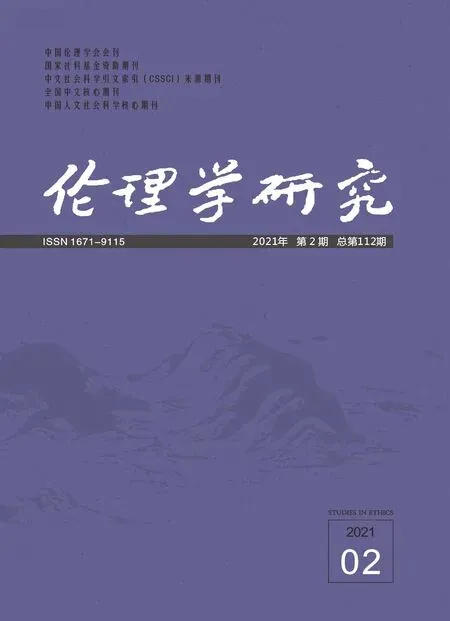先秦儒家“法先王”的倫理之維
“法先王”是中國古代的傳統政治觀,發揮著“準宗教性質”的倫理作用。侯外廬指出:“中國古代史里有一個最特殊的問題,它的嚴重程度是希臘羅馬所沒有的,這便是‘先王’問題。”[1](P200)先秦大多數學派都提出了“法先王”的主張,其中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影響最大,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靈魂,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文化現象和王道政治模式。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儒家“法先王”思想時遭詬病和批判,其合理性和價值常被消解和遮蔽。戰國時期的法家就曾貶斥儒家“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五蠹》),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史記·商君列傳》)。在近現代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法先王”思想受到三次大范圍的沖擊和批判。第一次是在20 世紀初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2](P7-49)中,一些人以救亡理性全盤否定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文化①,“法先王”成為儒家的罪狀之一。《新青年》猛烈抨擊孔子和禮教,稱其為“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3],認為應以“倫理之覺悟為最后覺悟之覺悟”[4](P37)。第二次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后的疑古風潮中,古史辨派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研究古代的歷史和典籍,提出了“層累說”②,推翻了由三皇五帝等概念構成的中國古史系統。疑古派對破除長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傳統觀念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其過度疑古也“將古史‘辨’成沒有”[5](P170),其對古代圣賢“遺教”和“六經”元典的否定,是對“法先王”思想的釜底抽薪。第三次是在20 世紀60年代及其后的政治運動中,一些學者以極端階級分析法批判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從孔子的“吾從周”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斷其為復古主義者,認定儒家是主張復辟倒退的保守派③。儒家“法先王”思想所遭遇的上述沖擊和批判,從思維方式上看,“無非意味著對歷史作單純主觀的闡釋,并且意味著這種主觀闡釋的極致,其在哲學上是以‘壞的主觀性’為依據的”[6],有違闡釋學“視域融合”及“效果歷史”的原則④,屬于主觀主義的極致行為。為了弄清先秦儒家“法先王”的真實面目,走出救亡理性、疑古風潮與極端階級分析法的窠臼和局限,本文嘗試從倫理向度厘清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的真實意蘊,探賾其“法先王”路徑與方法,揭橥其建構中國王道政治范式的價值與意義。
一、儒家“法先王”的“唯倫理性思維方式”
在儒家“法先王”一詞中,“先王”是指古代有重大貢獻和高尚道德的圣王。“法先王”思想萌生于西周統治者的憂患意識和德性覺醒,既是殷周之際社會巨變的產物,也是子學時代“唯倫理性思維方式”支配的結果。在牧野之戰中,“小邦周”推翻了有著六百年歷史的商王朝,這場“千年未有之大巨變”使周朝統治者陷入對天命深深的憂思,“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偽古文尚書·蔡仲之命》)與“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等“天命不保”的擔心催生了周人的憂患意識和倫理萌芽,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德性基因。如何才能使“靡常”的天命不再轉移,永久地眷顧周之子孫呢?當時的政治家認為,僅僅像紂王那樣虔誠地供奉和祈禱上天是無濟于事的,獲得上天青睞的關鍵在于統治者是否有“宜民宜人”之德。只有“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詩經·大雅·下武》),才能江山“本支百世”“于萬斯年”。“德”是周人首創的思想,周公第一次將“明德”作為統治者必備的素質,使政治道德在國家興亡中的作用充分凸顯。可以說,殷周之際的大變革,使“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尚書·康誥》)和敬德保民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旋律。伴隨著人們對“德”與“天命”關系的深刻認知,中國社會的“唯倫理性思維方式”日漸形成。所謂“唯倫理性思維方式”,是指“以倫理意識為核心內容和基本規范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這種“以現世性和實用性為思維取向的倫理意識,使古代中國人把脊背朝向大自然和虛無縹緲的形而上之存在(或‘上帝’),而專注于個人的道德生活”[7](P6)。它不僅造就了具有濃郁人文主義色彩的古代傳統文化,也奠定了中國倫理型社會的基石。在“唯倫理性思維方式”影響下,中國社會“潤澤以禮文”[8](P46),“以道德代宗教”[8](P85),“遂漸以轉進于倫理本位”[8](P46),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政治特質。統治者為了以德配天,以倫理規范治理社會,需要有可供效仿的倫理楷模和政治范式,這樣圣賢先王及其王道就成為時代的首選,基于此,“法先王”⑤思想便應運而生。“周人由于‘維新’,繼承了殷人的氏族制度,因而‘帥型先王’與倫理的思想相為一體;到了春秋戰國,諸子沿此遺緒,遂多以‘先王之道’證成己說。”[9](P135)
圣王是理性的化身,是道施化萬物的中介,其德性和治世方略可以為后人提供生存經驗和精神滋養,能夠給人類社會帶來秩序和意義。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肇始于周公。為了讓周王朝“天命永祺”,周公要求成王等姬氏子孫學習和效仿文王等先祖的嘉德懿行,以圖通過“儀刑文王”達至“萬邦作孚”(《詩經·大雅·文王》)。但“法先王”理論的真正建構者是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儒家運用“唯倫理性思維方式”,以“立德”“弘道”為價值取向對中華元典進行詮釋⑥,希望塑造可供效仿的圣王形象和圣王之道。例如,孔子以“德”解《周易》,曰:“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10](P481)孔子認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為了使“法先王”不“載之空言”,孔子及其后的儒家以“達乎德”為標準,詮釋元典,再造古代神話,把那些功績卓著的先王塑造成至圣至賢的倫理典范和文化英雄,以使后人效仿時有“深切著明”之感。作為“法先王”思想的奠基人,盡管孔子沒有明確提出“法先王”的概念,但其追尋周公,對圣賢先王贊美有加,推崇備至。他頌揚堯帝“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崇尚文武周公,終生以“吾從周”(《論語·八佾》)為使命;在記載其言論的文獻中有“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為政》)的語句。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了系統的“法先王”⑦思想,并將仁政確立為王道的本質意蘊。荀子明確打出了“法先王,隆禮義”(《荀子·儒效》)的旗幟,勾畫了中國古代王道政治范式的藍圖。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周初“法先王”思想的發軔,還是先秦儒家對“法先王”理論的建構及其實踐的展開,“唯倫理性思維方式”都貫穿始終,德性與倫理意識“過早過深地攫住了中國人的靈魂”,道德和倫理范疇在中國倫理型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起著脊柱般的作用”[11](P160)。在這種現世性和實用性為思維取向的倫理意識作用下,中華民族的先王被披上了道德楷模的五彩大氅,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被設計成了以仁政為內核的王道政治范式。
二、先秦儒家“法先王”之真實意蘊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法先王”一詞的含義存在著誤解和紛爭,例如,有學者就把“先王”等同于過去所有的帝王,把“王道”視為昔日的“王制”⑧,把“法先王”理解為效法先王所制定的一切典章制度。事實上,儒家不是凡“先”必“法”、是“古”即“復”,其推崇和效法的“先王”是那些“得天下以仁”的道德至圣之王,其“法先王”是效法先王之德和先王關于仁政、德治、禮樂的王道。
1.以立德為旨歸,效法先王之德
在先秦儒家那里,先王是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⑨這些道德典范和文化英雄的統稱。他們是儒家王道政治倫理的楷模,是具有克里斯瑪⑩特質的人物。儒家將其神圣化為一種政治倫理符號,希望后人效仿其道德人格,秉承其精神氣質。在古代典籍中,有不少關于先王之德的記載,儒家梳理和凝練這些先王之德,旨在為后人樹立榜樣。
其一,效仿先王的尊親孝悌之德和篤仁愛民之行。圣賢先王是至孝至悌的楷模,可為萬民之表率。《大戴禮記》贊堯“其仁如天”,禹“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五帝德》)。《史記》?稱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五帝本紀》)。《詩經》贊周文王“亹亹文王,令聞不已”,“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大雅·文王》)。《史記》記載文王“篤仁,敬老,慈少”(《周本紀》)。同時,古代圣王都大都慎用武力,憑仁德贏得民眾之擁戴。《大戴禮記》記載,黃帝“治五氣,設五量……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帝嚳“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堯“能明馴德,以親九族”;帝舜“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五帝德》)。《史記》贊美周公,“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魯周公世家》)。從黃帝的“撫萬民,度四方”(《大戴禮記·五帝德》)到堯帝的“欽明文思”“協和萬邦”(《尚書·堯典》),從舜帝的“敬敷五教”“柔遠能邇”(《尚書·舜典》)到大禹的“文命敷于四海”(《偽古文尚書·大禹謨》),這些彪炳史冊的先王德行反映了古代圣王“納眾歸一”的政治智慧,足以為后人楷模。誠然,把圣王作為至善的道德典范和至高的政治倫理化身,可能有史官或儒者美化夸張的成分?,但也折射出先秦儒家對圣王之德的美好想象和情感期待。
其二,崇仰先王超凡的文化創造力和精神氣質。與古希臘一樣,殷周時期也將人的職業能力視為“德”的內容。古代圣王都具有超凡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是世人眼中的文化英雄。歷史上,有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的傳說,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辭下》)的記載。伏羲創立八卦,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源;黃帝統一天下,肇造文明,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漢書》在描述《周易》的成書過程時,認為伏羲、文王和孔子三位先圣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共同完成了從八卦到六十四卦再到《易傳》的創作,從而使《周易》成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和設教之書。其乾坤兩卦的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作為君子的圣王們卓異精神氣質的沉淀和彰顯,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練和陶鑄,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歷史賦予這些先王以巨大的文化選擇權能,他們的思想方向決定,或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后來文化與價值的方向,從而對后來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12](P4)解釋人類學家克里福德·格爾茨認為:“一個族群的精神氣質是他們生活的一種風氣、特征、品性,是其道德與審美的方式和基調,標示著此一族群對他們自己和他們所處世界的根本態度,這種態度構成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13](P126-127)后人對圣賢先王所創造文化的學習,對其超凡精神氣質的敬仰,既是中華民族對優秀傳統的承繼,也是炎黃子孫奮力前行、開拓未來的不竭動力。
2.以弘道為目標,效法先王之道
先王之道簡稱“王道”。《漢語大詞典》將其定義為“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朱熹將其視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朱子文集·李公常語下》)。“王道”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洪范》?中。從歷史文獻的考證看,上古時期已經有了與王道相關的意識和實踐,但理論形態的王道政治思想始于孔子,豐富完善于孟子和荀子。在“唯倫理性思維方式”的支配下,先秦儒家確立了以弘揚禮治和道義為目標的“法先王”宏旨,其對王道政治范式的效法主要體現在內外兩個方面。
對內以“敬德”和“禮樂”教萬民。先秦儒家承繼了西周的敬德思想,使之成為王道政治的重要內容。孔子雖沒有明確使用“王道”一詞,但他已具有王道意識,從其對管仲的褒貶之語可見一斑。他稱贊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同時,又對管仲為臣而僭邦君之禮深惡之,謂之“器小”“不知禮”。在他看來,內心違“禮”的外部事功嚴格說來不是真正的“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仍是霸道之功,就其價值而言,與“王道”有著原則性的區別,因此,他強調:“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論語·子路》)可見,在孔子那里,對“霸”與“王”之抑揚已有端緒。孔子還提出了“為政以德”思想,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論語·為政》),認為“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論語·衛靈公》),為政者對百姓施政宜寬猛相濟。《左傳》載,“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當子張問如何“從政”時,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其所說的“五美”是“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四惡”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孔子不僅建議統治者以“德”化人,培養人們的廉恥之心,而且主張以“禮樂”教化民眾,贏得人心的歸附。他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的“詩禮樂”融合教化模式,指出“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樂者”“德之華也”“通倫理者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致樂以治心”,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記·樂記》)。在儒家看來,“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禮”能使萬物各安其位,“樂”可使萬物皆能化生,故“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禮記·樂記》)。因此,以禮樂教化民眾,構建禮宜樂和的社會秩序是先王之道的重要內容。
對外以“仁德”和“道義”服天下。秩序是人類的第一需要,“文明是解決沖突的方案”[14](P401),中華先民很早就產生了以文明方式治理社會的王道思維,《尚書·禹貢》中的“揆文教”就是通過以柔克剛、迂回曲折的方法來化解矛盾和沖突的。這種來自部落社會創制者們的“德義”傳統,體現了古代先王卓異的政治遠見和道德素養,是儒家王道思想的源頭。“王道”的本質特性在于其以“仁”為根本原則。孟子曾引用孔子之語,“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上》)“道”出于“仁”則入于“不仁”,不存在第三種選擇。孟子提出了系統的“仁政”學說,他把“仁”與“不仁”視為關乎“得天下”或“失天下”的根本問題,認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離婁上》)。他指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面對當時各諸侯國廣為采用的霸道政治,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戰爭與禍亂,荀子褒揚王道,抨擊霸道。他指出:“彼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荀子·王制》)荀子認為,王道“以德服天下”,將道義和仁德普施天下,使人心歸附;反之,推行“以力服天下”的霸道則會眾叛親離、走向滅亡。“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兇,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荀子·正論》)他勸誡君王們應效法湯、武,“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荀子·王霸》),以仁德和道義贏得人心,成為眾望所歸的王者。可以看出,“以德服天下”者“王”、“以力服天下”者“亡”,是先王之道的至要理念。
無論是先王之德還是先王之道,都是古代圣王個人修身和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儒家“法先王”是對這些經驗和傳統的承繼。每個人“都生活在過去的掌心中”[15](P37),都不可能斬斷自己與過去的聯系,不能將“傳統”視為沉重的包袱和無形的羈絆,我們只能在承繼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創造自己的未來。“過去可以被作為積極地重建現在的模型”[15](P215),先秦儒家“法先王”不僅是對先王之德和仁政王道的傳延,更是對當時及未來政治倫理模式的重建。王道作為“儒家政治學說的普遍主義表述”[16],是假借先王這一載體而展開的。恰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自己效勞,借用他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17](P669)先秦儒家不僅請出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先王的亡靈,借用其話語和神威,而且為其戴上倫理化、道德化的文飾,演出一幕幕“托古改制”的活劇,以推行其王道政治的社會理想。從倫理向度看,“法先王”的實質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為基本價值取向對先王形象的美化和塑造、對先王之德和先王之道的凝練和倡揚,是以效法先王之名推行仁政王道之實,是闡舊邦以開新命的政治智慧。
三、先秦儒家“法先王”的路徑與方法
先秦儒家主張“法先王”,但其所效法的先王之德和先王之道并不完全出自先王,而是經由原始儒家形塑而成。作為一個歷史性概念,“王道”是先秦儒家對上古先王治道的追溯、總結和理想化呈現。申言之,中國古代成熟的王道政治范式并非先王有意識的構建,而是先秦儒家從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倫理需要出發,根據“五經”中有關先王德行和王道的零散記載凝練總結而成;同時,先秦儒家還通過倫理向度的理論開新和中庸之道的創見,為王道政治理想奠定了堅實根基和方法論支撐。
1.以“可施于禮義”的倫理標準,凝練“五經”中的圣賢人格與王道理念
先秦儒家所推崇的先王之德和先王之道大多散見于“五經”之中。關于王道載于六經、孔子修六藝意在闡明王道的說法,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仲尼……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前漢書·地理志》云:“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朱子文集·李公常語下》云:“《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孔子通過遴揀和萃取,使“五經”中的政治倫理精華成為構建王道政治范式的重要資源。“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不僅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而且以“六經”為教,賡續古代圣王因襲相傳的政治倫理文化。以《詩經》為例,《史記》云:“謂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世家》)《論語》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顯然,孔子用“思無邪”與“可施于禮義”的倫理標準對《詩》的內容進行了甄選和編次。例如,他認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禮記·中庸》)。基于這種社會道德教化的需要,故將歌頌男女愛情、夫婦關系的《關雎》置于《詩》之首,其目的是以家庭中的夫婦倫理、父子倫理為內核,漸次擴展至國家層面的君臣倫理,最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在“雅”“頌”部分,也有不少關于商周先王和君子德行的內容,例如,“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周頌·維天之命》)。孔子對《尚書》亦有刪述之功?。《漢書》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篡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為之序。”(《藝文志》)這表明,孔子刪定以后又按時代做了排序。從《尚書》中每篇都重視古代帝王的德行和社會教化看,孔子亦是以“可施于禮義”的倫理標準來進行甄選的。孔子廣泛吸納了《詩經》《周易》《尚書》中的“文王之德”“君子人格”和“時中”“敬”“德”等道德元素,將其融合、凝練和升華為圣賢人格的標準,塑造了先王們的圣賢氣象。
先秦儒家還將“五經”中蘊含的先王之道凝練并提升為歷史規律和政治智慧。中國前諸子時代經歷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禮樂文化的演進過程,在周公制禮作樂、拉開禮樂文明的序幕之后,“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成為周朝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殷周相比,一個殺氣騰騰,一個雍容文雅”[18](P236),由此形成了“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論語·八佾》)的局面。西周社會雖然尚文崇禮、敬德保民,但尚無清晰、系統的仁政理念和王道思想。孔子繼承了《尚書》《詩經》和《儀禮》?等元典中的周禮思想和“文治”之道,將周公的“德”“禮”理念升華為“為政以德”“為國以禮”的治世方略,正如楊向奎所說:“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19](P279)孟子和荀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繼續吸納“五經”中的政治倫理和王道思想,這從他們數十次引用《書》《詩》可見一斑?。經過先秦儒家的熔鈞六經和持續接力,零散、碎片地出現在“五經”中的王道思緒逐漸匯聚成為條理化、體系化的王道思想。
2.從倫理向度進行理論開新,為王道政治理想奠定堅實根基
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不僅表現為對元典中政治智慧的傳承,更體現為對王道政治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其理論創見凸顯出儒家王道思維的合理性和獨特價值。
孔子納仁入禮。對先王及其王道,孔子不是“述而不作”(《論語·述而》),而是既“述”且“作”、開拓創新。“雖然孔子未必直接參與《六經》之經書的寫作,不是《六經》的現代意義上的直接作者,但《六經》的思想與義理皆傳自孔子,是孔子‘即述即作’的結果。”[20]“諸子當中沒有一個人的思想與傳統之間像他那樣有密切的關系,他繼承了傳統,更重要的是,他把傳統作了創造性的變革。”[21](導言)孔子把原始宗教中的天神轉化為道德意義上的天命,在下學而上達的自我實現過程中開出天人合德的境界。在“述”“五經”的過程中,他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智慧,撰“十翼”?、作《春秋》,對中國王道政治倫理的模塑作出了重要貢獻。《易傳》是一部與孔子關系密切的古代哲學著作,具有濃厚的儒家倫理色彩,其中,以德配位的為政理念,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君子精神,“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的仁愛思想,以及由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依次析出的倫理規范等,都是孔子思想的延展。《春秋》被司馬遷稱為“禮義之大宗”,面對子弒其父、臣弒其君的家國亂局,孔子用“春秋筆法”褒善貶惡,用“微言大義”闡發政治理性,用禮義標準評價是非曲直,正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基于士大夫“八佾舞于庭”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等“天下無道”(《論語·季氏》)的亂象,他納“仁”入“禮”,為王道仁政奠定了基石。透過崩壞的周禮,孔子看到了禮樂制度中人性和情感的缺席,發現了禮儀形式背后仁義、敬誠、忠信的缺弱。“仁而不仁,如禮何?仁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他認為如果離開了仁愛之心,禮就會成為“鐘鼓”“玉帛”之類的虛文。另外,《論語》中夫子門徒的言語都可視為孔子之“作”的延伸。在孔子那里,仁是禮的內在本質和價值依據,禮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仁和禮相互為體、相互作用是孔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和貢獻”[22]。通過納仁入禮,孔子把禮從外在強制性的儀制規范變成了符合人性和情感需要的自覺要求,仁與禮成了合理規約人們言行的道德規范。經過孔子的改造,禮被賦予了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這種人倫之禮為周公設計的禮樂制度注入了內在活力,奠定了中國倫理型社會的政治基礎。因此,柳詒徵指出:“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23](P391)孔子的“仁學為中國發展出一個道德的宇宙,因而也形成了一個以道德為中心的文化”[21](導言)。
孟子立仁政于性善之基,置民眾于君主之上。孟子繼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將仁政確立為王道的標志,賦予先王之道以核心和靈魂。針對戰國時期“捐禮讓而貴戰爭,棄禮義而用詐譎”“道德大廢,上下失序”[24](序)的亂世,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論,設計了仁政的治世方略。他認為仁、義、禮、智四心是人們本有的良知良能,是國家推行仁政王道的人性基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他主張用“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人倫規范化解矛盾沖突。孟子以仁政應對當時的社會危局,將愛民置于仁政之首。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君王要得民心,就必須行仁政。他告誡齊宣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這種重民輕君的民本思想和平權意識是孟子王道政治思想中的一抹亮色。
荀子隆禮法于性惡之基,視禮義為“道德之極”。荀子提出了人性惡的理論,為禮法制度的實施找到了人性根據。“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荀子·性惡》)“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榮辱》)他認為禮能“義以分而和”,從而化解人際紛爭,抑制人性之惡。在荀子那里,禮被視為“道德之極”(《荀子·勸學》)、王道之寶。“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荀子·強國》)如果君王能夠“隆禮貴義”,國家就可達到“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的“至平”治世(《荀子·君道》)。荀子是繼周公、孔、孟之后完整設計出禮治藍圖的人,他秉承和發展了孔子關于“禮”的思想,標舉隆禮重法的治世方案,將“禮”提到了落實王道的重要位置。他強調:“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荀子·大略》)。荀子重視對歷史傳統的承繼,認為“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荀子·大略》)。在他看來,禮樂制度是三代圣王的偉大創造,應該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如果不加傳承,擅自改變,就是破壞“共予”和“共識”,最終會因破壞秩序而走向毀滅。荀子主張“法先王”,認為“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荀子·勸學》)。他批評惠施等人“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與孔孟不同,荀子還提出了“法后王”的思想。在荀子那里,“先王是指理想化的古代帝王,如堯舜;后王是指后來能實現封建統治和統一的理想帝王,如周文王、周武王”[25](P483)。荀子認為:“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荀子·性惡》);“欲知上世,則審周道”(《荀子·不茍》)。因此,“欲言治道,必以周文為據。周文是多少已在歷史上實現的,故據周文重整治道,遠比‘言必稱堯舜’的德化之治之理想來得更切近而有效。”無疑,“荀子法后王即是法周,這與孔子從周的精神正是一脈相承的”[26](P12)。事實上,相對于荀子所處的時代而言,堯、舜、文、武、周公都是“先王”,可以說“荀卿是以‘復近古’為‘法后王’的”[27](P7)。與“五帝”等遠古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近世之“后王”所表征的價值和意義。
3.用“允執厥中”作密鑰,為王道政治理想的實現提供方法論
中庸思想是先秦儒家“法先王”過程中最突出的創見。如果說“法先王”是先秦儒家構建的王道政治的理想藍圖,那么中庸就是實現這一藍圖的密鑰。對此,孔子居功至偉。“孔子思想有一個中心,有個‘一以貫之’的‘道’,那就是‘中庸’。”[28](P199)在儒家典籍中,中庸一詞始見于《論語》。而中庸的“中”字,作為一種道德范疇和哲學思想,在《尚書》中已有記錄。“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尚書·盤庚中》)在這里,“中”被作為一種美德。《尚書》記載了由箕子傳給周武王的“洪范”九疇大法,其核心范疇“皇極”就是將“中道”與“王道”合而論之。孔安國《洪范》之傳曰:“皇,大;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29](P459)所謂“大中”,即無過無不及的中道。其后,周公提出了“中德”的觀念,要求為政者“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尚書·酒誥》)。孔傳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29](P553)《尚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偽古文尚書·大禹謨》)這段話被后人視為儒家的“十六字心傳”,蘊含著儒學的真諦和萬世不易的真理,被歷代皇帝看作是治國的依據和寶典。“允執厥中”的中庸之道也被朱熹視為“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既正且直”的王道所應遵循的最高原則。其實,中庸本是王道的應有之意,如真德秀所說:“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真德秀文集》)《周易》所貫穿的“得中得位”和“時中”思想則揭示了中庸的實質。孔子在“五經”之“中道”思想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中庸之謂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他以“四絕”——“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要求自己,反對極端,批評“執一”,主張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泰而不驕”。龐樸指出:“‘中庸’之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猶如軸之在輪,其為‘至德’也宜矣!”[28](P204)后世儒家在此基礎上全面闡釋了中庸的價值和意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并將其視為“須臾不可離”之道。先秦儒家對中庸之道的凝練和闡發,揭示了古代先王修德治世的成功之法和王道政治的秘訣所在。
綜上,肇始于西周的“法先王”思想,經由孔、孟、荀的形塑、傳承與開新,“先王”變得越來越豐滿、完美和高大,“王道”變得愈來愈豐富、充實和完善。從表面上看,“法先王”帶有懷舊情調和復古傾向,但從實質上看,“法先王”并非厚古薄今,而是效法由儒家自己以“唯倫理性思維方式”形塑和凝練的王道政治理想。當然,“法先王”作為“闡舊邦、開新命”的政治智慧,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其合理性不僅表現為對傳統政治倫理思想的承繼、對當時社會道德和政治的批判,更體現為對中國王道政治范式的構建;其局限性不僅表現為唯倫理性思維方式所導致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泛倫理化、泛政治化的特征[30]和中華民族的實用性功利化傾向,而且體現在先秦儒家賦予“先王”“克力斯瑪”式神秘光環所產生的非理性魅力和神圣感掩蓋了權力統治的真相,以及王道政治藍圖的理想主義色彩。這種理想主義色彩與春秋戰國時期盛行的霸道之治極不協調,以致儒家常被譏諷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中國堂吉訶德,儒家的王道理想也被當時的諸侯貶斥為迂闊無用的“烏托邦”。然而,儒家思想的偉大之處,正在于它的理想主義,在于其以哲學層面超越性的意義整合所凸顯的獨特價值。今天,學界關于“走出王道”還是“重回王道”[31][32]的辯爭仍在繼續,毋庸置疑的是,“中國要清醒地學習西方,前提是能夠深刻地認識自己;要自信地走向未來,前提是能夠冷靜地面對歷史”[16]。儒家以“法先王”為名而構建的王道政治范式的價值,在于其不同于西方叢林法則和“以力服天下”的霸道思維,在于其協和萬邦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以德服天下”的王道倫理。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王道政治理想正是人類向往和未來努力的方向。
[注 釋]
①林毓生打響了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反思“五四”的第一槍。他指出:“許多五四人物為了提倡自由、科學與民主,認為非全盤而徹底地把中國傳統打倒不可。這是與自由主義基本原則完全違背的。而這種‘全盤否定傳統主義’卻直接引發了‘全盤西化’那種大概只能產生在中國的怪論。”此后,激進主義和徹底的反傳統成為“五四”的一大特征。見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5 頁。
②參見顧頡剛:《古史辨》第1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自序。
③范文瀾認為:“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復古主義者。”任繼愈認為,孔子“一生致力于維護正在崩潰中的奴隸制度(周禮)”。蔡尚思認為,孔子“是創作革新的敵人,傳述襲古者的恩人”。分別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206-207 頁;任繼愈:《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63 頁;蔡尚思:《蔡尚思全集》第4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77 頁。
④“視域融合”和“效果歷史”是伽達默爾詮釋學的核心概念。在解釋學看來,文本的意義存在于讀者視域與文本視域的融合之中;任何理解都是處于歷史中的理解,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見伽達默爾:《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431—433 頁。
⑤先秦諸子中,除了法家、名家少數學派反對“法先王”外,大都有其尊崇的先王,例如,儒家尊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墨家尊崇堯、舜、禹等,道家尊崇神農、黃帝等。
⑥潘德榮稱孔子對“六經”的詮釋方式為“德行詮釋學”,它是一種以“實踐智慧”為基礎、以“德行”為核心、以人文教化為目的的詮釋學。見潘德榮:《“德行”與詮釋》,《中國社會科學》2017 年第6 期。
⑦在《孟子》中,古代先王的名字高頻出現,堯42 見,舜80 見,禹21 見,湯26 見,文王33 見,武王14 見,周公14 見,這凸顯了先王地位之重要。
⑧劉澤華認為,“王道”的核心是“王制”,越是張揚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為一種理論追求,那么所謂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但這種觀點與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的歷史生成過程及內涵不符,儒家所法先王之“王道”的核心是“仁政”而非“王制”。見劉澤華:《論“王道”與“王制”》,《天津社會科學》2014 年第5 期。
⑨關于“先王”,后世儒家還加上了孔子,孔夫子被稱為“素王”。所謂“素王”,是沒有土地、沒有人民,只要人類歷史文化存在,其王位的權勢就永遠存在。《論衡·定賢》云:“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春秋》。”《經曲阜城》云:“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先生號素王。”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認為,孔子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無王者之位,故稱素王。
⑩“克力斯瑪”即英文Chrismatic(超凡魅力)的音譯,由馬克斯·韋伯最早使用,特指那些具有獨特人格魅力和超凡能力的歷史人物。
?《史記》中關于五帝的記載多來自《尚書》;《大戴禮記》雖成書于西漢,但據傳為孔子的弟子們所作、西漢戴圣所編,主要記載了先秦的禮制,是一部關于先秦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
?中國古代文化被稱為“史官文化”,這些史官大都具有儒家傾向。同時,古史中的帝系宗譜呈“倒敘的層累”現象,即在“神代”意義上越早出現的神話,出現在歷史文獻中的時間反倒越晚。例如,“少典氏帝系”(包括炎帝、黃帝)的形成晚在春秋戰國之際,《論語》中最多追溯到堯,《莊子》中黃帝乃至伏羲都有出現。而在西周時代,堯、舜還屬子虛之談。見謝選駿:《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2 頁。
?《洪范》作于何時,學界眾說多歧。徐復觀認為其為周初作品;劉起釪認為其為層累地加工而成,經過了周代史官的粉飾,最遲不晚于春秋前期;李學勤、裘錫圭根據叔多父盤銘文判定《洪范》為西周作品;姜建設根據陰陽與五行兩種學說結合是在戰國中晚期,判定《洪范》為戰國晚期作品。總體上看,學界認為該篇為西周初年作品的觀點占主流,本文采用此說。
?據漢代《緯書》記載,《尚書》原來有3240 篇,經由孔子刪至百余篇。
?關于《儀禮》的作者有“周公說”“孔子說”和“孔子后學說”,但無論哪種觀點,其中都包括有周公制禮作樂時創制的禮儀,體現著周公制禮作樂的宗法思想和等級理念。
?據劉起釪統計,《孟子》引《書》38 次,《荀子》引《書》22 次;阮元統計《孟子》引《詩》38 次;趙伯雄統計《荀子》引《詩》83 次。
?“十翼”即《易傳》。關于《易傳》的作者學界有爭議,有“孔子說”“孔子后學說”等,但一般都不否定孔子對《易傳》作出了重要貢獻。孔子本人“五十以學《易》”,對《易》推崇備至,并將《易》的精神傳授其后學。可以說《易傳》的內容基本上反映了孔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