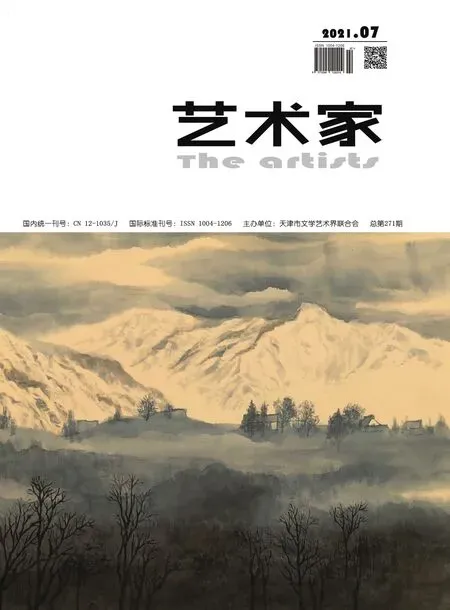湘楚意象繪畫藝術內涵研究
□段湘華 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科研管理處
一、湘楚意象繪畫
湘楚地區屬于亞熱帶茂密的叢林,楚人長期與飛禽走獸為伍,崇尚萬物有靈,這里孕育了巫楚文化、道家文化,接納過多次移民,在這里,多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兼容并蓄,形成浪漫瑰麗的湘楚文化藝術語境。莊子的散文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先驅,對楚文化有深遠的影響,《逍遙游》氣勢磅礴、意境高遠,《莊子·齊物論》中“莊周夢蝶”提出生死物化的浪漫哲思。《離騷》中“香草美人”的意象、楚辭《漁父》《莊子·漁父》中漁父的意象對中國傳統文人山水畫、花鳥畫、詩歌創作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南朝劉宋時期的宗炳隨做官的父親長期居住楚地,受湘楚文化、老莊文化的熏陶,融合佛家思想創作的《畫山水序》為以后的文人山水提供了理論支持。老莊思想、《楚辭》、“瀟湘”母題創作的山水意境、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藝術珍品,以及楚地彩瓷、灘頭年畫、苗繡等滲透著湘楚地域特色,奠定了湘楚意象美學的基調。
二、湘楚意象傳統美術的藝術內涵表現
(一)傳統的色彩藝術內涵
中國傳統“五色觀”(青、黃、赤、白、黑)千百年來形成別具一格的東方色彩文化。《孫子兵法·勢篇》稱:“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道德經》十二章載:“五色令人目盲”。五行學說,金、木、水、火、土,分別對應白、青、黑、赤、黃。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張興國總結出不同的朝代有相應的代表色,作為所謂的天命色彩,如夏朝崇尚青色,商朝崇尚白色,周朝崇尚赤色,秦始皇崇尚黑色,漢朝崇尚黃色。關于階層的用色,黃色為皇族的專屬用色,紫色是貴族用色,普通官員用青色,貧民用白色。經典詩詞中大量運用色彩代表階層,如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朱門酒肉臭”,劉禹錫《陋室銘》中“往來無白丁”,白居易《琵琶行》中“江州司馬青衫濕”,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之七中“淚滿黑貂裘”,黃巢《不第后賦菊》中“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中國的二十四節氣也有相應的色彩對應,如驚蟄的蝶粉、立夏的綠沈、秋分的藤黃、小寒的相思灰,表現了時節流轉間,物、色所沉淀的美和內涵。來源于自然的色彩,在人的世界中擁有了感情、觀念、寓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有相應的色系使用文化,并代代傳承。
(二)傳統湘楚工藝美術的藝術內涵
湘楚意象語境下的工藝美術擁有獨特的色彩體系和形式表達,如鳳鳥崇拜,崇尚黑色、朱色,彰顯了古老神秘的巫楚文化浪漫的情調。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系列珍品,如羅地“信期繡”用朱紅、棕紅、深綠、深藍和金黃等絲線繡流云、卷枝花草、長尾鳥圖案;黃褐色絹地“乘云繡”,具有現代文創價值,黃褐色絹地上用淺綠、淺棕紅、橄欖綠三色表現云紋,朱色桃形花紋中間鎖繡密圈呈眼球,似神鳥乘云狀,端莊明艷;云鳳紋漆盒,器表黑漆,器內紅漆,盒蓋用紅色漆勾勒出三只鳳鳥,形態互相呼應,線條精細,構圖嚴謹;T形“非衣”帛畫淡墨線和朱砂線勾勒,朱砂、藤黃、石綠、石青、白堊賦色,造型生動,技巧高明,營造了一個天上、人間、地下的絕妙空間,畫面上部呈現扶桑樹、玄鳥、彎月、神女、蟾蜍、神馬、神豹、門神,中部華蓋下是墓主人辛追夫人、婢女、家眷,下部有地神、鰲魚、怪獸、貓頭鷹,井然有序地展示著關于死亡、重生與永恒的宇宙圖景,雖然距今2200 年左右,但是畫面神秘浪漫的氛圍和色彩表現出的藝術成就依然無與倫比。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油彩雙層漆圓奩盒,黑底,朱、綠色卷云紋,用白色線條勾邊,這種處理方式一直影響著中西方的裝飾藝術表達。湖北江陵馬山一號墓出土的塔形紋錦,由小矩形構成抽象紋飾,淺棕、土黃、深棕、朱紅等顏色呈帶狀分布,顯得鮮艷多變、高貴華麗;四方神靈現華服——龍鳳虎紋繡羅單衣,以紅棕、棕、黃綠、土黃、橘紅、黑、灰等多色鎖繡技法繡成,龍鳳虎纏繞穿插排列,有種飄逸神奇的美,反映了楚人的宇宙觀和審美觀[1]。
楚地彩瓷主要包括長沙窯、岳州窯等,一般運用五種色:青、白、褐、綠、紅,唐代陸羽《茶經》稱“岳瓷皆青,青則益茶”,青釉褐紅彩是典型用色。其裝飾內容多用詩詞和山水畫,因為遠銷海外,裝飾有西域和印度等地的文字、宗教信仰圖騰,中西融會貫通,又有顯著的湘楚美學特質。
灘頭年畫就地取材,運用當地楠竹和礦物巖自制的“五色”紙,遵循道家五行的宇宙觀,融合梅山文化傳統,造型多以寫意手法,拙樸大氣。因梅山先祖崇拜火神祝融,尚赤,其一般運用丹紅、玫紅、群青、橘紅、藍、翠綠、煤黑等純色搭配,畫面明快喜慶,粗狂響亮,猶如楚人的個性潑辣又浪漫,展現了濃郁的楚南地方色彩[2]。
古代湘繡多用龍、鳳、虎等紋繡,表達對神明的崇敬信仰和貴族身份。近代湘繡成為閨閣必修,以山水畫、梅蘭竹菊和花鳥自娛。現代湘繡成為文創產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加入紅色題材,如《毛主席像》等。湘繡以針代筆,造型細膩逼真,色彩豐富。《雪宦繡譜》記載,湘繡有正色青、黃、紅、黑、白5 種,88 種原色,共745 種色彩[3]。苗繡具有極高藝術審美價值,運用苗龍、修狃、楓樹、蝴蝶、姬宇鳥、魚形等圖案傳承苗族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表達了對祖先與神靈的崇拜,主要運用紅、黑、花、青、白等色彩,常用互補色搭配表現明快鮮艷的視覺效果[4]。土家織錦的“西蘭卡普”常用玄、赤、青、白、黃等色彩,多以幾何形、菱形連續對稱形成小蛇花、陽雀花、臺臺花等紋樣,記錄土家族的起源和美麗傳說,設色古樸厚重又不失艷麗。
(三)以“瀟湘”為母題創作的文人山水意境
傳統文人山水畫構建出特有的瀟湘意象思想圖譜,梳理其文化脈絡,不難發現,其從未曾離開過湘楚意象美學的語境,以“瀟湘”為母題創作的文人山水畫成為傳統山水繪畫的重要組成部分。五代、唐宋時期,楚地成為貶謫重地,杜甫、柳宗元、范仲淹等一流大文豪寫下了許多與瀟湘相關的著名詩篇,從董源《瀟湘圖》到宋迪《瀟湘八景》,瀟湘圖被反復再創作,歷代“瀟湘”母題創作的文人山水畫不勝枚舉,“瀟湘”從楚地重要的水域演變成跨越時空的美學意象群。漁父圖像符號和漁隱意象是傳統文人山水中最常見的表征,漁父的概念可追溯至楚辭《漁父》和《莊子·漁父》,“漁父”是“隱逸”的代名詞,是班固《漢書》里的“上中仁人”,是遠離功名的世外道人,是通達世事、歸于平淡的禪修者,也是等待時機準備出仕的謀略家。湘楚意象美學中“漁父”所喻的文化內涵引發了歷代文人畫家的共鳴,漁隱意象的表達穿越整個文人山水的創作歷史,經久不衰。瀟湘八景指江天暮雪、山市晴嵐、瀟湘夜雨、煙寺晚鐘、遠浦歸帆、漁村夕照、洞庭秋月、平沙落雁,這些對仗工整的名詞被賦予深意,專家考證瀟湘八景對應湖南的八處風景名勝,其分別在張家界、崀山、衡山、巴陵、紫鵲界、莽山、酉水、壺瓶山。文人山水畫從一開始就承載著太多的內涵,宗炳最早提出山水畫“暢神而已”是為“臥游”;米家山水“自適其志”,抒寫“胸中盤郁”,是“墨戲氣韻”;倪瓚的畫是“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文人畫家通過山水繪畫這一文雅的方式,來表達被貶謫后的悲傷和無奈,含蓄地表達了政治異議,是高潔修為的標榜,也是對詩意棲居的向往。
三、湘楚意象繪畫的當代表達
當代本土畫家自覺運用湘楚意象進行創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風景油畫大家陳和西、繪本大師蔡皋、油畫大家段江華。
陳和西的作品利用豐富的色底進行作畫,借鑒版畫的技巧,描繪路邊的草、田壟菜園、尋常人家,逸筆草草和兼工帶寫并存,畫面靈動和深沉相映,灑脫又莊重。他主張風景的描繪就是心中詩意棲居的所向,作品多沿用馬王堆古樸典雅的色彩體系,如玄黃、黑色、深紅、湛藍等,富有裝飾意味,也有文人水墨意境。
蔡皋的作品充滿了不求形似的逸趣,喜歡用黑色調作畫面結構,如《寶兒》中的黑色框架下,人物、場景和物件色彩活潑、憨態可掬,又文雅至極。她的畫是一種自我療愈,她曾經下放到農村作小學老師十多年,向往田園生活,感恩那段鄉村歲月帶給她的美學熏陶,所以畫出《桃花源的故事》。她的《花木蘭》表達了樸素的精神訴求,直面艱難的生活;《孟姜女》是對生命的感喟;《月亮粑粑》的色彩猶如絢爛的交響樂,充滿了湘楚藝術的浪漫氣息。
段江華運用西方表現主義形式和綜合材料技法畫歷史題材,他的《王和后2 號》選取馬王堆題材,突破了油畫范疇,充滿了歷史的厚重,技法形式前衛。他用標志性的建筑,樓、墻、碑、塔、廣場、城、遺址表達了沉重的歷史感和湘楚意象,被認為是中國油畫史上里程碑式的存在。
結 語
創作者受地域文化影響,自覺將本土文化藝術中集體無意識的美學影響因子傳承在作品中,形成賦有地域意象美學的藝術。湘楚意象繪畫將傳統湘楚意象美學元素融入繪畫創作中,表現了湘楚特有的地域美學意象和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