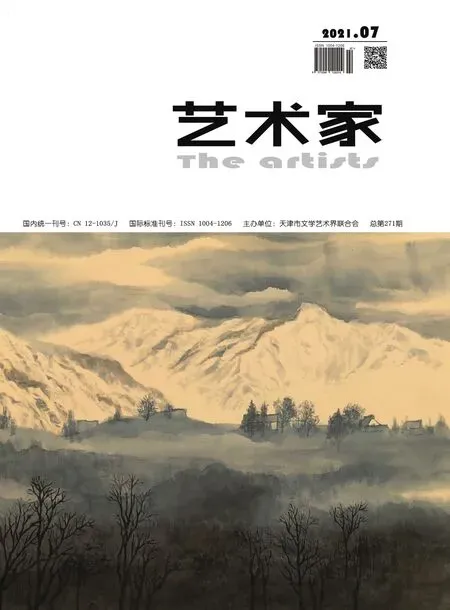新藝科:學科擴容與人才培養的內在辯證
□劉 彧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在信息化、技術化蔓延至學術界的當下,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范疇的藝術學,需要重新梳理學科現狀,遵循內在規律與邏輯,以自身的發展需要對新文科趨勢做出積極回應。藝術學科要想實現其學科進一步前進,必須重新厘清和規劃其學科本體內涵、與其他人文學科間的關系,以及探索“新文科”大視野下藝術類人才培養的新模式。
一、在新文科視野下思考藝術學科的歸屬、本體與前路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學科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有著千絲萬縷、一脈相連的結構性關聯。在深入探討“科際融合”前,我們首先應對藝術學科的本體進行界定,歸納與判斷藝術學科主體性最重要的內涵是什么。這并不是用概念將藝術束縛在一個本質主義色彩的框架之下,而是要分辨出藝術學科的異質性所在,其所指何為。
藝術學科本體應是“美”與“真”并行與交融的存在。藝術是感性與感知共同體的集中體現,是富有構造性的想象力與物質媒介形態的結合。藝術因其具備可見性的實踐形態而被關注,因高水平的技藝與創作被認可。藝術是審美性與科學性的綜合體,創作與理論是藝術學科的一體兩面。在建構“新藝術學科”(新藝科)的當下,我們首先要改變由于不完全符合現行評價標準,因而認為藝術學缺乏“科學性”的狹隘判斷。因此,從本體論考察作為“真”與“美”聯結與互證之共同體的藝術學就構成了“新藝科”建設的起點、前提與關鍵。
但是,“藝術不僅是一個美的問題,而是與整個文化各方面都緊密相關的問題,只有進行多樣性的跨學科研究,才會把藝術多面的特性豐富地展現出來”[1]。實際上,藝術學需要被置于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之下加以考量,在更深層次上重新權衡藝術在文化坐標系中的定位,立足時代,在實踐中與多學科進行密切而深入的交流與對話。只有重新思考藝術學科的歸屬與本體,藝術學科才能夠真正跟上“大文科”的步伐,吸取成熟學科的給養,從而在更為廣闊的人文社會語境中,挖掘藝術學科自身更為深刻的學科內涵。
二、共生與共振:藝術與非藝術的“跨界”
各個學科發展有其內部生長的必然動力與自覺意識。同時,為適應時代性要求和社會趨勢,學科建設亦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外部環境會解構其體系中脫節的知識結構,重構學科發展姿態,重新書寫其發展軌跡。
新技術文明催生了新文科理念。在人類社會邁入5G 時代,基本實現“萬物互聯”的必然趨勢下,我們的教育體系格外需要新文科理念。在數字化生態下,文科學術話語界域也必然不能是“孤島化”的形態,藝術學科內部的分野對立局面也要尋找走向具有“間性對話”的新型藝術學科體系,同時打破學科間的障礙與專業壁壘,從而產生合力效應。
學生如果僅學習藝術中的一種單向度的知識,就會囿于現有的框架,必然會在認知上形成一種封閉的圈層。藝術學科內部必須以應用和實踐為方法,從而彌合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縫隙,構建實用藝術與純藝術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高屋建瓴的可知性必須與能夠實踐的可行性相結合。
因此,學科間邊界的擴容應該成為自覺性的態勢。藝術學科只有培養學科間的融合思維,在與其他學科對話中,豐富目前的研究對象、方法論與理論范型,才能對當下的藝術形式予以更加深刻的討論。例如,動畫利用了現代科技手段與美術繪畫的有機凝合而產生的全新的藝術形式;當代電影更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不僅與科技進步相聯系,而且覆蓋了傳統文化、當代社會生活經濟因素及對未來的烏托邦沖動”[2]。
為了能夠迅速趕上當下科技時代涌動的潮流,例如AI 技術的進步、“互聯網+”的推進、區塊鏈與數字經濟的迅速蓬勃發展,對藝術學科與藝術人才的培養也必然要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求藝術學科必須具備更強的綜合性與開放性。藝術學科未來可以從以下方向入手探索進一步融合的路徑與方式。
(一)藝術與其他人文學科的結合
藝術與文學、哲學等均屬于意識形態,每門學科都包含著理性、感性與審美的精神文化現象,相互之間在拓寬思維、補充學理上可以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知識場域,構建“新文科共同體”。例如,藝術史中的視覺性問題,從視覺對象的角度切入探討,經常被認定為是社會文化建構而成的,總是與哲學、文學、社會學與歷史等相關;克拉里的注意力譜系從福柯的“知識型”考古學而來,并推論出一種具身化的觀察者。因此,其他人文科學將給藝術學科帶來更多的啟迪與理論推進。
(二)藝術與技術的結合
目前,AR 與VR 技術的應用在數字媒體藝術中具有諸多革新性的影響,例如,其虛擬的創作模型對公共空間的重構與超現實的開發,對再媒介化的影視產品創新等。許多其他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諸如虛擬數字技術與人在微觀上交互的深入,未來將會深刻改變人的感官知覺模式,這在宏觀層次上將促使學界圍繞藝術與技術之間的關系產生一種哲學上的思考。雖然諸多理論批評家對科技持有批判的態度,并認定技術帶來的工具理性主義使人類日益走向自動化模式,但不可否認的是,將藝術賦予技術,可以為技術增添無限的預見性與想象力。
(三)藝術與社會的結合
美國著名藝術社會學家溫迪·格里斯沃爾德吸收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理論模型,提出了關于世界、文化客體、藝術家和觀眾的“文化菱形”(Cultural Diamond)理論,使用一種科學化的社會學方法對藝術外部的組成規律要素進行了研究。藝術的社會性研究問題還包括藝術的生產與接受、藝術的商業組織與產業銷售等,這些都為藝術社會現象的分析提供了溝通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有效渠道。
三、時機與契機:藝術人才培養轉型必經的轉折路口
藝術學科要想在未來繼續邁進,首先需做到藝術類人才培養的轉型。事實上,“新文科”這一概念由美國希拉姆學院于2017 年率先提出,是指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的課程中,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跨學科學習。例如,交互設計專業是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MU)的強勢學科,一部分設置在藝術學院的設計系中,而側重于通信、工業、人機等方向的交互設計分別設置在工程學院及計算機學院。CMU 具有強大的理科背景和計算機專業的實力,因此,每個藝術類專業都加入了科技的影子。這為我們的新文科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和方向。
藝術與人文學科乃是大學教育的靈魂,藝術教育與人才培養戰略應以藝術學科發展為基礎,保持人才培養與學科發展呈平行螺旋式上升的態勢。課堂是學生獲取知識的最直接的途徑。因此,我們可以從打通二級學科專業課程設置著手,推動人才培養轉型模式的突破,從而使學生更傾向于關注社會發展的前沿問題,最大限度地觸及、掌握不同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鼓勵他們拆除思維邊界而讓創意肆意流溢。具體實現方式包括以下幾點。
(一)推動藝術二級學科內部的“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互補融合
僅強調理論學習則會忽視藝術實踐下感性美學經驗的獲得,而這類經驗又是藝術作品生成中的重中之重;只強調技藝的高低,則會忽略綜合素質培養的初衷,人文知識可以使技藝、技法增添厚度與深度,讓創作不只是一種直覺性、情緒性的表達,更是經過思考后,擁有理論支撐的人文作品,增加了理性的厚重感。所以,單獨強化哪一方面的訓練都是孤立與片面的,會使學生形成學術體系上的割裂。
(二)定制綜合性且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人文社科課程群
藝術教育應以藝術學科為知識體系基礎,同時以“大文科”教育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與此同時,根據動態的人才培養模式進程及時調整、革新課程設置,為具體的新文科人才培養不斷注入活力。鋪設以藝術為核心,以其他人文學科為放射性結構的、綜合性的、各方面知識均衡的藝術課程體系,學生應在“創作、批評、藝術史及美學四個領域進行螺旋遞進式的學習”[3]。從表層看,實踐類學科與理論類學科之間有著一定阻隔,實則在學術歷史上,學科之間常常互相借鑒、啟發,均可以實現互通有無的交叉與融合。
(三)藝術生產要樹立立足現實并面向未來的培養目標
藝術實驗室化不是強行將實驗與藝術進行嫁接,而是以考察市場機制為方式,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和洞悉社會問題的能力,將藝術產出與國家事務聯系起來。目前,哈佛大學已經建立了藝術實驗室,對跨學科藝術實踐研究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結 語
一個學科如果只在自身框架范疇定位內,勢必形成“內卷式”的發展模式。只有“開窗通風”,才能形成學科間良好氛圍的“對流”,并立于其他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哲學與歷史學,它們與藝術學科的研究對象、方法不盡相同,而且跨學科的常態化更無法一蹴而就,但這也是新文科建設面對的挑戰。在當下社會發展和學科建設的必然趨勢導向下,我們需要通過反復嘗試,力圖使藝術學科逐漸擴容,從而有全新的學術增長點與話語權,最終形成具有中國語境特色的藝術學科與人才培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