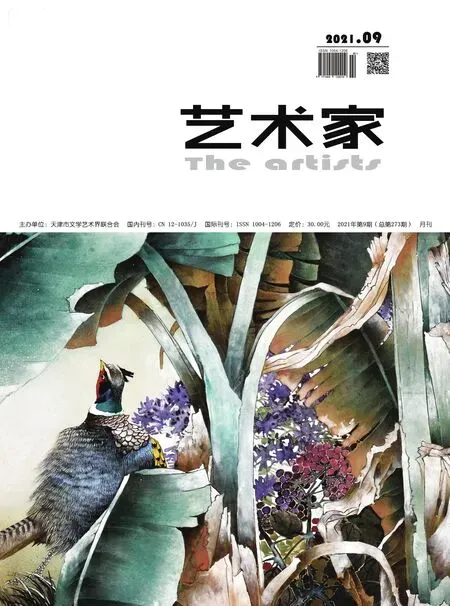把農村人的希望和現實畫出來
——談唐德福的水墨人物畫
□張 娜 重慶美術館研究部
中國的社會變遷深刻影響著城市與鄉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唐德福在現實主義人物畫領域為我們總結了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為傳統技法向當代轉換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唐德福把當代人的意識和觀念融入作品,搭建了與時代直接對話的通道,完成了藝術母題在當下的轉換。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文化語境中,唐德福圍繞時代和百姓的生活,聚焦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故事,懷著對傳統文化價值的認同和延續民族文化的傳統文脈的初衷,以東方獨特的思維方式展開了對水墨人物畫的現代話語轉換,并以獨特的筆墨、生動的語言,描述了當下巴渝紛繁復雜的市井百態和新山村的風俗畫卷。出身于農村家庭的唐德福曾在他的中國畫作品《春喜巴山》創作檔案中提道:“要把農村人的希望和現實畫出來。”唐德福對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當下生活體驗和精神狀態的關懷,不是理想的或者浪漫式的遐想,而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和告白。
一、形式語言的內在建構
唐德福細致地觀察和體驗著巴渝地區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的生活狀態,始終在創作中保持著和緩舒展的精神狀態。他的水墨畫人物創作大多以描繪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的現實生活為題材,采用大場景,畫面人物動輒百余人,客觀真實地描繪人物形象,并刻畫出其獨特的姿容、神態、個性,頗有難度。正如范璣所言:“畫以有形至忘形為極則,惟寫真以逼肖為極則,雖筆有脫化,究爭得失于微茫,其難更甚他畫。”[1]唐德福習慣用相機記錄普通老百姓演繹自己生活故事的瞬間。經年累月的素材積累,使他對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觀察更為細致,對人物形神與心理活動的處理也更加游刃有余。面對物象時,他對大場面的經營位置、比例透視,對人物群像從形態到神態,對技法從線的排布到疏聚布白,一一做到胸有成竹,由心生畫,眾生百態,工寫結合,神形頓生,是“傳其神”“寫其心”的典范。
唐德福以“徐蔣體系”北方人物畫技法為基礎,塑造人物形象時,提煉概括現實生活中人的典型特征,并融匯了南方人物畫的特點,注重筆墨情韻。畫家以寫實手法,高度提煉并概括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以工筆為主,兼局部小寫意襯景的手法進行創作,從畫面中心人物到遠景,用工筆的形式深入刻畫畫面中的每一位人物,在每個人物形象的不同細節中,細致、妥當地處理不同人物的形態與眼神,在普遍性的基礎上強調不同人物的個性特征,在關鍵處著意刻畫,突出平凡中的不平凡之處,用精練、準確的筆墨語言將情感浸透于筆墨中。這也是畫家在繼承“徐蔣體系”的寫實主義水墨體系中所做出的學術性思考。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神情傳達上,畫家秉持“傳神”的藝術精神,由心生畫,由心作畫,用豐富且有層次感的筆墨語匯塑造了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樸實動人的生活百態,畫中的人物形象也凝結為新時代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精神面貌的縮影。
在中國畫創作與教學中,“徐蔣體系”的素描寫實訓練容易導致人物形象板滯,而筆墨則倡導表現力與靈性的發揮。西方寫實語言的再現性和筆墨的表現性,在唐德福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沖突。唐德福在水墨人物創作實踐中,對寫實語言不斷進行反思與消化,積極思考如何利用傳統筆墨語言來塑造人物形象。在群像人物的處理中,畫家筆下的人物形象盡管嚴謹寫實,但是筆墨已經有了很大的主動性,不僅追逐物象表層的陳述,還集中于更為深刻的生命與精神體驗。寫實水墨人物畫作品在創作語言和藝術風格中很難擺脫寫生狀態。唐德福在群像人物創作中,非常重視結構因素和線的表現力。
唐德福擅畫人物群像,作品中人物繁多,以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為原型,力求每個人物形象刻畫均細致、具體,個性氣質鮮明、獨特,用樸實的繪畫語言賦予畫面躍動的生命感。畫家嘗試通過各種具體的場景將新山鄉的生活畫卷一一展開。他對人物形象性格的研究深入具體,對人物個性氣質的表現鮮活、生動,對人物復雜的內心狀態的描繪細致入微,對人物形神的刻畫筆簡意深。畫家賦予了畫面中每個人物特定的個性,真實地展現了每個人物的不同形態,捕捉了每位人物復雜而微妙的心理感受。
唐德福對新時代山鄉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創作靈感,并不是來自兩三次的藝術采風或者幾次的“農家樂”玩耍。在人物畫創作實踐中,唐德福是一個“在場者”,他的創作視角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深入體驗和親身經歷后的一種更有溫度的關懷。他描繪新山鄉百姓生活的作品,更像是以一個“在場知情者”的身份,以自己的生活為創作原型,親繪的圖畫傳記,也不失“旁觀者”的冷靜與思考。經過主觀的藝術化處理,他的作品既感性又理性,滿目現實,又充滿期望,真正做到了“把農村人的希望和現實畫出來”。
二、現實主義的人文情懷
中國人物畫在傳統美學體系的影響下,長期受到“成教化、助人倫”的思想約束,誠如曹子建所謂存乎鑒戒者,圖畫也。張彥遠所謂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者也”。如果把人物畫局限于寫實求真的現實意義,未免過于膚淺。人物畫自誕生之初,就繼承了儒家思想的現實關照精神,被賦予了記錄時代特征的使命。唐德福直面人性,直面現實,延續并創新人物畫的筆墨語言,真誠地記錄時代特征,描繪新山鄉百姓現實,反映當下社會變遷,將自身對人性的認知與表達,對新山鄉百姓的現實關照與人文關懷通過畫面的形式語言和筆墨造型進行有溫度、有情懷的呈現,實現中國人物畫人品與畫品、語言與精神的高度統一。
唐德福作品中強大的現實主義創作慣性與人文情懷與他自身的生活經歷和人生體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早年的農村生活及在四川美院國畫系的學習經歷,奠定了唐德福現實主義人物畫創作實踐的基礎。時代、社會、家庭、性格等多重因素使他對人性與現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完成了對新時代山鄉百姓現實與希望的精神追問。與生俱來的人文情懷使他對現實、社會和生活有著深入、細致的觀察與理解。
《老屋梨花綻笑顏》中呈現了豐都山村蔚為壯觀的社壇壩壩席——一個廚師,一口鍋,一頓一兩百人的露天農家飯。《春喜巴山》中描繪了山鄉舉辦的新式婚禮。新時代山鄉生活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畫家用作品記錄的不僅是一對新人幸福的瞬間,還有社會的變遷和時代的烙印。《老屋梨花綻笑顏》《春喜巴山》所體現的新山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源于畫家對真實呈現的訴求、對時代精神的關注,還與他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出身農村家庭的唐德福,親身經歷了農村的日常生活,目睹了新時代農村生活的變遷和百姓精神狀態的變化。他對農村這種天然的血濃于水的樸素情感,影響了他的人物畫創作實踐,孕育了他創作實踐中的現實主義情懷與人道主義精神。他對鄉村生活的真實感受和對百姓精神的深度關懷和情感傾注,是一種家園情懷、民族情懷,更是一種家國情懷,是他對人性的認知與關懷,對人生的體驗與感悟,對社會的理解與表達。唐德福在四川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的學習經歷深受“徐蔣體系”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影響,繼承了徐蔣寫實人物畫的實踐經驗,尤其是對人生與藝術的態度,現實主義創作慣性、傳統儒家思想的現實關照精神、知識分子的內在修為、對現實社會的真實感受、對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的真切關注、對樸實人性的深刻表達等,始終貫穿于他的人物畫創作實踐中。
結語
石濤說:“筆墨當隨時代。”唐德福熱衷于描繪他所熟悉的山鄉人民、市井百姓的真實生活,兼顧寫實技巧與寫意精神,將詩情畫意的意境融入其人物畫創作實踐中。他將目光穿梭于山鄉社壇壩壩席、農村婚禮、田里耕作的農民、城市里的棒棒軍、小面店里的廚娘等,將個人的情感力量融于形式語言,以增強畫面張力,用個人的主觀感受呈現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直指他們的生命價值與精神意義。畫家對自身體驗和內在感情的表現、對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的關注、對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的思索,使他的作品始終縈繞著一種最樸素的溫情和最真摯的希望。唐德福擅于組織大場景,畫面頗具視覺張力,給觀眾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人物造型語言生動凝練,人物眾多卻不顯冗余,所有人物均統一于同一個主題,以簡單、質樸的形式語言細致入微地刻畫每處細節,力求將自己最樸素、最真誠的情感傳遞出來,在溫情的敘事中融入對善良與希望的美好訴求。這體現了他對人性的關懷,對新時代山鄉人民和市井百姓生活現狀和精神面貌的深度表現,彰顯出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他的作品直指現實,直抒情感,直面人性的生命價值與精神意義。畫面中的每根線條、每塊墨色、每個人物、每處細節,都承載著畫家個人的情感力量,飽含溫情與堅忍,蘊含了現實主義的人文情懷,把“農村人的現實與希望”通過畫面的形式語言進行了極致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