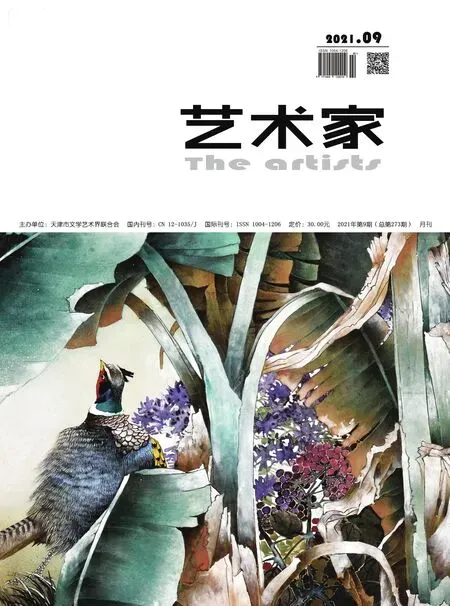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文獻綜述
□蘇 丹 中國音樂學院
一、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現狀
研究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現狀的文章,有樊祖蔭教授在第二屆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研討會上的報告《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與教育現狀及展望》,樊祖蔭教授從四個方面概括了民族音樂教育領域:隊伍逐漸壯大;成果不斷涌現;教育漸被重視;學科縱深發展。他在文章中提道:“近年來少數民族音樂事業加入了許多青年力量,一大批音樂專業的碩博生紛紛加入了這個隊伍,這使得民族音樂事業改變了原學歷結構,使研究的課題更加的多樣,學術視野也變得開闊。”[1]此外,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成果不斷涌現,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三個研究方面更為集中,即少數民族樂種、宗教樂種研究和民間樂種研究。理論整體的整理、完善和發展對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學科建設具有指導作用。在理論基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少數民族音樂教育長期被忽視甚至漠視的狀況有了較大的改變。
二、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目標
研究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目標的文章有張應華和謝嘉幸載于《中國音樂》的《我國當代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目標、功能探析》,文章中很明確地說到少數民族音樂學校音樂教育的目的有兩大方面:理解多元文化發展,參與文化交流和合作;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培養新一代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播者[2]。其中重點提到21 世紀教育最重要的特征為多元文化教育,文化理解是世界民族音樂教育的基本前提,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發展少數民族音樂教育能使學生更加了解各少數民族的音樂,尊重不同地區的民族音樂,理解包容音樂文化的多樣性。此外,“非遺”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寶貴財富,保護“非遺”不僅是一個文化問題,也是發展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路徑之一。
三、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策略
研究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操作策略的文章有張應華和謝嘉幸載于《音樂藝術》的《我國當代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討》。筆者總結了兩位知名教授的觀點:(1)課程經驗反思,根據地區和施教對象的不同,可將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分為“少數民族音樂專業教育”“師資教育”“高校教育”及“中小學教育”四種類型;(2)課程觀念的批評,引用趙塔里木教授的一句話總結“目前課程的內容基本是歐洲傳統音樂文化的經驗總結,而民族音樂文化的知識充其量只是‘民族化’口號下面的,沒有實際內容的點綴”,這句總結引人深思。(3)課程結構的探討,民族音樂教育的整合模式——基礎層面的整合、學校規范教育與自我傳承教育——結構層面的整合;(4)教材建設及其資源利用等——教材建設的結構探索及教材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結合以上觀點,筆者總結出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策略:(1)教學方法需要實踐創新,從民族特色出發,“請進來,走出去”,開發新模式;(2)師資建設與培訓,建設以民間藝人為必需的教師隊伍,把握本土音樂文化變化的脈搏,同時培養新一代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專職教師;(3)教學評價策略,借鑒藍雪霏教授的“綜合式測評方式”,即“課后演唱民歌”“期末知識測試”和“演講民間音樂節目”等;(4)教學策略的理性思考,借鑒教學論、系統論等不同學科領域的觀念對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教學予以觀照,進行有效的探索和研究[3]。
四、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在高校音樂教育中開展的實例
內蒙古地區和新疆地區高等藝術院校開展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實例有郭德綱載于《中國音樂》的《論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傳承與內蒙古高校音樂教育》。郭德綱為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原院長,他在文章中提出,高校對加強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缺乏重視,以及目前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在內蒙古高校中有缺憾,其總結現狀并對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做了以下指導:在采風中體驗少數民族音樂,并在實地體驗中把理論和實踐進行有機結合,為實踐搭建展示的平臺,以采風促進高校教學等[4]。內蒙古師范大學開設了民族音樂系列課程,如蒙古族音樂史、馬頭琴藝術、長調藝術、呼麥演唱、民歌模唱、民族音樂學、內蒙古鄉土音樂概論等,并擁有中國少數民族藝術碩士點,有“長調演唱與理論研究”“馬頭琴與理論研究”和“北方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三個方向。這是極具本土音樂特色的音樂教育,筆者認為這一點可被高等師范學院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廣泛借鑒,以培養少數民族音樂傳承及教學人才。關于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章有肖學俊載于《新疆藝術學院學報》的《對新疆藝術學院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回顧與思考》[5]。木卡姆藝術是新疆主體民族維吾爾族的集歌、舞、樂于一體的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形式,新疆藝術學院有專門的“木卡姆”專業人才培養基地,培養本科層次的人才,對新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做了革命性的舉措。
結語
少數民族音樂乃是少數民族精神的所在,是中國音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最為光彩的一部分[6]。少數民族音樂能夠自成一派,充分顯示了各民族音樂的獨特性,因此,實現少數民族音樂的傳承和發展對中國音樂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7]。以教育的手段實現傳承的目標是每個藝術工作者努力的方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的少數民族藝術會擁有完善的學校音樂教育,并獲得良好的傳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