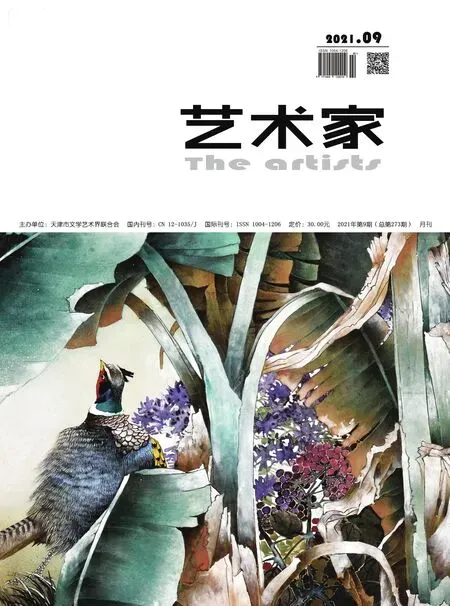田漢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鑄成的抗戰(zhàn)精神武器
□周 熹 鄧德祥 邱戀淇 王夢楠 重慶郵電大學(xué)
精神是人類意識、思想的高度凝結(jié),藝術(shù)作品通常蘊含著由藝術(shù)家的意識和思想構(gòu)筑起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藝術(shù)家的精神和藝術(shù)價值觀。回望20 世紀上半葉充滿硝煙與死亡的抗戰(zhàn)年代,抗戰(zhàn)烽火將一批先進文藝人士推向時代前沿,激發(fā)他們在創(chuàng)作時對個體與集體、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思考,為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創(chuàng)新、升華做出了貢獻。田漢就是這樣一位用藝術(shù)進行革命的先驅(qū),他以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撐起抗戰(zhàn)藝術(shù)的精神大旗,以抗戰(zhàn)藝術(shù)鑄就抗戰(zhàn)的精神武器。
一、民間戲劇啟蒙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
田漢是著名革命家、文藝批評家、中國現(xiàn)代戲劇三大奠基人之一,出身于湖南省長沙縣東鄉(xiāng)茅坪田家塅一個貧農(nóng)家庭。在湖楚之地的三湘四水中,皮影戲、傀儡戲、花鼓戲和湘戲等民間藝術(shù)紛紜多樣,是田漢學(xué)習(xí)戲劇的啟蒙和起點,也是田漢在負責抗戰(zhàn)宣傳時期文化眼界高遠,又站在平民立場進行創(chuàng)作的原因之一。
皮影戲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tǒng)民間戲曲形式,是由影戲藝人操縱平面皮影,通過燈光將影像透映于幕窗上并配以音樂和唱念來表現(xiàn)劇情的一種傀儡戲[1]。皮影戲在劇目的選擇上多為傳統(tǒng)的歷史典故、寓言童話等,如鑿壁借光、精忠報國、三打白骨精等。皮影戲的語言是當?shù)氐姆窖院统唬瑑?nèi)容通俗易懂且妙趣橫生。因此,皮影戲不僅是老百姓閑時的娛樂項目,還是開展啟蒙教育和道德教育最普及和有效的方式。皮影戲等民間戲劇和藝術(shù)以其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結(jié)合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內(nèi)容,實現(xiàn)了超越文字的交流和情感共鳴,對田漢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的形成產(chǎn)生了很深的影響。可以說,田漢在民俗藝術(shù)的影響下既擁有精英知識分子的思想,又兼?zhèn)淦矫竦牧觥L餄h在進一步掌握了戲曲藝術(shù)的形式后,認為“廣大軍民最熟悉的藝術(shù)形式便是舊劇”,并認識到中國民眾,尤其是中國農(nóng)民對民俗藝術(shù)有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因此在抗戰(zhàn)時期的曲藝創(chuàng)作中將抗戰(zhàn)主題暗寓其中,為抗戰(zhàn)在民間進行了有效而廣泛的宣傳。抗戰(zhàn)十四年,田漢通過這種形式為祖國和民族的命運奔走疾呼了十四年。
田漢遵循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同時將“藝術(shù)以其民粹性和傳播性而成為政治的先驅(qū)”的觀念在文藝界進行宣傳和呼吁。他在為抗戰(zhàn)漫畫宣傳隊的機關(guān)刊物《抗戰(zhàn)漫畫》推出“全美術(shù)界動員特輯”的序言中表明立場,無論國統(tǒng)區(qū)還是解放區(qū)的文藝先進工作者必須形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聯(lián)合呼吁團結(jié)抗戰(zhàn)的精神,并提醒藝術(shù)家不要因國難困頓于個人的精神世界而難以釋懷,鼓勵藝術(shù)家放棄崇奉個體價值和創(chuàng)作自由,加入社會變革、抗戰(zhàn)救亡的運動中。
二、平民藝術(shù)引領(lǐng)抗戰(zhàn)運動
抗戰(zhàn)烽火將藝術(shù)家推向時代的前沿,催生了一批以民族獨立、救亡運動為創(chuàng)作主題的藝術(shù)家。他們匯聚到上海這個全民抗戰(zhàn)的樞紐,惺惺相惜。
田漢對民俗曲藝藝術(shù)有較高見解,也在美術(shù)上有深厚的造詣。1925 年,徐悲鴻慕名拜訪田漢,兩人之交從此正式建立。1926 年,田漢在上海成立南國藝術(shù)學(xué)院,邀請徐悲鴻擔任美術(shù)系主任。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來往,徐悲鴻將田漢引為知己,并達成共同的藝術(shù)觀點——要將平民藝術(shù)的引領(lǐng)價值發(fā)揮到抗戰(zhàn)運動中。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藝術(shù)實踐中,田漢與徐悲鴻成了莫逆之交,建立了深厚的戰(zhàn)斗友誼。1935 年初,田漢被國民黨逮捕,徐悲鴻曾言:“垂死之病夫偏有強烈之呼吸,消沉民族里乃有田漢之呼聲。其音猛烈雄壯,聞其節(jié)調(diào),當知此人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亡。”徐悲鴻與田漢的共識既是二人友誼的見證,也昭示著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的發(fā)端。
田漢和郭沫若是革命戰(zhàn)友。二人早年“以詩交友”,為共同的文學(xué)事業(yè)吶喊;抗日戰(zhàn)爭中“以筆為武器”,不斷激勵廣大同胞自強不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共同為中國的文化藝術(shù)事業(yè)而奔波。田漢曾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表示,在藝術(shù)觀上提倡新浪漫主義和平民立場,要做中國未來的易卜生。他強調(diào),“我們做藝術(shù)家的,一面應(yīng)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來,排斥世間一切虛偽,立足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當引人入一種藝術(shù)的境界,使生活藝術(shù)化(Arti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Beautify),使大家忘掉現(xiàn)實生活的苦痛而進入一種陶醉法悅渾然一致之境,才算盡其能事”。
被侵略民族為求生存而抗戰(zhàn)是神圣的,唯有充分表現(xiàn)這種真實的文藝才是目前真正的藝術(shù),才有它歷史的不朽性[2]。田漢等抗戰(zhàn)文藝工作者站在民族主義的高度進行平民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代表廣大同胞為捍衛(wèi)國家和民族尊嚴發(fā)聲,既拉近了藝術(shù)與人民的距離,又對發(fā)揚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藝術(shù)創(chuàng)作筑起抗戰(zhàn)救亡的鋼鐵長城
田漢同全國人民一道,在國難當頭時擔負起“披荊斬棘”的“前鋒任務(wù)”,以藝術(shù)的形式為發(fā)動全民抗戰(zhàn)打下思想基礎(chǔ)。田漢在抗戰(zhàn)期間創(chuàng)作出了一批抗戰(zhàn)戲劇,旨在宣揚和表現(xiàn)抗日愛國的精神,鼓勵人們前往最前線為國家流血斗爭。其中的杰出代表有《回春之曲》,作者以詩意盎然、優(yōu)美動人的語言書寫了愛國華僑高維漢與梅娘抗日救國的愛情故事,以滿含深情的筆調(diào)贊美了抗日青年的愛國熱情。
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被稱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后,《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八百壯士”孤軍營內(nèi)鼓舞士氣的戰(zhàn)歌之一。“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是田漢在文化戰(zhàn)線上決心要為民族救亡慷慨赴義的表達,他通過藝術(shù)的形式呼吁、號召千萬同胞為抗戰(zhàn)前線鑄成鋼鐵長城。他雖未沖上前線英勇殺敵,卻用藝術(shù)的價值與感召力筑起一道新的長城,觸發(fā)千萬同胞的情感共鳴,為抗日救亡進行了最具效果、范圍最廣的宣傳和引導(dǎo)。
在田漢的發(fā)動和感召下,戰(zhàn)時報刊、圖書出版發(fā)行空前繁榮,文藝社團林立,戲劇講演等活動空前活躍。這些藝術(shù)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揭露、打擊了漢奸賣國賊,捍衛(wèi)了民族尊嚴,充分體現(xiàn)了藝術(shù)價值與民族抗戰(zhàn)精神之間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
四、抗戰(zhàn)美術(shù)鑄成迎擊日軍的精神武器
歷史機遇使美術(shù)以挽救日益凋敝的民族氣節(jié)為切入點起到了美育的作用,美術(shù)不再是畫家筆下自我好惡的表達,而是用顏料和畫筆在抗戰(zhàn)中“團結(jié)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武器的作用。
1938 年7 月底,武漢捍衛(wèi)戰(zhàn)爭進入最關(guān)鍵的階段,負責藝術(shù)宣傳工作的田漢向?qū)傧碌牡谌?美術(shù)科)代理科長正式下達制作以“全國總動員,保衛(wèi)大武漢”為主題的大壁畫的命令,并撥出800 元專款購買畫材。來自全國各地的十多位藝術(shù)家在田漢的組織下參加了黃鶴樓大壁畫的創(chuàng)作。這幅大壁畫幾乎占據(jù)了整面城壁,高度約12 米,長度約45 米。創(chuàng)作小組搭起了腳手架,夜以繼日地開展壁畫的繪制工作。隨著日軍對武漢的日益逼近,壁畫繪制工作不得不在敵機頻繁來襲的艱險條件下推進。
田漢作為壁畫的監(jiān)制,將自己豐富的舞臺經(jīng)驗運用于壁畫的創(chuàng)作中。比如,在大壁畫的驗收環(huán)節(jié),他提出在畫面的空隙處補入郭沫若在街頭向群眾宣講的場面。畫成后的壁畫分為兩部分,前方抗日將士奮勇前進的場景與后方軍民挖戰(zhàn)壕、抬傷員、運彈藥形成呼應(yīng),壁畫中的人物超過了300 人,展現(xiàn)了抗戰(zhàn)救亡的恢宏景象。如果沒有田漢這位具備豐富舞臺經(jīng)驗和善于處理龐雜角色的導(dǎo)演,僅靠學(xué)院派的藝術(shù)家是很難完成這樣一幅兼具細節(jié)和恢宏場面的黃鶴樓大壁畫的。在完成了黃鶴樓大壁畫的繪制工作后,9 月27 日、28 日,美術(shù)科全體工作人員在武漢各重要街頭共完成了壁畫14 幅。
這一次,田漢集合藝術(shù)家以反戰(zhàn)壁畫為“精神武器”來迎擊日軍,表達全民抗戰(zhàn)的決心。雖然武漢淪陷后,壁畫被毀,但是抗日救國的民族精神不可磨滅。
結(jié)語
綜上所述,民間戲劇啟蒙了田漢,使其逐漸形成了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在時代背景和個人機遇的雙重影響下,田漢的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逐漸成熟,并應(yīng)用于實踐,由此創(chuàng)作出很多振奮人心的優(yōu)秀作品,鑄成了抗戰(zhàn)救亡的精神武器。通過分析田漢的平民藝術(shù)價值觀與創(chuàng)作實踐可知,藝術(shù)工作者應(yīng)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創(chuàng)作,這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深入人心、經(jīng)久流傳的作品。